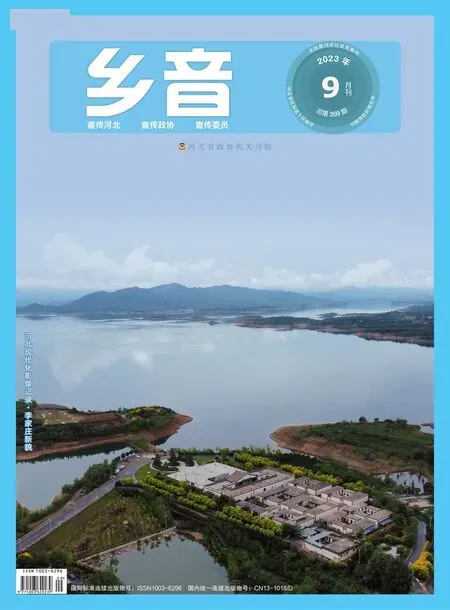號角與戰鼓
——晉察冀邊區的群眾文藝運動
■ 劉夏蘭
1937 年7 月7 日,全民族抗戰爆發。7 月8 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御外侮。8 月,根據黨中央部署,聶榮臻率部創建了華北敵后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晉察冀邊區是實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最為堅決的一個區域之一,也是貫徹民主政治最為堅決的區域之一,被黨中央譽為“抗日模范根據地和統一戰線模范區”。
在晉察冀邊區,廣大農民群眾踴躍參與各式各樣的組織,參與到黨領導的事業中,其中就包括文藝事業。除參與者之外,群眾文藝事業還需要“領頭羊”——廣大文藝工作者。與農民不同,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富于政治敏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積極性。聶榮臻十分尊重知識分子,他在晉察冀根據地的建設中曾說過:“我國知識分子隊伍好得很。在革命戰爭時期,對根據地的建設,對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來到晉察冀的文藝工作者都得到了重視,安排工作,接受教育。他們毛錐作槍,素箋為鼓,為根據地的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晉察冀邊區的群眾文藝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模式,也找到了文藝大眾化的正確道路。

街頭詩運動起源于延安,圖為延安群眾觀看街頭詩朗誦
群眾文藝運動在晉察冀邊區的開展形式是多樣的,街頭詩、歌唱、戲劇創作、寫作等都是其中的形式。這些不僅有力地配合了黨的抗日宣傳,配合軍事斗爭,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在揭露日軍殘暴的侵略、頌揚抗日英雄事跡、喚起民眾的抗日熱情方面起到了“沖鋒號”和“擂戰鼓”的積極作用,也為文藝的大眾化、普及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回顧這一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既是對革命先輩們的緬懷,也對今天的文藝創作具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擂戰鼓振雄心”——街頭詩運動
街頭詩又稱墻頭詩,是抗日戰爭時期一種特殊的詩歌形式,最早發源于延安。詩作的特點就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振聾發聵,傳播速度快。
1938 年,詩人田間、柯仲平、邵子南、史輪等西北戰地服務團成員在延安發起了“街頭詩運動日”。他們一起走上街頭,把自己的詩作抄寫在紙上,貼在街頭,這就是最早的街頭詩。詩人們的活動在延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后來,這種詩歌形式隨著西戰團的到來而傳播到了晉察冀根據地。在以田間為首的戰地社和錢丹輝領導的鐵流社的帶動下,街頭詩很快就風靡晉察冀根據地,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街頭詩運動。
在理解街頭詩的時候,需要明晰以下兩個概念。一是街頭詩是一種特殊的詩歌形式,主要是指其傳播方式而言。街頭詩不像通常的詩作那樣,通過報刊發行或印刷成冊,而是制作成詩傳單發放給革命軍民,或者干脆就寫在墻壁上。白粉筆、黑木炭,或是簡陋的油印設備,承載著詩人們的創作激情。他們走上街頭,振臂高呼:“不要讓鄉村一堵墻,路旁的一片巖石白白地空著。……我們要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這大時代中,從全國各地展開偉大的抗日詩歌運動。而街頭詩運動……就是使詩歌服務抗戰創造大眾詩歌的一條大道。”二是街頭詩的創作者來自于不同的群體。包括西北戰地服務團、東北挺進縱隊干部部隊、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團、前線文藝工作團的部隊文藝工作者,以及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總校和二分校的師生們。甚至后期還有自發加入寫作的抗戰軍民。這樣龐大的創作群體,來自于不同的地域、社會階層和文化背景。以不同的眼光來觀照現實,這就激發了詩人們的創造性,保證了街頭詩作品的多樣性和文學性。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歌詠運動

《冀中一日》出版于1941 年,是一個油印的版本。不久,冀中根據地遭到日寇的全面進攻和“圍剿”,很多稿件在戰火中被毀。直到解放后幾經周折,由冀中人民用生命保留下來的僅有的一份文稿才被找到,并得以重印出版發行。70 年后,《冀中一日》得以再版發行。本張照片為此書中的一張歷史照片,時任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前左一)與戰斗英雄交談
民族救亡歌詠運動,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以音樂作為對敵武器的愛國運動。在抗日戰爭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歌聲極大地喚起了大眾的愛國熱情,激勵著廣大軍民前仆后繼、奮勇殺敵,成為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同時也向全世界傳達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英勇不屈的精神風貌。
晉察冀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們,根據生產戰斗實際,結合本地音樂素材,如民歌或地方戲曲等元素,創作出大量的優秀作品,深受軍民的歡迎。晉察冀根據地歌詠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相互比賽唱歌,成為當時軍民集會的常規項目。合唱這一外來的藝術形式,在其中大放光彩,不僅傳達著團結抗戰的精神力量,更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深受人民歡迎,傳唱至今。
晉察冀邊區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抗日金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是其中最為大家耳熟能詳的代表曲目。
“冀中一日”群眾寫作運動
“冀中一日”是晉察冀邊區所轄冀中區發起的群眾寫作運動,它是冀中黨政軍民各方面有組織的集體創作,是文藝走進群眾的一次重要實踐。1941 年4 月,冀中區黨政軍領導程子華、呂正操等倡導冀中區軍民仿效茅盾主編的《中國一日》,在冀中區開展一次“一日”寫作運動,此舉得到冀中區文藝工作者的積極響應,他們在群眾中廣泛、深入地宣傳“冀中一日”創作。不僅如此,群眾在這一過程中也變得活躍。10 萬軍民拿起筆,將個人親為、親聞、親見的事情不加潤飾,怎樣真就怎樣寫,有的不識字,由別人幫著寫口述,他們用質樸而真誠的筆觸,實事求是地反映冀中軍民抗戰的一天,當成一種對自己的鼓舞,對敵人的示威。總編室的稿件源源不斷,達5 萬篇之多,最終到了要用麻袋裝、用擔子挑、用小車推、用大車拉的程度。
“冀中一日”群眾寫作運動不僅在當時普及了文字,更為后世留下了根據地軍民奮勇抗戰的第一手記錄。繁榮了晉察冀邊區的文藝事業,激發了群眾參與文藝運動的熱情,“是用腦和手的勞動寫成的,也是用血和肉創造的”,展現了冀中人民堅強不屈,浴血奮戰的樂觀主義精神。
“吹響前進的號角”——戰地劇社
戰地劇社運動是配合黨的抗日宣傳,深入群眾的最好形式。文藝工作者們創造性地結合了北方秧歌劇和西方歌劇,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戲劇類型。
戰地劇社在晉察冀根據地廣泛開展,抗戰期間晉察冀各軍區、軍分區及地方行政機構組建劇社36個,地方藝術表演單位8 個,其他鄉村劇團更是雨后春筍。

群眾在觀看火線劇社演出的秧歌劇《兄妹開荒》
在晉察冀戲劇中,大量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的作品真實地展現了戰火紛飛年代最原初的氣息。首先是關于子弟兵母親的戲劇。1940 年,火線劇社的陳喬,根據冀中軍區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母親的真實事跡,創作了話劇《馬母》。《馬母》在舞臺上再現了馬母被日寇抓獲后堅貞不屈、勇于犧牲的英雄母親形象,極大地激勵了廣大晉察冀軍民的抗日斗志和決心。1944 年4 月,胡可根據邊區擁軍模范戎冠秀的事跡創作了多幕話劇《戎冠秀》,劇中人物被親切地稱作“子弟兵母親”。再就是關于子弟兵戰士的戲劇。1944 年冬,杜烽創作了四幕五場話劇《李國瑞》。這部作品以晉察冀第四軍分區某部“燈塔連隊”的李國瑞的真人真事為基礎,展現了李國瑞從思想落后典型到先進戰士模范的心路轉變歷程,反映了部隊內部的矛盾和士兵的思想問題,被稱為“幾年來反映子弟兵的少有的成功作品”。
此外,還有很多取材于真實事件的戲劇也很值得關注。如取材于真實戰斗戰場的戲劇《陳莊戰斗》《狼牙山五壯士》等;取材于真實事件的戲劇《五十六個殉難者》《槍斃王家祥》等。這些作品切實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冀中軍民在生與死、血與火中的英勇頑強。
晉察冀邊區抗戰時期的群眾文藝運動,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其發揮的歷史作用卻是特殊而重大的。冀中軍民積極配合抗戰,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迅速地創作出反映時代的作品,在抗日戰爭以及之后的解放戰爭中起著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這些群眾文藝運動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準確把握黨的抗日救國綱領和統一戰線政策,堅持走與群眾相結合的文藝宣傳道路。廣大文藝工作者把宣傳活動當作對敵作戰的武器,到距離敵人最近的地方演出,不斷向人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增強了我軍和我黨的政治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