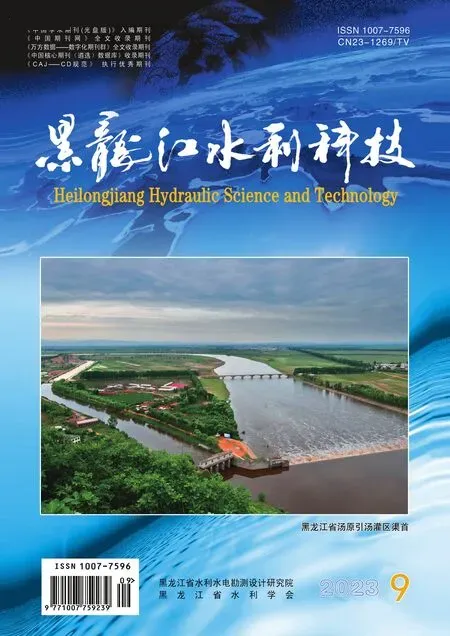降雨強度和城市化對城市湖泊水環境的影響
楊 益,張彥寧
(北京市密云水庫管理處,北京 101500)
0 引 言
近幾十年來,由于氣候變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城市湖泊越來越多地遭受一系列環境問題的影響。氣候變化一直是一個關鍵而實際的問題,其對湖泊水環境的負面影響是不可避免的[1]。氣候條件的變化,特別是降雨過程的變化,將導致湖泊水動力和水環境的重大變化。此外,城市演變可能與氣候變化相結合,產生潛在的破壞性影響。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量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對湖泊水環境構成嚴重威脅。因此,降雨強度和城市化是城市湖泊水質惡化的重要原因[2]。
隨著數值模擬技術的快速發展,許多學者將其應用于流域徑流和湖泊水環境的模擬。該方法已成為研究湖泊水環境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目前,主要的城市面源污染模型包括雨水管理模型(SWMM)、風暴和DR3M-QUAL等。其中,SWMM是一種動態降雨-徑流模擬模型,用于徑流量和質量的單次事件或長期(連續)模擬[3]。由于其計算效率和靈活的機制,該模型已被廣泛用于估計城市地區的地表徑流及其污染負荷。湖泊水動力和水質數值模型取得了很大進展,廣泛使用的模型包括EFDC、MIKE21、CE-QUAL-W2和WASP。這些模型軟件仿真精度高,但大多需要大量的測量數據,預處理工作相對復雜。基于此,文章選取基于DEM的二維(2-D)水動力和水質模型來描述湖泊流場和水質濃度的動態變化,將DEM數據作為計算網格,省略了預處理過程。然后考慮非點源污染的遷移和轉化,建立了面源污染與湖泊水動力-水質的組合模型[4]。以某湖泊為試驗條件,進一步揭示湖泊水質對暴雨強度和城市化程度的響應。研究結果對變化環境下城市湖泊水環境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科學意義。
1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某城市湖泊面積為52.19km2,流域面積240.38km2,是典型的亞熱帶淺水湖泊,平均水深1.85 m。該地區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平均氣溫 16.9℃,年平均降雨量1249.36 mm。降雨具有很強的季節性,64.9%的降雨發生在4~8月之間。近年來,隨著工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建設用地的大量擴張極大地改變了湖泊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使得湖泊生態環境不堪重負。城市發展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水環境問題。2001年以前,某城市湖泊整體水質較好,能達到III類。2001年后,水質逐漸惡化至IV 類,處于輕度富營養化階段。2014 年后,水質進一步惡化至V類,處于中度富營養化狀態。且部分湖泊的水質均劣于V類,無法達到水質管理目標。
1.2 數據來源
非點源污染模型所需的數據包括:分辨率為30m的數字高程模型(DEM)數據,由空間分辨率為30m的Landsat 遙感獲得。湖泊水動力-水質模型所需數據主要包括:風速風向數據、某湖泊水下地形數據、湖泊日水位數據、2022年采樣點實測水質數據、排污口實測水質數據等。
1.3 非點源污染模型
文章選擇雨水管理模型(SWMM)來模擬湖流域的非點源污染。在SWMM 模型中,子流域按地表滲透性分為3類,包括無凹陷不透水地表、有凹陷不透水地表和透水地表。對于無洼地的不透水地表,其徑流量是從降雨量中扣除蒸發量后得出的。對于有凹陷的不透水地表,徑流等于降雨量減去蒸發和凹陷。對于透水地面,徑流量是在扣除洼地蓄水量、蒸發量和滲透量后得出的。滲透損失由霍頓模型計算得出。地表徑流過程的水文計算以非線性水庫理論為基礎。管道的水流運動基于一維圣-維南方程。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分為3個過程,包括積聚過程、沖刷過程和遷移過程。文章采用指數函數作為SWMM模型的地表污染物積聚和沖刷算法。污染物在管道中的傳輸過程采用完全混合一階衰減模型進行模擬。
1.4 二維水動力和水質模型
對于淺水湖泊,一般假定沿水深的分布是均勻的。文章采用基于DEM的二維水動力和水質模型來描述湖泊流場和水質濃度的動態過程。采用DEM矩形網格作為模型計算網格,可與GIS系統無縫耦合,省去了網格劃分等預處理工作。與傳統的體擬合網格和非結構化網格相比,大大提高了模型的標準化和模塊化程度。
1) 流體力學方程:淺水湖泊的二維水動力方程包括連續性方程和動量方程,可表示如下:
(1)
(2)
式中:h為水深,m;x和y分別為水域的垂直長度和水平長度,m;T為時間,s;q為水量源匯,包括降雨、蒸發、滲流等,m/s;u和v分別為水流的垂直速度和水平速度,m/s;z為水位,m;n為粗糙度系數;εx和εy分別為垂直和水平渦流黏滯系數,m2/s。
2)水質遷移和轉化方程:沿水深方向取長dx、寬dy、高h的水柱。根據質量平衡原理,可以得到二維水遷移轉化的基本方程,如下式所示:
(2)
式中:C為湖泊中某種污染物的濃度,mg/L;Ex和Ey分別為分子擴散系數、湍流擴散系數和在x和y方向上的擴散系數之和;∑Si為水質指數的源項。
2 計算結果和數據分析
2.1 不同降雨情景下的徑流和流入污染負荷
文章選取重現期為1a、5a、10a和20a的24h設計降雨量來分析降雨強度對湖泊水環境的影響。根據SWMM模擬了不同情景下的徑流和流入污染負荷,見表1。結果表明,隨著降雨強度的增加,徑流深度明顯增加。在降雨重現期為5a、10a和20a的情況下,徑流增加率分別為 81.2%、30.6% 和 25.2%,表明隨著重現期的增加,徑流改善率逐漸降低。此外,可以得出降雨強度越大,流入的總氮TN和總磷TP污染負荷越大的結論。

表1 不同情況下徑流和流入污染負荷的模擬結果
2.2 湖泊水質對降雨強度的響應
基于非點源污染模型模擬了不同降雨強度下某湖泊的總氮TN和總磷TP濃度的變化。平均水質濃度由湖中所有網格點模擬水質值的平均值得出。可以看出,在降雨的前16h內,湖泊中總氮TN和總磷TP 的平均濃度上升緩慢,且回歸期越大,平均濃度上升越快。在16~17h內,湖泊的平均濃度明顯增加。17h后,在20a重現期(P=20)下略有下降,而在其他重現期下則保持穩定。在1a、5a、10a和20a重現期,某湖泊TN平均濃度分別為2.92mg/L、3.10mg/L、3.20mg/L和3.23mg/L,TP平均濃度分別為0.237mg/L、0.240mg/L、0.244mg/L 和0.251mg/L,進一步表明降雨強度越大,某湖泊的水質濃度越高。
以重現期為20a的24h設計暴雨為例,分析了湖泊水動力和水質的時空分布特征。暴雨前水流緩慢,大部分區域流速<0.01m/s。暴雨過后,湖水的流動性明顯改善,流速大大提高。具體來說,東湖的進水口、出水口和交界處流速相對較高,最大流速達到0.58 m/s。在降雨流入和湖泊流出的影響下,水流從徑流入口向湖泊出口呈定向流動。
2.3 不同城市化階段的徑流和流入污染負荷
某湖泊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可分為3個階段:早期城市化階段(1990年以前)、快速發展階段(1990—2020年)和后期城市化階段(2020年以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湖底地表特征發生了顯著變化。為了研究湖泊水質在不同城市化階段的響應,利用Landsat數據,通過監督分類方法提取了1990 年、2018年和2022年的土地利用類型,分別代表城市化早期階段(第一階段)、快速發展階段(第二階段)和城市化晚期階段(第三階段),見表2。

表2 不同城市化階段的土地利用類型
基于SWMM模擬了某湖泊流域三個城市化階段的徑流深、徑流系數和流入污染負荷,如表3所示。在模擬過程中,為避免降雨強度的影響,3個階段輸入的降雨數據均為24h暴雨,重現期均為5a。如表3所示,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徑流深度、徑流系數和污染物負荷明顯增加。與第一階段相比,第三階段暴雨后的TN和TP總污染負荷分別增加53.49t和8.88t。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后期(第三階段)不透水面積大幅增加,導致入滲量減少,入湖徑流增加。因此,徑流的沖刷效應增強,流域總污染負荷增加。且城市化的發展不僅增加了城市內澇的風險,也加劇了湖泊的污染問題。

表3 不同城市化階段徑流和流入污染負荷的模擬結果
3 結 論
文章建立了基于SWMM和基于DEM的水動力-水質組合模型,以描述湖泊流場和水質濃度的動態變化。該組合模型考慮了非點源污染的遷移轉化過程,可直接描述非點源污染進入湖泊的途徑。隨著暴雨強度的增加,進入某湖泊的徑流量和總氮TN、總磷TP污染負荷明顯增加,但改善率逐漸降低。暴雨過后,湖泊水體流動性明顯改善。在前期降雨中,總磷TP和總氮TN濃度逐漸增加。暴雨強度越大,水質越差。而在降雨后期,湖泊水質略有改善。因此,合理利用降雨洪水資源可有效改善湖泊的水動力和水質。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不斷增加,導致湖泊水環境惡化。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由于不透水面積的擴大,徑流量也在不斷增加,導致城市洪澇災害風險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