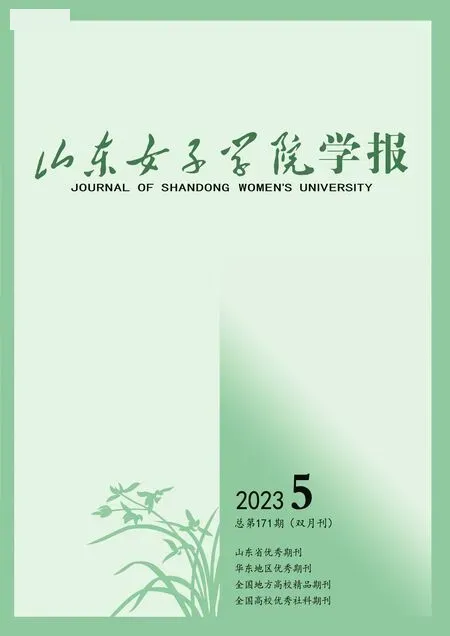低生育水平下中國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與變動
宋 健,陳文琪
(中國人民大學(xué),北京 100872)
一、研究背景
中國自1992年起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進入低生育率社會。盡管2013年后中國的生育政策不斷寬松化,但出生人口數(shù)在2016年達到1786萬人的小高峰后持續(xù)下降,直至2022年總?cè)丝诔霈F(xiàn)負(fù)增長。出生人口數(shù)下降不僅受到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長期效應(yīng)、生育主體代際更替效應(yīng)、新冠疫情下婚育行為延后效應(yīng)等多種因素影響,也與育齡女性規(guī)模下降、育齡女性年齡結(jié)構(gòu)老化、年齡別生育率低迷密不可分。深度探究低生育水平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穩(wěn)定出生人口規(guī)模,對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
圍繞生育議題,學(xué)界目前已經(jīng)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大多數(shù)研究以女性個體或“育齡女性”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因為女性既是生育的直接承擔(dān)者,也是育兒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在“生”和“育”兩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婚育年齡的推遲,以及離婚率的不斷升高,并非所有育齡女性都具有生育的現(xiàn)實可能性。一些學(xué)者意識到應(yīng)將夫婦雙方共同納入生育分析框架中,認(rèn)為夫婦從生育意愿開始就相互影響,只有在整合彼此的生育計劃后,才會實施共同的生育行為,并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生育結(jié)果[1-2]。還有一些研究把父輩納入生育分析框架中,發(fā)現(xiàn)中國的家庭傳統(tǒng)使父輩廣泛且深度參與到子輩的育兒實踐中,這不僅有助于緩解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還弱化了丈夫的育兒角色[3];父母通過照料支持和表達自身生育偏好顯著影響女性的二孩生育計劃[4]。現(xiàn)實生活中,只有在同居共爨的基礎(chǔ)上,夫婦伴侶的婚育行為才可能實現(xiàn),而父輩參與嬰幼兒照料往往是在生育之后發(fā)生,且通常伴隨父輩或子輩一方的遷移流動和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化。無論是育齡女性還是育齡夫婦的生育行為,亦或是父輩的育兒參與,都需要以家庭為基礎(chǔ)。然而,既有文獻中對育齡女性或育齡夫婦所在家庭基本情況的研究還較少。
家庭制度是生育制度的基礎(chǔ)[5]。在中國,生育不是個體行為,而是家庭內(nèi)部資源調(diào)度和協(xié)商分配后的重大決策。中國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從家庭層面對人們的生育數(shù)量和相關(guān)行為進行干預(yù)。然而迄今為止,關(guān)于中國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結(jié)構(gòu)及其變動等基本特征并不清晰。常見的一些家庭戶相關(guān)信息,如2020年中國平均家庭戶規(guī)模為2.62人等,展示的只是中國家庭規(guī)模小型化、單人戶和純老戶比例不斷上升等多元化趨勢特點。我們感興趣的是,具有生育潛力的中國家庭數(shù)量及其在全部家庭戶中的比例有多少?在過去幾十年間呈現(xiàn)怎樣的變動趨勢?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利用全國人口普查和抽樣調(diào)查等數(shù)據(jù),估計中國進入低生育率社會以來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變動特點,以深入了解低生育水平的原因。
二、概念界定、數(shù)據(jù)來源與分析思路
(一)育齡家庭的概念界定
本文界定“育齡家庭”為:家庭成員中包含至少一對在婚育齡夫婦(包括在婚未孕/備孕/曾孕未育/已育夫婦),其中女方處于20~49歲育齡期的家庭。
既有文獻中,國外有學(xué)者將處于孕期或育兒期的夫婦組成的家庭稱為生育/撫育家庭(childbearing/childrearing families)[6-7];中國學(xué)者雖曾使用“育齡家庭”概念,但由于其主要介紹其他國家的家庭支持政策[8],對概念本身缺少明確界定,實際針對的也仍是生育/撫育家庭。生育/撫育家庭概念脫胎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論[9],多聚焦于因生育而開啟的家庭拓展階段,通常限制家庭中最大的兒童年齡在出生到30個月范圍內(nèi),討論與生育過程或結(jié)果有關(guān)的家庭政策。而國內(nèi)相關(guān)研究中的生育主體,一般涉及“育齡女性”(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育齡夫婦”(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等,雖然也會考慮諸如父母、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員及家庭社會經(jīng)濟資源等對其生育決策的影響,但關(guān)注點并不在家庭本身。本文所建構(gòu)的“育齡家庭”概念從生育行為主體出發(fā),關(guān)注具有生育潛力或可能性的家庭,涵蓋生育/撫育家庭,包含在婚育齡夫婦,其核心在于兼顧“家庭”和“育齡”。首先聚焦“家庭”,基于生育發(fā)生在家庭的現(xiàn)實,強調(diào)家庭成員圍繞生育進行決策互動和資源分配。其次關(guān)注“育齡”,即具有生育潛力的主體。由于生育行為的實際承擔(dān)者為女性,而女性一生中具備生育能力的時期有限且邊界相對清晰,所以從生育能力出發(fā),以女性是否處于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育齡期為基礎(chǔ),考慮其婚姻狀況及其與配偶是否共同居住等條件,將至少有一對在婚育齡夫婦的家庭視為育齡家庭。建構(gòu)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將具有生育潛力和生育能力的家庭從一般意義的家庭中剝離出來,這樣更有利于政策聚焦和精準(zhǔn)施策。鑒于中國法律對女性最低結(jié)婚年齡的規(guī)定(不得早于20周歲),在本研究中以20歲作為在婚育齡女性的年齡下限。
由此可見,育齡家庭包含于家庭之內(nèi),其核心單元是在婚育齡夫婦,其中在婚育齡女性是育齡家庭概念界定的依據(jù)及生育觀察的重點。
(二)數(shù)據(jù)來源
目前尚未有公開數(shù)據(jù)直接提供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由“家庭—育齡家庭—在婚育齡夫婦—在婚育齡女性”的概念層級,我們利用現(xiàn)有的全國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對育齡家庭規(guī)模進行估算。
自1990年以來每10年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diào)查以及年度全國1‰人口變動抽樣調(diào)查均提供了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的人口數(shù)據(jù),可據(jù)此得到在婚育齡女性數(shù)量。考慮到中國總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且目前統(tǒng)計年鑒中缺失1991年和1992年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的人口數(shù)據(jù),本文以1993年作為估算的起始年份,以展示中國進入低生育社會后的圖景。
按照一夫一妻制原則,在婚育齡女性數(shù)量等于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每個育齡家庭中可能包含一對及以上在婚育齡夫婦,但從公布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中難以得到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分布信息。我們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shù)據(jù)得到分布和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信息,以彌補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不足。
作為一項全國性、大規(guī)模、多學(xué)科的固定樣本追蹤調(diào)查項目,CFPS家庭問卷使用了獨特的T表設(shè)計,以代答的方式采集了家庭中所有成員的父母、配偶和所有子女的關(guān)系及這些直系親屬的基本社會人口信息,可構(gòu)造和區(qū)分各類家庭結(jié)構(gòu)。其2010年開展的基線訪問,樣本覆蓋全國25個省區(qū)市(1)調(diào)查未覆蓋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海南省、西藏自治區(qū)、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和臺灣地區(qū)。的近1.5萬個家庭戶,調(diào)查對象包含樣本家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后續(xù)每兩年開展一次的追蹤調(diào)查的對象包含基線家庭成員及其新生血緣或領(lǐng)養(yǎng)的子女,追蹤成功率在同類調(diào)查中保持國際領(lǐng)先水平(2)參見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官網(wǎng),“CFPS小課堂|如何用CFPS做性別研究”,http://www.isss.pku.edu.cn/cfps/cjwt/cfpsxkt/1348079.htm.。2010—2020年的CFPS家庭成員關(guān)系庫提供了受訪者本人、配偶、父親、母親和所有子女共計三代人的基本社會人口特征,因此可通過是否同屬于一個家庭、在婚有配偶的女性是否處于20~49歲育齡期等關(guān)鍵信息,依次識別該家庭不同代際含有的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有一對及以上在婚育齡夫婦的可判斷該家庭屬于育齡家庭。由于CFPS家庭成員關(guān)系庫包含了一個家庭中可能的在婚育齡夫婦代數(shù)上限(即使是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也幾乎不可能有四代及以上的女性同時處于20~49歲育齡期),因此基本不會遺漏育齡家庭。
全國人口普查和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實際上屬于“家庭戶”統(tǒng)計,即居住在同一個住房單元的家庭成員,而非僅通過成員的婚姻、血緣、收養(yǎng)關(guān)系進行“家庭”界定。為了銜接不同來源的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我們使用“是否居住在家”這一指標(biāo)來判定CFPS數(shù)據(jù)中的家庭成員是否屬于該家庭戶。這種以同住一處判定“家庭戶”的口徑在一定程度上也更符合本文以生育為側(cè)重點的“育齡家庭”界定。
(三)分析思路
基于現(xiàn)有數(shù)據(jù)估算全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有兩種方案。方案一是根據(jù)CFPS數(shù)據(jù),得到調(diào)查年份的育齡家庭規(guī)模及其在全部家庭中的比例,擬合育齡家庭比例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將其應(yīng)用于根據(jù)全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得到的1993年以來全國家庭戶規(guī)模,推導(dǎo)出全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基本思路是:


方案二是根據(jù)CFPS數(shù)據(jù),觀察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情況,擬合這一分布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借助“家庭—育齡家庭—在婚育齡夫婦—在婚育齡女性”的內(nèi)在層級關(guān)系,反向逆推1993年以來全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基本思路是:



上述兩個方案都利用了CFPS數(shù)據(jù)和全國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其中方案一的優(yōu)勢在于較充分利用了各年份全國家庭戶規(guī)模數(shù)據(jù),不足在于主要依據(jù)CFPS數(shù)據(jù)所得的育齡家庭在全部家庭戶中的比例,比較依賴這一比例的估計趨勢值;方案二的優(yōu)勢在于較充分利用了各年份在婚育齡女性即在婚育齡夫婦的基礎(chǔ)數(shù)據(jù),不足在于主要依據(jù)CFPS數(shù)據(jù)所得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分布情況,比較依賴這一分布的擬合結(jié)果,且所得育齡家庭規(guī)模略有高估。兩種方案互為映襯,本文將上述兩種方案結(jié)果取簡單算術(shù)平均值,即:


之所以采用兩種方法的簡單算術(shù)平均值,原因主要在于每種方法可能存在不同的偏差和局限性,通過取平均值可以減少單一方法引入的偏差,減少異常值及個別方法局限性的影響,降低整體誤差,增加估算的穩(wěn)健性,更好地反映真實情況。取簡單算術(shù)平均值也是使用混合方法時的一種慣常做法(如組合賦權(quán)法對不同方法權(quán)重的處理方案)。
由公式3可得到1993年以來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及其變動情況,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計算得到育齡家庭在全部家庭戶中的比例。
三、中國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及其變動情況
(一)全部家庭戶中育齡家庭所占比例:方案一估算結(jié)果
首先通過方案一對育齡家庭規(guī)模進行推導(dǎo)。CFPS數(shù)據(jù)結(jié)果顯示(見表1),在2010—2020年調(diào)查年份,中國育齡家庭在全部家庭戶中所占比例從接近六成到不足一半,整體上呈現(xiàn)下降態(tài)勢。2010年育齡家庭比例為56.85%,2016年降至44.82%,此后略有回升,但未能突破50%,2020年為48.98%。

表1 全部家庭戶中育齡家庭所占比例(2010—2020年調(diào)查年份)
對上述數(shù)據(jù)繪制散點圖,發(fā)現(xiàn)基本符合線性變化趨勢。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的比例與時間變量呈現(xiàn)較強的線性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相關(guān)系數(shù)=-0.7961,p<0.1),因此擬合時間序列線性回歸方程(3)R2=63.40%;F檢驗?zāi)P惋@著。得到:
Pt=-0.0096t+0.7229 (公式4)
其中Pt為擬合得到的第t年的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比例;t為時間(t∈[1,28]對應(yīng)1993—2020年)。
依據(jù)公式4和公式1推導(dǎo)得到方案一結(jié)果(見表3)。
(二)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方案二估算結(jié)果
其次通過方案二對育齡家庭規(guī)模進行推導(dǎo)。觀察CFPS數(shù)據(jù)中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情況發(fā)現(xiàn)(見表2),在2010—2020年調(diào)查年份,93%~97%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僅含有一對在婚育齡夫婦,3%~6%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含有兩對在婚育齡夫婦,育齡家庭內(nèi)部含有三對及以上在婚育齡夫婦的比例不足0.2%。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一對為主、兩對較少、多對極少”的結(jié)構(gòu)及相應(yīng)比例在幾次調(diào)查中保持著相當(dāng)程度的穩(wěn)定性。

表2 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2010—2020年調(diào)查年份)
為了保證包含不同數(shù)量在婚育齡夫婦的育齡家庭比例加總等于100%,采用兩次擬合,首先基于CFPS的6次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對包含不同數(shù)量在婚育齡夫婦的育齡家庭規(guī)模擬合線性回歸,得到分別包含一對、兩對、三對及以上在婚育齡夫婦的三類育齡家庭數(shù)量及合計值,計算各類育齡家庭在全部育齡家庭中所占比例,以確保三類育齡家庭比例合計為100%;然后將上述比例擬合時間序列線性回歸方程(4)過程中的規(guī)模擬合方程囿于篇幅未呈現(xiàn)。本文還嘗試了其他非線性擬合方式,各有優(yōu)劣,且結(jié)果差異不大。為簡便起見,采用線性擬合結(jié)果。得到:
at=0.0015t+0.9185 (公式5)
bt=-0.0015t+0.0813 (公式6)
ct=0.00003t-0.0002 (公式7)
其中at為擬合的第t年含一對在婚育齡夫婦的育齡家庭在全部育齡家庭中的比例;bt為擬合的第t年含兩對在婚育齡夫婦的育齡家庭在全部育齡家庭中的比例;ct為擬合的第t年含三對及以上在婚育齡夫婦的育齡家庭在全部育齡家庭中的比例;t為時間(t∈[1,28]對應(yīng)1993—2020年)。
依據(jù)公式5、公式6、公式7和公式2推導(dǎo)得到方案二結(jié)果(見表3)。

表3 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估算值(1993—2020年)
(三)綜合兩種方案結(jié)果的育齡家庭規(guī)模及其變動
兩種方案估算出的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在1993—2010年期間較為接近,相差不到10%。2011—2018年期間兩種方案結(jié)果差異較為明顯,根據(jù)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分布估計的方案二結(jié)果顯著高于根據(jù)育齡家庭比例估計的方案一結(jié)果(見表3)。說明根據(jù)CFPS調(diào)查年份的育齡家庭規(guī)模及其在全部家庭中的比例所擬合的2011—2018年育齡家庭比例可能偏低于實際比例,導(dǎo)致低估育齡家庭規(guī)模;或者依據(jù)CFPS調(diào)查年份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所擬合的2011—2018年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平均數(shù)量可能偏低于實際值,導(dǎo)致高估育齡家庭規(guī)模。換言之,2011—2018年實際的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的比例可能略高于方案一的擬合結(jié)果,實際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平均數(shù)量可能略高于方案二的擬合結(jié)果。2019—2020年的擬合結(jié)果兩種方案差距縮小,其中,2020年方案二估計結(jié)果略低于方案一估計結(jié)果,可能原因在于,根據(jù)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計算得到的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較以往相對偏低(分子偏低),而根據(jù)CFPS2020年數(shù)據(jù)計算得到的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平均數(shù)量變化相對穩(wěn)定(分母幾乎不變),由此導(dǎo)致方案二估計結(jié)果相對偏低。綜合兩種方案,依據(jù)公式3得到1993年以來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估算值,并根據(jù)全國家庭戶規(guī)模計算育齡家庭所占比例。
表3結(jié)果顯示,育齡家庭無論在規(guī)模還是在變動趨勢上,都與全國家庭戶的特點有所不同。1993年以來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保持在2.1億~2.5億戶區(qū)間,相較于區(qū)間在3.0億~4.9億戶的全國家庭戶規(guī)模更為穩(wěn)定。2016年以來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呈現(xiàn)較為明顯的下降態(tài)勢,從之前2.4億戶左右的規(guī)模降至不足2.3億戶,2020年育齡家庭規(guī)模相較高峰期2006年的2.5億戶減少了2526萬戶。而同期全國家庭戶總規(guī)模呈現(xiàn)上升態(tài)勢,2000年之前不足3.5億戶,2006年突破4億戶,2020年達到4.94億戶。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的比例因此隨時間呈現(xiàn)明顯的下降態(tài)勢,所占比例從2006年之前的60%以上,降到2019年以來的不足50%。
由于育齡家庭與家庭戶在規(guī)模與變動趨勢上的差異,研究生育問題以育齡家庭為基礎(chǔ)和以家庭戶為基礎(chǔ)可能會產(chǎn)生不一樣的結(jié)果。
注:方案一按照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比例估算;方案二按照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數(shù)量分布推算。兩方案結(jié)果差異=[(方案二結(jié)果-方案一結(jié)果)/方案一結(jié)果]*100%。
四、總結(jié)與討論
中國進入低生育率社會已逾30年,應(yīng)對低生育挑戰(zhàn)需要對低生育的原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有效實施也需要聚焦生育核心人群。迄今為止,中國的生育仍以婚姻為前提、以家庭為基礎(chǔ),但目前關(guān)于育齡家庭規(guī)模和特點的研究還較為匱乏。本文通過建立“家庭—育齡家庭—在婚育齡夫婦—在婚育齡女性”的嵌套概念框架,基于CFPS2010—2020年數(shù)據(jù)獲得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戶的比例以及育齡家庭內(nèi)部在婚育齡夫婦的數(shù)量分布情況,進行時間回歸擬合后,利用1993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估算低生育水平下中國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和比例,揭示其隨時間變動的趨勢。
研究發(fā)現(xiàn),育齡家庭無論在規(guī)模還是在變動趨勢上,都與全國家庭戶的特點有所不同。1993年以來,中國育齡家庭規(guī)模保持在2.1億~2.5億戶區(qū)間,相較于區(qū)間在3.0億~4.9億戶的全國家庭戶規(guī)模更為穩(wěn)定。育齡家庭在所有家庭戶中所占比例為44%~73%,規(guī)模及比例隨時間推移均呈現(xiàn)較為明顯的下降態(tài)勢。與分家立戶和遷移流動造成的家庭戶規(guī)模不斷增加相比,育齡家庭規(guī)模不僅變化較小,且在2011年后呈現(xiàn)明顯下降態(tài)勢。這一態(tài)勢固然受全部家庭戶中育齡家庭比例不斷下降的影響,也反映了低生育率時期的家庭分裂會造成更大比例的由未婚獨居青年或中年及老年“空巢”家庭所組成的非育齡家庭。
對“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及其變動特點進行分析,相當(dāng)于對既有研究中常用的“家庭”概念在生育維度加以聚焦,有助于進一步揭示中國家庭生育動力弱化的現(xiàn)實,深入解釋出生人口數(shù)不斷下滑的內(nèi)在原因。面對低生育率的嚴(yán)峻挑戰(zhàn),近年來中國生育政策不斷做寬松化調(diào)整,但釋放的生育需求終究有限。家庭雖仍作為中國生育制度的基本單位,但能夠承擔(dān)生育功能的育齡家庭規(guī)模和比例不斷減少,家庭對于生育功能的維系和支持越發(fā)脆弱。
在生育率陷入長期低迷、提振生育水平刻不容緩的當(dāng)下,如何彌補育齡家庭生育功能的不足具有重大而深遠(yuǎn)的意義。生育的最終受益者是全社會,而目前生育養(yǎng)育的高昂成本卻主要由家庭承擔(dān),生育這一正外部性促使育齡家庭傾向于減少自身的人口生產(chǎn)乃至不生產(chǎn),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斷弱化。社會需要通過構(gòu)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制度來支持生育。一方面,借助普惠型托育服務(wù)以及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來減少育齡家庭的負(fù)擔(dān),支持人們充分實現(xiàn)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增強和恢復(fù)育齡家庭的生育功能,通過采取以家庭為單位的稅收返還、生育津貼等措施為家庭增加經(jīng)濟收入,科學(xué)實施各類時間支持措施以減緩工作與家庭沖突,促進家庭內(nèi)部的性別平等以提高生育意愿,以及鼓勵家庭成員居住在一起或附近,這些綜合性措施的效果考驗著當(dāng)前中國的家庭政策構(gòu)建和生育政策改革。
本文的創(chuàng)新和貢獻在于,分別以育齡和婚姻為限定條件聚焦“育齡家庭”及其內(nèi)部的“在婚育齡女性”,排除了其他家庭類型和其他婚姻狀態(tài)的干擾,有助于準(zhǔn)確把握生育潛力,使生育相關(guān)的家庭政策更為精準(zhǔn)。不足在于,對育齡家庭的規(guī)模估算取決于根據(jù)CFPS連續(xù)6輪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獲得的結(jié)構(gòu)和分布數(shù)據(jù)擬合結(jié)果。王躍生曾計算了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不同類型家庭的構(gòu)成,從其論文表5數(shù)據(jù)中可推算2000年全國育齡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不應(yīng)超過84.35%(育齡家庭≤全部家庭-單親核心家庭-單人家庭-缺損家庭)[10],可作為本文估算結(jié)果中2000年這一數(shù)據(jù)點(66.40%)的一個佐證。但由于相關(guān)文獻太少,后續(xù)還有待更多來源數(shù)據(jù)進行核實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