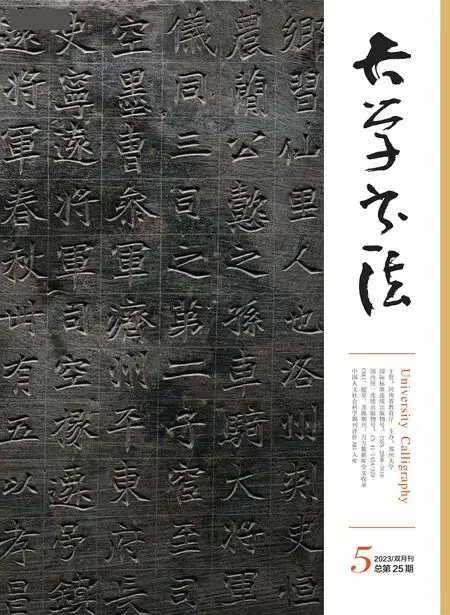論書法藝術的道家與道教意蘊
⊙ 王魯辛
引言
書法藝術承載著深厚的哲學理念,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具象性表達。對我國古代思想略做考察可知,儒道兩家當是最重要的兩大流派,不過兩家在藝術觀上有著本質區別。儒家思想所建構的禮樂文明,注重藝術的功用性,藝術起著教化人心、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作用,人們對待藝術宜秉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庸原則。而道家的藝術觀則強調藝術服務于人們的真情實感,秉持“真實”“自然”的原則。從這一點看,書法藝術與道家的藝術觀更為契合,接下來,筆者試圖從道家與道教兩方面揭示其與書法藝術間的內在聯系。
一、道家思想與書法創作
道家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產生于先秦,代表人物有老子、莊子、列子等。與儒家思想重社會、人倫、綱常的立場不同,道家思想以自然主義視角審視宇宙、社會和人生,對我國古典藝術包括建筑、園林、繪畫、雕刻、書法、音樂等領域,產生深遠影響。關于書法藝術,筆者將從道家的辯證觀、自然觀和形神觀角度來揭示其內蘊。
(一)道家辯證觀與書法
一幅書法作品的生成過程,首先考驗書者的是對“黑”與“白”、“實”與“虛”關系的把握,如整幅書法的謀篇布局、大字與小字的搭配以及字與字間隙大小等,這些直接關系到書法作品的優劣品級,需在落筆前就做到成竹在胸。其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家辯證思想,老子講“有無相生”“知其白,守其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揭示了黑字與白紙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辯證關系。就字體間留白有“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1]原則,也是道家辯證思想的現實運用。
書法創作的辯證觀不僅體現于黑字與留白上。墨法上,墨有干濕、濃淡、潤燥之分,需根據書法表現主題做到恰當取舍。筆法上,需有正有斜、有急有緩、有藏有露、有提有按,這樣寫出的字才剛柔兼濟、方圓兼容。結體上,需講究平衡照應,朱和羹說:“作字如應對賓客,一堂之上,賓客滿座,左右照應,賓不覺其寂,主不失之懈。”[2]如何處理好書法創作中的辯證關系,孫過庭《書譜》論述有:
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

文徵明 行書《上巳日獨行溪上有懷九逵》扇面
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3]
(二)道家自然觀與書法
李建春認為:“自然,是孕育藝術生長的母體,藝術與自然有一種不解之緣。作為藝術之一的書法,其誕生、發展和成熟過程,一直是同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4]而對“自然”內涵之解讀各方家則莫衷一是,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三方面闡釋。
1.書法產生是一自然過程
從淵源上探究,書法最早可推及文字的發明,而文字的產生源于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現實需要,這本身即一自然過程,正如陳醴講:“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5]自文字產生,大致又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的流變路徑,這一變化也是一自然發展過程。例如,秦代小篆的推行是為適應秦朝大一統的政治需要,漢隸替代小篆,出于人們書寫方便,便于政令的及時發布和漢字的普及傳播。鄭枃云:“草本隸,隸本篆,篆出于籀,籀始于古文,皆體于自然,效法天地。”[6]
書法作為一門藝術登上人類歷史舞臺當始于東漢時期,蔡邕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7]道出了書法產生的自然性。魏晉時期,書法藝術達到一個高峰,劉因對此評論:“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為名,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8]書法興于魏晉并非偶然,魏晉時期國家四分五裂,社會動蕩不安,相當部分士人遠離政治,全身保性,把精力投注到哲學和藝術領域。這一時期,西漢以來的儒家宗教神學觀也日漸式微,喪失了統治人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給予個體更多關照的老莊哲學,其隨之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
2.書法取象源于自然物象
書法的自然性還體現在書家創作靈感多來源于自然物象,如山水、田園、花鳥、蟲魚等。張懷瓘講:“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9]郝經說:“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云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10]孫過庭云: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11]
韓愈評張旭書法說:
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12]
在運筆上,人們也常借自然物象來比喻,如“如錐畫沙”“如屋漏痕”“如折釵股”,“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13],“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歐陽詢對書寫筆畫做如下總結:
(點)如高峰之墜石,(臥鉤)似長空之初月,(橫)如千里之陣云,(豎)如萬歲之枯藤,(戈鉤)勁松倒折落掛石崖,(撇)利劍截斷犀象之牙,(捺)一波常三過筆,(折)如萬鈞之弩發。[14]
3.書法是真情實感的流露
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并非我們常說的“大自然”,而是“自其然而所以然”之義。書法藝術中所秉持的自然觀更深層之義即在于此,強調書者應將自身真實情感融入其書法作品之中,即書家講究的“意到筆隨”。莊子講:“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15]于此,諸多書法理論大家如是強調:蔡邕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16]。孫過庭講:“達其情性,形其哀樂。”[17]張懷瓘指出:“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得簡易之道。”[18]《記白云先生書訣》云:“把筆抵鋒,肇乎本性。”[19]劉熙載講:“學書者有二觀,曰觀物,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20]

成都青羊宮影壁“道”字書法 作者供圖
真情實感得以流露,首先需書者心無雜念,置自身于虛靜恬淡之境。蔡邕《筆論》講:“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21]否則,“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22]。《題衛夫人〈筆陣圖〉后》載:“夫欲書者,先乾研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23]唐太宗李世民說:“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24]以上書家對“靜”的強調,其思想淵源來自道家思想,老子講:“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25]“重為輕根,靜為躁君。”[26]指出“靜”更為根本,這無疑為書法創作提供了形上依據。
創作好的書法作品更需書者忘名利、忘法度。周星蓮講:“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27]《新唐書》說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28]。戴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29]黃庭堅答弟子說:“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30]以上均說明 “忘”的重要性,這些思想與莊子“三忘”之說相契合: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后成見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31]
以上對“真”“靜”“忘”的強調,充分體現出莊子“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害己”,不“追于時”,不“拘于財”,不“屈于勢”的理想人格追求,從而達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32]的“逍遙游”化境,實現人生的“無待”狀態。盡管這種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但在藝術王國里卻不是烏托邦,當書者以這種“無待”精神狀態創作時,便進入“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遙游,……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33]的境地。而書法中最能體現道家“逍遙游”思想內涵的書體莫過于草書,其筆畫連綿,線條無拘無束,筆墨在白紙上恣意揮灑,表達出道家追求的自由狀態和逍遙境界。宗白華說:“行草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的點畫自如,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34]例如,張旭“每醉后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35],懷素“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36]。
(三)道家形神觀與書法
道家思想“貴柔”“守雌”,推崇“女性”“嬰兒”“流水”的品性,視柔美淡雅、朦朧含蓄、靈動飄逸為美。表現在書法藝術上,字體線條富于變化,方與圓、曲與直、長與短、粗與細、濃與淡、輕與重、緩與急、疏與密、虛與實、斜與正、巧與拙巧妙組合,且字體線條多屈曲柔和,傳遞出道家“貴柔”“尚虛”的理念,賦予字體以動感和生命氣息。索靖《草書狀》講:“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婀娜以羸羸,欻奮亹而桓桓。”[37]
此外,道家在審美旨趣上不僅僅停留在具象層面,老子講“大象無形”,指出有形之物背后之“象”最為根本,書法創作更應追求其內在精神和意境。王僧虔《筆意贊》講:“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38]張懷瓘《文字論》說:“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39]這里的“神”屬書法意象層面,正如老子所講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0],莊子的“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41]。關于對書法意象的把握,虞世南說:
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學者心悟于至道,則書契于無為,茍涉浮華,終懵于斯理也。[42]
二、書法中的道教情結
道教作為宗教,與道家有著本質不同。它由張道陵于東漢末年創立于巴蜀,最初稱“五斗米道”,在吸收道家黃老思想基礎上,糅雜進方仙道、巴蜀巫術、佛教和儒家思想等內容。書法作為藝術形式進入文人視野也始于這一時期,時間上二者相契合。魏晉時期,早期五斗米道有一個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過程,宗教素質獲得提升。這一過程中,書法藝術與道教間發生頻繁社會互動,建構起廣泛內在聯系,這可以從崇道之士與書法和道教與書法兩方面加以探討。
(一)崇道之士與書法
這里所講的“崇道之士”并不僅限于道士,還包括對道教有著情感歸宿的各類人士,他們多身兼數藝,其中諸多還是書法大家,最為突出的要數王羲之與王獻之父子。王羲之篤信道教,其家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且“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43],晚年又與道士許邁交游,二人共修服食,不遠千里采拾藥金。他還曾書《道德經》換鵝:“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44]王獻之也是道教信徒,曾請道士避邪驅鬼,并交代了自己一生最為悔恨之事——與前妻郗道茂離婚。米芾《畫史》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45]“畫符”與“神咒”均為道教法術,由此可窺見王獻之的崇道情結。
東晉道士楊羲,字羲和,道教上清派重要傳承人,《茅山志》記有“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并名海內”[46]。據此知,當時楊羲書法成就與王羲之齊名,關于此,陶弘景《真誥》評論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并于‘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故也。”[47]
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也工于書法,《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說他“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勁媚”[48]。《宣和書譜》說他:“主草隸,而行書尤妙。大率以鍾、王為法,骼力不至而逸氣有余。”[49]可見,陶弘景將道教所推崇的柔美、飄逸、脫俗氣質融入其書法。《與梁武帝論書啟》記載有他關于書法“形”與“意”關系的論述:
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名偕,……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50]
當然,陶弘景作為道教徒,其關注點不僅僅是藝術追求,更重要的是他深切的宗教情感,他曾說:“時人今知摹‘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真經”[51],還曾百般周折搜尋道教真跡書法,《云笈七簽》載: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孫游岳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真本,而經歷摹寫,意所未愜者,于是更博訪遠近以正之。戊辰年(488)始往茅山,便得楊、許手書真跡,欣然感激。至庚午年(490)又啟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并得真人遺跡十余卷。[52]
唐顏真卿,字清臣,一代名臣和書法家,雖非道士身份,卻屬崇道之士,這首先從其“真卿”之名可獲知,杜光庭《墉城集仙錄》曰:“食四節之隱芝者位為真卿。”[53]《太平御覽》云:“三清九宮,并有僚屬,例左勝于右,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54]顏真卿早年與道士就有交往,據載:“子有清簡之名,已志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煉神陰景,然后得道也。”[55]顏死后逐漸被仙化,獲得仙籍,《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有“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56]之語。關于其書法,李建春說他銳意改革,推陳出新,一改東晉以來“二王”書體。“不管是初唐四大家中的歐陽詢和虞世南,還是褚遂良,都盡心盡力效其法,不敢任意亂越雷池,以至于在他們的書體中,總能或多或少地見到‘二王’影子。……然而,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特殊環境中,盛唐書家顏真卿卻能‘眾叛親離’大膽創出與‘二王’書風毫不相干的《贈裴將軍詩帖》。”[57]
杜光庭,五代時著名高道,一生輾轉于浙江、長安及蜀地等,游歷全國多處名山大川,看透人世間沉浮滄桑,這使其擅長的楷書灌注清幽脫俗、瘦勁奇崛、仙風道骨的韻味,自成一家。《宣和書譜》評有:
嘗撰《混元圖》《紀圣賦》《廣圣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僅百余卷。喜自錄所為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58]
崇道之士們擅長書法的情況不勝枚舉,如葛洪、寇謙之、蘇軾、虞世南、張旭、宋徽宗趙佶、黃庭堅、趙孟、張雨、任法融等,在此不一一贅述。
(二)道教與書法
關于道教與書法關系,首先應從道教神秘主義文字觀談起,道教宇宙論秉持“道生元氣”觀,文字由道氣化生。《三皇經》云:“皇文帝書,皆出自然虛無,空中結氣成字,無祖無先,無窮無極,隨運隱見,綿綿常存。”[59]《太上洞淵神咒經》曰:“天書玄妙,皆是九炁精像、百神名諱,變狀形兆,文勢曲折,隱韻內名,威神功惠之所建立。”[60]《云笈七簽》云:“自然飛玄之氣,結空成文,字方一丈。”[61]《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講:“上清寶書,以九天建立之始,皆自然而生,與氣同存。”[62]《隋書·經籍志》說:“所說之經亦亶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63]《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描述了“真文玉字”產生過程:
生于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靈文暗藹,乍存乍亡,二儀待之以分,太陽待之以明,靈圖革運,玄象推遷,乘機應會,于是存焉。天地得之而分判,三景得之而發光。靈文郁秀,洞映上清,發乎始青之天而色無定方。文勢曲折,不可尋詳。元始煉之于洞陽之館,冶之于流火之庭,鮮其正文,瑩發光芒,洞陽氣赤,故號赤書。[64]
道教認為天上的“三元五德八會”之炁自然結成“天書云炁”,黃帝“以云為紀”創造出“云書”。《真誥》云:“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群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云篆明光之章也。”[65]“三元八會”與“云篆明光”指兩種書體,前者是道教最原始、最高級別書體,僅神明能識別和使用,后者則由“三元八會”體衍生而來,用于人神溝通,是道教符書來源。
《說文解字》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66]《漢書·文帝紀》云:“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67]應邵注曰:“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68]張晏注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易也。”[69]可知,所謂“符”,是將文字或圖案鐫刻于竹簡上,分兩半保存,一半留京師,一半留郡縣,每當使臣奉帝王旨意到達地方,憑符合取信。因此,“符”又有“托付”之意,《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于上,付使傳行之也。”[70]道教產生后,借用“符”的內涵,在符上書寫“云篆明光”式文字,內容多為神真名諱、形貌、符咒等,并托之神仙所頒,施之于鬼神世界,以達到招神劾鬼、鎮邪扶正、消災祛病目的。正像《道法會元》中描述的:“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精精相附,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紙,號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對。”[71]又《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曰:“符者,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隨符攝召下降。”[72]
由于受神秘主義宗教觀支配,道教符書文字形狀怪異,晦澀難辨,莫知所云。盡管如此,符書文字還是源于現實,是道士對漢字的有意識改造,例如《太平經》中收錄的幾百個符,幾乎都是漢代隸書若干字合體,為增強神秘感,又突破了漢字筆畫束縛,創造出更加奇異難辨的文字。因此,道教符書作為一種獨具意味的書法形式,要求必須由擅長書法的道士書寫,道符書寫優劣直接影響其靈驗與否,道門中有“畫符若知竅,驚得鬼神叫;畫符不知竅,反惹鬼神笑”的說法。
畫符道士往往承擔抄寫道經任務,促進了書法藝術發展。長期的書寫實踐中,他們將道教中貴柔尚虛、輕舉飛升、重神守一的義理灌注于書法,賦予道教書法瘦勁飄逸、奇異灑脫之美。另在抄經過程中,為追求速度,道士往往將字體筆畫連綿在一起,客觀上促進了草書的發展。但這也遭到陸修靜指責,認為草書抄經是奉道之心不誠的表現,他說:“愚偽道士,既無科戒可據,無以辯劾虛實,唯有誤敗故章、謬脫之符,頭尾不應,不可承奉,而率思臆裁,妄加改易,穢巾垢硯,辱紙污筆,草書亂畫。”[73]
道教符書與書法的相通還表現在書寫前的準備上。一幅好的書法作品,強調書者應“凝神靜心”,以達到“心靜體松,以意引氣”和“靜中求動,形神合一”的書法意境。王羲之《書論》講:“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74]虞世南說:“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則顛仆。”[75]以上強調的與道教所講的“存神”“守一”實為同源之語。《道法會元》講:“入靖,具列香爐、水盂、朱墨、筆硯、符箓于前,煉師端坐,收視返聽,滅念存誠,呼吸定息,物我兩忘。于大定光中,運心上朝慈尊,略述齋意,乞降符箓奉行。”[76]不過,道士書符過程更強調書者之誠心,《三洞神符記》強調:“收視反聽,攝念存誠,心若太虛,內外貞白,元始即我,我即元始,意到運筆,一炁成符。若符中點畫微有不同,不必拘泥,貴乎信筆而成,心中得意妙處也。”[77]
盡管如此,道教符書與書法分屬不同范疇,二者有著本質區別:首先,書寫目的不同,文人創作書法以求寄托書者思想情感和人生追求,而道教符箓則充當人神溝通的媒介,以達到召劾鬼神、鎮壓精怪、祛病消災的目的;其次,在書寫過程中,道士必須滿足的首要條件是“心誠”,不能任自己主觀喜好任意發揮,這限制了符書書寫的自由,更不可能像草書筆墨天馬行空式地游走;再次,表現力不同,書法追求的是書體的美感,而道教符箓作為人神溝通載體,追求的是宗教神圣性,以使信眾產生敬畏和崇奉之心。基于此,道教符箓字體繁復連綴、神秘莫測,不知所云;此外,道教符箓也會施之以圖繪,用反映彼岸仙境的圖形意象以表現道教的玄幻縹緲。
結語
綜而論之,書法藝術與道家及道教間是一種相表里的存在,要想從書法簡單的線條走勢中獲得審美體驗,需從中領悟道家思想所蘊含的辯證觀、自然觀和形神觀。其中辯證觀揭示了書法藝術在布局、墨法、筆法、結體方面的創作原則。從自然觀上審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書法的產生是一個自然過程;第二,書法取象源于自然物象;第三,書法是真情實感的流露。要想書寫一手上乘的書法作品,除了熟練掌握基本的書法技巧外,還需要涵養自己的精神境界,修煉出“真”“靜”“忘”“游”的人格品性。形神觀反映了書法藝術在審美上的道家旨趣,在追求線條柔美飄逸風格的同時,更看重線條背后所承載的意境和神韻。道教與書法藝術間則折射出廣泛、多層次的社會互動:一方面,道教與書法藝術登上人類歷史舞臺在時間上比較契合,且都曾普遍受士人青睞,歷史上崇道之士較其他人更多地擅長書法,他們不自覺地把對道教義理的領悟融入書法創作中,創造出諸多獨具道教韻味的“煙霞體”,并且促進了行書和草書的發展;另一方面,書法藝術為道教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在書寫形式上衍生出道教符箓體文字,促進了道教符箓術的產生和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