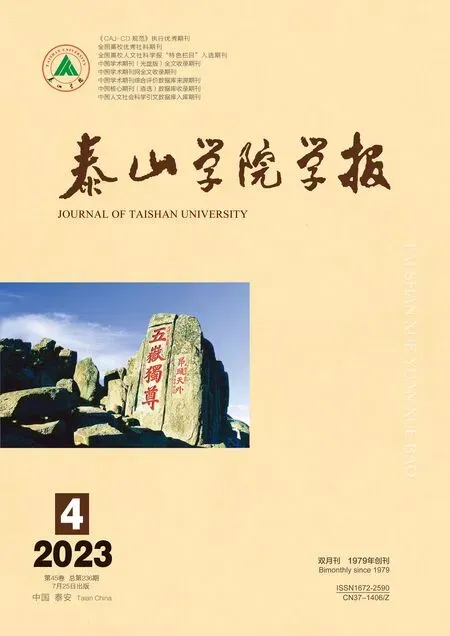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分析
丁雨凡
(安徽工業大學 商學院,安徽 馬鞍山 243000)
引言
“二十大”提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源是有限的,且邊際效益遞減,通過要素的投入獲得經濟產量的持續增加模式不可取,長期的經濟增長需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鄉村振興,鄉村振興離不開鄉村產業發展,鄉村產業發展對于小康社會成果的鞏固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推進發揮著重要作用。2020年7月,農業農村部印發的《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2020-2025)》指出要發掘鄉村功能價值,需聚集資源要素,優化要素配置,加快發展鄉村產業,提升產業質量效益。(1)農業農村部印發《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2020-2025)》的通知[EB/OL].(2020-07-16)http://www.moa.gov.cn/govpublic/XZQYJ/202007/t20200716_6348795.htm.在此背景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要在深層次上找尋經濟增長的潛力,要以優化要素配置、促進全要素生產率、促進鄉村產業發展為導向。
國內外學者對于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鄉村產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路徑研究。研究認為,首先,勞動力作為重要的資源要素,其流向對鄉村產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勞動力外流從供給數量、質量、結構上改變農村勞動力配置,改善農業資源配比關系,(2)唐偉成,彭震偉,朱介鳴.誘致性制度變遷下的村莊要素配置機制研究——基于長三角的案例分析[J].城市規劃,2019,43(06):40-46.(3)張世貴.城鄉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協同機理與改革路徑[J].中州學刊,2020(11):70-76.勞動力的流出驅動農戶進行要素替代,增加農藥化肥、機械類等資本性投入,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的要素水平,(4)JI Y,YU X,ZHANG F.Machinery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23(1):71-80.同時勞動力的流出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勞動力的過度配置問題。(5)Ngai L R.,et al.China’s mobility barriers and employment allocation[J].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9,17(5):1617-1653.勞動力返鄉能夠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率,土地會在不同的勞動生產率主體之間進行重新配置,通過土地流轉間接影響勞動生產率。(6)Adamopouios T,Restuccia D.Land Reform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Micro Dat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20,12(3):1-39.而勞動間的專業化分工也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促進鄉村產業發展。(7)張鳳兵,王會宗.勞動力返鄉、要素配置和農業生產率[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03):73-84.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會進一步促進農戶生產積極性,促進鄉村產業發展產出水平。(8)Alam A S A F,Begum H,Masud M M,etal.Agriculture insura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case study of Malays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0(47).其次,優化市場配置效率對于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建立更高標準市場體系具有重要作用。(9)王一歡,詹新宇.僵尸企業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基于全要素生產率分布的視角[J].當代財經,2021(4):3-15.商品市場化的同時并未建立城鄉統一、競爭有序的生產要素市場,這就導致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難以實現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要素生產率并未實現最優化。同時,地方政府對市場要素配置存在過度干預,這就使得市場的作用發揮不顯著。(10)徐鵬杰,王寧,楊樂晴.要素市場化配置、政府治理現代化與產業轉型升級[J].經濟體制改革,2020(5):86-92.我國要素市場存在扭曲配置,與商品市場相比存在滯后,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勢在必行。應充分發揮要素市場導向作用,激活要素、市場、主體,以鄉村的企業為載體,引導資源傾斜于鄉村。(11)王留鑫,姚慧琴,韓先鋒.碳排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與農業經濟增長[J].經濟問題探索,2019 (2):142-149.最后,堅持融合發展,優化要素配置,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堅持產業融合發展,優化農業、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配置,促進兩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進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12)王陽.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與經濟發展效率——以勞動力要素城鄉配置變化為例[J].經濟縱橫,2020(7):67-76.
以上是當前研究的主要成果撮要,可以發現全要素生產率與鄉村產業發展的研究尚屬少見,更多的是考慮兩者之間的關系。其中,全要素生產率與鄉村產業發展的研究主要是偏向定性分析,缺乏實證研究。本文擬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探尋其存在的邏輯機理,并通過實證進行驗證。同時,要素配置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居多,其中多為土地要素配置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農業用地政策的變化,土地要素會對資本和勞動要素產生連帶影響,最終通過影響資本、勞動要素配置以適應新的生態狀況,(13)羅慧,趙芝俊,錢加榮.要素錯配對中國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8(1):97-110.故本文不再將土地作為單獨的要素進行研究。技術、數據等也是重要的要素,但它們最終還是通過影響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要素的相對成本來影響生產率,(14)徐杰.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進的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優化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21.故本文主要從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進行研究,分析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
一、機理分析
要素錯配與要素最優配置相對立,要素錯配實質上就是要素配置結構不合理,未達到最優的配置效率。整體上看,我國行業間勞動要素配置扭曲情況較為嚴重,如果能夠按照優化原則矯正扭曲,則會提高全社會產出總量和全要素生產率。(15)任韜,孫瀟筱.中國行業間勞動要素配置扭曲及對經濟的影響分析[J].數理統計與管理,2021,40(2):352-365.有學者在研究農業部門要素錯配時指出,城鄉勞動力要素錯配引起全要素生產率的負效應,資本要素的錯配及不均衡使得農民福利損失。(16)郭珍,郭繼臺.鄉村產業振興的生產要素配置與治理結構選擇[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2 (6):66-71.農業部門配置過多勞動力和過少資本,抑制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有效消除兩者間的不合理配置,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可能會再增長。(17)羅慧,趙芝俊,錢加榮.要素錯配對中國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8(1):97-110.對農業而言,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關鍵,也是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的關鍵。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很好地衡量農業生產效率,因此需要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來推進鄉村產業發展。(18)劉志彪,凌永輝.結構轉換、全要素生產率與高質量發展[J].管理世界,2020,36(07):15-29.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利于促進鄉村產業長期可持續發展,(19)金紹榮,任贊杰,慕天媛.農業保險、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與農業經濟增長[J].宏觀經濟研究,2022(01):102-114,160.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衡量技術進步、技術效率、配置效率、規模效率,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20)朱晶,晉樂.農業基礎設施、糧食生產成本與國際競爭力——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檢驗[J].農業技術經濟,2017(10):14-24.(21)林青寧,毛世平.產業協同集聚、數字經濟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2,27(8):272-286.現代化的資本、人才將流向鄉村,形成規模效應。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將其與農業發展相融合,并在“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下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及效率,有助于鄉村產業振興的深入推進,提升鄉村產業發展。要素錯配不利于鄉村產業發展的要素水平及產出水平,也抑制產業結構升級,各產業部門之間的要素錯配也影響著部門之間的密切融合。
二、數據與指標測算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參考薛超和周宏(22)薛超,周宏.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方向與要素結構匹配度的區域差異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9,35(5):136-140.的指標選取,資本要素投入用農林牧漁業中間消耗表示,中間消耗包括用種、化肥、農藥、用電等農業生產性支出,勞動要素投入用農林牧漁業就業人數表示。本文依據國家統計局口徑將全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甘肅、陜西、青海、寧夏、新疆。本文選用2011-2020年數據,運用Stata17.0軟件進行數據測算,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統計年鑒。本文對數據進行收集與整合,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進行處理。
本文選擇2011-2020年的相關數據,源于兩方面:一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農業發展進入穩定向好階段,以農產品加工業為代表的一二產業融合與以鄉村旅游業為代表的一二三產業融合加速發展,促使鄉村產業發展逐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十九大報告中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更是推動了鄉村產業加速發展。二是在2010年我國全民生產總值連續兩個季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政府提出經濟增長將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這就意味著2010年前后的經濟發展將是差異巨大的兩個賽道,同時“改善民生”成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加大節能減排的政策調整造成國內經濟中心由傳統工業向鄉村產業遷移。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順利啟動、西部大開發十年以來取得重大成果等,使我國內外經濟發展面貌煥然一新,國內經濟形勢在2010年后迎來新一輪的發展。
本文涉及的要素相關價格指標如下:勞動力價格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資性收入代替;資本價格以5年期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官方基準利率的3倍表示。根據國家統計的要求,從2014年開始,采用農民人均可支配工資性收入指標反映農民收入水平情況,不再使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指標,所以2011-2013年的勞動力價格使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指標,之后的2014-2020年使用農村居民可支配工資性收入指標。
(二)指標測算
1.要素配置測算
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若要素的邊際產品收益與邊際產品一致,表明要素配置是最優狀態,若存在不一致則表明存在要素錯配。本文尋求改善要素錯配來優化要素配置,故以要素錯配情況來判斷要素配置的優劣。有學者運用要素價格扭曲指數來測算要素錯配指數,(23)王衛,綦良群.要素錯配、技術進步偏向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于裝備制造業細分行業的隨機前沿模型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8,40(12):60-75.(24)白俊紅,劉宇英.對外直接投資能否改善中國的資源錯配[J].中國工業經濟,2018(01):60-78.然而,對于農業發展而言,受環境、其他非農就業機會及金融市場等限制,即使要素價格不變,也會出現要素配置非最優情況,以要素價格扭曲指數來測算要素錯配指數易產生誤差,致使測算結果可信度低。(25)羅慧,趙芝俊,錢加榮.要素錯配對中國糧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8(01):97-110.因此,本文將要素錯配指數設定為要素投入的實際成本份額Zj與其產出彈性Lamj的差值,當差值大于0,則表示配置過度,若小于0則表示配置不足,選用絕對值表示要素錯配指數,具體如式(1)所示:
(1)
其中εj為第j種要素的產出彈性,cj為第j種要素的實際成本,本文主要考慮兩種生產要素,分別是資本要求K和勞動要求L。
依據上述測算方法,本文對2011-2020年各省市的要素錯配指數進行了測算,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20各省平均總要素錯配及其指數
從表1可知,各省在2011-2020年都存在著要素錯配的現象。從整體來看,各省市的總要素錯配指數均大于1,其中總要素錯配指數排在前三位的是西藏1.498、青海1.456、海南1.343,資本要素錯配指數排在前三位的是廣西0.816、四川0.813、云南0.805,勞動要素錯配指數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1.049、上海1.047、西藏0.858。這說明西藏、青海、海南存在相對嚴重的資本、勞動兩要素錯配,廣西、四川、云南存在相對嚴重的資本要素錯配,北京、上海、西藏存在相對嚴重的勞動要素錯配,需引起相關部門對這些地區的關注。對比各省市的資本、勞動要素錯配指數,大多數省份的資本要素錯配指數要大于勞動要素錯配指數,北京、天津、上海、山西、西藏、甘肅、青海、寧夏的資本要素錯配指數要低于勞動要素錯配指數。北京、天津、上海、山西這四個地方的經濟水平較高,資本利用率更加充分。西藏、甘肅、青海及寧夏這四個地方的經濟水平較低,且勞動人員流動性較低,可能是導致這樣情況發生的原因。
2.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測算
為了更準確的分析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很多經濟學家嘗試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進行實證分解。本文借鑒其他學者的研究方法,(26)涂圣偉.我國農業要素投入結構與配置效率變化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7(12):148-162.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TFP分解為技術效率、技術進步、規模效率以及配置效率四個部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分解方程如式(2)所示:
(2)

lnYit=α0+γ1lnKit+γ2lnLit+γ3t+γ4(lnKit)2+γ5(lnLit)2+γ6t2+γ7lnKitlnLit+γ8tlnKit+γ9lnLit+θit
(3)
式中Yit代表t年第i省的產出,Kit、Lit分別表示為t年第i省的資本要素投入與勞動要素投入,θit為誤差項,β1-β9均為估計參數并用于計算要素的產出彈性,α0為常數項。
依據上述超額對數生產函數模型進行生產函數估計,該模型主要考慮資本、勞動要素及時間對產出的非線性和組合作用。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依據生產函數的估算結果測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分解項的結果如表2所示,各省份2012-2020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均為正值,其中排在前兩位的是西藏0.048、青海0.048,排在后兩位的是廣東-0.003、山東-0.001。山東省呈現負值主要是由技術效率變化而導致,廣東省則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呈現負值而導致的。山東整體上屬于工業省份,對于農業發展的技術投入相比工業要薄弱一些,廣東農業現代化發展存在基礎設施水平相對落后、農業現代化技術投入相對滯后等問題。同時,各個省份的技術進步貢獻率總體最高,其次是配置效率的貢獻率,貢獻最小的是規模效率。其中河北、江蘇及吉林的技術進步貢獻率最高。河北、江蘇屬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的經濟水平相比中西部較高,技術創新的進程相比中西部也較快。吉林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處于前三位的原因是國家十分重視吉林的農業發展,具有大批技術性人才,基礎建設比較好,大型技術裝備比較充足。
3.鄉村產業發展的評價體系構建與測算
目前關于鄉村產業發展的綜合評價體系研究較少,主要集中于鄉村振興(27)申云,陳慧,陳曉娟,等.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分析[J].世界農業,2020(02):59-69.(28)康書生,楊娜娜.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效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2(02):110-118.、鄉村產業結構、鄉村產業融合發展(29)田聰華,韓笑,苗紅萍,等.新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應用[J].新疆農業科學,2019,56(03):580-588.(30)楊賓賓,魏杰,宗義湘,等.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測算[J].統計與決策,2022,38(02):125-128.、農業現代化(31)李婕妤,姚鳳閣,路少朋.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現代化關系研究[J].學習與探索,2017(03):131-137.及農業高質量發展(32)辛嶺,安曉寧.我國農業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與測度分析[J].經濟縱橫,2019(05):109-118.等。
本文基于產業發展理論,對前人的指標進行了分類及拓展,增加了鄉村產業要素水平(33)要素是產業發展的基礎能力,是考察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不可或缺的部分。指標。將鄉村產業發展評價體系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鄉村產業要素水平、鄉村產業產出水平、鄉村產業結構水平及鄉村產業融合水平,在指標體系測算方面,現階段用于指標體系權重的常用測算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Delphi法、AHP法、熵權法等。由于熵權法的測算是依據數據變異程度反映的信息,所以客觀性較強,能較好避免主觀賦權的隨意性,因此本文選用熵權法對指標體系進行測算,選了14個二級指標,具體指標體系詳情如表3所示:
本文依據熵權法對2011-2020年31個省市的鄉村產業發展綜合評價水平進行了測算,同時對2011-2020年各省市十年的結果進行了均值測算,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知,各省市2011-2020年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大致處于上升趨勢,表明中國各省市的鄉村產業發展水平都在不斷提升。對比各省市十年來鄉村產業發展均值水平,排在前六位的省市為上海0.600、北京0.600、浙江0.481、天津0.469、江蘇0.423、遼寧0.389,這6個省市均屬于東部地區,表明東部地區的鄉村產業發展相對發達。排名后六位的省市為西藏0.313、甘肅0.284、貴州0.280、廣西0.279、云南0.275、海南0.267,除海南以外,其余五省都屬于西部地區,表明相對而言,西部的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在東中西三地區中最弱。
三、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
為分析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鄉村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論證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設置具體模型如下:
RIDLit=α4+δ11Disit+δ12Controlit+ε1
(4)
△TFPit=α5+δ21Disit+δ22Controlit+ε2
(5)
RIDLit=α6+δ31Disit+δ32Controlit+δ33△TFPit+ε3
(6)
其中,RIDL為被解釋變量,代表鄉村產業發展水平;△TFP為中介變量,代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Dis為解釋變量,代表要素錯配指數;Control為控制變量,包括城鎮化水平和政府干預水平;α4、α5、α6、ε為常數項及誤差項;i、t表示省份及時間。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討論
本文利用中介效應模型對要素錯配、全要素生產率與鄉村產業發展的測算結果進行實證分析。首先運用逐步分析法檢驗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具體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模型(1)(4)(7)(10)以被解釋變量為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來進行式(4)的回歸分析;其次以被解釋變量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來進行式(5)回歸分析;最后對式(6)以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為被解釋變量來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知,從全國層面來看,三步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均顯著,模型(1)(2)綜合要素錯配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26、-0.029,模型(3)中綜合要素錯配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14、0.407,表明全國的要素配置在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機制中存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中介作用,要素錯配程度越高,部分會抑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從而抑制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的提高。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的模型(5)中綜合要素錯配在10%顯著水平下,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到了抑制作用。模型(6)△TFP在1%水平下顯著,其系數為0.390,表明東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助于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模型(5)(6)的綜合要素錯配系數均在顯著水平下,即存在中介效應,模型(6)中綜合要素錯配的系數為-0.190,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東部地區的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存在直接抑制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部地區的模型(8)中綜合要素錯配的影響系數為-0.028,模型(9)△TFP在10%水平下顯著,其系數為0.023,模型(8)(9)的綜合要素錯配系數均在顯著水平下,即存在中介效應,模型(9)中綜合要素錯配的系數為-0.170,在5%水平下顯著,表明中部地區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存在直接抑制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西部地區的各步驟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均顯著,模型(10)(11)的綜合要素錯配的影響系數分別是-0.149、-0.015,模型(12)的綜合要素錯配指數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是-0.139、0.677,表明西部地區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存在直接抑制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對比全國及區域層面,就直接抑制效應而言,全國大于東中部,西部最小;就中介效應而言,全國大于東西部,中部最小。產生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東中部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區,其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也高于西部地區,東中部后期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提升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所驅動的動力有所減弱,因此東中部要素錯配對鄉村產業發展帶來的直接影響要高于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所帶來的中介效應要弱于西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就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對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運用中國2011-2020年31個省相關數據,分別采用要素錯配指數、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解法、熵權法對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進行測算,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實證分析要素配置如何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這一過程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進而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研究結論如下:(1)考察期內要素錯配抑制鄉村產業發展,同時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起到抑制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助于鄉村產業發展;(2)考察期內要素配置在鄉村產業發展的影響機制中存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中介作用,要素錯配程度越高,部分會抑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從而抑制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的提高;(3)就直接抑制效應而言,東部地區大于中部地區大于西部地區,就中介抑制效應而言,西部地區大于東部地區大于中部地區。
(二)政策建議
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堅持技術創新,改善外部環境,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技術進步高低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方面,將技術進步與創新和改造傳統產業相結合,運用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強化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并加大支持力度,注重將新技術更直接更迅速地用于生產。政府應加大改善鄉村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緊跟步伐。當前產業發展面臨著要素錯配的問題,傳統農業升級的研發支持不足,企業高層次創新人才不足,勞動力要素的質量不高,因此,需進一步改革中國現有的產業政策,繼續促進要素配置由外生干預型向內生自主型轉化。
二,改善要素錯配,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需要完善要素市場,將農村農業生產要素激活,形成“農民+企業+社會”三方結合的鄉村發展格局。
三,鄉村產業的優化升級離不開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需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二三產業發展需要農業農村資源為依托,形成農業產業鏈,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注重農村產業的交叉融合,依托當地特色資源,培育發展優勢主導產業,有效增加農民受益,帶動鄉村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