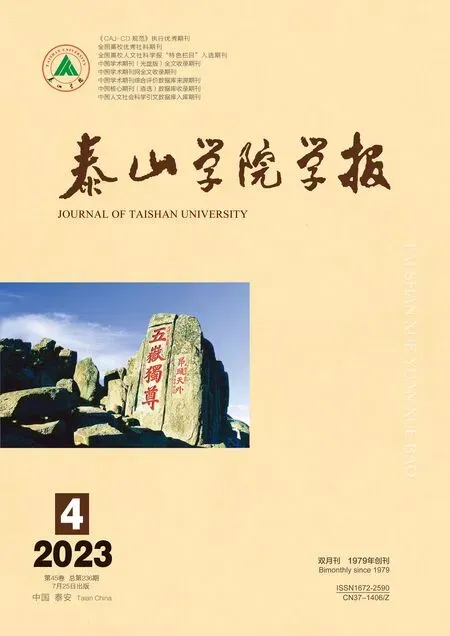系統論視角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演化過程與機制研究
——以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為例
陳 振,馬揚梅,童登峰,張 津,陳 麗
(1.安徽職業技術學院 文化與旅游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2.安徽師范大學 地理與旅游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3.合肥一六八新店花園學校 教學部,安徽 合肥 230000)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社會發展重點需求為基礎,對國家全局與長遠發展極具引領帶動作用,且存在重大技術突破與成長潛力特征的產業(1)劉志陽,程海獅.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群培育與網絡特征[J].改革,2010(5):36-42.。根據M.E.Porter的產業集群理論,集群是系統各要素協同作用力的耦合(2)Porter.M.E.Competitive Advantage,Agglomeration Economies,and Regional Poliey[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lew,1996(19):85-95.,產業要素間形成競爭與合作并存的“競合”網絡(3)劉超,梁月鋒.場域理論視闕下產業學院的生成、困囿與發展路徑[J].豫章師范學院學報,2023(1):103-107.(4)羅慧芳.新興產業集群內知識創新網絡的構建與分析[J].商業時代,2012(27):113-114.是產業集群的關鍵。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作為新興產業要素集聚的新模式,學者們已經從網絡競合、區域創新環境、產業圈、共享經濟、政府干預等多角度界定其定義(5)張敬文,李曉園,徐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發生機理及提升策略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6(11):106-113.(6)鄧龍安,劉文軍.產業技術范式轉移下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自適應創新管理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1,29(2):7-11.(7)張治河,黃海霞,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形成機制研究—以武漢·中國光谷為例[J].科學學研究,2014,32(1):24-28.(8)王歡芳,何燕子.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式發展的路徑探討[J].經濟縱橫,2012(10):45-48.(9)牛立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與演進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1:133-137.(10)李楊,沈志漁.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創新發展規律研究[J].經濟管理與研究,2010(10):29-34.。概括而言,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核心,行業重點項目、龍頭企業,關聯產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輔助機構等共同構成的空間上的集中,具有創新驅動、知識溢出、協同競合等特征的空間結構(11)劉華軍,王耀輝,雷名雨.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及其演變[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7):99-116.(12)汪秀婷.戰略性新興產業協同創新網絡模型及能力動態演化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2(11):51-57.(13)李煜華,武曉鋒,胡瑤瑛.基于演化博弈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策略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30(2):70-73.,本質上是以當代技術革新為基礎,大力提升附加值的新興產業集群(14)陳衍泰,程鵬,梁正.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演化的四維度因素分析—以中國風機制造業為例的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2,30(8):1187-1197.。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是現代創新科技與未來社會需求的深度融合,它強調利用系統網絡實現跨越組織界限的協同創新與共享,最終提升整個集群核心競爭力(15)李曉華,呂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征與政策導向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0(9):20-26.(16)熊勇清,李世才.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耦合發展的過程及作用機制探討[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31(11):84-87.(17)王新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律及發展對策分析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1,29(4):1-5.。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由粗放向集約轉變的關鍵節點,在集約型增長背景下,經濟發展將更多地依賴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2016年12月我國出臺了《“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更加明確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向。合肥作為我國制造產業帶動城市飛躍的典型,近年來已形成以當代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國際技術型重點項目與地方優勢產業為主導的先進制造業體系,具有典型的地方專業化產業特征。為加快實現“中國制造2025”戰略部署與推動區域地方經濟創新發展,充分發揮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濟輻射作用,合肥加快推進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集聚發展的建設。2016年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培育和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2019年合肥市新型顯示器件產業集群、人工智能產業集群及集成電路產業集群成功入選國家第一批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在系統論視角下,本文以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為例,系統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演化過程、特征與動力機制,以期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研究有所貢獻。
一、相關理論選取
引用系統科學探討產業集群演化過程與機制是該類研究的新視角。系統論提出系統是由多個系統要素構成,系統演化過程實質上為系統要素從無序到有序的演變過程。非平衡系統在能量交換作用下,系統要素協同運動,最終在時空功能上實現系統結構的有序與平衡。
協同理論認為研究對象是由眾多子系統聯合構成,子系統間不斷運動,通過不斷突破臨界值(TC)促進整個系統演化,序參量(P)主宰系統演進。當P>TC時,系統發生質變,演化進入新的階段。
參考相關研究成果(18)魏江.產業集群—創新系統與技術學習[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52(19)哈肯.高等協同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47-53.(20)Harrison B.Industrial districts: old wine in new bottles[J].Regional Studies,1992(26):469-483.(21)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 483-499.(22)Novel li M,Schmitz B,Spencer T.Networks,clusters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A UK experience[J].Tourism Management,2006,27(6): 1141-1152.(23)Jackson J,Murphy P.Clusters in regional tourism: An Australian cas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6,33(4): 1018-1035.(24)朱俊成.基于共生理論的區域多中心協同發展研究[J].經濟地理,2010,30(8):1272-1277.,將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看成由核心子系統、關聯子系統、輔助子系統共同構成的系統結構(見圖1),具有非線性、非平衡性、復雜性與開放性等系統特征(25)李后強,艾南山.人地協同論—兼論人地系統的的若干非線性動力學問題[J].地球科學進展,1996,11(2):178-184.。其中,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中的重大項目、龍頭企業等產業要素(京東方、惠而浦、聯寶、蔚來等)構成其核心子系統,與核心子系統關聯的上下游產業要素(現代服務、現代物流、大數據產業、信息產業等)構成其關聯子系統,為系統提供關聯支持與保障的機構(政府,科研機構,行業協會等)構成其輔助子系統。各個子系統在序參量(P)推動下相互作用,促使整個系統結構不斷演化。

圖1 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結構
“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系統結構是新模式下的新興產業要素集聚,相對于傳統產業集群而言,有自身特點:一是集聚要素與產業業態不同。傳統產業集群主要集聚傳統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等),集聚業態主要體現為傳統生產業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集聚新興生產要素(人才、創新環境、政策支持等),集聚業態體現為高附加值新興生產業態。二是系統驅動機制不同。傳統產業集群系統主要靠規模驅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主要靠創新驅動。三是產業要素間連接形式不同。傳統產業集群主要通過產品價值鏈連接,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主要通過技術創新價值鏈連接。四是空間指向不同。傳統產業集群是資源、資本、勞動力等各種導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是技術、創新環境導向。五是創新形式不同。傳統產業集群側重于產品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側重于技術革新。
二、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演化過程分析
根據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要素間相互作用階段特征,以2005年合肥正式確定“工業立市”發展方針、2019年世界制造業大會召開并確立合肥為永久舉辦城市為時間節點,將其演化過程分為萌芽期、培育期與快速成長期三個階段,通過實地調研、政府官網等途徑收錄產業要素信息。
(一)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萌芽階段
2005年之前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萌芽階段,協同系統結構尚未形成,系統功能未能發揮,產業關聯度不足,系統創新環境不足以支持新興產業集群。這一時期,合肥制造業重大項目、龍頭企業入駐極少,核心子系統尚未發育完成。與高端制造產業相配套的上下游產業要素匱乏,關聯系統產業關聯度弱。同時,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行業協會、科研機構對于現代制造產業推動作用不明顯,輔助子系統效果不顯著。
(二)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培育階段
2005年至2019年是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培育階段,2005年合肥正式確定“工業立市”發展方針,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協同系統結構開始形成,系統功能開始發揮,產業關聯度明顯增強,系統創新環境不斷改善,系統要素間協同作用逐漸發揮。這一階段合肥擁有了多個千億級新興產業集群,以裝備制造、家用電器、平板顯示及電子信息、光伏、新能源及汽車零部件為主導產業,打造新興產業聚集地,形成以“芯屏汽合”“集終生智”為代表的數條重點產業鏈。這一時期,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重大項目、行業龍頭企業不斷增多,其核心子系統功能開始發揮。核心子系統吸引上下游關聯產業要素不斷集聚,政府、行業、科研等機構創新服務功能顯著增強,其關聯子系統、輔助子系統不斷完善。
(三)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快速發展階段
2019年以后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系統快速發展階段。2019年世界制造業大會在合肥召開,并將合肥確定為永久舉辦城市,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加速升級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2019年至2021年,三屆世界制造業大會共為合肥集中簽約項目2019個,總投資額高達19350億元人民幣。這一時期的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開始從“合肥制造”向“合肥‘智’造”轉變,系統更為注重創新能力,出現了協同競合網絡,集群內要素整合效應、技術溢出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共生經濟效應逐漸增強。現代合肥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建設始終以國際最前沿制造技藝為根本,不斷更新與調整配套產業結構,現已成長為以制造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區域優勢產業為主導、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新體系。
三、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演化機制分析
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協同系統結構主要通過系統內部與外部的物質能量交換及要素間相互作用形成序參量(P),其主要受地理租金、產業租金及創新環境三方面的影響(圖2),即:

圖2 合肥制造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協同系統結構演化動力機制
序參量(P)=f(地理租金、產業租金、創新環境)
首先,特定空間區位為新興產業要素帶來了超額利潤,成為“地理租金”(26)臧旭恒,何青松.試論產業集群租金與產業集群演進[J].中國工業經濟,2007(3):5-13.。空間非均質性促使產業要素為獲得“地理租金”而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空間區域形成了集聚。合肥傳統生產要素資源稟賦(土地、市場、勞動力等)與新興生產要素更新(信息產業、大數據、科研創新等)構成了核心子系統的空間非均質性,尤其是新興生產要素的不斷改善吸引了眾多制造業重大項目及龍頭企業入駐合肥。空間上的非均質性使得合肥對于制造企業吸引力大為增強,形成其系統序參量“地理租金”。在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初期,由于空間非均質性不顯著,對于新興制造產業核心企業吸引力不足,其系統演化緩慢。隨著“工業立市”方針確立、世界制造業大會召開,合肥科研實力增強,創新環境改善,促使合肥空間非均質性增強,新興制造產業不斷落戶,核心子系統不斷擴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不斷演化。
其次,市場經濟背景下,產業要素流動具有利潤指向性。新興產業要素會由利潤低的產業領域流向利潤高的產業領域,形成“產業租金”(27)臧旭恒,何青松.試論產業集群租金與產業集群演進[J].中國工業經濟,2007(3):5-13.。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重點項目、龍頭企業的入駐不僅在縱向上吸引上下游關聯產業要素,同時在橫向上影響同類相關品牌。在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核心子系統不斷發展的同時,因系統依附作用,其關聯子系統也不斷演化。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重點項目、龍頭企業的上下游配套設施、依附產業不斷完善,進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產業利潤,促使新興產業要素不斷流向該領域,系統序參量“產業租金”不斷增強。系統不斷演化的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合肥新興產業要素不斷向“產業租金”方向流動,在循環累積效用下,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吸引力大大增強。
最后,合肥制造業新興產業集群在產品技術革新過程中形成了集群創新競合網絡,要素間相互滲透,協同發展,構成了其系統序參量“創新驅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演化的根本動力在于產業技藝的不斷突破。合肥創新平臺不斷改善,孕育出突出的創新成果。截止2021年,合肥擁有各類研發機構超過1400家,共建26個創新平臺,培育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2574戶,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789家,集聚各類人才190多萬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子系統集聚大量創新要素,制造新興產業重點項目、龍頭企業及關聯產業要素又促進了創新成果的轉化,讓科技創新有了生命力。創新、人才、新興產業要素集聚三者形成良性循環,相互協同、互為融通,構建了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創新體系。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受政府強力推動和現代市場需求拉動,集群外部性特征驅動與內部要素共同推進其演化。
四、總結與啟示
從系統論視角,以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系統結構為框架考察,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其演化過程與機制、集群發展創新模式對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及研究有以下啟示:
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作為現代新興產業要素集聚的創新模式,與傳統產業集群在集聚業態、創新網絡、競合關系等方面存在本質不同,其發展演化主要由內部子系統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能量交換完成。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演化主要經歷了萌芽期、發育期和快速成長期三個階段,其演化動力機制主要源于空間非均質性所產生的“地理租金”、利潤指向所產生的“產業租金”、競合網絡所產生的“創新驅動”。
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知識與產業創新的結果,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影響力更多體現在創新區域生態系統,通過不同子系統間的良性互動,提升創新績效。合肥制造業新興產業集群帶動了區域產業創新網絡在構建過程中的互動協調,培育了核心企業、支撐企業及配套企業,促使產業鏈升級與都市圈的產業協同。
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作為復雜的系統結構,其演化研究仍然還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體系。基于系統論視角的闡述仍然存在諸多不足。一是受數據資料限制,能對集群內部重點企業間的產業鏈、技術鏈、創新鏈、競合網絡、共同成長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梳理。二是對子系統間相互作用關系未能進行準確測量,系統內部關鍵要素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推動功能未能深入研究。如世界制造業大會作為合肥制造新興產業集群演化的重要推動事件,其發展的作用力測度等問題,應做為進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