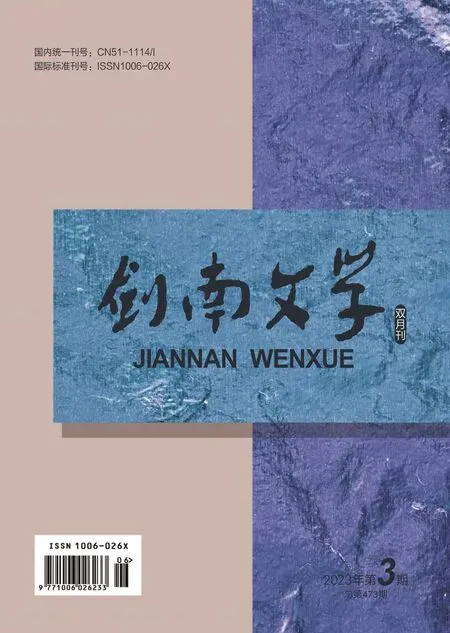讀唐筆記:詩歌與境界
□ 甫躍成
唐朝人姚合有一句詩:“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意思是說,我只要有一天去翻看了授官的名錄,那么我一整年的修行都給毀了。通過這句詩,姚合表了個態,就是,他認為“看除目”很掉價,一個淡泊名利的、有境界的人,不該留心于官職的升降、薪俸的多寡這類俗事——這大概是姚合想向讀者展示的自我形象,或者說是他的自我期許。然而也正是通過這句詩,我感覺到——原諒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姚合其實是動了“看除目”的心思的,否則無緣無故地,他為什么會想起來寫“看除目”這件事?整部《全唐詩》 里,“除目” 這詞也就只有他提到過。所以與其說姚合是真的不關心“除目”,倒不如說他是在動了“看除目”的心思后,寫下這么一句詩來勸阻自己。就是說,姚合事實上可能并不是一個不在乎世俗得失的人。雖然他有清高的表態,但我們總能從這表態后面覺出一些別的味道。在讀了他的一批詩歌后,我更加確信我的判斷。
姚合的詩歌當然很不錯,對后世影響極大,一千兩百年后,仍然有業余愛好者如我,虔誠拜讀。可以肯定,我們現在活著的這些詩人,沒幾個能取得這種跨越千年的成就。我舉上面的例子,不是要對姚合的詩歌有所非議,而是想說,一個詩人,無論他怎么雕琢,怎么描畫,怎么高自標舉,他都很難在詩歌中藏起他真實的自己。什么樣的人,就只能寫出什么樣的詩。你可以在詩歌中苦心經營一個形象,但如果這個形象不是你本來的模樣,一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腳;你可以在詩歌中努力表現你的悲憫、思考和真誠,但前提是你得有實在的悲憫、思考和真誠,生造出來的,很容易就被一眼看穿。從這個角度講,詩歌最大的瓶頸是詩人。詩人的層次,決定了詩歌的層次。
前不久在網絡上聽臺灣大學歐麗娟老師的講座,她做了一個有趣的對比:不同的詩人,他們筆下的聚會,形態有什么不同?
孟浩然說,“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杜甫說,“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李商隱說,“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而白居易說,“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前三聯淳厚,深情,洗盡鉛華;后面這聯,就只能說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了。
這樣的對比,乍一看,似乎對白居易有所不公,因為那一聯的主角畢竟不是他自己。可是我們不妨想:第一,世間的場景有千萬種,為什么你一提筆,腦子里首先蹦出來的,偏偏是這種?第二,對于這一場景,你持什么態度?讀完整首《琵琶行》,至少我,完全感覺不出白居易對這個擊節碎、翻酒污的場景有什么反感或不適。——沒有反感或不適,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所以與其說,不同的場景,是詩人有意識的選擇,倒不如說,是他們不自覺的流露;與其說是造境的、修辭的差距,不如說是詩人自身境界的差距。
而詩人自身境界的差距,在我看來,乃是詩歌最底層的差距。白居易跟杜甫的差距如是,姚合跟王維的差距亦如是。一千多年前的詩人,我們沒有親見,但他們的差距卻深深地刻在文本里,明明白白,不容置疑。這是一種令人絕望的差距:如果你不洗心革面,改造三觀,那么無論你如何尋章摘句,搜索枯腸,你都只能在原先的段位上來回蹦跶,而永遠無法更上一層樓。
在閱讀當代詩人的作品時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相當普遍的情況是,一個不太優秀的詩人,不管他寫了多少年頭,出了多少詩集,你只要讀他的三五十首詩,差不多就能看出他的精神底色和他不高的段位。也許在更多的詩歌里,他會涉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表象上可能千差萬別,但在內核上,他總還是徘徊于同樣的層次,很難有顛覆性的進步。他的眼界,他的關注點,他認可的東西,他的期待與抱怨,他的執念,基本上就是他的詩歌的天花板。而這個天花板,完全沒辦法靠作品數量的增加或寫作技巧的提升來捅破。老話說,功夫在詩外。詩內的功夫,能使你跳得更高,伸手碰一下天花板,卻不能給你一把梯子,讓你爬到上面那層。
所以相較于詩歌的技術問題,一個作者,寫到一定階段后,更需留意的,也許是自身的境界問題。技術問題相對淺表,不外乎是給同樣的意思,打磨一套更為有效的表達方式,對 “意思”本身并不審視。境界問題就隱蔽得多,它滲透進潛意識,神不知鬼不覺地作用于詩歌的大方向與小細節中,往往令作者不經意間,就落了下乘,任他怎么矯飾,都收效甚微。
這一發現對我不啻當頭棒喝。重讀以往寫下的諸多不如人意的詩,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它們所以不如人意,本質上,并不是字面的技巧出了問題——正如博爾赫斯所說,“對真正的文學而言,一個句子的優美或粗糙無關緊要。”——而是眼界本就狹窄,想法本就老套,甚至混雜著種種陰暗的小心思。說穿了,成為短板的,其實是整個人的精神質地。
這些年來,閑暇時讀書,吸引我的往往不是“美”在表面的清詞麗句,而是矗立在文字后面的偉大靈魂。我時常做這樣的對比:杜甫、王維、辛棄疾,他們的詩歌在處理什么?蒲松齡、曹雪芹,他們在處理什么?魯迅在處理什么?——而我們,又在處理什么?
這樣的對比讓人無地自容。當我們目力所及,永遠超不出自己的小計較、小世界,永遠停留在事物千篇一律的表面,且不說寫得如何,單是格局,還未落筆,便已輸了一大截。
但是那些偉大的靈魂實在太高太遠。我們雖然人還活著,還能讀,還能寫,還能追求,但你知道,他們的高度,可能終其一生,我們也達不到了。這很令人沮喪,但同時也確保了我們有事可做:我們離那些高度還有萬仞之遙,我們還遠遠未到應該停步的時候。
一個人詩歌的層次,大抵不會太多地偏離于他本人的精神層次。那些震撼人心的偉大詩歌一再向我指出這一點。閱讀偉大的詩歌,向它們偷師學藝,借得一點表達的技巧,其實是末事;重要的是,它們不斷提醒我,幫助我,去成為一個更加開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