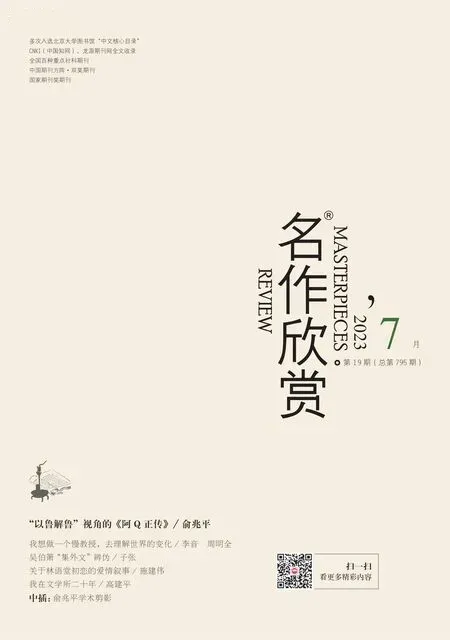編研交輝 著作等身
——記趙伯陶先生的學術人生
貴州 張亞新
趙伯陶先生生于1948 年,1982 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先后在中華書局、文化藝術出版社、《文藝研究》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計任圖書編輯十六年,學術期刊編輯十五年。在編輯之余及退休之后,沉潛于中國古代文學(集中于明清詩文與小說)及民俗文化研究,先后出版有學術專著及論文集《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明清小品:個性天趣的顯現》《中國文學編年史·明末清初卷》《落日輝煌:雍正王朝與康乾盛世》《秦淮舊夢:南明盛衰錄》《十二生肖面面觀》《義理與考據》《〈聊齋志異〉新證》《遠岫集——趙伯陶文史論叢》等十一部,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古夫于亭雜錄》《宋詞精選》《袁伯修小品》《明文選》《歸有光文選》《王士禛詩選》《張惠言暨常州派詞傳》《袁宏道集》《七史選舉志校注》《新譯明詩三百首》《〈聊齋志異〉詳注新評》《〈三國志〉選注譯》《徐霞客游記》(選注)等十七部,在《文學遺產》《清華大學學報》《蒲松齡研究》等學術期刊、報紙發表有《偷句、偷意與借境》《〈徐霞客游記〉的文學書寫》《心理與病理:〈聊齋志異〉別解》等論文、書評、序跋等一百八十余篇,包括即將問世的古籍整理等書籍,其總字數已經將近兩千萬字。這些著作填補了不少學術空白,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新的開拓。不難看出,在當代的學者型編輯中,伯陶先生是相當突出的一位。
曲折問學路
伯陶先生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的語文教師,母親在該校醫務室工作。1955 年七歲時入讀私立培元小學(次年轉為公立,改稱王府井大街小學);小學四年級時因搬家,轉學至八道灣小學;五年級時又因搬家,轉學至趙登禹路小學。從趙登禹路小學畢業后,考入位于按院胡同的男八中,一直讀到初中畢業。
從小學到初中,伯陶先生所受到的都是正規、良好的教育。培元小學校風嚴整,老師敬業樂群,男八中在當時的北京是僅次于男四中的名校,當時的好些人和事都給伯陶先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讀男八中時,一次西城區多校聯合舉辦查字典比賽,要求用一節課(四十五分鐘)的時間查出一百個難讀的字,并標出漢語拼音或注音字母,伯陶先生只用二十二分鐘即查完交卷,拔得頭籌,得到語文老師們的嘖嘖稱贊。
然而,到1964 年中考時,雖然每個考生可以填報多達十八個志愿(高中、中專、技校各六個志愿),但由于受父輩事情的影響,伯陶先生竟成為全班三個落榜生之一。于是,他響應當時“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號召,服從分配來到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機械隊做學徒工,開混凝土攪拌機,又曾到機修車間做機械修理工作,一干就是十四年。
在當機械工人期間,伯陶先生在工余努力自學機械制圖、電工學、鉗工技術、金屬熱處理、液壓技術等知識和技術,目的是想在需要時能派上用場。一次,北京建工局組團到建筑工地檢查機械,兼考察工人的專業知識,一般專業問題伯陶先生均能問一答十,后竟被問起齒輪模數、異步電機與同步電機的區別等更為專業的問題,結果均得到了滿意的答復。伯陶先生還隨身攜帶著當時還能尋覓到的王力先生所編的《古代漢語》四冊、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以及言文對照《古文觀止》等書,作為工余讀物。《演員的自我修養》《和聲對位》《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等在書荒年代凡能找到的書,他也都讀得津津有味。同工棚的師傅有一本家傳的《辭海》,平時放在通鋪上供大家翻閱,伯陶先生是其中主要的“看客”。如此堅持學習,為伯陶先生增加了知識積累,也為在機會來臨時考進大學打下了基礎。
1977 年恢復全國高考,因自己并非“老三屆”,伯陶先生開始并未動心。半年后,大學準備再次招生,周圍人慫恿伯陶先生以同等學力報考,伯陶先生心動,報考之,結果以四百多分(五門課滿分五百)的成績,在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開啟了人生的新歷程。
由于未經歷過高中三年的系統學習,年齡又偏大,大學四年的學習不免感到吃力。但由于有幸親炙眾多名師的教誨,伯陶先生得以實現專業上的飛躍。當時擔任過古典文學課程教學的有費振剛、褚斌杰、倪其心、沈天佑、周強等先生,開設過古代文學及相關學科選修課的有林庚、袁行霈、吳小如、季鎮淮、馬振方、陳鐵民、趙齊平、周祖謨、金開誠、張少康、侯忠義、馮鐘蕓、王力等先生,開設過講座的有陰法魯、裘錫圭、嚴紹璗、向仍旦、許樹安以及外系、外單位的鄧廣銘、劉乃和、史樹青、葉嘉瑩等先生。此外伯陶先生還旁聽過蔣紹愚先生的古代漢語課程。這個教師團隊可謂名師薈萃,陣容強大。講課內容除中國古代文學外,還涉及古代文獻、古籍整理、古代文化、地理、婚姻、中日學術交流、古代科舉制度、古代職官、出土文物、歷史紀年法、敦煌石窟、西域交通等眾多方面,極大地夯實了伯陶先生的專業基礎,開拓了伯陶先生的學術視野,同時也使伯陶先生了解了學術研究的門徑。北大圖書館有關中文工具書檢索的書籍,伯陶先生在課余幾乎都瀏覽過,后來寫畢業論文研究中唐詩人李益,搜集有關資料頗能得心應手,還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柏林寺分館發現了尚未引起學界關注的李益詩集的不經見版本。經倪其心先生指導,寫成了《李益及其邊塞詩略論》,后來發表于《文學遺產》。
編學相濟
1982 年從北大畢業后,伯陶先生被分配到中華書局,在文學編輯室任編輯。根據需要,伯陶先生被安排做明清文學部分的編輯,從此伯陶先生將明清文學確定為自己的專業方向。伯陶先生擔任了孔凡禮先生編年輯校的《增訂湖山類稿》等書的責任編輯。《增訂湖山類稿》是南宋末愛國詩人汪元量的詩詞集,孔凡禮先生從明抄本《詩淵》與傳本《永樂大典》中輯出汪元量詩詞達一百二十余首,這使《增訂湖山類稿》成為收輯汪元量作品最為完備、精善的別集。為校勘原稿抄寫的一些訛誤,伯陶先生曾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查閱《詩淵》,有皇皇二十五冊之多,其字跡雖工整,但密密麻麻連成一片甚不易讀,伯陶先生為此花費了不少心力。
1988 年末,伯陶先生調入文化藝術出版社。伯陶先生擔任了袁行云先生《清人詩集敘錄》等書的責任編輯。《敘錄》共八十卷,近二百萬言,著錄清代詩人二千五百余家。始撰于20 世紀50 年代中,歷時三十余年,篳路藍縷,輯佚鉤玄,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甚見功力。但未及蕆事,作者忽染沉疴,彌留之際將《敘錄》出版之事托付與伯陶先生。該書尚存在體例參差、人名書名乃至人物生卒年或有錯訛等問題,伯陶先生花了大量時間予以修正,但限于條件限制,加之當時出版社經濟壓力空前,為避免最后出版之事落空,只得搶占時機付梓印行,留下不少遺憾。好在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修訂重版此書,伯陶先生被聘擔當重任,審閱校樣,校改、增補共萬余處(包括新產生的諸多衍奪訛誤),終使該書成為一部經得起考驗的宏著。
1998 年,經中國藝術研究院調整,伯陶先生又調至《文藝研究》雜志社,轉型成為學術雜志的編輯。2008 年到點退休后,又被返聘五年,至2013 年初方徹底告別編輯工作。在《文藝研究》期間,伯陶先生處理、編發了大量學術論文,還曾應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之邀,成為《季羨林全集》編輯委員會六位社外特邀編輯之一,仔細拜讀了季先生的大部分著述,并履行編輯職責,處理了文稿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由于得到了“走近大師”的機會,更深入地了解了大師,后寫了書評《走近大師——寫在〈季羨林全集〉出版之后》,在對這位當代學術大師的諸多造詣表達欽慕之余,也指出坊間將季先生稱為“國學大師”是一種“錯位”,認為“誤讀一位學者絕不是一種尊重,這或許也是季先生力辭這頂‘桂冠’的原因”。
在長達三十一年的編輯生涯中,為把好文稿的最后一道關,伯陶先生表現出了高度的職業操守和素養。伯陶先生認為,作者的文稿百密一疏,在所難免。編輯對于文稿沒有越俎代庖的權利或義務,但補苴罅漏、精益求精卻是十分必要的。要當好一名合格的編輯,就不能迷信作者,即使作者頭上可能罩有諸多耀人眼目的光環。比如,文通字順是對論文寫作的起碼要求,然而不少作者竟難達標,甚至包括有的教授乃至“博導”。文字不通者還往往缺乏自知,自我感覺良好。此外,文獻功底不足也是一大問題,許多文章經不起文獻的核查,輾轉相引者姑且不論,即使出自元典的引文,不是篇名訛誤,就是斷章取義,甚至郢書燕說,完全是一副“六經注我”的做派。遇到這類問題,伯陶先生都要字斟句酌,加以修改,或與作者坦誠交換意見,敦促其加以修改。伯陶先生主張編輯要有吹毛求疵的精神,這無疑是一種既對作者負責更對學術負責的精神。
要能及時、準確地發現和處理文稿中的問題,責任心固然重要,但沒有水平和眼光也是不行的。伯陶先生為此對自己提出了“編學相濟”的要求,即應在工作中加強自我的學習和提升,使之與編輯工作相互補益、相得益彰。為此伯陶先生還具體指出了達成這個目標的途徑。
一是讓自己成為一個雜家。伯陶先生固然是贊成學有專攻的,但由于編輯工作的特殊性,須有廣闊的知識面,因此他也希望編輯成為一個雜家。方方面面的知識編輯未必需要精通,卻一定要概念清楚,明其犖犖大者,這樣才能在必要時加工處理好來稿。伯陶先生認為,他早年博覽群書,對他做好編輯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做編輯工作后,他更有意識地朝這個方面努力,取得了卓異的成績。
二是向老編輯學習,努力成為一個學者型的編輯。伯陶先生認為,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老編輯,在編學相濟方面做出了表率,他們職司編輯卻學有專長,甚至可與大多數著名學者相媲美。伯陶先生表示,中華書局周振甫、傅璇琮、程毅中等眾多編輯的學者化,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
三是利用編輯工作有與眾多學者密切接觸的便利條件,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轉益多師。孔凡禮先生編年輯校《增訂湖山類稿》時所運用的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方法,對伯陶先生走上編學相濟的道路產生了很大的啟迪、推動作用。著名長江學者、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是伯陶先生在《文藝研究》做編輯時的作者,同時,伯陶先生又成為陳文新教授所主編的某些叢書的作者。彼此傾誠交往,相互促進和成就,成為樁樁學壇佳話。
四是通過科研達到編學相濟的目的。伯陶先生剛到中華書局時,受到異常濃厚的學術氛圍的影響,開始在完成編輯的本職工作之余辛勤耕耘,不久在《文學遺產》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清代初期至中期詩論芻議》。此后發表的論文逐漸增多。發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 年第2 期的《〈四溟詩話〉考補》一文,披露了不見于全集本的謝榛所撰《〈四溟詩話〉自序》及不見于通行本的《四溟詩話》的詩話若干則,這是從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清順治間陳允衡所編《詩慰》初集所載《四溟山人集選》卷一中發現的,成為伯陶先生從文獻出發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成功實踐。到文化藝術出版社,特別是到《文藝研究》雜志社后,伯陶先生的學術研究更得到長足發展,其重要的學術成果泰半出自任《文藝研究》編輯時期。學術研究與校注古典文獻并重,成為伯陶先生在編輯之余治學的一大追求,也成為其達到編學相濟目的、并成為一個雜家和學者型編輯的最重要途徑。
沉潛學術
伯陶先生在編輯之余及榮退之后潛心著述,且著述頗為宏富。總觀其著述,有以下三點給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一)點與面結合,義理與考據并重
點與面結合是就其研究范圍而言。伯陶先生的研究重點在明清文學,而明清文學的研究重點又在《聊齋志異》、明清小品、明清時期的市井文化、歸有光、王士禛、張惠言暨常州詞派、《徐霞客游記》等,而對《聊齋志異》的研究最為用力,成果最為豐碩,在學界的影響也最大。
2016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伯陶先生的《〈聊齋志異〉詳注新評》,平裝四冊,共二百五十萬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學界被認為是古代文言小說的巔峰之作,在海內外不僅擁有眾多的讀者,也擁有眾多的研究者。《聊齋志異》版本眾多,后出的本子特別是其中一些好的本子雖總的說來具有“后出轉精”的特色,但仍總不免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如《詳注新評》所用的底本即任篤行先生所輯校的《〈聊齋志異〉全校會注集評》,是此前最為完備的本子,但也存在注釋謬誤、該注未注及句讀、校勘等方面的問題。2008 年伯陶先生在武漢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周絢隆先生(現為中華書局總編輯),談起清人及今人有關《聊齋志異》的注釋、校勘、標點等問題,一致認為與其修訂舊本,不如另起爐灶,這成為伯陶先生詳注新評《聊齋志異》的動因和動力。其注不避煩瑣與艱深,廣為尋求詞語的源頭、出處,并多列書證,為讀者從簡單接受(只讀懂故事)邁向復雜接受(了解作品的深層含義和作者創作的良苦用心)打開了方便之門。其評如伯陶先生自己在《前言》中所說:“或明其本事,略作比勘;或連類而及,闡幽發微;或辨析人事,以史為證;或夷考風俗,稍加引申;或發明本義,總結技巧;或探究事理,科學商榷;或摭拾眾說,鉤沉索隱。”內容豐富,多有新意,讀后總能給人以啟發。由于特色鮮明,多有突破,該書出版后得到學界,特別是《聊齋志異》研究界的一致好評,著名《聊齋志異》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馬振方先生、山東大學教授袁世碩先生都給予了高度評價。后該書榮獲2016 年度優秀古籍圖書獎。
在整理和研究《聊齋志異》的過程中,伯陶先生因發現前人和他人有諸多疏謬,遂從2014年開始,陸續撰成系列論文近四十篇,在《社會科學輯刊》《東南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上發表。這些論文從文獻出發,以考據的方法,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揭示了《聊齋志異》的蘊涵及其思想文化價值,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后伯陶先生將上述論文結集為《〈聊齋志異〉新證》一書,共四十六萬言,2017 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也頗得學界好評。
除上述研究重點外,伯陶先生還有更為廣闊的研究面。從縱的方面說,其研究不僅涉足明清,從先秦至唐宋也都有所涉足。從橫的方面說,不僅研究文學,還研究歷史、地理、民俗、士林文化、市井文化等;不僅研究小說、詩詞、散文,還研究小品、筆記等。而就研究中所涉及的知識點而言,則更如汪洋大海,漫無涯際,如《聊齋志異》研究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物名、制度、官職等,《徐霞客游記》研究中所涉及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礦物學、植物學、名物等,《十二生肖面面觀》中所涉及的文化人類學、神話學、民族學、動物分類學、哲學、宗教文化、軍事文化、天文歷法、婚姻習俗、歲時風俗、迷信禁忌、民間傳說、美術造型藝術等,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伯陶先生根據需要一一加以破解、運用,如果沒有深厚的積累和攻堅克難的能力,是絕難做到這一點的。
在處理復雜紛繁的問題時,伯陶先生往往能夠提綱挈領、舉重若輕。比如《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一書所探討的問題,如伯陶先生自己所說是“真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的茫無頭緒之感”。但伯陶先生通過對對象從縱與橫兩個方面的反復考察、比較、分析與綜合,終于從動態、有機的多重聯系中,將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的發展歷程、豐富內涵、獨特品質、多彩風貌與旺盛活力做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揭示。再如《明清小品:個性天趣的顯現》在對小品的特征進行概括時,由于小品文體的超越性,伯陶先生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類別劃分,而采用了一種概念交叉的劃分法,化繁為簡,很好地解決了問題。
點與面結合,需要作者有開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儲備,同時在若干點上要有深邃的修養,實際上是廣博與專精的結合,需要有雜家與學者這雙重身份者才有條件措手。事實證明,伯陶先生正是這雜家與學者雙重身份的擁有者。
義理與考據并重,則既是就其研究內容而言,也是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前面已經提到,伯陶先生的許多著作,都是文獻與義理并重的,其撰述都經歷了從考據到義理的一個過程。由于能從文獻出發,因此選題能做到有的放矢,論述能做到腳踏實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大大增強了著述的學術性、科學性。由于能從文獻出發,就總能發現前人和他人尚未涉足的一些領域,或有所忽略乃至存在謬誤的一些問題,因此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會落前人窠臼,就會有創新。伯陶先生將自己研究《聊齋志異》的論文集取名為《〈聊齋志異〉新證》,一個“新”字,就既點出了該書的特色所在,也點出了該書的價值所在。又由于自己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研究與校注古典文獻并重,伯陶先生將自己的論文集取名為《義理與考據》,這短短五個字,可以說概括了伯陶先生治學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經驗,同時也點出了伯陶先生能在學術上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讀懂”與“打通”
伯陶先生對箋注、研究文本提出了讀懂、打通的要求。“讀懂”,即箋注者、研究者不僅要通曉文本的使事用典,還要明白其引申義、隱含義、言外義乃至情韻義;有關作者的心態及其交游、時事、背景等也要弄清楚。“打通”則是要重構作者抒情運思的線索聯系,比如蒲松齡的詩歌創作經常化用唐人詩意,箋注者就應予指出,令古今意象相通,以體味其詩豐富的內涵。“讀懂”是箋注古籍的起點,“打通”則是對箋注提出的更高要求。伯陶先生對此極為重視,一再加以強調,其撰寫的《〈聊齋詩集箋注〉商斠舉隅》《一代“游圣”的尋蹤——與朱惠榮、李興和譯注〈徐霞客游記〉商榷》《〈三國志〉注譯發微》《文本細讀與清詩注釋——〈張鵬翮詩集校注〉詮解商榷》等文,或指瑕,或稱譽,全就“讀懂”與“打通”問題立論。伯陶先生自己在“讀懂”與“打通”方面自然是身體力行,而從其相關論述及實踐看,其具體路徑及追求是在研究中求真、求深和求新。
(三)現代性的自反性與全球化。深入研究“世界歷史”以及全球化,離不開對現代性的深入探究和把握。因為,現代性內在地具有全球性,全球化內在地具有現代性;二者不僅在形式上同屬揭示人類歷史時代發生紀元式總體性變革的概念,而且在內容上相互依存、彼此促進。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不僅是與其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所闡發的現代性思想密切關聯在一起的,而且他還由此洞察到現代性的自反性對全球化造成的深刻影響:“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求真,就是要準確地把握研究對象,準確地占有材料、提出問題,腳踏實地地進行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對研究對象無論是做宏觀把握還是微觀探索,都決不能離開文獻、文本及作家作品做天馬行空般的解讀、分析或詮釋,自然也不能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在《〈三國志〉注譯發微》一文中,伯陶先生具體提出了“精準注譯”的命題,“精準”二字,準確地概括了伯陶先生對于“求真”的追求。
求深,就是對文獻、文本、作家作品要讀得更深細,理解、領會得更深切,分析得更深刻,以發現、了解、揭示對象深層的意旨,以幫助讀者了解作品的深層意蘊,并幫助他們獲得深層次的審美愉悅。
求新,就是要從文獻、文本中發現新問題,從前人和他人的研究中發現不足,作為自己研究的切入點、出發點,從而提出有價值的選題,提出新的看法,得出新的結論。
為了達到求真、求深、求新的目的,伯陶先生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考鏡源流。考鏡源流包括考鏡版本源流、詞語本源及作品與前代著作的關系。伯陶先生研究、整理、校注任何一部著作,都必弄清其版本源流,對不同的版本進行比勘,認為任何研究、整理、校注的工作都應植根于文獻版本,不同版本的一字之差有時會謬以千里,不能不認真對待。還在中華書局工作時,為了梳理謝榛的詩論,搞清楚謝榛《四溟詩話》版本的來龍去脈,伯陶先生就曾不厭其煩地到當時的北圖善本閱覽室查考有關文獻。在做校勘工作時,伯陶先生還一再強調要慎之又慎,不可大意,否則容易造成新的錯誤。
追溯詞語的本源,考察作品與前代著作的關系,目的在更準確、深刻地理解詞語和作品。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就頗善于從古代典籍及前人詩文中取資,借鑒、襲用、化用有關詞語、句式、典故等,這對增添小說的典雅之趣及其蘊含、韻致,對營造某種意境,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蒲松齡的文學修養極高,所襲用、化用的詞語往往踏雪無痕,因此伯陶先生在詳注《聊齋志異》時爬梳剔抉,探幽索微,花費了極大的心力。伯陶先生還專門寫了一組論文,探討《聊齋志異》與《晉書》《世說新語》《隋書》及兩《唐書》的關系。又在《〈聊齋志異〉新證》中專辟一章,探討《聊齋志異》與《尚書》《周易》《詩經》及“三禮”等典籍的關系。這對讀者了解《聊齋志異》的藝術構思及藝術特色無疑大有好處。
三是文本細讀。研究文本,特別是校注文本,伯陶先生一再強調首先要細讀文本,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探驪得珠,理解文本的真義;而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就難以讀懂古人,甚至發生郢書燕說、南轅北轍的毛病。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僅以讀懂文本的字面意思為滿足,對文本所隱含的微言大義、言外之意、韻外之致也都要了然于心。
以上所說的各個方面,自然是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比如“求真”“求深”及文本細讀都必然得有文獻版本的異文校勘工作及詞語的追本溯源工作做基礎。而在這個各方面相互交織、作用的過程中,“讀懂”“打通”的目的、“求新”的目的必然地就都會得到實現。伯陶先生的著作、論文,總能在前人和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現、提出、解決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在《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一書中認為市井文化是“產生于封建社會內部的一股異己勢力”,一直在“不斷沖擊、侵蝕著封建專制統治基礎”,“是一種蓬勃發展卻又夾雜著一些污泥濁水的文化”;在《明清小品:個性天趣的顯現》中對明清小品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對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一直評價不高的小品做出了新的評價。《〈聊齋志異〉新證》《〈聊齋志異〉詳注新評》《義理與考據》《〈三國志〉選注譯》《徐霞客游記》(選注)等著作彌補、糾正了此前箋注者、研究者眾多的疏誤,更是新意迭出。比如,《聊齋志異》卷一《妖術》中之“高壺”,此前箋注者或注為“酒壺”,或注為“圓口方腹”之水壺,或譯為“沉重的漏壺”,或謂“原文疑有誤”。而伯陶先生指出:其實“高壺”就是古代投擲游戲時所用的圓腹筒狀的“投壺”,且從《金瓶梅》第七十二回中找到了書證。卷三《促織》中“成氏子以蠹貧”一句中的“蠹”字,從清何垠注到今天的高中語文課本,皆注為“蛀蟲,這里指里胥”,而伯陶先生認為這里當謂禍國殃民的人和事,喻指皇宮“歲征”蟋蟀的弊政,語本《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徐霞客游記》(選注)對徐霞客在旅游大半個中國的歷程中,因各地方言的相互影響與旅程中相關典籍的難以尋覓而導致的一些人名、地名的錯訛及記述錯位做了糾正,《〈三國志〉選注譯》解決了此前有關注、譯本相關書證缺位以及制度、名物、地名乃至譯文存在的諸多問題,等等。這類事例,在伯陶先生的著作及論文中隨處可見,不勝枚舉。無疑,這些都是對學術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特別是對《聊齋志異》的研究,使人一新耳目,把《聊齋志異》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今后《聊齋志異》研究的一個新的起點。
(三)掌握新方法,無往而不利
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伯陶先生的研究觀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廣度、深度都在不斷發生變化,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常做常新。這里僅就其研究方法做一點探究。
要真正讀懂文本,準確無誤地將文本中眾多的典源、語源找出來,絕非易事。直接見諸典籍文獻的典實詞語,可能尚不難查考;但常見作者化用前人的語句或意境為我所用,這種化用有時還不著痕跡,這就很不容易找到檢索的路徑了。伯陶先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除有關工具書常常不離左右外,就是常跑圖書館,同時自己買書,開始是親自跑去書店買,后來是網購,漸漸地家中竟有了十三書柜(多數帶頂柜)藏書。這雖然能夠幫助解決很多問題,但實際上還遠遠不夠,不僅查找耗時費力,而且好些材料還很難查到。伯陶先生很快找到一件利器,這就是互聯網。隨著文獻典籍開始了數字化的進程,電腦逐字檢索軟件開始應用,PDF 版、DJVU 版乃至UV版電子書先后問世,給文獻檢索帶來了一場革命,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快捷性及對資料廣闊的覆蓋面可以說是空前的。伯陶先生得風氣之先,成為最早掌握互聯網技術的一批學者之一,這使得他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相關研究工作自然也就駛入了快車道。他不僅因此順當地解決了在古籍中查找典源、語源等問題,甚至還利用互聯網有關“博客”中地方文化學者所提供的資料,解決了《徐霞客游記》中部分模糊不清的地名問題。當然,互聯網還有一個能不能熟練、巧妙地加以運用的問題,如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前面所提到的作者“化用”典籍的問題就將難以化解,而伯陶先生通過不斷地摸索、實踐,也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當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形勢下,對研究方法的選用也不能故步自封。伯陶先生能夠順應學術發展潮流,及時對研究方法加以調整,從而大大拓展了與古人對話的空間,得以在古籍的汪洋大海中縱橫捭闔,進退自如,這是極富啟示意義的。
余話
伯陶先生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是行家里手,他還十分熱衷寫作文言文特別是駢體文,有時還寫寫古詩。他寫作的序跋、后記多為文言特別是駢體,已有數十篇之多,這在當今的學者中是極為罕見的。駢體文的基本要求是詞語對偶、句式整煉、使事用典,非博學能文之士絕難寫好,而伯陶先生卻能駕馭自如,特別是成語典實運用起來能毫不費力,信手拈來,一氣直下,絡繹繽紛,蔚為壯觀,不難看出其腹笥之充盈、才思之敏捷。據伯陶先生自云,嘗試用古人常用的文體寫作,目的在于了解古人創作的甘苦,以促進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否則做研究就好似扣槃捫燭,或形同隔靴搔癢,難中肯綮。創作與研究相輔相成,伯陶先生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四十年如一日地進行研究,其間甘苦,可想而知。但伯陶先生卻以學術為安身立命之本,沉潛其中,不舍晝夜,不知疲倦。不僅不覺其苦,相反還能自得其樂,他曾在《〈蒲松齡小品〉后記》中說:“坐擁書城,南窗自傲,‘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又曾在《〈聊齋志異詳注新評〉后記》中說:“書城徜徉,自忘倦于移晷;學海浮泛,常興舞于雞鳴。”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既好之且能樂之,此伯陶先生之謂也。伯陶先生能幾十年如一日地沉潛學術并取得巨大成功,其奧秘就在這里。
投身學術長達四十年,其間當然不可能沒有遇到過挫折,沒有留下過遺憾。早年在中華書局時,領導安排伯陶先生點校清人張問陶的《船山詩草》,這是伯陶先生作為編輯初涉古籍整理工作。張問陶論詩力主性靈,創作喜歡化用事典,加之當時點校用嘉慶二十年乙亥刊本作底本,而校本無多,點校者的眼光受到局限,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疏誤。后來巴蜀書社2010 年出版《船山詩草全注》,即以中華書局1986 年版《船山詩草》為底本,一些錯訛因襲了底本的失誤,伯陶先生為此深感遺憾,一再自責,后來還特地寫了《性靈與學識——〈船山詩草全注〉問題舉隅》一文,對《船山詩草全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檢核、辨正,也算是對自己早年的疏失做了一個徹底的救贖。在學術上如此苛嚴地要求自己,這無疑也是伯陶先生能夠在學術上日益精進的一大原因。
目前伯陶先生手上還有四部書稿尚未問世,一部預計三百五十萬字的《徐霞客游記全注評批》的工作正在進行中。孜孜矻矻,筆耕不輟,不知老之已至。愿伯陶先生在保重身體的前提下,不斷嘉惠學林,貢獻新作。
202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