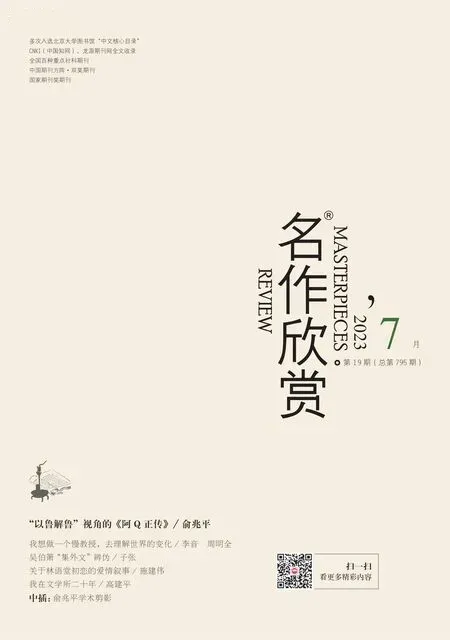我在文學所二十年
北京 高建平
我是1997 年7 月從瑞典留學回國,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到2017 年3 月退休,在文學所工作了整整20 年。在這個集體中,經歷了很多事,結識了很多朋友,面臨過很多挑戰,更有很多收獲。一個機構,具有自身的文化,個人往往是與這種機構文化共同成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所這個集體對我的學術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從人生的階段上講,從1977 年參加高考上大學,到1997 年學完回國,是我輾轉求學的20 年,從1997 到2017 這20 年,則是我在學術上發力,工作上做成一些事的階段。現在,我已經退休六年,回顧過去,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初進文學所
我于1996 年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美學專業的博士學位。那時,中國人在國外讀書的不多,去瑞典留學的就更少。在我完成答辯后的慶祝會上,參加答辯的瑞典漢學家羅多弼說:這是瑞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頁,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在瑞典被授予了博士學位。烏普薩拉大學是一所古老的大學,1473 年建校,是整個北歐五國所建立的第一所大學。建校時還沒有宗教改革,瑞典還處在中世紀,信天主教,哥倫布還沒有發現美洲。這所學校在歐洲是一所名校,出了不少科學史和學術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我回國的那些年,中國的教育界和科研學術界更看重美國的名校,在人們的心目中,總覺得歐洲的學位差了一截。盡管在國外,特別是人文學科,是美國深受歐洲的影響。
由于這種崇美輕歐的現象,又由于當時的文學所剛剛經歷了一件事,因此我一來報到,就感到一種壓力。文學所此前曾引進過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博士生。院里和所里都很重用他,在很多方面都顯示出對他的特殊待遇。可他來了一段時間卻又突然離開,回美國去了。一時間人們對此事議論紛紛。在那個年代,從國外引進一個人,要經過復雜的報批手續,克服很多困難。終于辦成引進了,還任命他擔任了重要職務,全所矚目,全院關注,這時卻突然離開,自然反響強烈。在那個時代,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引進了女婿,氣跑了兒子。這是說,對引進來的人太關注了,使單位原有的人員受到打擊。如果這個女婿再跑了,就會人心浮動,領導也要吸取教訓。
我正是在這個時間到文學所的,人們自然而然會將對那位剛離開的留美博士生的感覺投射到我身上,這也使我時時感到一種觀望的目光。在國外有八年之久,剛回國時我自己一開始也對國內的環境,辦事方式不太適應。當時,文學所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包括人事處長郭一濤、科研處長嚴平和負責外事的科研干事郝敏,以及辦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員,對我都很關心,幫助我解決了不少具體問題。
進入文學所,分配我在理論室工作。當時理論室的小環境特別好,杜書瀛和錢競任正副主任,思想開明,在學術上持兼收并蓄的態度;錢中文任《文學評論》主編,許明任副主編,他們也經常參加理論室的活動。記得那時理論室人很多,老一輩的王春元、楊漢池、張國民、李傳龍、李大鵬、欒勛、湯學智等許多人,有的還沒有退休,有的剛退休不久,還常到理論室來。與我同輩的學者有孟繁華、靳大成、王緋、羅筠筠、黨圣元、彭亞非、金惠敏,還有一位年輕的學美術出身的冷林,是一個熱鬧、歡快、其樂融融的集體。這樣的氛圍逐漸緩解了我剛入文學所時的不適感。
當時還有一些煩惱。有些煩惱是很具體的,要逐一奔走解決。例如,工作關系從天津轉過來,先是天津的學校不同意,后來同意了,被莫名其妙地罰款幾萬元。孩子上學是就近入學卻要交擇校費,又是幾萬元。妻子的工作,安排好了,用人單位又突然變卦,一時還落實不了工作單位,如此等等,其中任何一件都讓人焦慮不安。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所也盡其所能地幫助我,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問題逐漸得到了解決。
在剛回國的幾年中,許多朋友見到我,都曾問我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回國?對這個問題,一兩句話很難回答,但文學所的科研環境、國內的學術需要、我后來在學術上的發展,都能證明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在文藝理論研究室
在文學所的20 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文學所理論室從事科研工作和科研組織的工作。從2002 年到2015 年,我總共當了14 年的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
文藝理論研究室是文學所的一個大室,鼎盛時期有20 多人,曾經是全國當之無愧的文藝理論研究國家隊。當時,在蔡儀先生的帶領下,編輯《文學概論》教材、《美學論叢》集刊、《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等出版物,從20 世紀50 年代到80 年代,在全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到了90 年代,文藝理論研究室在所里仍受到高度重視。當時的引進人才指標,都優先給理論室。因此,后來的一些研究骨干,都是先進了理論室,后來又經過理論室而轉到了其他研究室和其他單位。例如許明、葉舒憲、趙京華、孟繁華、黨圣元等,原來都是理論室的成員。我剛進室時,聽說室里正在做幾個大項目。這就是后來出版的王善忠任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史》和杜書瀛任主編的《中國文藝學學術史》。
我接任理論室主任以后,一些人調往其他研究室,一些人退休,理論室的人有所減少。這一時期,進來了一些新人。現在理論室的一些研究人員,都是在本世紀陸續進來的。
這些年理論室的工作,除了日常的研究任務以外,還開了一些會議。為了傳承和弘揚理論室的優良傳統,我曾組織過幾次蔡儀美學思想研討會。這些會議的論文,由王善忠和張冰主編了一本論文集《美學的傳承與鼎新:紀念蔡儀誕辰百年》,使這些研究成果集中起來,供學術界研究參考。那些年文學所的經費緊張,召開有關蔡儀先生的會,都要找當時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許明和在深圳大學工作的吳予敏贊助。他們兩位是蔡儀先生的弟子,又有能力出資,當然這也是對我和理論室工作的支持。近年來我與這兩位還常有接觸,見面時常對當年克服種種困難,努力搞一些學術活動的往事感嘆不已。
我擔任理論室主任期間,嘗試開啟了與一些地方高校合作舉辦雙邊會議的模式。例如,與天津師范大學合作舉辦的“創新與對話——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當代社會”的學術研討會,參加者除了文學所理論室全體在崗人員,已經退休的三位老先生錢中文、杜書瀛和毛崇杰,還有兩位國外學者阿列西·艾爾雅維奇和泰勒斯·米勒,會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此外,理論室還曾一道去保定,與河北大學文學院合作舉辦會議。理論室的同事們還一道遠赴拉薩,成功與西藏大學合作召開了雙邊合作會議,在雪域高原縱論文學理論和中國文學的發展。
我擔任理論室主任時,每逢春節,都將理論室的退休老人請來,在崗的人員也全員參加,理論室的研究生們也來,退休人員、在崗人員、研究生,三代人濟濟一堂,暢敘交流。每年的聚會,大家都很高興,喜氣洋洋,出現了許多感人的場景。還記得何西來老師慷慨陳詞,教導年輕的學子在思想上進步和學術上提高;錢中文老師說出了他的名言:學術要前沿,不要時尚。大家在一起回憶過去,講述理論室的光榮歷史,對當下的工作提意見和建議,并寄托對青年的殷切希望。會后一道聚餐,劉保端老師曾唱起她參加北平地下黨時學會的進步歌曲;錢中文用俄文唱他在留學蘇聯時學會的俄國歌曲;喜愛音樂的毛崇杰唱一些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歌。靳大成的民族唱法、彭亞非的美聲唱法,也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都成為令人難以忘懷的美好記憶。
理論室的工作還有一件大事值得說一說,這就是創新工程試點。院里開始進行創新工程工作時,要求各所先試點。這是一件此前從未有人做過的事,要有人先行先試,摸著石頭過河。文學所就決定由文藝理論研究室和當代文學研究室打先鋒。
萬事開頭難。當時,我與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白燁圍繞創新方案,先寫出初稿,開會討論,所里一次次征求意見,反復修改,再報上去,根據上級機關的意見再改。這種修改經歷了很多次,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件辛苦的事。上級機關的意見常常不一樣,有時稿子要改過去,再改過來。原因在于有時是院里的學部委員們審,強調學術性;有時是院部職能機關的領導審,強調導向性。這些要求不一樣,此事以前也沒有做過,沒有固定的模板。于是,申請書反復修改,總是很難達到要求。我與白燁的生活習慣不同,我喜歡早睡早起,白燁則喜歡熬夜。于是在那段時間里,他后半夜把改好的稿子發給我,我則五點起床,改到下午再發給白燁,兩人通力合作。這個互助組前后陸續忙了大概有兩個月,終于最后順利過關。試點走出了新路,以后創新工程全面鋪開時,創新工作方案就有了標準版,做起來就容易多了。
我在退休前為文學所理論學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申請“優勢學科”。大約是在2015 年,當時,文學所研究文學理論的人員已經不再僅僅限于理論室,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室成立了,所里其他的部門也有一些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這時,院里有一個新的動作,要求各所申報優勢學科,平均每所給一個名額,并給予一定的資助。于是,我將理論室、馬文室、《文學評論》中的理論編輯,以及包括《中國文學年鑒》和網絡工作室等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人員整合在一起,主持寫成申請書,再到院里的評委會上陳述。有了此前做創新工程方案的經驗,這次做就順利得多。經過一番努力,最終申請成功。從此,文學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有了固定的經費資助。這對此后直至今天理論室工作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參與文學所的工作
2010 年,我被任命為文學所副所長。在此前也曾參與過一些文學所層面的學術服務工作:
首先是參與組織了一些比較大的學術會議。記得第一次參與組織的,是1999年在社科院附近的“京都苑”召開的“全國文藝名家論壇”。當時的文學所領導決定,讓我和黎湘萍、呂微三人做會議學術方面的工作。
由此,就形成了一個慣例,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文學所幾乎每年都舉辦全國性的會議,邀請國內各高校文學學科的研究骨干參會。這些會議均由我們三個人在科研處長嚴平的領導下承擔學術方面的服務工作。這其中包括起草會議的通知、會議新聞通稿、領導講話的報批稿、會議綜述,以及會后的各種匯報等會議文稿,還包括編輯會議手冊和會議論文集,等等。另外,會議期間臨時出現的各種學術方面的問題,也是我們負責處理。會議的地點,大多在香山飯店或友誼賓館。一年又一年,很多次這種有關文學的綜合性的、跨學科的會議,都如期順利舉辦。我們三個人在科研處的領導下通力合作,使每一次會議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這類會議的舉辦,一方面加強了文學所與國內和國際文學學術界的聯系,展示了文學所的科研實力,吸收了國內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加強了文學學科內各二級學科之間的對話,以及文學所內部不同研究室之間的學術聯系。
在這20 年中,在文學所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還策劃和組織了幾次重要的國際會議。第一次是200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國際美學協會聯合主辦,由文學所承辦的會議,題目是“美學與文化:東方與西方”。這次會議在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舉行,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參加了會議,院長李鐵映接見了與會的國外代表。來自國際美學界的20多位學者,其中包括當時的國際美學協會主席佐佐木健一、前主席阿列西·艾爾雅維奇、秘書長柯蒂斯·卡特,以及著名的美學家阿諾德·貝林特、沃爾夫岡·韋爾施、理查德·舒斯特曼,意大利的美學家格爾琪奧·瑪琪亞努、芬蘭美學家索尼婭等多人,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者也有40 多人參加。這次會議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反響強烈,非常成功。會后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論文集《美學與文化:東方與西方》。這些國外參會者中不少人當時是第一次到訪中國,此后,他們來中國多次,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朋友。
2011 年,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了“中荷文化交流:文學、美學與歷史”論壇。這是受社科院國際合作局委托,與荷蘭合作舉辦的雙邊會議,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萊頓大學、烏特勒支大學等著名大學以及文學研究所的研究骨干共20 多名學者參加了會議。
另外,文學所還分別與澳大利亞與俄羅斯舉辦過雙邊合作會議,還在徐州主辦了一次邀請包括國際美學協會六位前任和現任主席在內的國際學術會議。這些會議都很成功。
此外,還有一些文學所走出國門參加的會議,由文學所與國外的大學和科研單位合作。其中有與斯洛文尼亞科學院和科佩爾大學合作舉辦“文學的哲學闡釋”雙邊國際合作會議,由文學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長楊義先生的帶領下,赴斯洛文尼亞參會。與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合作舉辦會議,文學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長陸建德先生的帶領下,赴日本東京參會。這些會議都由我負責聯絡和牽頭,做協調和組織工作。對于文學所來說,這也開了一種在國外召開雙邊合作會議的先例。許多參會者表示,組團出國開會,開拓了視野,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也展現了文學所的學術實力。
從1997 年到2017 年這一段時間,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是從新世紀到新時代的過渡時期。全球化的浪潮,促進了學術上對外聯系大門的打開,這種國際交流的發展,對于我們借它山之石,發展中國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在擔任文學所副所長期間,除了承擔一些日常工作外,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這就是與同事們一道考察文學遺跡。我和文學所的許多年輕同事去了內蒙古、四川、重慶、江蘇等很多的地方,進行實地考察。我們曾去萬州在何其芳墓前行禮,去江蘇無錫參觀錢鍾書故居,在重慶去了郭沫若、蔡儀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每年出去一次,回來都寫出詳盡的考察報告,積累了不少文稿。那些文稿應該還在所里吧,期待將來會有人整理出來發表。
兼職當編輯
在文學所,我的主業是做學術研究,自己寫論文,同時也前后參編或主編過幾份雜志,它們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文學評論》《外國美學》《中國文學批評》《中外文論》。
我參編的第一份連續出版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這是從2000 年至2010 年期間,在文學所領導下,由當時的各研究室主任參與編輯的一個集刊。記得當時為這個集刊付出比較多的,有蔣寅、呂微、黎湘萍、趙京華等人,所里指定由我在學術上負總責,嚴平處長和科研處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上協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對稿件的要求很高,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成熟一期就發一期。在那些年,后來流行的三大評價體系(南京大學的CSSCI、北京大學的中文核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評價院的AMI)還沒有那么流行。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還能征得不少好的稿件,特別是一些篇幅較長且內容厚重的稿件。這個集刊發表過不少質量很高的文章。記得有一次參加社科院文學語言學科方向的優秀科研成果評獎,有四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的成果被各研究所經過評審而推薦上來,最終有三篇獲獎。這個數字遠遠超越文學語言學科幾個研究所主辦的一些國內權威刊物。到了2010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由于不再能獲得經費支持,只好停刊,現在想來很是可惜。如果能堅持下來,一定能在國內有很大的影響,也能進入一些評價體系之中了。
我參編的第二個刊物是《文學評論》。我從2011 年起至2016 年任副主編,主要負責編輯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方面的稿件。《文學評論》原來就是國內的名刊。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但我們作為編者也不能只是乘涼,也要為這棵大樹澆水培土,除蟲剪枝。這是一個從辦刊經費困難,需要多方籌款,到辦刊經費能夠維持,雜志走向正規化,向符合國際通行做法轉變的時期。在我參與雜志編輯工作期間,做了幾件事:第一,雜志實現改版,從封面和版式的設計到一些專欄的固定化,做了一些階段性工作。第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的建立。第三,電子投稿和審稿系統的嘗試使用。隨著社科院的雜志創新工程的實施,對刊物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于是,根據院里的要求,我與同事們一道為雜志制定了一些措施,并努力實施這些措施。在一個變革的時代,做到了與時俱進,保持了這個雜志在文學期刊中的權威地位。
第三個刊物是《外國美學》集刊。《外國美學》集刊是1985 年由社科院原副院長汝信先生創刊并任主編的集刊,這是20 世紀80 年代美學熱的產物,原本就在全國有很高的聲譽。2000 年以后,由于原出版單位商務印書館人事方面的一些變動,刊物處在停滯狀態,有五年沒有出刊。受汝信先生的委托,我從2005 年開始接過此刊,并聯系由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資助出版。從2005 年至今,已經有18 年了。從剛開始接手時每年編一輯,或者每兩年編一輯,到了2013 年以后固定每年編兩輯,這個集刊已經逐漸成型。這個集刊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院里經濟上的資助,辦起來很艱難。當然,也正是由于一開始就沒有資助,才不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那樣,斷了資助就只好停刊。過去的18 年,一路走來很不容易。此前汝信先生編了18 輯,我接手后至今已經編了20 輯。目前,這個集刊的質量不斷提高,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從2016 年起,這個集刊連續被評為CSSCI 集刊,2017 年起,被社科院科研局評為創新工程認可的集刊,2023 年又評為AMI 核心集刊,在國內和國外的影響力在不斷上升。
我參編的第四個刊物是《中國文學批評》。這個刊物由社科院原副院長張江先生任主編,我參與負責學術方面的工作。刊物于2015 年創刊,創刊之初,稿源困難,在學界也不受重視。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已成為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類的一份重要刊物,2017 年被評上全國百強期刊,此后,相繼進入CSSCI 來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AMI 新刊核心期刊。在中國文學類的刊物中,這個刊物欄目特色鮮明,問題意識強,有了很好的聲譽。
我參加的第五個刊物是《中外文論》。這個集刊原本是《中國中外文論學會年刊》,從屬于中國中外文論學會,最初是學會年會的論文選。我接手中國中外文論學會的工作并先后擔任秘書長和會長以后,改名為《中外文論》,每年兩期。這個集刊的具體編輯工作,主要由學會秘書處負責,目前正在努力,爭取獲得更大的影響。
除了以上五個刊物外,我還曾參加了院里的一份英語人文學刊的編輯,參與者有黃平、朝戈金、陸建德和我。可惜這個集刊編了一期以后就沒有能持續下去。
國際美學協會
我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學習的是美學專業。1997年回國以后,積極加入美學界,參與中華美學學會的工作,同時也幫助中華美學學會建立國際聯系。
我在國外學習時,就多次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通過這些活動,結識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在這些活動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參加世界美學大會和國際美學協會。
1995 年夏天,我赴芬蘭的中部小城拉赫底參加了第13 屆世界美學大會,這次會議的參會者有四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美學家。我在會上見到了包括阿瑟·丹托、今道友信、斯蒂凡·穆洛夫茨基、約瑟夫·馬戈利斯等前輩學者,也見到了當時國際美學協會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如阿諾德·貝林特、佐佐木健一、阿列西·艾爾雅維茨、柯蒂斯·卡特等人。這次會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會上做了發言,發言稿后來發表在波蘭的英文雜志上,這是最早向國際美學界介紹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和80 年代“美學熱”的文章。
這次參會的經歷使我感到,中國美學學者應該參與到國際美學組織和世界美學活動中去,這對中國美學學者了解世界、國際美學界了解中國美學都非常重要。過去的國際美學界受西方漢學家的影響,對中國古典美學有一些粗略的了解,但對現代中國美學的發展情況,則幾乎是一無所知。這樣一來,他們就將中國看成是一個活化石。從孔子美學到清代畫論,構成了他們對中國美學的全部印象。20 世紀的中國美學,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空白。中國美學研究者應該積極參與,向世界介紹現代中國美學,改變對中國美學的印象。同時,這種國際交流,對于在中國復興當時還處在蕭條狀態的美學學科,建立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美學,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我希望能在這方面做一些事。回國以后,我就積極爭取,經過申請,來往多次通信,提交相關的資料,使中華美學學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了國際美學協會。
1998 年夏天,我赴斯洛文尼亞的盧布爾雅那,參加了第14 屆世界美學大會。當時出國的經費還很困難,那次會議的旅費,部分是由國家人事部的留學回國人員辦公室報銷,部分由文學所報銷。這一次,我是作為中華美學學會的代表參會的。我在會上介紹了中華美學學會的情況,也使國際美學界對與中國美學界建立聯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世界美學大會每三年舉辦一次。2001 年的第15屆世界美學大會在日本千葉召開,這是世界美學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召開,對于中國美學走向世界來說,這次會議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此前中國學者參加國際美學會議,還是零星的、偶然的,在會上也很邊緣。這次在日本召開的會議,由于日本辦會方的熱情安排,組織了一組亞洲美學論壇,分別有日本、韓國、中國、南亞。在這些論壇中,有一個中國美學論壇,由我和葉朗、彭鋒、羅筠筠、樸松山發言。除了這個中國美學圓桌的參與者以外,中國學者對這次會議的參與也是空前的,大概有20 多位來自中國大陸各個高校的學者參會。中國和亞洲學者的參與,受到了國際美學界的歡迎,也在新世紀之初給國際美學界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2006 年,在中國成都舉辦了國際美學協會執委會的中期會議。我在這次會上促成了2010 年在北京舉辦第18 屆世界美學大會的決定。
2007 年,我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先生率領的一個代表團,赴土耳其安卡拉參加了第17 屆世界美學大會。中國美學界對國際美學活動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也持續增長,大約有40 多名中國學者參會。從這次會議起,我開始擔任國際美學協會的秘書長。
2010 年,由國際美學協會主辦,中華美學學會和北京大學美學美育中心承辦,在北京舉辦了第18屆世界美學大會。這次會議盛況空前,國外有400名學者參會,中國的美學家和藝術家共有近1000 人參會,中國美學家們與國際美學界的交流大門從此打開。
記得在北京的這次大會上,日本著名美學家、國際美學協會前會長佐佐木健一先生說:
日本原來乒乓球很好,后來就被中國超過了。看來美學也會是如此,中國要超過日本。
隨著美學這個學科在中國的復興,中國美學也在走向世界。我從2007 年至2013 年擔任了國際美學協會的秘書長,2013 至2016 年擔任會長。2016年卸任會長以后,為了保持中國美學界與國際美學界的聯系,我仍繼續參與國際美學協會的工作,同時,推薦和鼓勵中國美學界年輕、外語好的學者積極參加這方面的工作,爭取被國際美學界認可。從1995年至2019年,我連續參加了9次世界美學大會。
其他學會的工作
過去的一些年,我主要參加了四個學會的工作,這四個學會分別是:國際美學協會、中國中外文論學會、中華美學學會、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
國際美學協會的工作,前面已經概述過。這個學會1913 年成立,是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學會,是國際美學界最重要的一個學術組織。我擔任過三年副秘書長、六年秘書長、三年會長,現已卸任。目前還在參加一些協會的活動,并努力推薦年輕的中國學者參與這個協會的工作。
中國中外文論學會成立于1994 年,原來是由前輩學者錢中文擔任會長。2008 年,我被選為學會秘書長。從2013 年起,我任學會會長至今。在過去的這15年間,該學會每年都舉辦年會和各種學術會議,對推動中國文藝理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學會下屬敘事學、符號學、巴赫金研究、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等分會。
中華美學學會是1980 年成立的全國性美學組織。此前先后由朱光潛、王朝聞、汝信三位相繼擔任學會會長。我從2015 年起被選為學會第四任會長,擔任此職務至今。學會每年舉辦年會,下屬的十個學術委員會或專業委員會也各自舉辦各種活動,這些活動活躍了學術氣氛,有力地促進了美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于2014 年成立,由原社科院副院長張江擔任會長,我擔任學會的秘書長,參與了學會的創建工作。2019 年換屆后,我擔任學會副會長至今。這個學會致力于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結合,以《中國文學批評》雜志為陣地,同時也每年召開年會,推動文學學術研究的發展。
個人的學術著作、論文和翻譯
我回國到文學研究所工作之前,在瑞典曾撰寫和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中文著作《畫境探幽——中國藝術的精神結構》,在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另一本是英文著作《中國藝術的表現性動作》,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出版。另外,還在國外的一些雜志上發表了20 多篇中英文文章。
回國后在文學所工作的20 年,即從1997 年至2017 年,先后寫作出版了四本學術著作,分別是《全球化與中國藝術》《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西方美學的現代歷程》《美學的當代轉型》。在這期間,還翻譯出版了四本學術著作,分別是《先鋒派理論》《藝術即經驗》《美學史:從古希臘到當代》《弗洛伊德的美學》;主編了《西方文論經典》(6 卷本)、中英對照的《美學與文化:東方與西方》;發表的論文有一百多篇。
2017 年退休后,迎來了一個學術著作出版的高潮,先后出版了《文學與美學的深度與寬度》《回到未來的中國美學》《當代中國文藝批評觀念史》《中華美學精神》,主編出版了《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研究(1949—2019)》(2 卷本)、《20 世紀中國美學史》(4卷本),以及主編出版了三本文選,分別是《西方文論經典精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精讀》《西方美學經典精讀》,主編一本教材《美學核心素養》。除此以外,還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美學與藝術:比較視野下的傳統與當代中國》,在加拿大的Royal Collins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法文著作《中華美學精神》,另外還發表了近百篇中英文學術論文。
現在,我正在做兩個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一是重大專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基本問題研究”,一是重大招標“美學與藝術學關鍵詞研究”,成果最終會結集出版。
展望下一步,各種學術行政、學會、編輯的工作,都會陸續卸下,但寫書、編書、譯書的工作還不會斷。記得美學家朱光潛在80 歲后談工作計劃,結尾時說了一句話:春蠶到死絲方盡。朱先生是大學者,說的話也那么動人。我想說的是,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吧。工作是愉快的,堅持做工作是會使人長壽的。
當然,我會常回文學所看看,見老朋友敘敘舊,與年輕人聊聊天。我人生最好的年華是在文學所度過的,對文學所有一種永遠的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