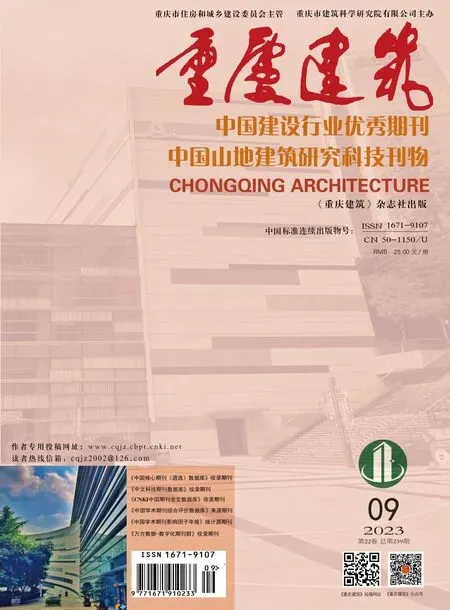自然生長與文化導引
英國建筑師艾爾索普曾提出“生長的建筑”理念,認為城市中的建筑都有其時代性,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人們對建筑的功能,對街區的規劃,都有新的需求,因而,建筑不是建造即永久,而是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地更新和發展。這當然體現在目前大量進行的既有建筑改造項目中。全國各地,一些歲月斑駁的廢棄樓宇,經建筑師、工程師的巧思和妙手,轉瞬就成了備受年輕人青睞的“打卡地”。這樣,歷史與現代得以共生,古舊的磚瓦重獲新生,城市少了令人生厭的大拆建和老破小,多了富于歷史底蘊和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間。
然而,“生長的建筑”理念,并非歷來受到歡迎,相反,它只是社會發展到當下的一種思潮而已。如果不是這樣,如何解釋一百年來那么多對于古建舊居的無情摧毀?這在當時固然已有不少有識之士的奮力阻止,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幾滴回浪,改變不了大河的方向。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當前建筑的這種“生長”,是“自然生長”,還是受到了文化的規制和導引?
比如,當我們考察重慶“遠山有窯”項目時,從建筑的角度,發現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保留了原有的土墻,以及引起游客興趣的燒制瓷器的破窯洞,等等。雖然結構上這些陳年老墻老洞顯得多余,但在文化上它卻成為必需。試想,在一座荒涼山坡,支幾個鐵棚,也能成為可以俯視遠眺的場所,但它卻少了載滿歲月痕跡的土墻帶來的濕潤踏實的感覺。“遠山有窯”這樣的項目,之所以能夠遠近聞名,一方面是正好順應了當下鄉村振興的宏大敘事,另一方面,建筑師作為文化工作者,在項目中投入的思考、智慧、專業知識、文化品味等等,成就了項目最終的樣態和特色。許多人慕名來到這個曾經荒蕪偏僻的作坊,悅賞山間美景,感悟四季鄉村,享受時光閑暇,這本身又成為一道美麗的文化風景。
建筑師曾解釋其中的機緣巧合,喜歡攝影的他,繞蜿蜒小道一路步行上山尋景,偶遇這個建在半山腰的瓷器小作坊,與老板交談中,了解到作坊經營困難,已瀕臨倒閉。建筑師表明身份,與老板討論起幫助改建的可能性,隨后,項目進入實施,逐漸成型,開始運營。這里,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文化下鄉”的典型代表。在沒有進入建筑師的視野前,這里只是荒野山坡上一處偏僻鄉民居所和日益破敗的瓷器廠房,而一旦被建筑師捕捉到,就成了可以打造成為特色項目、引人入勝的風水寶地。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和美的胚子)的眼睛。重慶等地近年大力開展“三師進社區”的工作,所謂“三師”,就是規劃師、建筑師、工程師;而社區,當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城市社區,更多的是鄉鎮地帶,因為,這里最缺最需要這樣的專業人才。然而,經驗可知,鄉村百姓大都已經在自家宅基地建好了一棟棟“別墅”。對此,城市人羨慕的是可以有這樣的大片土地、新鮮空氣、有機食物……,但惋惜的卻是,清一色的磚混樓房,直挺挺的大方塊,毫無生氣可言,連后墻的窗戶都開成了鬼魅般陰深的眼睛,與鄉村敞亮明快的自然風光格格不入。也就說,對于許多村鎮而言,“三師”去得太晚了。在最需要的時候,“三師”不見身影,而一切幾成定局時,“三師”姍姍來遲,他們來了,即使以其慧眼發現了如“遠山有窯”那樣富有潛力的原始本底,也已經再難有大的作為。
當然,“三師”并非就已經全無發揮的空間,房子雖已建,但還需要“生長”,“三師”自然可以在鄉村建筑如何科學生長上發揮專業指導作用。同時,還有建筑的內部改造,包括適老化、信息化改造等等。這就是在鄉村建筑的自然生長之外,終于再注入了先進的理念和技術,得到了文化的導引,讓現代化從城市走向農村,從市民走向村民。可喜的是,當前我們的鄉村自然生態,正在朝著無比美好的方向發展,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普及以及集約化發展的推進,鄉村越來越綠意充盈,越來越山清水秀、生機勃勃。而這正是得益于國家戰略下的政策和文化導引。
當前,無論鄉村還是城市,建設都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越來越少的增量,越來越多的改造。如果說曾經轟轟烈烈的城鄉大拆建中,我們錯失了很多以文化為導引的良機,那么在未來的建筑改造和持續“生長”上,為避免進一步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不應再有專業、思想等等文化因素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