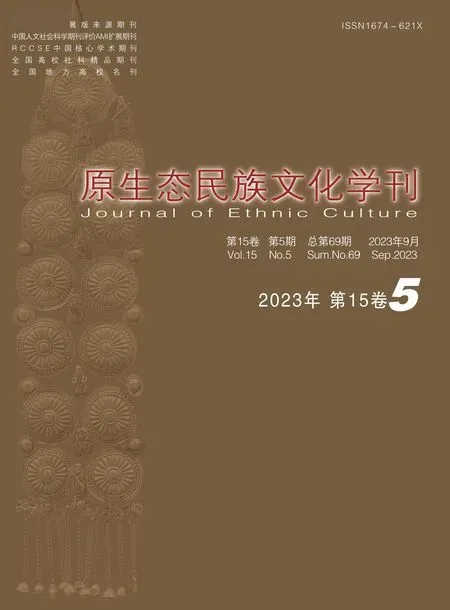清代例木采運(yùn)制度與困境及其應(yīng)對(duì)
鄧一帆
一、引言
木是大工業(yè)出現(xiàn)以前廣泛用于社會(huì)生產(chǎn)與生活領(lǐng)域的重要自然資源之一。自國家層面的建造、軍事、漕運(yùn)至社會(huì)層面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交通運(yùn)輸乃至日常爨薪等,無一不與木植緊密關(guān)聯(lián)。作為棟梁之材的木植,更成為被皇家權(quán)歸利用的重要資源。明清時(shí)期,宮廷、園囿、皇家陵寢等建筑工程,采辦并使用了種類繁多、數(shù)量龐大的優(yōu)質(zhì)木材。明代皇木采辦的主要形式是量工需用,奉部文委任專官采辦,以楠木為主,無定期也無定額。清承明制,繼續(xù)就需求的大型建筑工程中使用這種辦法外,也有了另一種辦木方式,即本文所要討論的由部分省份按年定額采辦木植運(yùn)京用以營建的辦法,稱年例木植,簡稱“例木”或“額木”①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0《工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5 輯,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4855頁。。當(dāng)然,清廷偶爾也會(huì)收取官員報(bào)效的木植,因數(shù)量和頻次較少,并未形成制度。
清人對(duì)皇木采辦中“奉文”采辦與年例辦解有明晰的區(qū)別。乾隆年間,湖北巡撫永常奏折中所言:“(湖)北省奉文采辦杉木并非年例辦解。”①永常:《奏為遵旨查覆南漕北上之候每多欽工木簰從中分?jǐn)_至一閘口輙與漕船搶先奪路事》(乾隆朝),宮中檔奏折,文獻(xiàn)編號(hào):409000363,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藏。據(jù)此,本文所關(guān)注的皇木采辦中的年例辦解有別于奉文采辦的臨時(shí)性采運(yùn)。前者為京城或?qū)m廷工程提供了穩(wěn)定的優(yōu)質(zhì)木植來源,也是繼大規(guī)模楠木采運(yùn)逐漸衰退之后宮廷自南方采辦木植的主要渠道。厘清清代例木制度,有利于更深入探析宮廷采木制度化的一面。
學(xué)界有關(guān)明清皇木采辦的研究成果更偏重明代,尤其是明代楠木采運(yùn)。明代宮廷營造頻繁,需用木植較多,采木活動(dòng)規(guī)模宏大,對(du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自然資源造成的負(fù)面影響更加突出②藍(lán)勇:《明清時(shí)期的皇木采辦》,《歷史研究》1994年第4期;羊棗:《試論明清時(shí)期的木政》,《曲靖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4年第4 期;姜舜源:《明清朝廷四川采木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4 期;李良品、彭福榮:《明清時(shí)期四川官辦皇木研究》,《中國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09年第1期。。相比之下,對(duì)清代皇木采辦尤其是例木采運(yùn)的關(guān)注仍顯不足。既有研究中,藍(lán)勇最早明確提出了皇木采運(yùn)中存在臨時(shí)性和按年辦運(yùn)兩種形式,但并未對(duì)后一種形式進(jìn)行深入討論。日本學(xué)者相原佳之(Yoshiyuki Aihara)率先提出了例木制度,并利用《明清檔案》《采運(yùn)皇木案牘》(以下簡稱《案牘》)等史料,梳理了清代例木制度中辦木額數(shù)、過程及其增減的基本概況③相原佳之(Yoshiyuki Aihara):「貴州東南部清水江流域における木材の流通構(gòu)造:『採運(yùn)皇木案牘』の記述を中心に」、『社會(huì)経済史學(xué)』72巻5號(hào)、2007年、第547-566頁;「清朝による木材調(diào)達(dá)の一側(cè)面——清朝前期の例木制度」、『中國研究論叢』第3號(hào)、2003年、第22-38頁。。高笑紅在此基礎(chǔ)上,著重探討了湖南辦木委員與清水江流域木材市場、商人之間的互動(dòng)。瞿見對(duì)《案牘》的整理研究同樣圍繞湖南的辦木活動(dòng),深入考證了辦木委員及其幕僚在辦理例木過程中的人際關(guān)系、經(jīng)費(fèi)使用狀況,呈現(xiàn)了在制度實(shí)踐中更為生動(dòng)的歷史情境④高笑紅:《清前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流通與地方社會(huì)以〈采運(yùn)皇木案牘〉為中心的研究》,碩士學(xué)位論文,復(fù)旦大學(xué),2014 年;《清前期湖南例木采運(yùn)——以〈采運(yùn)皇木案牘〉為中心》,張新民主編:《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清水江文書與中國地方社會(huì)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集》,巴蜀書社,2014年,第616-635頁;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潘美月,杜潔祥:《古典文獻(xiàn)研究輯刊》第28 編第8 冊(cè),花木蘭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2019年。。凡此,為本文梳理例木采運(yùn)的流程及方式,進(jìn)一步探析制度實(shí)踐中例木辦運(yùn)所呈現(xiàn)得復(fù)雜面向提供了重要基礎(chǔ)和依據(jù)。但是,以上研究著重關(guān)注清代湖南的例木辦運(yùn)狀況,仍然欠缺以全局性視野對(duì)例木制度更完整地梳理。茲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機(jī)構(gòu)所藏檔案及清人筆記、碑刻等史料,明晰清廷皇木采運(yùn)中的例木制度形成及清廷中央與地方制度實(shí)踐中的調(diào)適,重點(diǎn)討論例木制度與辦木實(shí)踐之間的張力,以及各省為彌合矛盾采取的應(yīng)對(duì)措施。
二、例木額征與辦木實(shí)踐中的木植數(shù)量差異
例木額征的種類包括桅木、杉木、桐皮杉槁、架木等項(xiàng)。桅木即大徑圍的杉木,一般用于宮殿、皇城梁柱;或作為號(hào)桿、旗桿使用;也多用作戰(zhàn)船、漕船之桅桿。杉木中長大者,或用于成造物件;天地壇、紫禁城內(nèi)宮殿燈桿木亦有選用。杉木中圍徑小者稱杉槁,用于扎搭棚架、柵木墻,或用作船櫓等。架木則是工程中搭造棚座的輔助性木料。上述木植多來源于南方且需用甚多,為了保障木料供應(yīng),清廷逐漸建立了相應(yīng)的辦木制度以備工程需要。
清初,清廷對(duì)于木植辦買并無相應(yīng)規(guī)程。自順治六年(1649 年)起,由工部差專官去往江南會(huì)同地方官按時(shí)價(jià)采買運(yùn)京。隨后逐漸擴(kuò)大辦木范圍。順治八年(1651年)“題準(zhǔn)各工需用木植令正定、山西、江西、浙江、湖廣五處地方購買。”①伊桑阿等:(康熙)《大清會(huì)典》卷132《工部·營繕清吏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3 輯,文海出版社,1993年,第6583頁。時(shí)至康熙十五年(1676 年),因工用架木不能速到,為免貽誤工期,清廷行令江寧巡撫“動(dòng)支本部正項(xiàng)錢糧,毎歲辦解二千根備用”。②伊桑阿等:(康熙)《大清會(huì)典》卷132《工部·營繕清吏司》,第6586-6587頁。隨后為滿足欽工需用,行令江寧按年辦理架木,此即為例木制度的開端。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又因工程用木數(shù)量陡增,清廷在江南辦木之例的基礎(chǔ)上,詳細(xì)核定,確定了此后各省辦理木植的數(shù)額與尺寸。諭自該年起,令江南、江西、湖南動(dòng)支正項(xiàng),每歲各辦解桅木20 根,杉木380 根。江南解架木2,400 根,江西、湖南各1,400 根。每省各解桐皮、杉槁200根。浙江省捐辦架木1,400根,桐皮、杉槁200根。”③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0《工部》,第4853頁。此處江南辦木主要由江寧蘇州等府辦理。并于張家灣設(shè)木廠,由工部司官監(jiān)管驗(yàn)收。 清廷對(duì)“皇木”的尺寸有嚴(yán)格要求,且僅可按照部價(jià)核銷。如表1所示:

表1 康熙二十六年(1687)例木尺寸例價(jià)表④允祿等:(雍正)《大清會(huì)典》卷199《工部·營繕清吏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9輯,文海出版社,1995年,第13418頁。
隨著例木制度施行日久,各省大徑杉木漸漸艱于辦買,工部驗(yàn)收江西、江蘇所辦木植發(fā)現(xiàn)尺寸多有短少。由是,乾隆三十年(1765 年),工部酌定:湖南解到木植“具與額定丈尺相符”仍照舊例辦理,江西、江蘇二省所解杉木若尺寸短少,可折算查收⑤缊布:《為核議江西巡撫題請(qǐng)核銷嘉慶六年份辦解桅杉架槁木植用過價(jià)值銀兩事》(嘉慶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2-01-008-002634-000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以下未標(biāo)注出處的檔案均為該館所藏)。。又詳細(xì)核定:除桅木尺寸不變,其余木植分為三等辦送。核定尺寸如下表:
如表2所示,二三兩等木植尺寸相較于原本標(biāo)準(zhǔn)均有減低,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辦木壓力。隨后不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又增桅木“短少添補(bǔ)”之例,雖強(qiáng)調(diào)各省采辦桅木務(wù)必按照額定丈尺辦理,若桅木采運(yùn)“偶有一二不能合式者,準(zhǔn)其添補(bǔ)”。再考慮到大徑木植采運(yùn)為難,工部恐辦木官員避繁就簡,將桅木全數(shù)換算為小徑木植添補(bǔ)充數(shù),特強(qiáng)調(diào)不允許將所有桅木“牽算搭解”①據(jù)乾隆四十二年,湖南辦木官員記錄:“南京、江西所處桅木、段木可另將木植補(bǔ)算,惟湖南只可牽算。”《采運(yùn)皇木案牘》,第119頁。補(bǔ)算:如若該省交付木植部分丈尺不符,則可補(bǔ)充一定數(shù)量的木植抵充木料缺額。牽算:即平均計(jì)算,木倉按照交付木植丈尺平均數(shù)作為接收標(biāo)準(zhǔn)。,并要求辦木委員將丈尺于報(bào)部文內(nèi)標(biāo)明,以備查核②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0《工部》,第4858頁。。

表2 乾隆三十年(1765)核定例木尺寸表⑥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0《工部》,第4856-4857頁。
例木數(shù)量通常較為穩(wěn)定,但京城及宮廷修葺工程規(guī)模原無一定,且取用木植種類、數(shù)量各異。如工程需用較多,則會(huì)導(dǎo)致工部木倉貯存木植不敷使用。所以,如果工程緊急又“倉貯木植給發(fā)無存”,工部即在例木原額上添辦一定數(shù)量的木植;反之,則循例辦理或停止辦理。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題準(zhǔn)桅杉架等木存貯足用,停其辦解,三十八年(1699 年)又題請(qǐng)恢復(fù)。③允祿等:(雍正)《大清會(huì)典》卷199《工部·營繕清吏司》,第13418頁。乾隆元年(1723年),工部查木倉所存各省解到桅木300余根,杉木2,100余根,架槁二木共122,900余根,儲(chǔ)量足用。其中除了各處需用桅、杉木植甚多,令湖廣省仍照常辦解外,所有湖廣額辦架、槁二木,并江南、江西額辦桅、杉、架、槁等木,俱暫停辦。”次年,因工用料較多,“倉貯桅木杉木俱經(jīng)各工取用無余”,又令各省恢復(fù)辦解④乾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寧巡撫徐士林揭報(bào)本年應(yīng)辦杉木所需價(jià)銀,《明清檔案》第99 冊(cè),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6年版,第A99-125頁。。可見,工部會(huì)視工程需求以及木倉存貯情況,靈活調(diào)整例木辦運(yùn)數(shù)量,在保證“工程敷用”的同時(shí)“不致靡費(fèi)錢糧”⑤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撫開泰題報(bào)采辦桅杉架稿木植用過價(jià)腳銀兩,《明清檔案》第167 冊(cè),第A167 -67頁。。
常額之外的添辦木植同樣是例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并非時(shí)常發(fā)生。茲就清代例木采運(yùn)調(diào)整額數(shù)在相原佳之討論基礎(chǔ)上加以完善,整理如下:
表3 中可見,制度施行過程中,例木數(shù)量一直處于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中。究其原因,木植數(shù)量的變化與工程規(guī)模和興造節(jié)律成正比。因乾隆朝興工頻繁,需用木料甚多,相應(yīng)的例木添辦次數(shù)與數(shù)量較其他時(shí)期更多。此外,若需木植甚急,清廷也會(huì)增加辦運(yùn)數(shù)量。如光緒十四年(1888 年),太和門忽遭火患,又逢光緒帝婚期迫近,急需重建太和門,所以內(nèi)府急催各省添辦大量木植。

表3 例木辦運(yùn)增減數(shù)額表
除卻工程需木增加造成的例木數(shù)量的變化之外,實(shí)際采辦中木植的數(shù)額也會(huì)較定額多出數(shù)倍。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湖南例木實(shí)際起運(yùn)木植總量約在20,000 根左右,是該省例定辦運(yùn)木植數(shù)量的十倍①《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1《抵灘》,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149頁。。例木運(yùn)輸由正木、余木以及保水護(hù)木組成。正木,即按例辦理尺寸相符的木植。各省需要在正額木植之外酌量備帶木植,稱為余木,用于補(bǔ)充工部驗(yàn)收時(shí)因不合式駁回的正木缺額。各省備帶余木一般無定額。余木之外,還有“保水護(hù)木”之名目,是為保護(hù)正木所用。只因木植多經(jīng)水運(yùn),需“經(jīng)歷江湖黃運(yùn)各河,又須購買幫護(hù),以免沿途磕觸傷損。”②《皇木案稿》,轉(zhuǎn)引自吳蘇民,楊有賡:《“皇木案”反映“苗杉”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4期。保水護(hù)木能夠極大降低運(yùn)輸中自然災(zāi)害造成的損失。乾隆年間,湖南委員運(yùn)木“簰抵洞庭之圍山,陡遇風(fēng)暴,吹至舵桿洲,將簰欖推斷”全仰賴保水護(hù)木抵御風(fēng)濤,雖漂失護(hù)木2,500 根,但“桅、杉大木尚無疎失”③《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2《稟藩臺(tái)》,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165頁。。若遇到木植經(jīng)過部驗(yàn)不合式,又無木補(bǔ)交,則需管官或木商賠補(bǔ)。如此,即造成連年累賠不斷,官商皆苦的局面。所以,采辦者為了避免駁換賠補(bǔ),辦木過程中備帶木植自然多多益善。
三、例木采辦的例價(jià)與經(jīng)費(fèi)不敷的應(yīng)對(duì)
自順治朝至康熙朝前期,各省辦運(yùn)均以時(shí)價(jià)為依據(jù)報(bào)部查驗(yàn)核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諭準(zhǔn)木植可隨市場價(jià)格波動(dòng),按照時(shí)值估價(jià)支付,避免商民負(fù)累④伊桑阿等:(康熙)《大清會(huì)典》卷132《工部·營繕清吏司》,第6583頁。。兩年后,四省循年辦木已成定例,工部進(jìn)一步核定了木植頭梢圍徑、長度尺寸標(biāo)準(zhǔn)及報(bào)銷標(biāo)準(zhǔn)價(jià)。江南⑤康熙六年(1667),江南分省為江蘇布政使司和安徽布政使司,此處江南所指當(dāng)為江蘇。、江西、湖廣按照標(biāo)準(zhǔn)價(jià)辦解,報(bào)明工部,在地丁銀項(xiàng)下核銷。浙江因僅辦理架槁木植,價(jià)值較低,準(zhǔn)實(shí)用實(shí)銷,在地方官府備公銀兩內(nèi)動(dòng)支。
乾隆三十年,因重新厘定各省辦木尺寸及數(shù)量,價(jià)格亦有調(diào)整。此后,江西、江蘇二省例木除桅木尺寸保持不變外,“其余杉木架槁并浙江省架槁木植,均照乾隆三十年定例,分作三等辦解,所需價(jià)值亦分為三等報(bào)銷。”⑥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2《工部》,第4930頁。按照例定木植數(shù)量及例價(jià)核算,湖南共可核銷3,952.36 兩,江西3,308.274 兩,江蘇4,855.687 兩,浙江368 兩⑦康紹鏞:《奏為動(dòng)支地丁銀兩采辦年例木植事》(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 - 01 - 37 - 0090 -038;《劉坤一集》第2 冊(cè),陳代湘點(diǎn)校,長沙:岳麓書社,2018 年,第345 頁;曹振鏞,穆彰阿:《為核議江蘇巡撫題請(qǐng)核銷道光八年份辦解桅杉架槁木植用過價(jià)值銀兩事》(道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題本,檔號(hào):02-01-008-003716-0009。。如有添辦木植,則按照相應(yīng)例價(jià)加入報(bào)銷數(shù)額。
然而在實(shí)際辦理過程中,上述固定數(shù)額的“預(yù)算”幾乎無法覆蓋實(shí)際消耗的辦木經(jīng)費(fèi)。其原因有二:一是例木價(jià)格自康熙二十六年核定以后,僅于乾隆三十年有細(xì)微調(diào)整,此后直至清末再無更定。然而各省辦木均自市場采買,市場價(jià)格低昂無定,相同數(shù)額的經(jīng)費(fèi)逐漸難以覆蓋所有辦木經(jīng)費(fèi)。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湖南采買桅木市價(jià)甚至高達(dá)40余兩⑧《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3《致居停(十)》,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253頁。。而據(jù)清廷規(guī)定是年當(dāng)?shù)匚δ久扛鶅H可核銷20 兩,市價(jià)與例價(jià)的差價(jià)難以彌補(bǔ),給后期采辦造成極大不利,這種現(xiàn)象直到清末都未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清末江西巡撫馮汝骙分析其緣由認(rèn)為:“自百余年前當(dāng)時(shí)百產(chǎn)豐盈,物價(jià)輕減,傭工雇役,取值極微。考之掌故及前人記載,大率其時(shí)每銀一錢抵今日三錢之用,故同一銀數(shù)若則有余,今則不足。凡屬例價(jià)無不皆然。”①馮汝骙:《奏為商辦額木仍請(qǐng)改歸官辦由》(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錄副奏折,文獻(xiàn)編號(hào):183699,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藏。二是木植采購運(yùn)輸中的附加雜費(fèi),名目繁多且無處開銷,更是加劇了例價(jià)與辦木實(shí)際消耗經(jīng)費(fèi)之間的矛盾。據(jù)湖南省辦木丁役稱:“查年辦例木額定價(jià)值,由來已久。不但歷年無加增,且繳部、科飯食銀一百八十兩,并回覆采買丁役飯食,扎簰筼纜、板片、犁錨、篷索、漲船等項(xiàng),以及長途駕運(yùn)人夫工食,一切雜費(fèi),又悉無開銷,向于額定木價(jià)之中,均勻動(dòng)用。大凡市物之貴賤,今昔懸殊。此差歷辦以來,日漸艱難②《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2《稟藩憲》,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167頁。。如此,致使各省辦木時(shí)常陷入“例價(jià)不敷”的窘境。
為應(yīng)對(duì)日益棘手的“額費(fèi)不資”問題,各省據(jù)自身財(cái)政情況采用了靈活的方式籌措經(jīng)費(fèi)。據(jù)乾隆時(shí)期湖南官員記錄:
備悉江西辦運(yùn)例木,因額費(fèi)不資,系詳定通省州縣內(nèi),按廉派幫;而南京例木,亦因官辦維艱,系由江寧府將額價(jià)發(fā)交木行總商承辦,于辦齊后,仍令木商繳出一切運(yùn)費(fèi),交與委員北運(yùn)。是楚省既無州縣派幫之例,又無殷實(shí)木商堪以承辦,全在委員因時(shí)調(diào)劑,節(jié)用得宜,方于公務(wù)無誤③《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2《稟藩憲》,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167頁。。
可見江蘇例木多倚靠木商辦買并出資運(yùn)輸,官解運(yùn)京。而湖南省主要以壓縮成本“節(jié)有余以補(bǔ)不足”為主。江西則以“按廉派幫”作為經(jīng)費(fèi)籌措的主要手段。
“按廉派幫”即“攤捐”,是指地方政府以強(qiáng)制攤扣官員養(yǎng)廉銀的方式籌措無法“作正支銷”的公務(wù)經(jīng)費(fèi)④周健:《清代財(cái)政中的攤捐——以嘉道之際為中心》,《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12年第3期。。此法不惟江西一省獨(dú)有,江蘇、浙江兩省辦木公費(fèi)主要來源均出自攤捐。江蘇雖然委商代辦,但木商仍需領(lǐng)價(jià)采購,經(jīng)費(fèi)亦多拮據(jù)。于是江蘇有木植協(xié)貼之項(xiàng)“屬常年額捐之款也”。蘇省三十三州縣辦木協(xié)貼原額銀5,700 余兩,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竟增至近9,728.273 兩之多。若與該省辦木例價(jià)一并計(jì)算,該年江蘇辦木實(shí)際用銀當(dāng)接近15,000兩,例價(jià)僅占實(shí)際支出的33.3%,辦木“預(yù)算”嚴(yán)重不足。隨后,于道光三年(1823年)起,江蘇辦木捐輸額得以酌減四成,其余六成則將司庫銀發(fā)典生息,在生息銀內(nèi)按數(shù)撥補(bǔ)⑤《蘇藩政要》卷3,道光朝抄本,第29-30頁。。
浙江例木直至乾隆初期仍屬實(shí)用實(shí)銷,于州縣養(yǎng)廉銀內(nèi)動(dòng)支,不動(dòng)正項(xiàng)錢糧。乾隆八年(1743年),浙撫常安以浙省辦木“動(dòng)用存縣備公不敷辦理,捐解為難”為由,上奏請(qǐng)求改為動(dòng)用司庫備公銀兩,“按年造報(bào),永除派擾”⑥常安:《為題請(qǐng)浙江年辦架槁木植悉照今定之?dāng)?shù)按年在于司庫備公款內(nèi)動(dòng)支委員承辦解部事》(乾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題本,檔號(hào):02-01-008-000526-0015。。此奏雖獲戶部批允,但工部在核銷時(shí)發(fā)現(xiàn)浙省辦木所費(fèi)銀數(shù)“甚屬浮多”,架槁木植每根竟至1.25兩,遠(yuǎn)超例價(jià)十倍有余,合計(jì)竟需銷銀1,760 兩⑦據(jù)乾隆三十年所定例價(jià),浙江辦木例價(jià),頭等架木例價(jià)0.24 兩,二等0.2088 兩,三等0.1792 兩。槁木例價(jià)頭等0.16兩,二等0.1428兩,三等0.1196兩。托津等:(嘉慶)《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670《工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5輯,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4930-4931頁。。工部命浙撫核減,并照江蘇等省按例價(jià)辦運(yùn)。然而一經(jīng)核減,官員長途運(yùn)木的腳費(fèi)、飯食便無處支領(lǐng),并且“浙省向非產(chǎn)木之地,又非聚匯之區(qū)”,木價(jià)與江蘇等省價(jià)值不同,也無木商幫襯,所費(fèi)倍于江蘇亦是情有可原①唐綏祖:《為題請(qǐng)核估浙江采辦架槁木植需用銀兩事》(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hào):02 - 01 - 008 -000693-0022。。工部堅(jiān)稱如動(dòng)司庫銀兩“自應(yīng)照依他省報(bào)銷價(jià)值采辦”。浙省只能以定額例價(jià)368 兩核銷,其余“解部飯食等項(xiàng)銀兩”“令各該縣自行辦理”。浙江此次動(dòng)用司庫銀兩之請(qǐng)不僅沒有解決經(jīng)費(fèi)問題,還需補(bǔ)還乾隆八、九兩年(1743年,1744年)多報(bào)核銷的司庫銀兩。此后,即使辦木最少的浙江仍需照其他三省按例于地丁銀內(nèi)核銷,而不敷經(jīng)費(fèi)則以“縣存?zhèn)涔y兩”作為補(bǔ)充②唐綏祖:《為題請(qǐng)核估浙江采辦架槁木植需用銀兩事》(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hào):02 - 01 - 008 -000693-0022。。
與此三省不同,湖南鄰近黔貴川木業(yè)繁盛之地,官員主要通過經(jīng)營木業(yè)籌措經(jīng)費(fèi)。湖南辦木多委派道府官員,在去往苗疆購覓正項(xiàng)木植,或以護(hù)木為名,“大小兼買,多置貨物”,隨例木一道運(yùn)輸,至南京發(fā)賣以充公費(fèi);或以借皇木運(yùn)輸通關(guān)便利,替商人運(yùn)木賺取費(fèi)用,補(bǔ)貼稅款③《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4《至居停(十二)》,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227,257頁。。此外,湖南省還采取少報(bào)木價(jià),偷漏稅款的非常規(guī)手段減少辦木成本。湖南例木自常德起運(yùn),需歷九江、蕪湖、龍新三關(guān),木稅以價(jià)格為基準(zhǔn)計(jì)算“每兩征稅三分”,所費(fèi)甚多。雍正七年(1729年),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參奏楚省辦木虛報(bào)木價(jià)稱:“粘單所開杉木圍圓三尺,著捏稱向作價(jià)八錢”實(shí)際木價(jià)為五兩,而“采買皇木價(jià)值則系發(fā)銀十兩”④王柔:《奏陳臣受人誣謗折》(雍正七年二月),宮中檔,文獻(xiàn)編號(hào):402009317,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藏。。王柔本意是為揭露楚省皇木辦運(yùn)虛報(bào)木價(jià),似有短少關(guān)稅、侵吞木價(jià)之嫌,卻從側(cè)面反映了楚省例木很可能通過短報(bào)木價(jià)以減少工關(guān)稅費(fèi)支出。
這種經(jīng)費(fèi)拮據(jù)的問題在太平天國運(yùn)動(dòng)爆發(fā)之后更加嚴(yán)重。因軍費(fèi)浩繁致使各省庫款短少,加之社會(huì)失序?qū)е碌倪\(yùn)道梗阻、木植銳減,例木制度運(yùn)轉(zhuǎn)一度停滯。自咸豐三年(1853 年)后各省木植均未采辦運(yùn)京。湖南省軍興后,停止辦運(yùn)三十余年⑤李宗羲:《奏為江蘇應(yīng)解普祥峪菩陀峪吉地工需架木請(qǐng)折價(jià)解京就近采買事》(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01-37-0123-003。。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 年),因普祥峪、菩陀峪萬年吉地與圓明園同時(shí)興工,需木甚多,內(nèi)務(wù)府與工部核議主張重啟例木采運(yùn),仍令四省辦理⑥奕誴:《奏為吉地欽工需用架木擬請(qǐng)分別采買飭催事》(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 - 01 - 37 -0114-022。。然而,重啟過程并不順利,南方產(chǎn)木山場多被焚劫一空,一時(shí)難于恢復(fù),黔省作為南方最重要的杉木產(chǎn)地亦被卷入戰(zhàn)亂,大木資源嚴(yán)重匱乏成為采運(yùn)最大的阻礙。戰(zhàn)后四省均陷入無木可辦的窘境。蘇省稱兵燹以后“山木砍伐幾盡,出產(chǎn)稀少,市肆居奇”“合式大木殊不易覓”⑦李宗羲:《奏為江蘇應(yīng)解普祥峪菩陀峪吉地工需架木請(qǐng)折價(jià)解京就近采買事》(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01-37-0123-003。。不僅優(yōu)質(zhì)木材極難得,平常木植價(jià)格也已翻數(shù)倍,例木辦運(yùn)“所需價(jià)值與例價(jià)相去懸殊”又無處籌補(bǔ)經(jīng)費(fèi)。江西“被兵十余年,大木早已砍伐無遺,新種之木尚未成材”“一時(shí)實(shí)系無從采買”⑧《劉坤一集》第1冊(cè),陳代湘點(diǎn)校,岳麓書社,2018年,第371頁。。連歷來僅辦理架槁等小徑木植的浙江省亦奏稱:“被兵后,焚毀砍伐,幾無遺種。”⑨《清同治間重修圓明園史料之匯集》,故宮博物院文獻(xiàn)館編:《故宮博物院十九周年紀(jì)念文獻(xiàn)專刊》,1944年,第87頁。加之此時(shí)運(yùn)河失于維護(hù),節(jié)節(jié)淺阻,挽運(yùn)木植北上殊為困難。
在以上要素影響之下,浙撫梅啟照不得不奏請(qǐng)變通浙省辦木原本“動(dòng)支耗羨,攤捐幫補(bǔ)”的經(jīng)費(fèi)構(gòu)成,重新采用實(shí)用實(shí)銷的核銷方式①梅啟照:《奏請(qǐng)核銷浙江省同治十三年試辦架槁木植實(shí)用銀兩事》(光緒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錄副奏折,檔號(hào):03-6599-072。。其余三省則在原有例木辦理方式之外提出將例木“折例價(jià)解部”以消解長途挽運(yùn)、木植匱乏的困難。但是,清廷深知京內(nèi)木少價(jià)昂,即使例價(jià)增加一倍仍不足用,這一權(quán)宜之策并未得到部允。江蘇督撫不得不改換策略,力促工部同意江蘇援照浙省成案“于該年地丁項(xiàng)下實(shí)用實(shí)銷”。最終,江蘇該年份辦理例木耗銀22,164 兩,均出自正項(xiàng)②沈葆楨,吳元炳:《奏為蘇省試辦同治十三年木植價(jià)腳等項(xiàng)銀兩請(qǐng)實(shí)用實(shí)銷事》(光緒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錄副奏折,檔號(hào):03-6596-058。。此端一開,隨后江蘇在自光緒元年(1875 年)開始的多年中,如二年、八年和十四年(1876年,1882年,1888年)里,辦理木植時(shí),均采用實(shí)用實(shí)銷辦理。此項(xiàng)實(shí)屬各省應(yīng)對(duì)辦木經(jīng)費(fèi)短缺的無奈之舉,而其本質(zhì)是地方督撫將經(jīng)費(fèi)壓力轉(zhuǎn)歸中央的策略。也進(jìn)一步說明,兵燹之后,例價(jià)報(bào)銷逐漸被隨行就市,實(shí)用實(shí)銷的經(jīng)費(fèi)報(bào)銷形式所取代。
此后,例木雖恢復(fù)辦運(yùn),但仍多滯塞。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經(jīng)工部核算“湖南省欠解額木二十三批,江蘇省欠解額木八批,浙江省欠解額木二批,江西省欠解額木十六批。”③松溎:《奏為請(qǐng)旨飭催湖南等省欠解額木事》(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錄副奏折,檔號(hào):03-7164-050。例木制度幾近瓦解。
四、例木采辦方式及其變通
在例木制度中對(duì)于木植種類數(shù)量有明確要求,但是對(duì)于各省采辦的方式并無明確規(guī)定。四省采辦方式亦各不相同,影響其方式選擇與變通的要素較為復(fù)雜,最主要的是經(jīng)費(fèi)與木植存量。為了能夠在有限的經(jīng)費(fèi)條件下完成差務(wù),各省多選擇經(jīng)費(fèi)消耗更少且易于辦理木植的方式。由此,例木辦運(yùn)方式基本可以分為由商人辦理官員解送和官員辦理官員解送兩類。
就“商辦官解”而言,最為典型的是江蘇和江西二省。清代活躍于長江中下游區(qū)域的徽州婺源商幫與江西臨、清商幫均是往來于“吳頭楚尾”經(jīng)營木業(yè)的巨商大賈,其經(jīng)營活動(dòng)為兩省例木辦運(yùn)提供了重要的協(xié)助和便利。此時(shí)江蘇雖“僻處海隅,素?zé)o崇山峻嶺,不產(chǎn)木竹”,但此時(shí)長江下游最大的木市位處江寧,是為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木植集散的樞紐④《常熟縣禁派木竹商行物料碑》,《明清蘇州工商業(yè)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頁。。故而,江蘇例木采購多委托資本雄厚的木商于長江中上游區(qū)域采買并交由官員驗(yàn)收解京。而江西本地既有南贛地區(qū)山場繁盛,歷屬產(chǎn)木之區(qū),又有本地木商協(xié)濟(jì)木差,委商辦理較為便利。
然而,商人作為辦木主體,不僅需要承擔(dān)更多辦木的經(jīng)濟(jì)與運(yùn)輸風(fēng)險(xiǎn),還需賠補(bǔ)被駁換的木植⑤彭家屏:《為題請(qǐng)核銷雍正十三年份江西辦買桅杉木用過銀兩事》(乾隆十四年六月初七日),題本,檔號(hào):02-01-008-000798-0002。。例木辦運(yùn)過程中,若遇天災(zāi)人禍,商人需認(rèn)賠其中大部分損失。以江西為例,直至乾隆六年(1741 年),江西仍令木商補(bǔ)運(yùn)雍正十三年(1735 年)部駁缺額之木⑥彭家屏:《為題請(qǐng)核銷雍正十三年份江西辦買桅杉木用過銀兩事》(乾隆十四年六月初七日),題本,檔號(hào):02-01-008-000798-0002。。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西例木交由委員解京途中,木植不慎被災(zāi),損毀殆盡。無奈最終木商與解官以八二為分認(rèn)賠①彭家屏:《為被焚木植銀兩已照數(shù)免賠請(qǐng)開復(fù)上饒縣知縣汪文麟原參處分事》(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題本,檔號(hào):02-01-008-000745-0022。。
由于商人辦木畏懼官勢,虧多盈少,所以多不樂于應(yīng)差。清初,江蘇征辦木植主要由江寧承辦,當(dāng)?shù)啬旧酞?dú)受其害,心生不滿,要求蘇州府木商一同應(yīng)差。隨后兩府即發(fā)生了圍繞辦理例木差務(wù)分配的訟案。最終,經(jīng)由江寧巡撫從中調(diào)解,方才判定“嗣后凡系采買架木,一循往例,在于江寧承辦”,“至于采買皇木一項(xiàng),在省、鎮(zhèn)兩灘②木商停靠、堆放木排的江河之濱,總稱為“灘”亦即“木灘”。省灘:南京城西上新河木灘。因多為徽商所據(jù),又稱“徽灘”。鎮(zhèn)灘:即鎮(zhèn)江木灘。王振忠:《明清徽商與長江流域的木材貿(mào)易》,《地方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查選足數(shù)則已。設(shè)有不敷,在于蘇常各府搜查有合式者,盡數(shù)協(xié)濟(jì)”③《蘇州府規(guī)定采買架木樁木皇木地區(qū)辦法碑》(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9年,第90-92頁。。乾隆時(shí)期,江蘇進(jìn)一步規(guī)范兩府承差辦法。在江蘇額辦木植章程案內(nèi)議定:“江寧、鎮(zhèn)江二府,一遞一年輪流委辦,其應(yīng)撥木價(jià)及水腳等銀,亦聽該二府輪年各領(lǐng)一次,在于應(yīng)管府分之藩司衙門動(dòng)撥辦理。”④薩載:《題為請(qǐng)撥江蘇省鎮(zhèn)江府應(yīng)辦乾隆四十一年木植所需銀兩事》(乾隆四十年七月初四日),題本,檔號(hào):02-01-04-16686-003。然而隨著長江流域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發(fā)展與山場無節(jié)制地開發(fā),符合例木尺寸的木植于江寧難以辦齊;加之雍正以后,黔東南豐富的杉木資源躍升為南方木業(yè)市場的寵兒。徽、臨商人多溯江流而上,從事木業(yè)。江蘇辦木轉(zhuǎn)委商人領(lǐng)取官帖,溯長江而上,往苗疆采購木植。這種官督商辦的形式一直延續(xù)至清中葉,繼而轉(zhuǎn)變?yōu)椤肮俎k官解”。
嘉道年間,隨著“商辦官解”施行日久,流弊叢生,木商“每為胥吏所脅,賠累不貲”。時(shí)任江寧補(bǔ)府知事的施應(yīng)謙有感于此“率同事稟江寧府,詳準(zhǔn)官辦官解,著為例,公私兼濟(jì)。”⑤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31《人物七·孝友五施應(yīng)謙》,民國十四年(1925)刻本,第2頁。施應(yīng)謙出身于業(yè)木金陵的望族婺源施氏,他的提議實(shí)際上代表了整體婺源木商的利益訴求⑥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31《人物七·孝友四施德欒》,第9頁;卷23《人物四·學(xué)林施彰》,第33頁。,如此觀之,商辦例木承擔(dān)經(jīng)濟(jì)風(fēng)險(xiǎn)著實(shí)為商人的難處,商人不再情愿承擔(dān)采辦事務(wù),而陳請(qǐng)改歸官辦。這也是因?yàn)?8世紀(jì)中后期,行業(yè)性會(huì)館公所的成長以及紳商合流的社會(huì)趨勢使得商人在官府交涉過程中獲得了更強(qiáng)的談判力量和更多的話語權(quán)的緣故⑦黃敬斌:《明清江南的鋪戶當(dāng)官與官商關(guān)系——基于碑刻資料的考察》,《史學(xué)月刊》2013年第10期。。
例木“商辦”所倚仗的是商人成熟的商業(yè)運(yùn)輸網(wǎng)絡(luò)及專業(yè)知識(shí)。蘇省舍棄辦木熟稔的木商轉(zhuǎn)而委托采辦生疏的道府官員去往黔楚辦理例木,其結(jié)果可想而知。很快,例木辦理即出現(xiàn)了問題。嘉慶二十一年(1816 年),木植由常州府督糧通判樊學(xué)淦領(lǐng)銀辦理,過程中屢遭蹇滯,輾轉(zhuǎn)兩年仍未辦結(jié),樊學(xué)淦也因此獲罪摘除頂戴⑧陳桂生:《奏為查明委辦例木之通判采運(yùn)遲延先行搞去頂戴事》(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01-35-0231-019。。直至道光年間,江蘇官辦木植“歷年淹滯”,又不得不轉(zhuǎn)委頗具名聲的婺源商人俞云燦措置,終于“兩運(yùn)皆暢銷”⑨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46《人物十二·質(zhì)行七》,第31頁。。 如此,“官辦官解”又被迫轉(zhuǎn)而商辦。
相對(duì)于蘇、贛“商辦官解”的形式而言,湖南、浙江兩省則以遴委專官辦木為主。湖南辦木得益于其地緊鄰黔省杉木產(chǎn)區(qū),水道相通,運(yùn)木便捷,遂多派遣本省中下層官員入黔采購木植。清初,湖南例木主要分派州縣自行采辦,后因“不肖官員藉名私派,有累民生”,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起,改由“動(dòng)支庫錢糧,委員于黔苗廣產(chǎn)木植地方購買”①《康熙三十八年湖南布政使告示》,轉(zhuǎn)引自程澤時(shí):《市場與政府:清水江流域“皇木案”新探》,《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第1期。。其中大徑杉木于“上辰州以上沅州、靖州及黔省苗境內(nèi)采取”,小徑木植如“架、槁二木,則須在常德聚木處購買。”②《皇木案稿》,轉(zhuǎn)引自吳蘇民、楊有賡:《“皇木案”反映“苗杉”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4期。據(jù)乾隆后期成書的《案牘》載,“楚南解京例木,向在貴治之毛坪、王寨、卦治等產(chǎn)木地方豎旗采辦,久經(jīng)通行在案。”③《采運(yùn)皇木案牘》卷2《移黎平府》,瞿見:《言出法隨:〈采運(yùn)皇木案牘〉校箋與研究》,第172-175頁。而位于清水江流域的毛坪等處,正是此時(shí)最為繁盛的杉木產(chǎn)地。
咸同兵禍之后,優(yōu)質(zhì)木植資源銳減。據(jù)江西藩司劉秉璋稱:“前此被兵十余年,大木早已砍伐無遺,新種之木尚未成材,解京額木徑長若干,例有尺寸,一時(shí)實(shí)系無從采買。”④《劉坤一集》第1冊(cè),陳代湘點(diǎn)校,岳麓書社,2018年,第371頁。各省不得不沿襲擇選委員出省辦運(yùn)的方式,前往木植豐富的區(qū)域購辦。由于山場久未恢復(fù),江西例木辦運(yùn)“桅木二十根僅得四根,其余十六根實(shí)因入山遍處采辦,欲求丈尺合式、頭梢均稱之大木,一時(shí)實(shí)難其選。”只能委員“赴湖南湖北趕辦”⑤德馨:《奏報(bào)運(yùn)解江西采辦光緒十四年一批額木起程日期事》(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01-37-0132-015。。這種官辦官解的形式,限于經(jīng)費(fèi)短絀,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不得不改為商辦。不久之后又因“承辦之商,往往借采辦貢木為名,擾累不堪”⑥馮汝骙:《奏為商辦額木仍請(qǐng)改歸官辦由》(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錄副奏折,文獻(xiàn)編號(hào):183699,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藏。,江西巡撫只得提請(qǐng)將商辦復(fù)歸官辦。同樣,浙省原本于省內(nèi)購辦木植,至清末時(shí),當(dāng)?shù)亍皦ㄉ饺松伲a(chǎn)木無多,求其長大,與例定圓圍丈尺相符更不易得”,只能派員出省去往上海一帶商賈輻輳之區(qū)采購⑦增韞:《奏請(qǐng)實(shí)用實(shí)銷辦解架槁木植用過腳價(jià)銀兩事》(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朱批奏折,檔號(hào):04-01-37-0147-023。。
五、結(jié)論
例木辦運(yùn)制度是清廷物料采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是文牘中固定的木植數(shù)額與報(bào)銷價(jià)格,也是現(xiàn)實(shí)運(yùn)行中靈活變通地辦木與經(jīng)費(fèi)籌措方式。例木制度的運(yùn)作不僅呈現(xiàn)了市場供求關(guān)系、地方官員、商人等社會(huì)力量以及環(huán)境在例木辦運(yùn)中的作用,而且更具象地看到這些力量交織運(yùn)作于辦木實(shí)踐匯總的動(dòng)態(tài)過程。
例木制度深切地嵌套在木業(yè)市場之中,這也意味著其必然受到市場的制約。例木制度的有效運(yùn)轉(zhuǎn)是權(quán)力與市場協(xié)作的成果,辦木經(jīng)費(fèi)與資源的多寡是影響例木辦運(yùn)的核心要素。例價(jià)與實(shí)際所耗經(jīng)費(fèi)之間的差額,促使例木辦運(yùn)實(shí)踐中衍生出多樣的木植采買以及經(jīng)費(fèi)籌措方式,顯現(xiàn)出皇木采運(yùn)并非是由官辦向商辦的線性過程,而是因地制宜,因時(shí)制宜地靈活調(diào)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