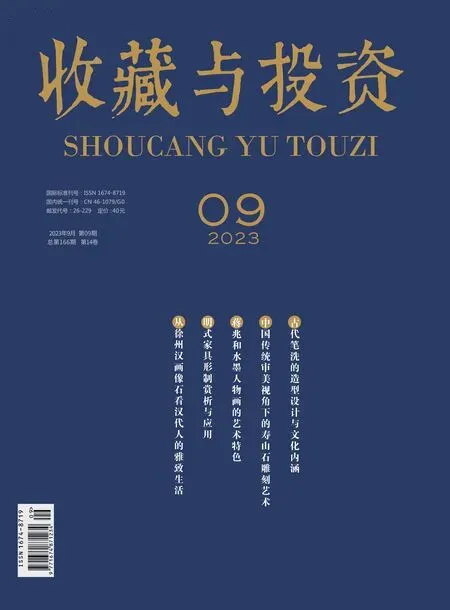西北民間美術造型特點分析
趙宇凡,石守猛(陜西師范大學,陜西 西安 710119)
古往今來,民間美術延綿不斷,并且給人以啟迪,人民在接受歷史、人文、倫理教化的過程中受到熏陶,形成了不同的美術風格。西北地區的民間美術凝聚了地方世代相傳的民風民俗,是當地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本文以繪畫、雕塑、剪紙為例,分析西北地區民間美術的造型特點及當代價值。
一、西北地區民間美術概述
民間美術指非專業藝術工作者結合生活創造的美術,其歷史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美術與原始美術一脈相承,原始美術表現了原始人類對宇宙、天地、自然的認識和美好祈求。民間美術作品的造型和圖案不僅帶有原始美術的痕跡,還表現了濃厚的地域特色,同時也體現了一定的民族理想和情趣喜好。
西北地區的文化底蘊相當深厚,尤其是民間美術的傳承和創作,至今仍保留著原始民間藝術的文化和思想內涵,在我國藝術文化領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和社會影響。西北地區民間美術和原始美術一樣具有生活和藝術共存的性質,既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要,又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要。例如陜西堪稱一絕的箱柜畫以及布堆畫,在實用的同時也帶給人們視覺愉悅感。不少民間美術作品都留有原始美術的痕跡,如我們今天所見的剪紙和刺繡的圖騰符號,在原始陶器上也依稀可見。
二、西北地區民間美術造型元素的種類及藝術特征
民間美術種類極多,且內容、用途各不相同,關于民間美術的種類歷來有多種闡述,有供人觀賞玩樂的造型藝術,當然亦有以實用為主的工藝品。西北地區有我國重要的古代都城和民族群落,民間藝術之豐富不容分說。從藝術特征來看,西北地區的民間美術主要包含繪畫、民間玩具、剪紙、雕塑、刺繡、建筑彩繪以及皮影等。按功能用途劃分,有建筑陳設及裝飾類、節俗禮儀類、祭祀供奉類、日常器物類以及觀賞把玩類[1]。
(一)單純質樸,緊貼生活——以繪畫為例
“一方水土滋養一方人”,民間藝術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種類多樣,且品質純厚質樸。西北地區的繪畫以它天趣盎然、率真質樸、活潑歡樂的氣質打動人心。西北地區的民間美術作品類型主要有箱柜畫、石窟壁畫、木板年畫、炕圍畫、玻璃畫等,種類多樣,受地域文化的影響,題材多表現的是勞作、祭祀供奉的場景或日常花鳥蟲魚等[2]。西北民間美術作品不僅有很強的地域性,同時富有趣味性,因作畫者多為農民,在繪畫造型表現上更加直接率真。
以延川布堆畫為例,布堆畫工藝流程繁雜,不僅涉及織、染,后續工藝還包括剪、繡等,雖然創作手法多樣,但是多以圖像形式呈現,故此將其歸入繪畫類型加以闡述。布堆畫造型奇特,色彩對比強烈,如圖1所示。高鳳蓮《萬歲爺》畫面部分采用對稱結構,背景和褲子以及人物面部均為紅色,衣服橙黃,頭飾和胡子繪以黑色。畫面既有整體暖色調,又在頭部和身體各部分加以細節,以粉色、藍色等表現,人物新穎的造型和鮮亮的色彩氛圍賦予了畫面歡樂喜慶的氛圍。

圖1 高鳳蓮《萬歲爺》 布堆畫
(二)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以雕塑為例
中國雕塑藝術源遠流長,延綿不斷,所謂雕塑又分為雕刻和塑造。我國西北地區歷史濃厚,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傳入我國西北部地區,便形成了極具地域性特色的石窟藝術,當然,也有不少蘊含我國本土氣息的雕塑作品,如漢代出土的大量畫像石、畫像磚和泥塑作品。
中國民間雕塑和西方雕塑有著極大的不同。西方雕塑注重寫實,而民間雕塑在注重寫實的同時,更注重作品的意蘊。雕塑的造型簡潔概括,人物則動作夸張,一般會有大起大落的處理,但幾乎很少見棱角,柔和圓潤。從漢代石雕作品《馬踏匈奴》和泥塑作品《擊鼓說唱俑》,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式雕塑因材施教、返璞歸真的藝術手法。中國民間雕塑著眼于作品整體形態的刻畫,而不拘細節,呈現一種質樸、大氣之感。從上述兩件作品中可以領略石刻作品渾然天成之大氣,說唱藝人手舞足蹈、興高采烈的形象被塑造得惟妙惟肖[3]。
中國造型藝術的最高境界即所謂的“氣韻生動”。“氣”是萬物的本源,實則指陽剛之美,“韻”則是風雅柔美的體現,“氣韻”是雕塑造型觀念的精神本質[4]。西北地區的民間雕塑作品多與當地的風俗節日以及生產生活有關,往往造型夸張,飽含人間風情。如圖2所示,陜西鳳翔彩繪泥塑《祥和虎》,泥塑虎呈靜坐狀,滿身繪有色彩鮮艷的紋飾,夸張的大耳及粗短的四肢,不注重比例,但并不妨礙虎的勇猛和生機勃勃的生動展現。

圖2 胡新明《祥和虎》 泥塑
(三)造型概括,構圖完整——以剪紙為例
在民間美術中,剪紙是最為常見的形式,同時也是中國最為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有著極為悠久渾厚的歷史。剪紙由于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最簡單,所以最為普及。剪紙雖歷史悠久,但由于材料輕薄等原因,作品保存極為困難,流傳下來的實物較少,現存最早的剪紙實物出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一帶的古墓中。
剪紙用途多與風俗及生活相關,是一種極具裝飾性的鏤空藝術。在具體創作時,各種造型元素必須連接在一起才能組成畫面。在剪紙中,最基本的藝術語言是線條,剪紙的結構、造型都得由線去表現,圖像中的點、面、幾何形也都由“線”區分和連接[5]。民間美術的主體形象往往傾向于夸張,顯得更加單純質樸。剪紙的特點是將形象的特征進行高度概括,構圖平面化處理,將復雜的形象簡單化,這一點和皮影以及刺繡極為相似。
剪紙作品多有美化、吉祥的寓意,不同地區的剪紙有不同的風格和特點。我國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居多,且地形偏僻,交通閉塞,剪紙文化與當地習俗緊密連接;由于創作者大多為農民,所以題材多為蔬菜花木、神話故事、民間傳說等;造型簡練概括,與漢代畫像石風格相似。在西北地區,生育、繁衍、保平安是剪紙的重要表現題材,例如抓髻娃娃。抓髻娃娃具有夸張的生殖器官,其手上的鳥、雞或兔子喻示著多子多孫。也有相對精簡的圖樣,如連續對稱的手拉手的小人,這種剪紙形象簡練,質樸生動。古人在過節時將這些剪紙貼在門窗上,用于辟邪、保平安,祈求子孫延續。
三、西北地區民間美術造型在人物畫創作中的具體應用
西北地區民間美術種類豐富,有巖畫、壁畫、皮影、刺繡、泥塑等。民間美術“遷想妙得”的理念、“以形寫神”的特點和“返璞歸真”的美感,吸引了不少人物畫家在借鑒西北地區民間美術造型方面作出大量的研究和實踐[6]。下面選取幾個較有代表性的畫家和他們的作品進行分析。
(一)劉二剛對古代巖畫的借鑒
劉二剛的繪畫作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人物簡練概括,形態生動,他不僅在透視關系和技法上與前人有所不同,還從哲學等角度來思考藝術。如圖3所示,劉二剛的作品《擔夫爭道》,描繪了在橋上相向而行的兩個擔夫,一人挑扁擔,一人擔柴火。人物五官簡單用線表示,頗有抽象意味,軀體則不注重比例,寥寥幾筆表現的四肢以及大筆渲染的衣著,顯得有幾分潦草。通過對比,不難看出他的人物畫與西北地區古代巖畫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如在賀蘭山巖畫中,人物和動物也只有外部輪廓,并未進行深入的細節刻畫。以此來看,劉二剛的畫作反而顯得古樸、質拙,多了幾分趣味和深意。同樣類型的作品還有《乘涼圖》,《乘涼圖》主要表現了三位老人月夜乘涼的場景,他們或敞衣飲茶,或低頭小憩,或搖扇賞月。微微拂動的楊柳烘托出月夜的涼爽,畫中人物全部簡練概括,沒有過多描繪五官等細節。接地氣的內容拉近了作品和欣賞者的距離,使人感到質樸和真摯。

圖3 劉二剛《擔夫爭道》紙本設色水墨 34 cm×45 cm 私人藏品
通過對比不難發現,劉二剛的繪畫作品和西北地區的巖畫作品有些相似的地方,人物造型簡單概括,只是大致地描繪出動作形態,畫面古樸,充滿稚趣。劉二剛所畫人物的五官和姿態雖比西北地區巖畫略微豐富,但生動質樸的趣味不減[7]。劉二剛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直筆書寫,不僅融入文化內涵,還帶給人們不一樣的輕松感和審美愉悅。
(二)柯明對年畫藝術造型的借鑒
柯明長期從事報紙美術編輯和書籍裝幀設計工作,在藝術創作道路上不斷探索和學習,尤其熱衷于我國傳統民間藝術,例如木板年畫、剪刻紙、皮影和泥塑等,其作品具有獨特的風格。柯明先生的娃娃畫尤有特色,從造型不難看出,是借鑒了民間年畫和彩塑娃娃的表現方式,圓臉、瞇成縫兒的眼、揮舞的四肢烘托了歡快的氛圍,這正表現了民間喜聞樂見的題材,借娃娃來寓意合家歡樂、多子多福等。柯明先生通過借鑒民間傳統美術,推陳出新,從中表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古樸和博大精深。
四、結論
綜上所述,民間美術與地域文化、民俗風情、社會環境等都息息相關,中國的民間美術種類豐富,西北地區民間美術造型所展現的“拙”氣,別具趣味,對現當代藝術創作有深刻影響。隨著社會潮流的發展,民間美術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繪畫中,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視覺產品設計者借鑒民間美術造型,在無形中使文化得以傳承,并以新的形式促進文化的發展。
在快速發展的當今社會中,如何結合當地特色,協調政府和群眾,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民間美術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民間美術歷史悠久,一方面要做好傳承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創新,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展現中國藝術的獨特韻味。例如甘肅慶陽以刺繡工藝聞名。每逢端午節,政府便以香包為龍頭開發民間刺繡藝術品,舉辦香包節[8]。甘肅慶陽香包的成功開發不僅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帶動了其他民間藝術品的發展,如布老虎等[9]。民間美術發展的形式多樣,除了借助政府的力量,通過開辦藝術節等活動,推廣本地民間美術外,機構和美術工作者個人還可以在學習傳統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的科技和表現手法讓民間美術作品呈現新的藝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