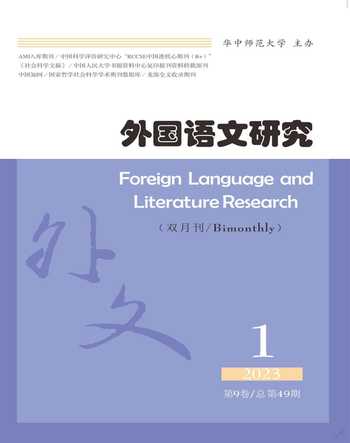流散視角下印度文化中的《黃帝內經》
蔣天平 王芷
關鍵詞:流散;傳統的發明;替代醫學;《黃帝療法》;梅毒
作者簡介:蔣天平,南華大學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王芷,南華大學研究生。
庫納爾· 巴蘇(Kunal Basu)是印度一位重要的流散歷史小說家。到2005 年時他已在西方定居了20 余年,是一名實實在在的流散者,非常了解他們的情感世界,常借歷史事件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如贊頌東方文化而反寫帝國等。2006 年巴蘇創作的《種族主義者》就對興起于19 世紀歐洲的偽科學——顱相學進行了批判(蔣天平、譚潔、劉娟 124)。有學者指出,“ 傳統醫學必須擁有古典遺產才能獲得正統地位”(查克拉巴提 303),因而巴蘇創作了系列關于東方醫學經典的作品,如《鴉片職員》(TheOpium Clerk)(2001)、《微雕藝術家》(The Miniaturist)(2003)、《種族主義者》(Racists)(2006)、《黃帝療法》(The Yellow Emperor's Cure)(2011)、《薩容基尼的母親》(Sarojiniss Mother)(2020)等作品,大都關注當地的替代醫學。如印度醫學中的順勢療法(Homeopathy)、手相學(Palmistry)等。2011 年作者又將眼光轉向了中醫經典《黃帝內經》(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創作出《黃帝療法》(The Yellow Emperors Cure)①,并通過對《黃帝內經》既傳承又創新的塑造(Taylor 93-111)方法實現了反殖的目的。
替代醫學(CAM)原指發生在殖民地上的土著傳統,現多指西方生物醫學的補救措施,是現代醫學發展的非正統形式,也是醫療系統的一個重要分支。替代醫學雖有補充現代醫學科學的療效,卻因其破碎性、傳統性和邊緣性被視為一種有別于西方現代醫學的非西方傳統醫學。從政治性與社會性上講,它對立于現代西方醫學,但對西方醫學產生深刻的影響。20 世紀初,替代醫學在來源國已成為主流,主要包括中醫學(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阿育吠陀醫學體系(Ayurveda Medical System)和伊斯蘭醫學(Islamic Medicine)等,被稱為世界最古老的三大醫學體系(Ebrahimnejad 3)。中國的替代醫學就包括作品中所提到的《黃帝內經》,這是“ 中華民族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習近平),被頌為“ 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王國強)。小說《黃帝療法》的情節發生于1898 年。當時第二次鴉片戰爭、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等運動正風起云涌。葡萄牙醫生安東尼奧因父親身患梅毒來到中國尋求《黃帝內經》中梅毒的治療方法,最終因八國聯軍侵華而無功而返。因作者的流散身份,本文主要利用離散理論來分析作者的創作意圖,以及流散理論的創作成效及實用性。
一、梅毒: 來自西方的生物病毒
細胞是具有獨立功能的生物體結構和基本單位。細胞衰老后,病毒入侵形成宿主細胞,并利用其中的蛋白質制造出自己的身體,將遺傳物質注入到細胞并感染細胞,形成病毒。病毒(virus)被發現于1892年,20世紀60年代產生病毒學(Virology),研究病毒與宿主間的本質和關系,即病毒細菌對細胞膜穿透的學科(蔣天平、胡啟海)。
梅毒是由螺旋體感染導致的,又叫蒼白螺旋體(Spirochaeta pallidum),主要通過性接觸和母嬰實現傳播。由性接觸傳播的疾病被稱為性病(Quetel 53)。梅毒是1980年代AIDS出現之前迄今為止危害性最嚴重的性病,在社會上受宗教和道德觀念的嚴重影響。據說梅毒是由哥倫布從新大陸帶到歐洲大陸的,被認為是由白人侵害所引發的印第安人的報復和“詛咒”(Basu 14)。在1495年,該疾病被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命名為“罪惡的麻子”,是上帝對人類罪過的懲罰(Parascandola 3)。在現代社會,殖民者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追求全球化貿易,推動了各洲之間人口的大流動和疾病的大交換,(克羅斯比)其中就包括梅毒。1498年查理八世率軍攻打那不勒斯時又將梅毒傳到了意大利、法國、德國,同年又傳到加爾各答、日本、中國等地,隨后梅毒在全球各地傳播開來。“每個國家都害怕鄰國將這種惡疾傳染過來”(海登 33),因而該梅毒被先后命名為白人的恥辱、那不勒斯癥、法國熱病、西班牙癢、西班牙瘡、德國皮疹或波蘭痘、廣東疹子、中國潰瘍、大水痘、梅毒等多個稱呼。
文化、社會、經濟塑造我們觀察疾病的方式(Patterson 8-28),因而“梅毒等性病更多地被看成是道德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是對原罪的挑戰而不是對健康的挑戰”(Parascandola 30)。西方人對梅毒的認知從醫學領域擴展到想象領域,從人類生活的私密領地延伸至社會公共空間,承載了許多來自道德、宗教、社會心理甚至美學的評判,成為上帝對人類原罪的懲罰(Dugger 10)。從臨床上看,“梅毒可催殘患者身體的所有組織”(William 5)。臨床上梅毒病癥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患者身上長出膿瘡、疹子,被戲稱為仙人掌花、玫瑰花蕾,如作品人物安東尼奧父親的身上首先綻放出一株玫瑰花蕾(Basu 10);第二階段梅毒癥狀消失后,第三期又產生麻痹性癡呆,性格巨變、道德墮落,“違反行為準則是道德墮落的重要跡象”(Lucy 9)。
作品中安東尼奧的父親患上了梅毒,全身呈現強烈的視覺觀感,“一滴乳白色的水珠從玫瑰花心里滲出,滴下來……父親全身泛著玫瑰紅色,從頭到腳,每一寸肌膚都布滿了紅疹……上面膿腫得像開花的仙人掌,睪丸腫脹得不能用雙手握住它”(Basu 10-11),因而成為道德墮落、邪惡的化身。當時他正處于麻痹性癡呆階段,情緒崩潰,行為不穩定,時常會在樹林里瘋子一般地四處游蕩(Basu 206)。“梅毒與性、性別發生聯系,男性是梅毒的受害者,而女性則是梅毒之源,不僅是傳播的載體,還是疾病本身”(Parascandola 3),妓女更是被看成生理和道德上的罪魁禍首,因此當安東尼奧看到父親感染梅毒時,女仆羅莎被嚇得趕緊為自己辯解。小說描述,當時梅毒已在歐洲社會大面積傳播,“不僅妓女,甚至是幸福結婚的資產階級婦女都會得梅毒”(Basu 132)。在當地,無論安東尼奧在里斯本哪個角落,都能感受到“腐爛生殖器的味道”(Basu 24)。面對西方社會梅毒泛濫的慘況,作者通過安東尼與一位軍需官的對話批判了梅毒來自東方的謬論,“船只上裝滿鴉片而不是梅毒。中國人都死于腹部內部以及以上的疾病,而不是死于腹部以下的疾病”(Basu 29)。作品進一步暗示,西方社會道德的墮落造成梅毒全球泛濫,“ 梅毒就像優質的馬德拉酒一樣,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新世界到舊世界,由眾多的拍板船運送過來,無人能抗拒其誘惑”(Basu 29)。歷史記錄,18 世紀推廣全球化貿易的西方殖民者把梅毒帶到了中國內地,相關史書也否定了梅毒來自中國的說法,“ 中國人給我們帶來的麻煩是賭博和鴉片”(海登 20)。因此安東尼奧接受朋友的建議,來到中國尋找救治梅毒療方,“ 黃帝……他的醫法比我們的祖先還古老……它們是否包括治愈的奇跡,一種抵抗感染的秘方,能夠阻止膿皰像野草一樣侵擾身體? ”(Basu 29)作者借此也確定了小說的主題,并通過里斯本梅毒的泛濫批判了西方道德的墮落,實現了反殖的第一步。
二、梅毒的政治隱喻:西方殖民的政治病毒與抗體
桑塔格認為“ 居住在由隱喻構成的疾病王國中而不受隱喻偏見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桑塔格 5)。在近現代,疾病不再是上帝的懲罰,而是病毒入侵身體的結果,病毒由此成為身體內部運作的核心意象,言說當下社會對污染、純凈、界限、進化、墮落的恐懼和擔憂。自19 世紀晚期起,德國哲學認為政治和科學相互指稱、相互依賴、相互利用,鼓勵人們借用獨立的生物體去思考其他領域的問題(Rothfield 97),“ 每一個國家或者組織機構構成一個單獨的生命體系,類似于人體細胞”(Otis 6)。因此醫學與政治相互隱喻,兩個及以上系統之間的復雜關系常被隱喻為病毒入侵,如法西斯、斯大林主義病毒等,隱喻對戰爭、共產主義顛覆的恐懼和擔憂。19 世紀末西方醫學產生了免疫學(Immunology),一種研究生物體對抗原物質的免疫應答及其方法的生物-醫學科學。免疫學中的免疫應答是機體對抗原刺激的反應,也是識別、排除抗原物質的生物學過程。抗原是指任何可誘發免疫反應的物質,即包括病毒細菌或死亡的細胞。免疫學把與抗原對抗的物質簡稱為抗體(蔣天平、胡啟海 30)。
東方學是“ 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是歐洲和大西洋諸國在與東方的關系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而不只是關于東方的真實話語”(薩義德8-260)。薩義德認為,“ 在殖民時期的印度傳統醫學中,東方學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查克拉巴提 296),因而在講述東方醫學故事時,作者結合中國醫學史、反殖史,塑造了雙重病毒的概念:生物病毒及政治上的殖民病毒。在一次訪談中巴蘇曾提到,“ 由于梅毒與艾滋病毒都存在著感染、痛苦、絕望、禁忌、療法等各方面的相似之處,我不想借助創作描述兩者相似之處,而希望通過情節的開展而呈現其相似。因而為貼近讀者,作者不得不借助歷史事件來達到其創作目的”(12)。
歷史上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簽定辛丑條約,標志著中國已完全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大批殖民者抵華都進行了政治、文化上的侵略。《東方學》中曾提到“17 世紀歐洲人開始在亞洲殖民地搜集書籍、文獻與器物,以便有系統地獲得但帶有偏見的東方學知識”(Said 39-40)。如作品中英國傳教士弗格森就侵占唐朝懷素②和尚大約746 年的字畫,掠奪了《永樂百科全書》、滿清皇帝康熙的親筆簽名等,都是“比大英博物館東方收藏品中的所有東西都珍貴的物品”(Basu 159)。歐洲醫學也在17、18世紀展開雙重旅程,研究東方各國的植物自然史和“純正的古代藥方”,包括中國傳統醫學經典《黃帝內經》。因為歷史上葡萄牙最先入侵中國,占領了大量土地,同時由于“在帝國頂峰時期,醫生是帝國事業的先驅和政治家”(Arnold 13),因而安東尼奧被作者塑造為葡萄牙外科醫生。他曾吹噓說“現在中國的一半屬于我們……中國淘金熱已經開始了!”(Basu 53-54)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殖民者的身份和本質,殖民者“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 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毛澤東 455)。
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掠奪來源于占有欲望,常被隱喻為一種文化病毒。歷史學界公認當時中國民眾掀起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粹民族主義”的歷史源頭,也“證明了在帝國主義者面前,中國人不再是‘原始的群體‘垂死的民族和‘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了。因而義和團戰士很容易被隱喻為針對梅毒的“抗體”,小說也多次稱其為“精神戰士和中國天賜的救世主”(Basu 135),為抗擊西方的殖民病毒,能夠空中飛行、躲避子彈和炸彈,追殺傳教士,摧毀圣像。因此,在小說中巴蘇沒有描述梅毒和艾滋病病理上的相似之處,而是通過把中國清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遭受的殖民侵略塑造為殖民梅毒,把義和團戰士隱喻為政治的抗體。
三、流散身份和東西文化的二元對立:西方醫學&替代醫學
“非西方英語文學的流散特征是在殖民、反殖民、民族解放運動、種族矛盾和國內戰爭等宏大‘事件中生成的,其主人公大都遭受過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塑造而在腦海中形成‘雙重意識,這就說明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間存在糾纏不清的復雜關系”(朱振武 157)。“流散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沖突,文化沖突也是流散之所以成為流散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只有生活在文化沖突的環境中才會產生流散者的身份認同、文化歸屬、種族歧視、家園尋找和離鄉與扎根等問題”(朱振武 155)。
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治現象,它生產和分配以文化特征為標志的社會政治關系(Ebrahimnejad 13)。因而19世紀帝國時期,醫學一直都是帝國重要的工具(Headrick),因此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關于醫學文化的研究似乎強調的是不同醫療“體系”之間的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界限,而不是體現西醫和非西醫的“歷史”(Ebrahimnejad 4),因而本文研究的重點是東西方醫學文化的沖突問題。
近代以來,西方在醫學科技及文化領域堅持“西方中心論”,堅持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后、邏輯與非邏輯、民主與專制、理智與沖突等的二元對立思維,特別在19世紀80年代細菌理論出現后,二元對立更加明顯(Kumar 78-87)。科學史家羅伊·麥克勞德(Roy Macleod)認為,所謂“殖民地科學”就是在非歐洲圈所從事的科學,由歐洲的“大科學家”(savants)設定有關問題,由比他們更“拙劣”的頭腦所進行的“派生的科學”。以歐洲為中心的眼光看,殖民地科學僅僅是“資料搜集”,最終被認為是“低等的科學”(low science)(Maelend 220-221)。印度科學史家德帕克庫瑪(Deepak?Kumar)認為,“ 殖民地科學” 是“ 從屬的科學”。與其說它是憑興趣研究的純粹科學,還不如說它是為了明確目的而進行的實用科學”(Kumar 6),是間歇性的,以抵抗和沖突為特征(Ebrahimnejad 15)。
由于醫學是科學的重要范疇之一,因而醫學可分為殖民醫學和殖民地醫學。西方醫學因而追求自然規律、強調事實、關注表征、忽視原因等是科學醫學或實證醫學(Leslie),相反混合了傳統和民俗醫學的非西方醫學(查克拉巴提 312),因其不可檢測性,甚至與科學實證原則相沖突等,都被“ 正統” 或“ 權威” 生物醫學降級為“ 補充”或“ 從屬” 狀態(Bivins),代表了“ 社會的落伍與倒退”(Cunningham & Andrews7)的醫學被稱為替代或補充醫學(alternative or Complementary medicine)(Stolberg322),“ 正統” 或“ 權威” 生物醫學態度相反,“ 現代” 會將其他“ 醫療系統” 降級為“ 補充” 或“ 從屬” 狀態(Bivins)。
根據以上內容,流散作者使用政治、文化隱喻塑造出了對立的殖民醫學和替代醫學的故事。作品開篇就直截了當地用疾病的隱喻理論將西方醫學文化及代表人物安東尼奧隱喻為殖民文化病毒,而將屬于替代醫學的中醫學經典《黃帝內經》及徐醫生、傅蜜隱喻為西方醫學文化病毒的抗體。作品中徐醫生、傅蜜就直接指出痘(梅毒)與醫生、侵略者與義和團等在醫學政治話語間共謀的關系,及其特點及異同:“ 你認為,人體是純潔的,梅毒是人體邪惡的入侵者,是你的敵人,所以你想殺死它。醫生必須像士兵一樣殺死病毒”(Basu 187)。同時“ 西方殖民者是入侵者、敵人,也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痘,也需要被消滅和殺死”(賈春華 138)。安東尼奧也意識到,無論義和團還是痘都需要通過暴力的發放時解決(Basu 163)。長久以來,學界也認同當時病毒與抗體的隱喻,殖民者是梅毒的隱喻,義和團是醫生或抗體的隱喻(高良敏、齊騰飛)。
朱振武教授認為,“ 流散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一種跨越,流散的核心問題就是異質文化間的沖突。有著流散經歷的個人或群體往往會面臨母國文化和異國文化的巨大差異”(張平功 88)。流散群里除了“ 本土流散” 和“ 異邦流散”,還有“ 殖民流散” 群體。殖民流散者一般站在文明等級的“ 最高端” 俯視非西方人和非西方文化(朱振武148)。“ 現代西方醫學與替代醫學之間的某些領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差異”(Ebrahimnejad6)。作品中最能體現東西方醫學沖突的是徐醫生和安東尼奧兩人。安東尼奧就是這類殖民流散者,一直蔑視中醫、排斥《黃帝內經》,強調實證主義,“ 西方科學的產生、發展都來自于實證主義”(Cunningham & Andrews 20),“ 學醫就是學事實”(Basu75),還多次申明“ 我不會相信這些未經測試和驗證的東西”(Basu 90),排斥、批判徐醫生對感覺的依靠,盲信先進的醫療儀器和實驗室做出的診斷。而替代醫學的支持者徐醫生、傅蜜則強調醫生應憑感覺來診斷、治療病人,“ 學醫就是磨礪感覺直至完美”(Basu 75),而不需要通過手術切開病人,同時質疑安東尼奧所信仰機器的功效,“ 你的機器能告訴你哪種疾病會發出什么樣的聲音嗎? ”(Basu 74)“
與異質文化沖突相伴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流散者的自我身份認同”(朱振武140)。由于安東尼奧一直認同西方的醫學身份,稱頌西方在機器制作方面上表現出來的民族優越性,如放大心肺節律的聽診器、可檢查視網膜受損情況的檢眼、測力計、溫度計等。多次吹噓“在歐洲,我們幾個世紀前就可以聽到病人的脈搏。血壓計可以幫助我們記錄人體動脈波,它比僅僅依靠耳朵效果要好得多”(Basu 74)。
同時面對殖民醫學流散者的抨擊,“非西方醫學(替代醫學)往往在民族主義精英的支持下,通過采用現代西醫的制度和科學工具與霸權作斗爭”(Ebrahimnejad 12),因而身為替代醫學的民族精英徐醫生、傅蜜等人為改變當時民族落后的現狀,積極了解安東尼奧的先進設備和學習其醫療方式,如女性生育所使用的法式鑷子、穿破子宮的穿孔器、清潔用的刮匙、防止感染的石炭酸噴霧泵、噴口吸入乙醚以減輕切口疼痛的燒瓶等,多次消除安東尼奧的誤會,提議“不,不……不是梅毒。她沒有廣東皮疹。也許你可以用你的器械清理她的腹部”(Basu 84)。
“思想的傳播不僅要通過積極的接受,而且還需通過消極甚至蓄意的反對和抵制來實現。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反對和抵制涉及到文化、經濟和人類學等建設領域。在另一些情況下,也是對實際知識或理論問題的回應”(Ebrahimnejad 14)。有學者認為,“日常生活中概念的爭論容易使人們認識到挑戰霸權的社會和政治意義,雖然這種挑戰并不是公然的對抗”(Haynes & Prakash)。“你不想和我爭論點什么嗎?”(Basu 90)但安東尼奧拒絕爭論,一直強調學習梅毒治療方法的意義(Basu 90)。這些都是殖民地精英階層對西方醫學的渴求,因為“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國家,采用現代科學往往是為了對抗西方政治和軍事力量”“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還是一種制度、社會和政治現象”(Ebrahimnejad 13)。徐醫生、福蜜與安東尼奧之間的較量和斗爭實質就是中國傳統中醫學文化與西方醫學文化的對立和斗爭。
四、邊緣化身份對西方傳統的師生、醫患、兩性關系的改寫
“非洲的原住民雖然沒有地理位置的徙移,沒有跨越國界來到異國,但卻有著切身的文化流散體驗和精神熬煎。殖民者的殖民侵略與殖民統治造成了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癥候。”所謂“本土流散”,是指非洲原住民雖然沒有海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移民的經歷,沒有產生通常所認為的由“空間位移”而造成的文化沖突,也沒有體會到闖入異國他鄉而產生的身份困境、無根的焦灼、家園找尋、認同與剝離等問題,但由于殖民者推廣殖民語言、傳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實行種族隔離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非洲原住民在自己的國土上被迫進入一種“流散”的文化語境。
故事情節發生在殖民時期的中國,因而徐醫生、傅蜜都屬于本土流散群體,與異邦流散者安東尼奧形成師生、醫患和兩性等關系。在傳統的西方文學中,西方形象占主導地位,東方形象是被動、從屬、邊緣的形象,“在與異質文化沖突相伴而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本土邊緣化處境”(Elmhirstsophie 41)。
但由于作為民族主義者,作者必然改寫東西方強弱的雙方關系,如徐醫生、傅蜜被描述為雙方關系的主導者:老師、醫生和兩性間強勢一方,而安東尼奧則被描繪為被動、弱勢的一方:學生、病患、兩性關系中的弱勢者。“ 殖民統治時期,西方主要的目的是塑造殖民地精英階層的主體性”(Elmhirstsophie 41)。為了表明作者的創作意圖,有意地體現了東西雙方的主體性。
首先,作者改寫了傳統的師生關系。在師生關系上,西方承擔著學生的身份,東方則承擔著教師的身份,同時采用的是傳統的模式——師徒制,以凸顯與現代的對立性。師徒制即“ 醫療知識是通過師徒制來取得,依循封閉的“ 系譜” 由一人傳給另一人,借由師徒制的美德來維持其正當性”(查克拉巴提 299)。同時因為安東尼奧和徐醫生雙方的殖民流散和本地流散的身份差異,人物間的關系就帶有了殖民特性。“ 科學醫學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甚至可以說就像帝國主義本身一樣主體就是權力,它是一種統治的藥,而且它也在其結構和性質上表達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Cunningham & Andrews10)。因而小說中西方文化的霸權性體現在安東尼奧對徐醫生不敬的態度上及教學內容的排斥上,尤其當時八國聯軍利用先進的技術征服了中國,安東尼奧更是從內心傲慢地認為有色人種道德墮落、品行低劣、愚昧無知,“ 我不會相信這些未經測試和驗證的東西”(Basu 90),“ 歐洲人可以直接要求中國人交出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必像學生樣謙卑……”(Basu 68)他對老師徐醫生傲慢、粗暴、無禮,粗暴地掐住老師的脖子喊,“ 告訴我真相。你能治好痘病嗎? ”(Basu 302)甚至懷疑老師是巫師、間諜、殺人犯。
同時,“ 替代醫學往往也在民族主義精英的支持下,通過采用現代西醫的制度和科學工具與霸權作斗爭”(Ebrahimnejad 12)。因此作為民族精英的徐醫生也毫不示弱,對安東尼奧的無禮針鋒相對,“ 你就像一個美國人,問不該問的問題”(Basu 73)。最終由于戰爭爆發,安東尼奧求醫無果的結局批判了“ 西方中心論”,實現了對西方殖民的詛咒,“ 你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總有一天要攤在陽光下”(海登 32)。
此外,為了達到抗擊殖民主義,作品還改寫了傳統的醫患關系、兩性關系。醫患關系是指醫生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產生的特定的醫治關系,是醫療人際關系中的關鍵,其治療成效一直是醫學界的研究熱點。在殖民語境下,傳統醫患關系往往具有殖民型、兩性型和師生型以及主動— 被動(activity-passivity)型等模式。西方文學中的主動—被動醫患關系完往往體現為具有絕對權威、男性中心思想的殖民醫生和邊緣的東方女性病人,反映出殖民時期的醫患關系。如《霍亂時期的愛情》講述了當地富家女費爾明娜和殖民醫生烏爾比諾的愛情故事。前者被疑患上霍亂而成為了后者的患者,是殖民地上典型的醫患關系、包含了種族性、兩性性的特征。之后醫患關系又延伸到夫妻關系中,因為《霍》文中費爾明娜嫁給烏爾比諾,并依順了他的生活習性,吃茄子、彈豎琴、做禮拜等。丈夫死后費爾明娜患上相思病,后被當地人阿里莎采用會話療法、順勢療法治愈。而在小說《黃帝療法》中,安東尼奧曾在北京患上“ 東方病(orientalsickness)”,接受著徐醫生和傅蜜的治療,扮演則著病患的弱者形象。同時,在兩性關系上,“ 種族關系很容易被看成性別殖民”(阿希克洛夫特 28),傳統文學中西方男性富有男性氣概、熱衷于獵艷,而女性則受盡壓迫、凌辱,是一名中規中矩的家庭仆人的形象。而《黃帝療法》中安東尼奧迷戀于傅蜜而失去自我,傅蜜卻一改傳統東方柔弱、被動壓抑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義和團戰士、大但、多情、開放的強者角色,因為她曾先后嫁給過雅各布、徐醫生,而故事中還接受了安東尼奧的追求。同時,傅蜜還有淵博的中醫學知識,傳授安東尼奧《黃帝內經》的知識,也治療過安東尼奧的疾病,因此很容易引起作為弱勢一方的安東尼奧的癡迷上強勢一方的傅蜜而忘卻了此行的目的,“融化了他的決心,讓他成為她的‘囚犯”(Basu 145),成為“一個患相思病的可憐蟲”(Basu 248)。最后他奴顏卑膝地向傅蜜求婚,遭到后者的拒絕(Basu 232-233),由此改寫了西方主宰東方的書寫模式,也鮮明地體現了傳統上沉默者的主體性。這樣傅蜜和安東尼奧都建構了新型的醫患關系及兩性關系及師生關系,也逆轉了殖民時期東、西方間兒童、女性、學生與成人、男性、老師的傳統關模式。
朱振武教授認為,“不同的流散作家在其作品中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這就需要深入文本內部,把握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及人物命運的最終走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既在理性層面把握流散的“名”與“實”,又在感性層面深切探查處在流散語境中具體人物的情感內涵”(朱振武 151)。故事結局安東尼奧由于戰爭尋醫無果,無功而返,落魄地離開了北京。他的心情也折射了東西方醫學文化斗爭的結果,“正如他為傅蜜受苦,為約阿希姆·薩爾達尼亞悲傷一樣,他們堅定了他繼續尋找健康和疾病秘密的意愿……他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與死者和生者相處的平靜”(Basu 275)。這種尋根思想 也作者成功地改寫了西方傳統尋寶探險敘事模式的結果。
五、流散作家的自我身份認同:《黃帝內經》的“傳統發明”
“與異質文化沖突相伴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流散者的自我身份認同。流散者攜帶在母國習得的經驗、習俗、語言、觀念等文化因子來到一個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進程迥然相異的國度,必然面臨自我身份認同的困境。”非西方國家作家在認知方面有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完全認可西方文化,拋棄了本土傳統;二是堅守本土文化,拒斥西方價值觀;三是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擠壓下徘徊、迷茫、懷疑、痛苦、無所歸屬,有的心靈扭曲,甚至走向毀滅(朱振武 144)。巴蘇屬于第二類流散,堅決捍衛先輩留下的傳統文化。常把被認同文化中的一個典型事例裝扮成歷史,并以神話形式虛構出來以證明歷史的合法性(顏英、何愛國 120)。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此方法命名為傳統發明的方法,即“‘抵抗西方醫學的辦法之一就是傾聽‘本土聲音,聽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說出明智和合理的話。人類學家和近代歷史學家都很欣賞傾聽他人聲音的必要性”(霍布斯鮑姆 2)。例如印度醫學史常會在東方學和民族主義理論指引下,強行聯系古典醫學經典來追尋、鞏固印度的古典傳統和正統地位,以及文化認同的根源和印度民族主義,因為“傳統醫學也容易成為對印度認同,以及復興所謂印度知識的過往榮光”(查克拉巴提 293-303)。
流散作家們也認同為維護或恢復他們原來的家園安全與繁榮,繼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以個人或間接的方式,將他們的民族意識和團結維系在一起(Safen 83-84)。由于巴蘇生于印度,中印兩國有著相似的被殖民經歷,“使得生于斯長于斯的作家在創作方面表現出相似的文化特征”(朱振武 136)。同時普拉提克· 查克拉巴提進一步指出,“ 傳統中醫學是被發明出來的”(查克拉巴提 310)。同時他又指出,“ 晚近發明出來的傳統究其原因往往是為了服務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查克拉巴提 293)。當時西方醫學是主流醫學,非西方醫學被視為迷信、巫醫等替代醫學或從屬醫學,《黃帝療法》無論從書名還是從小說內容上看都與傳統中醫學分不開,因此作者借助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殖民史創作了小說《黃帝療法》來講述了中國民族醫學經典——《黃帝內經》的故事,達到了追尋、鞏固、宣揚中醫學,批判西方殖民醫學的目的。作者在回憶《黃帝療法》的創作動機時也曾說過,幾年前他參觀北京的一家中藥博物館偶然發現《黃帝內經》的最早外文譯本,腦海里突然閃現19 世紀末一位歐洲醫生不遠萬里到中國搜尋梅毒秘方的場景(Mondal 275-299)。
在具體做法上,“‘ 被發明的傳統 試圖通過重復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范,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事實上只要有可能,他們通常就試圖與某一適當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過去建立連續性”(霍布斯鮑姆 5-8)。為了強化《黃帝內經》與歷史的聯系性,作品中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被塑造為小說背景,人物徐醫生、傅蜜等也參與到歷史中。故事情節就想象殖民者商人弗格森就掠奪到了一部《黃帝內經》,“ 這是一本舊的皇宮版的《內經》……兩千年前的書,里面有四萬個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醫學書籍。它描述了中國人對人體和宇宙秩序所知的一切”(Basu 140)。此外《內經》還聯系了上了康熙皇帝的親筆簽名與懷素和尚的字畫來凸顯中國傳統文化以證實《黃帝內經》“ 恒久” “ 永恒”、歷史連續性的特點(查克拉巴提 301)。
此外,作品還需不斷地重復歷史將其儀式化,“ 發明傳統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過程,其特征是與過去相關聯,即使只是通過不斷重復……一種強有力的意識體系圍繞著這些情況形成”(霍布斯鮑姆 7)。醫學經典《黃帝內經》內容中就涵蓋了內經大師、脈搏、針灸(銀針)等中醫學話語,小說也不斷重復徐醫生、傅蜜傳授安東尼奧中醫學知識以及后者的醫學實踐,“ 安東尼奧一邊把脈,一邊背誦傅蜜之前所教給自己的內經知識”(Basu 125)。“ 伸出手在脈搏讀數墊上,把三個手指放在手腕上仔細聽……”(Basu 179)這樣不斷地重復此程序最終形成診脈的儀式。傳統醫學則是通過遵循某種和西方或歐洲做法不同的傳統,以獲得正統性并建立信任。其獨特處在于它是西方醫學的“ 他者”。此外,針灸既是“ 最能幫助身體痊愈” 的醫療方法(Basu157),也是中醫話語的重要內容之一。徐醫生使用針灸治療太監王生、傅蜜傳授安東尼奧識別銀針形狀、治療方法及功能的技術,這樣不斷地重復針灸知識終于形成了中醫學中儀式性的動作,強化了民族主義。同時也改變了傳統文化中西學東用的觀念。
“ 為了當前的目的,作者常使用老故事來建構一種新形式的被發明的傳統。有時新材料可能被輕而易舉地移植到舊傳統上,有時則可能通過儲存下來的大量官方儀式、象征符號、道德訓誡”(霍布斯鮑姆 7)。徐醫生最后指出,當地官方治療梅毒的方法就是死亡,“ 死亡是簡單的治療方法”(Basu 257)。作品最后虛構了當時清政府舉辦了處理一批包括梅毒感染者在內“ 死亡游行” 儀式,即“ 拘禁罪犯、癮君子和患有不治之癥和傳染病的人去往屠宰場被吊死或斬首的路上,”其中就包括一位梅毒患者的貴妃或官員妻子,穿著白色襯衫,戴著頭巾,脫衣之后赤裸的身上長滿玫瑰花蕾,被丟在河岸的蘆葦叢中淹死(Basu 256)。小說詳細描述這一場面的目的就是“通過創新儀式,進一步增強了儀式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印象”(霍布斯鮑姆 191)。“追尋往昔,不斷地復活并改造傳統,甚至創造傳統”(霍布斯鮑姆 2)。醫學史上梅毒存在各種療法,如中醫學中把一只活公雞、鴿子或青蛙一切兩半,放置在患者的生殖器上(Quwtel 23)。近代最流行的兩種方法就是阿拉伯人使用的水銀(Quwtel 116-117),和印第安人的愈瘡木等(Hayden 48-49)。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但直到1943年人類才首次使用青霉素成功地治愈了梅毒(Parascandola 79),因而作品隱約提到“中國人知道一種治療梅毒的秘方,我們必須去他們那里找”(Basu 34),“文明世界已經放棄,就不得不救助東方醫學”(Basu 17),“治療梅毒的是中藥”(Basu 28)等都暗示中國這一神秘療法的存在,但沒有詳盡地說明《黃帝內經》中梅毒治療方法的具體步驟,只存在于想象與虛構中,目的是挑起讀者、西方和人物安東尼奧對《黃帝內經》的興趣與好奇。同時,小說也多次暗示《黃帝內經》梅毒治療法的虛構性,如安東尼奧就多次懷疑“徐能治梅毒嗎?”(Basu 255)而始終沒親眼見到《黃帝內經》中的梅毒療法,卻見到了另一種治療方法——死亡。同時,作品多次借用脈搏、針灸、陰陽、死亡等知識來宣傳中醫文化。因而,作者的目的就是塑造民族主義,“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一歷史研究方法發現一些表面似乎古老或永恒的科學觀念與傳統不過是晚近的發明,也有助我們理解各地傳統的醫學史正是殖民主義的產物”(查克拉巴提 249),最終達到反殖的目的。
結論
“文化沖突是流散的核心問題……只有生活在文化沖突的環境中才會產生流散者的身份認同、文化歸屬、種族歧視、家園尋找和離鄉與扎根等問題”(朱振武 154)。一般來說,流散文學的創作大多是流散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而創作的(石海軍 90),但作為19世紀晚期印度民族主義的流散作家,巴蘇的創作卻有著不同的目的,“除了向殖民國家爭取權力的政治斗爭外,還追尋印度人認同的根源,這也印度民族主義的特征之一”(朱振武)。尤其近代以來,理性主義大行其道,實證知識獲得了崇高地位,缺乏實證或實驗的知識,尤其非西方的醫學知識被貶為非理性知識,是西方醫學的替代和補充。由于“傳統醫學也成為對印度認同的目標之一”(查克拉巴提 300),因而同為民族傳統醫學的中醫學既是中國民族話語的重要內容和體現,也成為了印度作家可借用來宣揚印度本土文化和民族認同的有利內容之一。
本文通過對巴蘇流散作家身份及疾病隱喻的分析,挖掘出西醫和替代醫學文化沖突的過程和事實。由于“傳統醫學必須獲得古典遺產才能獲得正統地位”(查克拉巴提 358),作者通過傳統發明的方法,塑造了中醫傳統《黃帝內經》,明確了替代醫學的正統地位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就指出“中醫學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被稱為“ 替代” 醫學并構成了主流醫學,并在1950 年代由新中國創造并逐漸為人所知的”(查克拉巴提 312)。小說的創作成功地說明了庫納爾· 巴蘇之類的流散文學作家創作的目的就是保留當地的傳統文化,實現對西方殖民的統治的反抗,本部小說借助歷史學界的研究方法—— 傳統的發明,結合當地的傳統經典及神話故事,來塑造新的民族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同時此部印度小說正是通過中國的替代醫學文化典籍《黃帝內經》的故事證實了作家的流散身份對于作品創作的意義,以及傳統發明法是流散作家保證民族文化及本土流散作家保證其流散身份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