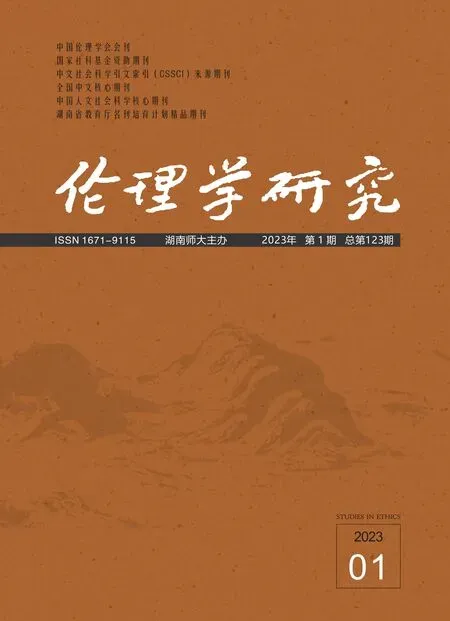《黃帝宅經》的居宅倫理奧義探論
陳叢蘭
“凡人所居,無不在宅”(《黃帝宅經》①文中使用的《黃帝宅經》版本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宅經》第八〇八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版),文中凡是引用該經典的內容不再一一出注。)。人生于世,通過定居于宅,將身心與空間大地緊緊聯系在一起,把“居”變成人的生活世界最自然的本質表達,從而使身心得以安頓和休息。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對居宅倫理文化的重視與求索,“宅茲中國”在文明中國價值譜系中始終占據本源的地位。相比其他民族,安土重遷和重視家居生活的中華民族對于屋宅有著更執著的追求與眷戀。已出土和現存的大量關于居宅文化的建筑文物、文獻典籍,反映了中國家國同構文明范式的型鑄。其中,《黃帝宅經》被譽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宅經,大致成書于在南北朝至宋,托名黃帝而成。它綜合了諸多史傳的宅典,融匯了道家、陰陽家的思想,還糅合了儒家關于人倫規范、人格修養的思想,將宅置于天道的宇宙論形上背景中,成為溝通天地人神的現實環節。宅的倫理目的被設定為家人、家庭和家族的平安幸福,同時儒家對人格完善的終極關切也貫穿于居宅及于其內展開的日常實踐中。它們共同成就了“宅法”,即《黃帝宅經》所謂的“最要者”“真秘術”,反映了這一時期文化合流的趨勢。
一、“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宅對人生命的建構意義
現代建筑理論指出,建筑的使命是讓人安居與融合。其中,住宅作為人類扎根于世界一角的最初宇宙,“是創造具體的、生活的存在象征,它賦予我們的存在于世以形式和結構”[1](76)。自其被建構出來,就承載了人類社會的價值而成為價值的凝結物。因此,每一棟住宅都有或溫暖或冷漠、或輕松或壓抑、或友好或敵意的特征,即“宅性”。《黃帝宅經》中的“宅性”由居宅的空間方位、時間等自然屬性決定,亦與其社會屬性密不可分。這兩方面都基于古人對理想宇宙秩序的認識,宅被置于天地人的宇宙生化序列中,在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轉化合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黃帝宅經》指出宅乃“陰陽之樞紐”。“宅者,人所讬居也。讬者,寄也。”[2](339)宅是人休養生息之地,傳統中國自三代以來所確立的“四極八方”空間觀念中,空間被視為具有幾何性質的物質容器,直觀表現該容器的就是由人創造的各種建筑形式或空間形式,而居宅于其中最為典型。“陰”“陽”代表由道化生且存在于宇宙空間中的兩種對立的物質力量和價值力量。《黃帝宅經》以宅為“陰陽之樞紐”,其含義有兩層。一方面,陰陽以宅為載體而得以顯現。《易經·系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或道作為宇宙之本根,化生出陰陽或兩儀,由兩儀生成的四象則表示四時四方,即時間和空間。八卦象征構成物質世界的天、地、雷、風等八類物質范疇。在這個從一到多的宇宙生成過程上看,宅雖是人所創造的物質形式,“象者日月、乾坤、寒暑、雄雌、晝夜、陰陽”,實因其厚載物乃像大地,本體上仍為陰陽化物而成,故傳統宅院多以長方形為形制,以符合古人“天圓地方”的空間想象。陰陽化生的天、地、人、物都各包含陰陽,但陰陽二氣乃運變無形之物,無法用感官觀察獲得,只有通過宅的具體形態才能認識。陰陽作用于宅,“為二十四路、八卦、九宮,配男女之位,宅陰陽之界”,決定了“宅性”,并借助宅性對人產生的影響來顯現自身。另一方面,陰陽二氣的辯證運動決定宅的倫理屬性。萬物“無陰陽斯無變化”(《易傳·系辭上》),陰陽二氣通過自己在居宅空間中的辯證運動來呈現自己,把宅變成陰陽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中心環節。在中國哲學的一體兩極四象八卦的宇宙萬物生成論中,陰陽的辯證運動具有絕對的價值,陰陽這兩種力量不是對抗對立而是辯證地生成與推動宇宙萬物的生成發展,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獨自決定事物的吉兇善惡,所以宅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由空間方位與時間變量共同決定。空間有四面八方上下等方位的吉兇變化,中院“從東南巽角順之戌為陰明”;時間的變量既有四季的吉兇變化,“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氣、死氣之位”,亦有二十四時辰的祥禍變化,“從巽向乾、從午向子、從坤向艮、從酉向卯……福德之方”,反之為“刑禍之方”。除此,《易經·系辭》云“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而“宅以形勢為身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木為毛發,以舍屋為衣服,以門戶為冠帶”,因此還須結合構成宇宙萬物的八種物質。這些都是居宅空間在時間、物質結構上的異質性,其價值屬性也復雜而充滿變數。
陰陽與刑德相應,由刑德進一步揭示陰陽的辯證運動及其對宅性的促成。“刑”本義為殺戮、征伐,“德”為獎賞、懷柔義。刑為陰,德為陽。“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彰)。”[3](265)由于陰陽在四季四時、不同居宅方位都會發生變化,刑德相應表現為一種時間的變化,成為一對時間概念。《黃帝四經一經·觀》云:“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生。”[3](217)同時,刑德還需要考量它的方位,《黃帝宅經》指出宅的刑禍方與福德方由陰陽屬性決定,如陽宅的刑禍方在東方、北方,福德方在西方、南方,陰宅正相反。“凡人婚嫁,買莊田六畜,致塋域,上官求利等,悉亦向宅福德方往來,久久吉慶;若為刑禍方往來,久久不利。”這使刑德又成為一對空間概念。刑德還是吉兇禍福的象征。《越絕書·計倪內經》云:“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兇……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4](30)借助刑德運行方位可占斷事之成敗、人生吉兇。這樣,陰陽借助刑德與吉兇、善惡聯系在一起,被賦予了價值內容,并以此決定了宅的價值屬性。
其次,《黃帝宅經》視宅為“人倫之軌模”。宅不僅是一種基于形上之道的空間組織結構,它作為家還是一種由這種結構明確下來的家庭及社會組織結構,直觀地表達著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家庭成員之間及其日常生活行為模式。人們在建構宅的空間結構時,將與傳統等級社會相適應的風俗、規范和信仰等借助規劃、建筑手法運作于空間中,使居宅成為一種社會價值的象征符號,擁有一座宮殿或擁有一間陋屋,既是富或窮的符號,還是特定社會階層和階級的習慣符號,標志著宮殿或陋屋的擁有者所從屬的階級以及所堅持的習慣結構[5](141)。《黃帝宅經》對人倫秩序的記載同樣以宇宙天道秩序為依據,遵循“天尊地卑/陰卑陽尊”的原則,將陰陽與男女、長幼、夫妻、父子等的家庭和社會的尊卑地位相匹配,以明確人們在日常生活空間中應該待的位置與活動范圍,宅的每個空間方位都有不同服務對象,相應的大小、裝飾等均不同,整個空間呈現出嚴格的秩序性與規范性。其要點有三:
第一,以“內”“外”分割厘清“男女有別”。《黃帝宅經》云:“陽宅多修于外,陰宅多修于內……不同八卦九宮分形列象,配男女之位也。”這里的陰宅、陽宅實指內外之宅。中國傳統的父系社會視“男女之別”為人倫之大,該原則被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并借由居宅空間的規劃得到具體的呈現。先秦時期就有對宅內外界限的清晰規定,《禮記·內則》載:“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外部是男性/陽剛之地,封閉的內部是女/陰的生活世界。中國古代日常生活實踐中,“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在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中,“男女之別”既描述生理之別,更表達男女的家庭社會價值和地位之別,屋宅明確了這種由性別決定的社會角色分工和由空間表達的權力配置,將女性束縛于家宅內院中,保證了父系血統的純正性和道德自律性。
第二,以“中”明確家族家庭的權力歸屬。中的位置在空間方位中具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價值。春秋時期初步確立住宅的“軸線設計圖式”整體造型:大門、庭院、正堂排列在同一中軸線上,其他的室、廂、寢等房間都依這條中軸線而建。中軸線終端有“堂”,《說文解字》云:“堂,殿也。”段玉裁注:“古曰堂,漢以后曰殿。”[2](685)堂建得比其他的房間都要高大雄偉。堂屋的方位坐北朝南,以獲得豐富的陽光,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家族、家庭的長者所坐之地,代表著國家、家族和家庭的權力中心,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主軸線中端是庭,雖不及堂高大,但也占據著一個中心位置,居宅內的各個組成單元居住的房間都對著庭院,既利于家庭成員親密接觸、融洽感情和整合家庭,“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禮記·坊記》),也方便中心的權威對家庭成員言行舉止的監控。
第三,以前后、左右等方位建構行為的規范模式。前與后在傳統價值體系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黃帝宅經》載:“乾將三男震、坎、艮,悉屬于陽位;坤將三女,巽、離、兌悉屬陰之位。”陽位與陰位分別對應著前后。這種區分主要源自身體與視覺的體驗,“前方空間是可視空間,它是生動活潑的,并且比我們僅僅通過非視覺線索所能體會到的后方空間要大得多。因為人們可以看到前方,所以前方空間是‘亮堂的’;人們無法看到后方,所以即便在有陽光照射的時候,后方空間也是‘黑暗的’”[6](40)。前方正對陽光,屬于陽,象征著尊貴,人們需要尊重和敬畏。后在可視范圍之外,屬于陰,代表黑暗和卑微。地位較低的人必須走在長者或地位尊貴的人之后,表示尊重和謙卑。房屋的前門被稱為正門,“正”乃方直不曲義。這樣,人的視覺體驗與陰陽價值論結合,“前”便賦有了正直、高貴、美好等價值,后則反之。與前后相比,左右的價值相對復雜,既有右尊于左說,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①張守節正義:“右室,上室。”(司馬遷:《史記》第6 冊,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1889 頁)路以右為尊,左為卑,要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記·曲禮》)。也有左尊右卑說,如《黃帝宅經》以八卦的巽為南、坎為北、震為東、兌為西②當人在宅中面南而坐時,左側在東方,是太陽升起之地,代表陽剛、神圣和尊重之地,右側是西方,是太陽落下的地方,代表陰柔、卑微與不祥。。
居宅的空間人倫軌模一旦被建構起來,就變成一種價值的象征符號,規范著居于其間的所有人。這些規范既包括具有儀式化象征意義的儀態、著裝,還包括遵守禮的舉止來實現身體對空間的臣服,每個人都必須知道在哪些空間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事情。人們從生至死幾乎整個生命都是在這些空間度過的,在其中起居,舉行婚儀、出生和成人等儀式,在對神的敬畏和對長輩的孝敬及對逝者的哀悼等日常行為中形成自己的行事方式,進而固化這些行為規范,把它們變成自己的性情并傳給下一代。
綜之,《黃帝宅經》所反映并代表的中國傳統居宅理論中,居宅承載著宇宙的結構,以“陰陽之樞紐”把天、地、人組織為一個關聯體,社會的、家族的和家庭的權力在居宅空間中集中和有序遞減,由此將家庭家族凝聚成一個結構清晰、秩序井然的倫理系統。以“人倫之軌模”直觀呈現出中國傳統家族本質的價值系統,使孝悌為本的倫理價值在其中得以實施完成,并成為社會倫理的出發點。這就是為什么宅被視為“人之本也”(《黃帝宅經》)的根本原因。
二、“宅因人得存”:人對宅的目的性意義
宅從宇宙自然到價值世界再到人倫規范的生成過程中,為家建構了一個秩序井然的生活世界,配置和培育了家庭乃至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同時《黃帝宅經》也指出:(宅)“雖大小不等,陰陽有殊,縱然各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惡。大者大說,小者小論。犯者有災,鎮而禍止。”每個房屋都有由陰陽變化而導致的吉兇、善惡的變化,那么人又如何確保自己趨善避惡呢?《黃帝宅經》指出,雖然由宅之陰陽運變“順之則亨,逆之則否……違命變殃者乎”,但也強調“宅因人得存”,人“不可獨信命”。賦予人決定和改變宅性的自由,邏輯上引出了“力”與“命”或自由與必然的關系。
第一,“凡人所居,無不在宅”,“宅”是人對居宅需求的結果,這既包括人作為自然與社會存在體的需要,也包括文化進程中話語和意識形態所體現的共同需要。“就人屬于感官世界而言,他是一個有需要的存在者。”[7](142)他只有依靠住房、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等產品才能生存和生活[8](161)。尋找一個安全的空間為棲息地,是所有動物的共有本性。先民曾不斷移動,后來固定在一個地方,一方居宅中。這些居宅將人們“帶入內部,并體現‘在某處’的基本需求”[9](226),成為傳統中國人的普遍欲求對象,并世代沉淀下來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對此,中國的主體文化傳統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與重視。《黃帝宅經·子夏》云:“失地得宮,子孫不窮,雖無基業,衣食過充。失地失宮,絕嗣無從,行求衣食,客死蒿蓬。”“宮”即“宅”。不管多么卑微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居宅,傳統中國人對于屋宅的需求與至死方休的追求可謂舉世無雙,還把這種需求帶入信仰的世界,建“陰宅”以滿足死去親人對宅的“需求”。也正是為了滿足居宅的需求,從穴居、巢居走向筑屋,人類把自己變成萬物中最具創造性的建筑師。
對身體需求的肯定邏輯上必然導出傳統宅法對人的感官體驗、經驗感知的肯定與依賴。如重視“陽”(乾)源自對人的視覺需求的肯定,這被視為“生命感”,即對光明與黑暗或“對暖和冷的感覺,甚至由心靈所激動的感覺(如通過很快交替著的希望或恐懼產生的)”[10](37),視覺的這種感覺質料,都源自人對光的需要,光驅散黑暗,人們借助它了解世界,有了溫暖的感覺和秩序的體驗。這也是“乾”(陽)在屋宅內具有至高無上價值的原因。再如倚重“中”的價值源自人對自己身體的感知,以及人對“自我意識感”需要的肯定。在己他關系中,人人都傾向于認為自己、家和家鄉是“中心的位置”,自己的國家是天下的中心。這種自我意識隱含著中心的存在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正是因為重視人的外在感覺需要,以《黃帝宅經》為典型的傳統宅論,總是有意構造日常生活中視覺的幻象,于是人們會“看到”家族祠堂的祖先總是在“注視”著他們,監督著他們的言行。住宅尤其是園林建筑強調虛實相間,而虛的存在就是為了制造視覺的幻象,如月亮升起、院中的花樹綻放時在月門與窗中構成的如山水畫般的幻象。這些感官體驗構造了傳統中國的獨特居宅藝術和生活世界,塑造了傳統中國人的倫理觀、審美觀。
第二,人根據趨善避惡的價值原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思考和決定、調整和規劃建造自己的居住空間。這也是被馬克思視為人不同于蜜蜂等自然界建筑師的本質所在。從宏觀看,人的這種主體性最突出地體現在對城市、居宅等建筑的規劃方面。現代建筑理論指出,建筑不僅僅“關乎實際需要和經濟因素,還關系到存在的意義。這種存在的意義源自自然、人類,以及精神的現象,并通過秩序和特征為人們所體驗”[9](7)。中國古代自商周就已形成的“幻方”(Magic square)模型被普遍地運用于城市規劃、居宅等一切空間秩序的建構中。《黃帝宅經》的道藏本、四庫本等版本的陽宅圖皆清楚地記載了該模型。這一模型是基于中國人對完善宇宙秩序的認識而建成的居住世界——一個定居的農耕社會的生活世界模型,目的是保持居住之地的陰陽和諧[11](10)。這樣的規劃把居宅變成了人的小宇宙,一個能夠看到和感受到的生活世界,它每天都會提醒生活于其中的人在家庭、社會和自然宇宙架構中的位置。
在居宅建造方面,為了能“居善地”,《黃帝宅經》充分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例如,確定宅址有“擇”,“人之居宅,大須慎擇”,它是識別那些兇險、有害于人之地的理性行為。《釋名》釋“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可見宅本身就包含著主體的選擇。再如在如何平衡陰陽運化方面,為保證“一陰一陽往來”,使宅造福而非禍害人,主張“移來方位”定之,即人不能固守一隅,要善于“移”,保證“陽宅有陽氣抱陰,陰宅有陰氣抱陽”(《黃帝宅經》),以成居吉。無論陰宅還是陽宅,移的目的在于避免“獨王”,“陽不獨王,以陰為德。陰不獨王,以陽為德”,使“天道天德月德生氣到其位”,陰陽二氣互為融通,相息相生。由此才可謂“福德之宅”。居住在這樣的宅中,“一家獲安,榮華富貴”。反之,若“重陰重陽”,打破陰陽的平衡,過高或過低、過大或過小,會使宅無魂無魄而成為兇宅,導致人精神失調,罹患疾病,“家破、逃散、子孫絕后”。假如宅院出現陰陽失調,還可以主動地“補”,“福德之方拓復拓”“刑禍之方縮復縮”;若宅有令人貧耗之“五虛”,可以“五實”彌補,避免厄運的發生。這樣,通過主體的選擇、規劃和建造活動,宅的陰陽辯證相得、和諧有序。
第三,強調“其田雖良,薅鋤乃芳;其宅雖善,修移乃昌”,主張人之于宅的道德主體性。儒家充分肯定感性需要之于人存在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把人設定為有善的潛能的存在體,這種善的潛能或天稟即“道德理性”。人的道德理性與感性欲求共同構成人性,在兩者之間,儒家是把著力點放在前者,強調道德理性更符合天道人倫。而日常的“仁宅義路”言行以宇宙論、天道觀等為形上根源,落實到現實層面就是人們對幸福的追求。《黃帝宅經》秉持儒家一以貫之的思想,在德福關系上,主張“德福之方勤依天道”,認為人“居善地”并不能絕對保證家繁代昌,它強調德福的一致性,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將自己的道德稟賦擴之充之,以彰顯自己的道德主體性。
對個體而言,需“正心誠意”以抵制外在的物質誘惑,節制欲望,建立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自知自省的能力,才能履行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生活幸福是人基于一定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舒適生活狀態,這些物質是每個人實現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一個人占有得多一些,其他人就相應獲得的少一些,尤其是共同生活在一個群體中的人。但人追求更多善的東西“是一種心理需要,更是一種社會特權,甚至是一種精神屬性”[6](58)。這種欲求使人擁有多大的空間都無法得到滿足。《黃帝宅經·宅統》云:“宅墓以象榮華之源,得利者所作遂心,失利者妄生反心。”貪欲、“行不得度”勢必造成對他人利益的剝奪,對“度”的破壞。在中國傳統的等級社會中,“度”由禮具體規定,每個行為都要遵守禮所規定的空間秩序,人的需要滿足應該與其社會身份相符合,“勿失天極,究數而止”(《黃帝四經·稱》)。例如,建宅時誡太過而損禮,“宮室過度,上帝所惡,為者弗居,雖居必路”(《黃帝四經·稱》)。但過分缺薄也是違禮,會致宅氣不足而損財祿。當拓展或縮小宅院時,可拓福德之方,但也不能超過量度,否則會轉成禍患。道德理性就是要讓人明白,合禮的屋宅既不能過大也不能小于居住者所需。
在人倫關系中,人們于宅內“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篇》)。根據宇宙論,人處于天地或陰陽之間,有責任去保持宇宙中諸如男女、長幼、主仆、親疏的陰陽平衡與和諧,和諧的本質為有序與融合。人們承擔家庭義務時遵循“五服”“九族”制和“親親”“尊尊”原則。《黃帝宅經》強調“子孫忠孝,天神佑助”。維持家庭生活的最重要規范莫過于長幼的規范,“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禮記·曲禮》)。“孝”是長幼規范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倫理文化、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孝把整個家族凝聚成一個結構有序的整體,這種秩序同樣適用于鄰里關系。除了有序,為了使日常生活溫情脈脈,使家宅變成人的身心歸屬之地,《黃帝宅經》還提出“其有長才深智,憫物愛生,敬曉斯門”,這與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思想一致,主體的仁或愛的道德情感貫穿于人們對禮儀規范踐履之始終,并以空間距離的遠近決定親疏的方式對人的言行發揮作用,真正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陰陽平衡協調。
要之,《黃帝宅經》整體肯定了人對宅的目的性和主體性,面對“凡人所居,無不在宅”的必然性,給予人發揮主體意識的空間,以對城市規劃、建筑營造的實踐,把居住地變成人的價值凝結物,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設計了一個家園。個體在日常生活自覺自為的道德實踐中,要勤“修德福”、去“刑禍”,使家宅內“五姓咸和,百事俱昌”。這也是中國人關于幸福的最切近想象。
三、“人宅相扶”:人宅和合成就人居環境倫理生態
人創造了住宅,但住宅并非柯布西耶所言的“機器”,也不是笛卡兒式的人宅分立。人作為“主體在廣義上的空間秩序和空間化內所處的位置及空間定位,是構成其認知、性格以及行為可能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12](92)。《黃帝宅經》以“人宅相扶”思想強調人與可感知世界間的相互成全、相互維持關系,在“人之善”與“宅之善”的辯證統一中,達致宅與人的共融共鳴狀態。
首先,宅通過對人的生命、財產和隱私的保護,使人休養生息、安居樂業而成就“人之善”。“善”為吉祥、美好義,宅之善即“地善,苗茂盛;宅吉,人興隆”。它通過作用于人而得以彰顯;“人之善”主要指“居之有信,懷才抱義,壯勇無雙”的道德善,道德善以心理為動源,以行為為表象,最終的指向是個體的人格、品格的完善。就此而論,“人之善”的起點來自心理上的安全感獲得,因為安全感是人其他一切價值感塑造的基礎。建筑本質上本來就是要讓人安居下來。基于人們對宇宙的認識,家、社區和城市都被設計成封閉的以代表大地,在這些封閉的空間內,人的隱私得到重重防護。宅院是封閉的,臥室是封閉的,床也是封閉的。這種特有的封閉模式予以傳統中國人以巨大的安穩感與完整性。那些圍合的四面墻壁、高墻深院護衛著人的生命、生活與財產的安全,把家變成一個安定的地方,所謂“上之軍國,次及州郡縣邑,下之村坊署柵,乃至山居,但人所處,皆其例焉”,古代的城市和里坊等聚居區都依此法形成一個封閉的、防御工事模式的生活世界,給傳統中國人帶來極大的安全感。
宅所成就的“人之善”指向個體就是本心、初心的保持。“心”內含性、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禮記·樂記》),性稟天道為靜,情感外物易動,不能反躬則為惡。心擺脫一切情欲干擾的狀態就是“靜”。因此,能使人心無旁騖、歸于原初的靜就是“宅之善”。《黃帝宅經》謂“居若安,家代昌吉”,《天隱子》解釋居之“安”處就是能讓人“深居靜坐”,有利于“心”保持反省和審視自我的狀態。在具體的房屋規劃建造時,保證宅的“清凈”是關鍵。例如要求“外金匱、青龍兩位,宜作庫藏倉窖吉……常令清凈連接,叢林花木藹密”;“宜置高樓大舍,常令清凈及集學經史”;“辰地府”等造福子孫之地,更宜清凈為要。對于房屋內部空間,要求保證陰陽調和、明暗適中,宅不可蓋太高,太高導致陽盛明多,也不可太低,低致陰盛暗多。陽盛明多會使人內心煩躁,陰盛暗多則會讓人萎靡壓抑。除了清凈,“適度”也是《黃帝宅經》建宅的基本原則,如此方能使人“修令清潔闊厚”,內心寧靜舒適。
宅所成就的“人之善”指向群體就是通過人們日常的道德行為,實現家庭和睦、鄰里和諧、社會有序。人通過兩性結合并在持續共居結成的群體中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和保持自己生命的進步。那么,基于婚姻而逐層建構起來的群體,其維持與發展都需要個體的欲望對群體的利益作出讓步,這就涉及公與私或義與利的關系問題。《黃帝宅經》整體站在家庭家族利益的立場去闡論“人之善”,強調人之欲“大犯家破人亡,小犯失爵亡官”等后果,體現出儒家崇公抑私的態度,是以居宅為人倫建構的行為軌模。由于男、長、夫不僅是一種家庭角色,更是宗法社會的權力象征符號,他們代表著群體的利益以及維持這一利益必要的道德權利,所以,這一軌模所要求家庭成員的孝、溫、良、恭、讓諸種品格,都需要個體持續對個人利益、欲望和沖動的抑制才能逐漸養成。這些品格塑造的目的都指向群體的終極價值——和睦有序。現代空間理論研究顯示,“當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工作時,一個人確實不會奪去另一個人的空間,相反,他因為給同事提供了支持而擴大了對方的空間”[6](64)。因此,家庭成員的這種節制與犧牲成就的友善與和睦關系會使人精神放松,感覺舒適與順暢,確保了家宅內父慈子孝、人丁興旺。反之,沒有這些品質,家庭內部就會充滿各種利益糾紛,不和、衰微乃至于覆滅,民間的“富不過三代”之語表達的正是此意。
其次,人通過自己的主體性,在規劃建造與修養實踐中,把宅變成自己創造和發展生命之所,成全了“宅之善”。正如《黃帝宅經》所云:“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宅之善”的核心在于宅與家合一。作為家的宅,保衛和護佑著一群有著同樣血緣、情感和價值的人,所有被視為“宅”的空間都應該是一個安定、安全之地,人們從那里獲得安全感和價值感。如前所述,人們把城市建成墻垣環繞、河池深挖的防御工事,把里坊、家宅建成高墻深院的重重防護世界,以保衛居民的生命財產不受侵擾,但也禁止他們任意踏出圍墻的邊界。鄉村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個熟人的社會,其足跡的經驗邊界形成心理上的“圍墻”,墻內的世界安寧、和諧,人與人雖有矛盾,但相比從這個空間獲得的保護就不算什么了,墻外的世界則是未知的恐懼。所以,“人以宅為家”道出傳統中國人對宅的執著,“是因為熟悉和放心,是因為撫育和安全的保證”[4](160)。
同時,宅作為家還在于它的規范和塑造功能。其中,規范是空間對行為的制約與束縛,“塑造”是空間對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引導與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如《黃帝宅經》所闡述的,斗轉星移、日月輪轉,陰陽于宅中“生化物情之母”“生化物情之父”,人在宅內度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歲月中,其整個日常行為都在接受一種倫理訓練,同時形成一種倫理和道德意識,當其履行了這些規定時就會感到榮耀,反之就會感到恥辱。這樣,居宅成功地塑造了人們關于是非判斷的道德感,人們也從中獲得了生活的安定感和社會的秩序感。
最后,通過人與宅的辯證成全,人們對家宅家鄉產生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既是經驗的,也是體驗性的,既是審美性的,也是倫理性的,它們使生活世界的天地人神之間產生鳴應或契合關系,證實和證成著儒家價值體系的“天人合一”。從超越的層面看,天地人神之間首先產生空間的垂直鳴應。居宅承載天道秩序,象征大地空間,代表人倫規矩,“人宅相扶”就可以“感通天地”。然而,“感通天地”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人與神的共生共鳴。就宅而言,它們“所獲得的不朽性就體現在自己被視為有卓越的秩序上。雄偉的城墻和城門劃分出了神圣空間。防御工事不僅可以保衛一個民族不受敵人的侵擾,而且保護它們不受惡魔和死者靈魂的驚擾”[6](173)。這可由人對霤神、四王神的敬畏提供,“凡欲修造動治,須避四王神,亦名帝車、帝輅、帝舍”,否則“犯帝車殺父,犯帝輅殺母,犯帝舍殺子孫”;但在傳統中國祖先崇拜信仰系統中,這更由人與祖先神靈之間的祭祀與護佑關系完成。傳統中國的家宅是一個由地下的墓穴(陰宅)、地上的屋宅(陽宅)和祖先之精魂(靈牌)居所構成的一個垂直的世界。《黃帝宅經》正是在這樣一個祖先—己—子孫的代際倫理層面思考人、宅和神的關系與幸福問題。祖先的神靈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祖先的肉身所居之地——陰宅,《黃帝宅經》始終將其與陽宅結合在一起思考,如《青烏子》云“其宅得墓,二神漸護,子孫祿位乃固”,要保證“墓宅俱吉”。祖先神靈的居處——宗祠牌位,它們發揮規訓監督子孫日常言行的作用,使子孫們遵循天道、勤修德性、廣行善舉以避免“先靈譴責,地禍常并”,否則就會“零落他鄉,流轉如蓬,客死河岸”。可見,傳統中國人的信仰體系和價值體系是同質的,人神關系與其他任何關系的融洽都必須通過德性的養成才能完成,德性是天地人神這一垂直關系產生共鳴的根本因素。
在天地人神鳴應關系形成的過程中,時間的因素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由日常時間呈現,賦有重復性、無窮無盡性。陰陽往來在宅的四季四時更替中循環往復,決定著宅的吉兇善惡變化,時間是這種變化的矢量。《黃帝宅經》云“日月乾坤,寒暑雌雄,晝夜陰陽等,所以包羅萬象,舉一千從”。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往復中,在創造和呈現日常各種重復的規范、儀式和行為的過程中,把宅變成生活的記憶庫,使其承載對回蕩在空間中的聲音和味道的記憶、對隨時間積累起來的公共活動和家庭歡樂的記憶。而對祖先的崇拜本質上就是一種時間的崇拜儀式。通過重復的時間,人的身體被空間建構,那被鐫刻在屋宅每個空間“所代表的特有的、被社會視為恰當的身體行為表達、手勢、日常慣例性的行為和節奏”[12](40),都根植于個體居民的軀體記憶中。也正是日常生活的這種無窮無盡重復,人們不斷生產著自己生活的空間,并力圖突破重復帶來的無聊,把它變成意義的空間、信仰的空間,變成身體的微觀尺度與人天地的宏觀尺度聯系在一起的介質,依靠這個介質,天、地和祖先的神靈與人們的自我認同、情感歸屬融合為一,變成人們的身體與生命存在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人宅相扶”之深意就在于人之善與宅之善相互成全而成就的天地人神鳴應的人居生態環境,這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所體驗的家宅空間超越了其物理幾何性質而變成人們的意義中心。人們在其中享受到家、家鄉和家園帶來的安全感和歸屬感,讓自己穩定下來,于其中創造和享受“子子孫孫受榮樂”的幸福,形成一種有價值的、有信仰的生活并由此彰顯自己的主體價值和力量。
結語
綜上可見,《黃帝宅經》整合了古人的宇宙觀、天道觀、倫理觀,其內含的價值體系通過居宅以及人們圍繞居宅展開的日常生活,成為人們的文化心理及行為方式,積淀為中華民族的性情氣質。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居宅建筑承載了人們對宇宙、人生和自己的觀念,寄托了人們的欲望、理性、希望和信仰。更重要的是,居宅作為家,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確定性與合乎目標實現的日常生活模式,千百年來,一直是傳統中國人思考生存與生活的根據。現代社會“不再是一個宇宙,而是充滿了四分五裂的信仰和相互沖突的意識形態”[6](116)。統一宇宙秩序的解構,意味著傳統空間秩序和人倫秩序的瓦解,人們獲得了不被空間秩序、人倫秩序約束的自由,但人與其生長的家庭、家鄉、家園和自己的關系都變得日益薄弱。人們占有著房屋,卻無法擁有它,它只是一方放置疲憊身軀的空間。因此,應該怎樣重建使人能安身立命的“家園”,使人能再次安居于家、安居于心中,并產生對所居之家的依戀、歸屬之深刻意識,無疑是進入后現代社會的人應當著力尋找和思考的重要人生和倫理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