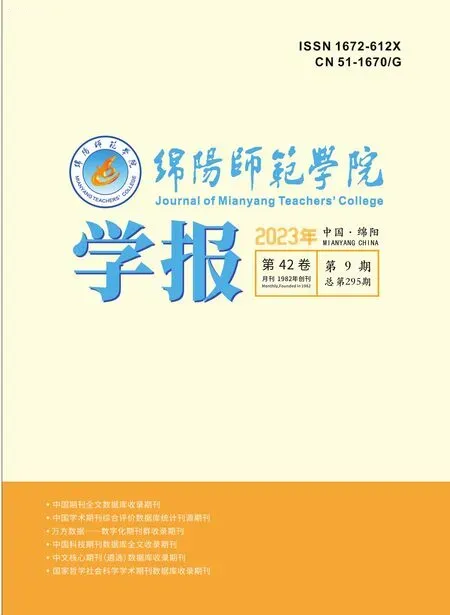中小型博物館重游率影響因素研究
——以綿陽博物館為例
馬遵平,趙乙也,謝澤氡
(1.綿陽師范學院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四川綿陽 62100;2.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開封 475001)
一、引言
在我國,中小型博物館通常是指那些相對于國家級、省級博物館而言的市、縣級博物館。這類博物館規模小、藏品少、資金匱乏、人員短缺,其教育、科研乃至陳列展示等功能也相應的受到了限制[1-2]。國家級、省級的大型博物館往往是中心城市重要的旅游熱點景區,每年吸引大量的外地游客前往參觀瀏覽,能極大地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3]。與之相比,中小型博物館的吸引力有限,主要面向本地居民。在國家文物局印發的《博物館事業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年)》中,強調要全面提升中小型博物館的展示服務功能,其目的就是要增強中小型博物館的吸引力,提高其場所設施的利用率。換句話說,增加參觀瀏覽博物館的人次,仍是中小型博物館管理的主要目標,而提高重游率即是實現該目標的主要途徑。
重游率即重游概率,它是指在相同的條件下,人們主動再次到訪某一游憩場所事件的可能性度量。重游率是反映游憩場所吸引力和設施利用率的關鍵指標。目前有關博物館重游方面的研究,幾乎都是關于“重游意愿”的研究,如Simpson[4]關于新西蘭北部一家鄉村博物館游客的期望、感知滿意度以及重游意愿的描述統計研究;Harrison和Shaw[5]關于博物館游客的體驗、滿意度與其游后行為意向關系的研究;Antn和Garrido[6]關于游客參與互動體驗項目與其未來參加博物館活動項目的意愿的研究;Kang等[7]基于擴展技術接受模型(the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對使用過韓國國家博物館移動導覽系統的游客重游意愿的研究;鄭春暉等[8]關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旅游動機和旅游限制因子對不同類型參觀者重游意愿的影響。這其中,僅有Brida等[9]關于意大利羅韋雷托(Rovereto)現當代藝術博物館游客參觀次數的研究涉及到重游行為。
從管理學的角度,重游率和重游意愿都是量測游客忠誠度的重要指標,但重游意愿只是反映游客的“態度忠誠”,而重游率則反映了游客的“行為忠誠”。重游意愿雖然對實際的重游行為有影響,但重游意愿轉換為實際的重游行為仍受許多內外部因素的制約,兩者并非簡單的線性相關[10]。中小型博物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本地居民,主要功能是向本地居民傳播、普及地方歷史文化知識,提升其文化素養,這顯然有賴于本地居民經常到訪博物館參觀瀏覽。因此,提高重游率就成為中小型博物館發揮其功能、彰顯其存在的關鍵。據此,本研究以綿陽博物館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現場調查獲取相關數據,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揭示中小型博物館重游率影響因素及其水平,并據此提出提高中小型博物館重游率的相關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綿陽博物館是一座地市級綜合博物館,位于四川省綿陽市游仙區,毗鄰富樂山風景區,占地面積約4.4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約3萬平方米。該博物館主要由“千載回望古綿州——綿陽歷史文化陳列”“岷山涪水——綿陽自然陳列”“流淌的記憶——綿陽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富樂夢想——綿陽搖錢樹陳列”“國之大用——綿陽漢馬陳列”“山間洞府——綿陽崖墓陳列”6個主題展廳構成,館藏文物7 000余件,有西漢人體經脈漆木模型、西漢銅帶蓋提梁壺、東漢舞蹈俑等一級文物65件。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搜集相關數據。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游客人口統計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月平均收入水平、出游距離(現居住地到博物館的實際距離)以及到訪博物館的次數,共6個問項;第二部分為游客體驗,包括設施體驗、知識設施體驗以及愉悅體驗等,共10個問項,采用李克特5級評分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上述問項中,到訪博物館的次數反映了游客的實際重游行為,其余問項則是重游率的影響因素。問項設計的理論依據源于博物館體驗以及游后行為意向方面的研究。按照Goulding[11]的觀點,博物館服務管理工作的目標是增強博物館的吸引力,這就要理解和重視游客的體驗。Nowacki[12]則從博物館的展品陳設、周邊環境、接待服務、紀念品銷售以及總體印象等方面建立了基于游客主觀體驗評價的服務質量評價模型。Harrison和Shaw[5]的研究則明確了游客個人的參觀體驗是其滿意度的重要來源,并會對后續的行為意向(向他人推薦或重游)產生影響,而游客的年齡、受教育狀況等人口統計特征則是上述關系的調節變量。Brida等[9]的研究表明,除了人口統計特征,游客為參觀博物館所付出的成本也會影響到到訪次數的概率,這其中就包括游客到達市中心和博物館所需的時間和距離。綜上,并結合國內相關研究[13-15],筆者設計了影響博物館重游率的體驗維度及其測量問項。
(三)數據收集與數據處理
2019年3月16日至31日,筆者在綿陽博物館出口處向游客發放問卷(被調查游客通過手機登錄“問卷星”填寫問卷,并給予1本記事本作為酬勞)。問卷分為兩部分:游客的人口統計特征和參觀博物館的體驗評價。在填寫問卷時,研究人員在旁做必要的說明,確保被調查游客理解問項的含義,共收集有效問卷244份。被調查的游客中,在綿陽常住的有192人(占78.7%);第二次及以上到訪博物館的有113人(占46.3%);年齡在19~35歲的有166人(占68.0%);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專科或本科的有138人(占56.6%);月平均收入水平在3 000~7 000元的有131人(占53.7%);居住地到博物館距離超過3km的有126人(占51.6%)。
觀察設施、知識以及愉悅3個體驗維度評分的描述統計(見表1),發現數據的分布存在較高的相似性,故分別計算3個體驗項目評分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及其Bartlett檢驗卡方值:設施體驗評分的KMO值=0.875,Bartlett檢驗卡方值=2 406.052(df=6,p<0.001);知識體驗評分的KMO值=0.786,Bartlett檢驗卡方值=1 491.280(df=3,p<0.001);愉悅體驗評分KMO值=0.778,Bartlett檢驗卡方值=1 615.138(df=3,p<

表1 體驗維度評分描述統計
0.001)。表明各體驗項目的測量問項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可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進行降維。結果表明,設施、知識以及愉悅3個體驗項目評分的第一成分總方差累積分別為97.21%、96.65%和95.43%,且只有第一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故各提取其第一成分值分別代表設施、知識以及愉悅體驗維度的評分。
(四)模型運算
本研究中的因變量重游率來源于游客的重游行為(y),屬于二項分布變量:y=0表示到訪過一次,y=1表示到訪過兩次及以上。自變量包括游客的個人特征和各個體驗項目的綜合評分,即年齡(x1)、受教育程度(x2)、月平均收入水平(x3)、居住地到博物館距離(x4)、設施體驗綜合評分(x5)、知識體驗綜合評分(x6)、愉悅體驗綜合評分(x7)。
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因果變量分析。因變量重游行為發生的概率P∈[0,1],不發生的概率1-P,P(Y=1|X)=

三、結果分析
模型的殘差偏差/殘差自由度≈1.218,接近1,說明模型不存在過度離散的問題,可接受該擬合模型,模型運算結果見表2。

表2 重游率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
不同年齡段的游客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不存在顯著差異(p=0.935)。Gitelson和Crompton[16]關于重游的經典研究認為,年齡較大的群體有著更強的懷舊情緒和休閑需求,因此更傾向于故地重游。不過該結論主要是針對中遠距離的游客群體,而中小型博物館主要面向本地居民,大多數人一般僅將其視為日常游憩休閑的公共場所,很少會表現出特定的年齡偏好。另外,Harrison和Shaw[5]的研究表明,年齡與博物館的滿意度呈弱正相關,但滿意度和重游意愿間并無顯著關系。這表明雖然年齡較大的群體對博物館的滿意度較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會重復到訪博物館。Brida等[9]的研究則證明,游客到訪藝術博物館的次數與其年齡大小并不相關。
不同收入水平的游客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不存在顯著差異(P=0.262)。以往的研究表明,高收入的群體,會更多地參與文化休閑活動,且更傾向故地重游。比如D’Angelo等[17]的研究表明,人們對博物館、劇院等文化游憩設施的需求與其平均收入呈弱正相關;王斌[18]和肖瀟等[19]的研究也表明,相對于低收入的游客,高收入的游客到訪大連市區和南京市郊珍珠泉景區的重游比例和重游意愿更高。這主要是因為較高的收入往往意味著出游費用(門票、食宿、交通)的預算約束低,這有助于提高重游率。但中小型博物館一般都是免費開放,到訪且其參觀群體多為本地居民,一般不存在預算約束問題。因此,收入水平對中小型博物館重游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就越大(β2=0.274,P=0.096),受教育程度的指數化參數估計值eβ2為1.315,即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游客受教育程度增加n個單位,重游率將上升0.315n倍。該結果與類似的研究結果相近,D’Angelo等[17]的研究表明,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對文化游憩設施有著更高的需求;Brida等[9]的研究也證實,游客受教育的水平與其參觀羅韋雷托現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次數呈正相關;陳波[20]的研究還發現,文化程度高的群體參觀博物館的時間更長,收獲也更多。不過,解學芳[21]的研究表明,學歷較高的群體對包括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產品的總體滿意度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游客的受教育程度、對博物館展品的滿意度與其是否再次到訪博物館,這三者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游客的居住地距離博物館越遠,其再次到訪的概率就越小,兩者呈顯著的負相關(β4=-0.194,P=0.047)。居住地到博物館距離的指數化參數估計值eβ4為0.824,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游客居住地到博物館的距離減小n個單位,重游率將上升0.177n倍。該結果符合游憩場所吸引力隨距離增加而衰減的一般規律[22],即與距離游憩場所較遠的群體相比,那些距離較近的群體使用該場所的頻率更高。Brida等[9]的研究即證實,游客居住地到羅韋雷托現當代藝術博物館的距離越遠,其到訪博物館的次數就越少。這說明即使是中小型博物館,也存在著距離衰減效應,這使其有效的服務范圍受到限制,促使其出現“社區型”博物館的趨勢。
游客的設施體驗越好,其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就越大(β5=0.609,P=0.006),設施體驗的指數化參數估計值eβ5為1.839,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游客對設施體驗評價增加n個單位,重游率將上升0.84n倍。設施體驗維度對重游率的影響程度高于其它因素。博物館的設施狀況(裝修、布局、標識、線路設計)對游客感官體驗有著直接影響。有研究表明,相較于初次到訪博物館的游客,再次到訪者對景區設施不便帶來的負面影響感知更為強烈[23]。即初次到訪的游客會更多關注展品的多樣性和質量,而多次到訪的游客則追求全面的游覽體驗。中小型博物館作為主要滿足本地居民文化休閑需求的游憩場所,其優良的設施對于吸引人們再次到訪的作用會更加明顯。
游客的知識體驗越好,其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就越大(β6=0.365,P=0.090)。知識體驗指數化參數估計值eβ6為1.441,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游客對知識體驗評價增加n個單位,重游率將上升0.44n倍。增長見識、獲得新的知識是游客選擇到訪博物館的主要動機[24]。許春曉等[25]的研究證實,游客的知識教育動機對博物館的滿意度有直接影響,并通過滿意度的中介效應對游客的重游意向產生正向影響。從博物館的角度,游客的知識體驗既來源于展品內容的豐富性,也來源于展品信息的有效傳遞,而我國的中小型博物館顯然在這兩個方面都有所欠缺[26],這也導致知識體驗雖然對中小型博物館的重游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其影響水平低于設施體驗。
游客的愉悅體驗對其再次到訪博物館的概率沒有顯著影響(P=0.145)。愉悅體驗反映了游客在游覽參觀時的情緒反應和沉浸狀態[27]。一般情況下,游客愉悅體驗越高,其重游率就會越高。李永樂等[28]的研究表明,游客在參觀博物館時,其愉悅感源于輕松的心情、審美印象和求新體驗。這其中,優美的館內外環境可以舒緩游客的情緒,在此基礎上,通過新穎的陳列設計,縮短展品與游客的距離,增強游客在參觀過程中的主體意識,可使其獲得更佳的愉悅體驗。但大多數的中小型博物館,其主要功能是滿足本地居民休閑文化需求,缺乏資源和動力去創新展覽項目,游客因此很少獲得新鮮的體驗,審美印象逐漸固化,游客從中獲得的愉悅體驗有限,很難對其再次到訪產生積極的影響。
四、結論
中小型博物館是我國博物館的主體,與大型博物館作為目的地城市的旅游吸引物不同,中小型博物館主要的參觀群體是本地居民,吸引范圍有限,因此提高博物館的重游率是中小型博物館發揮其功能的關鍵。本文通過調查到訪綿陽博物館游客的相關數據,運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重游率的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游客的客觀因素:游客的年齡和收入水平對其是否再次到訪中小型博物館沒有顯著的影響;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再次到訪的可能性就越大;游客的居住地距離博物館越遠,其再次到訪的可能性就越低。
其二,游客的體驗因素:游客在中小型博物館參觀時獲得的設施體驗和知識體驗越好,其再次到訪的可能性就越大;游客在參觀時獲得的愉悅體驗對其是否再次到訪中小型博物館沒有顯著的影響。
五、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提高中小型博物館重游率的建議:
其一,博物館選址在人口多、交通方便的區域。部分中小城市在進行城市規劃建設時,通常會把包括博物館在內的一些公共文化設施搬遷至新建城區,以增加新城區的吸引力,但這往往導致設施的利用率下降。因為中小型博物館的重游率與游客的居住距離密切相關,且博物館的參觀群體主要是本地居民,而新城區的常住人口一般較少,導致博物館的重游率下降。因此,在修建博物館時,原則上應選址在常住人口較多且交通方便的區域,新建城區只有達到一定人口規模、公共交通較為完善時,才適宜將博物館搬遷至此。
其二,努力吸引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相比其他群體,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再次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更高,但與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規模小。因此,中小型博物館有必要針對這部分群體,推出專題展覽項目或相關活動,比如與陳展文物相關的地方史講座。與此同時,博物館應考慮與所在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機制,將定期或不定期參觀展覽及相關活動納入其教育或培訓計劃。
其三,改進設施和講解展示系統。博物館屬于城市公共休閑文化設施,其設施體驗構成了本地居民休閑體驗的一部分,對此有必要進行改進,以保持其吸引力,從而提高設施的重復利用率,具體措施如更新展廳裝飾陳設、優化展廳內外的參觀路線、美化相關標識系統設計等。與此同時,引入數字影像、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改進博物館講解展示系統,全面提升游客的知識體驗水平,增強其重游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