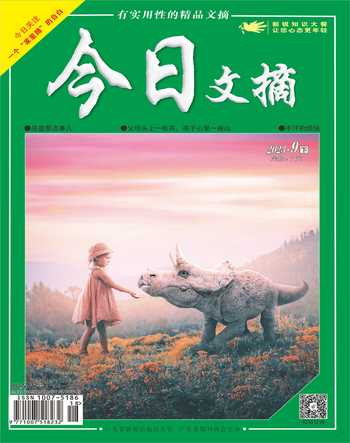“巴氏消毒法”:拯救法國釀酒業
周潔
巴斯德是法國的化學家、微生物學家,被認為是“微生物學之父”。他的一生做過4件非常重要的事:用巴氏消毒法拯救了法國的葡萄酒業、用顯微鏡發現病蠶上的感染源挽救了法國的絲綢工業、發現酒石酸的旋光性、發明狂犬疫苗。
其中,巴氏消毒法無疑是其中知名度最廣的一件,在1862年,巴斯德首次完成了巴氏消毒法測試。現在很多牛奶出售時,仍會標榜自己是巴氏奶。
巴氏消毒法,雖然名稱聽上去有些高深莫測,不過背后的原理十分簡單,即通過利用較低的溫度,殺死病菌的同時保持物品中營養物質風味不變。最初,這個辦法被發明時,卻是為了拯救法國釀酒業的一場危機。
某一年,法國里爾城的釀酒作坊里發生了一件怪事,原本香味芬芳的酒散發出了一股酸氣,酒的風味也發生了較大改變,一批批釀好的酒全部堆在酒窖里,再也賣不出去,酒廠老板十分焦急。
當時,法國的啤酒、葡萄酒享譽整個歐洲,酒廠的廠主們都有一套釀造出香醇美酒的方法。但有時候,即便方法正確,釀出的酒也會變酸,只得倒掉,白白浪費許多人力物力,這使酒商叫苦不迭。
人們普遍認為酒變酸是因為化學反應,卻并不清楚其內在反應機制,因此也談不上如何防止變酸。有的科學家認為,這是由于酒吸收了空氣中的氧氣而引起的化學變化。“發酵是蛋白質分解的結果”這一學說也非常普遍。
此時,有酒商找到巴斯德,希望這位他給到滿意的答復。巴斯德依靠著一臺老式顯微鏡,希望幫助酒廠解決這個困難。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比對觀察,他發現,好的甜菜漿中有小橢球形的生物,而在變酸的酒液中,則是小桿狀體取而代之。他得出結論:甜菜漿中被稱為“酵母”的小橢球體,并非是偶然的污染,而正是發酵的原因所在。好葡萄酒是酵母生長的結果,而葡萄酒變酸,是那些數不清的桿狀體,也就是乳酸桿菌活動產生乳酸的結果。
確定了酒味變酸的原因,不再需要用嘴品嘗,通過顯微鏡檢查一下酒的樣品,就能知道這瓶酒是否變酸。一開始,大家有些懷疑,酒廠老板紛紛帶著自家各種各樣的酒,來驗證巴斯德的發現。
隨著酒瓶的打開,巴斯德把酒逐個滴在玻璃片上,根據是否有乳酸桿菌來判定酒味是否酸澀,然后請品酒的老手來做最后的鑒定。
巴斯德的發現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不過,理解發酵過程的實質只是理論的進步,酒廠廠主更需要的,還是避免酒發酸的實際方法。
在跟細菌周旋的歲月中,歐洲人積累了不少有價值的發現。比如巴黎一位大廚也發明了一種食物保存方法,就是把食物裝在玻璃罐里,密封之后再煮熟,這樣處理過的食物,在常溫下放置幾個月都不壞。
巴斯德得到了啟發,他想,是否可以用加熱的方法來殺死酒里面的乳酸桿菌呢?他把整桶原汁,也就是甜菜漿(含酵母菌)高溫烹煮,經過高溫烹煮后的甜菜漿沒有變酸,但是,也沒有變成美酒。巴斯德的設想失敗了,因為高溫不僅能殺死乳酸桿菌,也能殺死釀酒的酵母菌。酵母菌被殺死了,想釀酒自然也不可能了。
于是,巴斯德決定把原汁加熱之后冷卻,然后再加入酵母菌。這個設想成功了,但拿到酒廠里實驗之后,酒還是有不少變酸的。原來,巴斯德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這么做,無菌操作能夠成功,但酒廠的環境,果汁加熱之后,后面一系列的操作里,隨時有被乳酸桿菌再次污染的可能。
巴斯德又開始了研究,他把封閉的酒瓶泡在水中,加熱到不同的溫度,試圖殺死乳酸桿菌,同時不破壞酒的風味。經過反復多次的實驗,他發現,溫度的高低是關鍵:加熱,但是不要達到沸點。只要把酒放在55℃的環境里,保持半小時,即可殺死酒里的乳酸桿菌,而酒的口感卻不受影響。
這個簡單的方法挽救了法國的制酒業和乳業,并被沿用至今,在食品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是著名的“巴氏消毒法”。
現在人們想到巴氏消毒法,第一時間能夠聯想起來的,不是酒,而是奶。這是為什么呢?
在19世紀之前,歐洲人喝牛奶都不加熱。他們認為牛奶一加熱就失去了珍貴的營養要素。然而,生牛奶中大量存在各種細菌、病毒和寄生蟲。
之所以當時大部分歐洲人喝生牛奶還活得好好的,是因為成年人,對生牛奶里的大部分致病微生物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如果一個剛生了孩子的母親不幸沒有乳汁分泌,像這樣單純用牛奶喂養的嬰兒,頭三個月內的死亡率高達92%。
內森·斯特勞斯就是這樣失去孩子的一位父親。他的兒科醫生告訴他,孩子死亡的原因就是因為喝了生牛奶,染上傳染病。他還告訴他,巴斯德十年前就發明了巴氏消毒法,只不過沒人愿意費事兒。
于是,作為美國梅西連鎖店業主之一的斯特勞斯決心做點什么,他選了紐約藍道爾島的一個兒童收容院做試點,自己掏錢讓收容院安裝設備,對所有牛奶使用巴氏消毒法滅菌。
當時的美國,醫療衛生事業水平比較低,人口死亡率比較高。這家藍道爾島兒童收容院,年度死亡率高達44%。而在巴氏消毒法實施后,下一年全院兒童死亡率下降到20%。
這個數據讓斯特勞斯大為振奮,于是,他跟夫人建立了一個牛奶站,常年為新澤西州雷克伍德城里的孩子們提供經過巴氏消毒的免費牛奶。他還以自己的影響力奔走呼吁,逐漸讓巴氏消毒法從紐約走向美國全國,最后成為食品工業的通用標準。
牛奶需要滅菌的概念,也終于成為一種常識。
(戴穎薦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