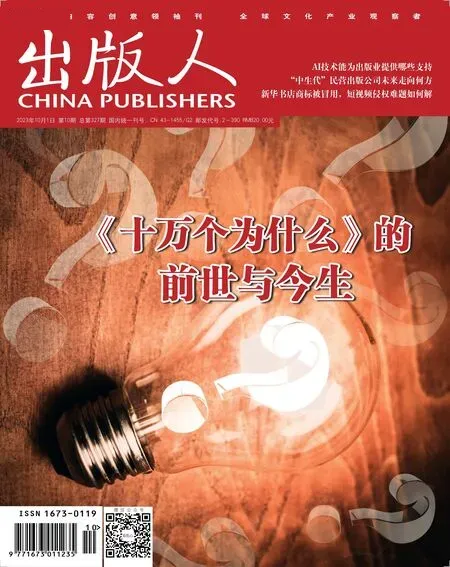薩瓦托的孤獨之書
文|谷立立
[阿根廷]埃內斯托·薩瓦托 著
徐鶴林 譯
譯林出版社
出版:2023年5月
定價:58.00元
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活了99 歲。如此漫長的生命,給了他足夠的時間去辨識人類內心的悸動。然而,在他前30 年的人生中,文學所占的比重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彼時,薩瓦托就像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圖特在其小說《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中所描寫的那樣,醉心于數理研究,很少關注科學以外的東西。很難說,他是不是會像拉巴圖特的人物一樣,漸漸意識到科學存在的悖論,再也無法“理解”身邊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945 年,34 歲的薩瓦托就看清了科學的本質。他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科學具有明顯的道德模糊性,從來不會因為科學家的出身經歷、價值取向改變自己恒定的屬性。這意味著,一旦失去了道德的約束,科學將會為人類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方程式,提起筆來,如此決絕地投入了文學的懷抱。有了這種大事張揚的鋪墊,我們應該不難理解薩瓦托為何會將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命名為《隧道》了。畢竟,隧道是幽暗的、漫長的、曲折的,就像他即將展開的人性探索。
《隧道》的開篇是一個簡單直白的句子:“我想只要說出我的名字——胡安·巴勃羅·卡斯特爾,是殺死瑪麗亞·伊麗巴內的那個畫家,大家就能夠回憶得起這樁案子,對我這個人也就無須多做解釋了。”然而,《隧道》既不簡單,也不直白。表面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詳盡地記錄了卡斯特爾的獄中自白,是他對自己所犯罪行的全景式回顧。我們完全可以從中找到懸疑小說才有的氣質。但其實,誰都不能將薩瓦托的杰作與尋常的懸疑故事畫上等號。
這就像薩瓦托自己,明明是“拉美文學爆炸”的先驅者,偏偏要學著弗洛伊德的樣子解析人類內心的秘密。顯然,諸如“四百五十頭大象在天上飛”的奇詭意象,可以觸動馬爾克斯的敏銳神經,卻未必能夠引出薩瓦托的聯想。相反,他就像勤勤懇懇的心理醫生,始終在人類精神的荒原上小心求證,尋找通往他們內心世界的隱秘小路。這樣的小路被他稱為“隧道”。而隧道之所以會成為隧道,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漫長與陰暗。
如此一來,似乎只要翻開《隧道》,我們就踏上了一輛高速行駛的地下鐵,它穿行在縱橫交錯的地下通道中,拐過無數岔道,途經不同站點,搭載太多思緒,最終駛向人物內心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于是問題來了,卡斯特爾究竟是怎樣的人?他又有著怎樣隱秘的心事。來看看薩瓦托的描述。在成為罪犯之前,卡斯特爾是一位不成功的畫家,性格孤僻內向,很少與人接觸;然而,他又很自負,更將自負當作推動“人類進步的崇高動力”。因為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目睹了母親的諸多舉動,并從“那些最美好的行為的后面發現了一種非常細微的自負或者驕傲”。
說到底,這不過是卡斯特爾的自我暗示。畢竟,他的人生很少出現令人驕傲的時刻。但這似乎并不妨礙他對外面世界投去懷疑的一瞥,更無法阻止他持續的吐槽。身為畫家,卡斯特爾常常質疑評論家的專業素質。在他看來,他們并不懂畫,更看不出畫作的精妙之處,卻總是自以為是地重復著同一類型的行話,就像是在紙上談兵。“如果我是一位杰出的外科醫生,而一個從未拿過手術刀的先生,一位不但并非醫生甚至連貓爪子也沒有接觸過的人來評議我手術中的錯誤,你們會怎么想呢?”
同樣的還有記憶。卡斯特爾應該不會太過相信記憶。在他看來,記憶毫無意義。這個世界“沒有什么集體記憶”,所謂的“集體記憶”不過是人類的一種自衛方式。常常,人們對過去深信不疑,相信過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在卡斯特爾看來,他們之所以如此執迷不悟,不過是“幸運地”忘記了壞事的存在。而他自己,盡管未必相信“過去的一切都是更糟的”,但卻因為在過去的年月里看到了、記住了太多災禍、無恥和殘酷的畫面,漸漸變得無情而又冷酷。于是,記憶就順理成章地變為一束可怕的光,照亮了他幽暗、荒涼的內心,并將它變成“一個充斥著恥辱和骯臟的博物館”。
即便如此,卡斯特爾仍然希望能夠遇到那個真正懂他的人。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幕:在某次畫展上,他意外地發現了一個陌生的姑娘。畫作前人來人往,然而似乎只有她才讀懂了他下筆之時隱含的孤獨。她名叫瑪麗亞·伊麗巴內·溫特爾。“她緊盯著畫上方窗戶里的景色。我敢肯定,她在看畫時與整個世界隔絕了:她既看不到也聽不到在我的畫前走過或停下來的人”。故事發展到這里,如果按照流行的套路,我們大概率會看到一段動人的情感:孤獨的畫家偶遇美麗的姑娘,兩人彼此交心,走到了一起。
當然,薩瓦托不會輕易滿足我們的想象,將自己對于人性的深刻洞見變成廉價的浪漫故事。在他看來,浪漫也好,情感也罷,終究敵不過人類內心的陰暗。它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時不時冒出頭來,顯露出最為真實的一面。具體到《隧道》,卡斯特爾是書中唯一的敘述者。他和所有獨角戲的男主角一樣,站在空無一人的舞臺上,喋喋不休地講述著自己的故事:年邁母親患有的病癥、同行的謾罵與非議、觀眾的無知和粗魯、陌生姑娘的清澈目光。甚至,就連夜里的噩夢都被他拿了過來,像拆玩具一樣大卸八塊。
但這又能代表什么呢?說到底,卡斯特爾仍然是他內心的奴隸。他說了很多,又什么都沒有說。所有的話語都從不同側面反襯出他的孤獨。它們堆積在他內心的隧道中,沒有人愿意接近,更別說伸出手去觸碰了。或許,就是這種越積越多的孤獨,成了壓垮卡斯特爾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他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恐懼自我的小世界一旦被打破,就會面臨翻天覆地的改變。以溫特爾為例,他很愛她。無數次,他默默地念著她的名字;無數次,他想象著與她不期而遇的場景。但到了最后,一切還是回到了原點:孤獨的卡斯特爾終究無法打開心結,坦然面對溫特爾的到來。
于是,他親手殺死了這個唯一能懂他的女人,并將自己推入了徹底的孤獨。那么,我們還能說什么呢?如果可以把《隧道》稱為薩瓦托的《孤獨之書》,大約也是貼切的。1988 年,77歲的他在與朋友交談時,明確地說出了他對藝術的看法。藝術是什么?藝術可以是很多東西,“但首先是一種絕望的溝通嘗試,通過語言這一媒介——不管是文字、繪畫還是音樂”。回到《隧道》,在與外面世界溝通的時候,畫家卡斯特爾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他的絕望。毫無疑問,這是藝術創作的必然。幸運的是,就在卡斯特爾毫無征兆地墜入孤獨的深淵的時候,他的創造者、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卻早已跨越了橫亙在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壁壘,安然地享受著世間的孤獨。■

[阿根廷]埃內斯托·薩瓦托(1911—2011)
埃內斯托·薩瓦托被譽為與馬爾克斯、略薩齊名的拉美“文學爆炸”先驅。薩瓦托畢業于拉普拉塔大學物理-數學系,曾赴法國居里研究所從事放射性物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他致力于科學以造福人類的夢想,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薩瓦托一生只寫了三部小說。《隧道》是他公開出版的小說處女作,開創了拉美小說一個新的方向和文學流派,受到阿爾貝·加繆、托馬斯·曼、格雷厄姆·格林等知名文豪的高度贊揚。1984 年,薩瓦托獲美洲國家組織頒發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文學獎,同年獲西班牙語國家文學界的最高獎——塞萬提斯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