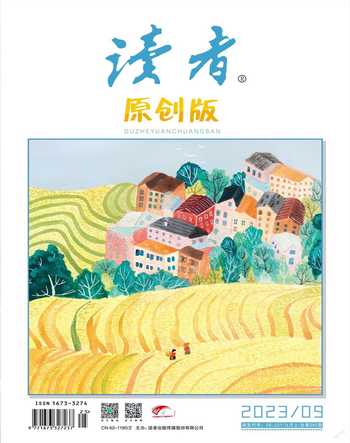林中紀行
方和斐
北方夏末的村郊,像池塘的水體一樣分層。底部是田野,芋頭挑著荷葉一樣的大葉,伙同成簇的花生一起,把棕土鋪成深綠的淤泥。稍高點兒是密密麻麻的玉米,碧綠的亂流一樣,劈開田間齊腰深的艾蒿和草叢。再高一些,竹林、蜜桃樹和山楂樹構成了青色的主體。最高的是白楊,在夏季的降水中膨脹成心形氣球,從頭到腳滿溢著墨綠的葉子。
我在林間行走。對于如我這般的地面生物,世界是二維的。萬物都從扁平的地面上生長起來,如同打開一本立體圖畫書。只有生活空間更廣闊的生物才能享受那些立體的部分,比如昆蟲、鳥類,以及擁有極富想象力的生物。
我在村口的公路邊,用望遠鏡追蹤一只準備起飛的紅隼。它從電線桿上單腿跳起來,伸開翅膀,越過連綿的村莊,踏在千米外的一棵楊樹的頂梢。柔嫩的細枝讓它稍一滑跌,翅膀撲騰幾下,又站到更遠的一棵大青桐高處的葉子上去了。
一只擁有飛羽的生物就這樣,在似綠色海洋的樹林間打了幾個水漂兒。
在樹叢里驚飛兩只菜粉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驚起兩只菜粉蝶,和一只是不同的。一只菜粉蝶眼神不好,而又喜歡追逐同類,頂多被孩童逗弄,跟著細繩吊起的白紙片上下紛飛。但兩只蝴蝶相遇,爆發出的舞蹈卻攝人心魄。
它們從樹叢中飛出來,離地面還很近,就已經被彼此的身影吸引,開始追隨對方的飛行軌跡。由于速度和動作都一樣,誰也追不上誰,只好在空中兜圈子。這圈子起初直徑很大,但隨著追逐升級,距離逐漸收縮,速度也越來越快。兩只蝴蝶賣力地撲翅,極盡一切飛行技巧繞轉,如同敏捷而蓬松的白貓追咬自己的尾巴,如同兩顆并合前夕的白矮星發出引力波,如同兩位身著白裙的花樣滑冰運動員,在舞曲的高潮踮起腳尖擁抱旋轉。人眼已經分不清這絢爛的舞姿。兩片白色的身影攪成一只小小的混沌的白環,逐漸向空中上升。飛轉的白環切開空氣,裹挾起林間的浮塵,形成一股粉白色的龍卷風,直沖林梢。
但很快,白色的舞蹈之環達到了閉合—兩只蝴蝶觸碰到了彼此。它們雖然視力不好,觸覺卻很靈敏。剎那間,它們都明白了對方不是異性。默契的舞伴頓時分開。它們各自憂郁而沉默地飛走,停回樹叢深處。
小河上游被齊腰深的雜草掩蓋著,周圍長滿了高矮不等的野樹,這種環境是野鳥的天堂。鄉村里捉鳥的閑漢向來不少,鳥兒們聽到我的腳步聲,隔著50米便警惕地飛離。
不同鳥的飛行氣質是不一樣的。夜鷺亞成鳥屬于笨拙的那類,兩片遲緩的翅膀勉強拖著一只“煤氣罐”移動;山斑鳩像油頭粉面的生意人,急匆匆地要去赴約,還怕弄亂一絲不茍的頭發;鴨類高頻揮翅,搖搖欲墜;銀喉長尾山雀在枝條和枝條之間快速移動;棕頭鴉雀悄悄地躲在草叢底部怪叫,到了真被看到的時候,又亮出黑漆漆的無辜大眼睛來。
麻雀是伴生人類的鳥兒,在遠離民居的地方,看不到麻雀的身影,最多的反而是家燕。燕子熟悉了人,飛行技巧又華麗,不怕被觀察。與卡通畫家筆下的黑色燕尾服不同,它們的背部泛著藍紫色,喉嚨處則是橙色的。傍晚是家燕飲水的時候,它們從樹林上方飛來,仿佛一枚枚導彈,倏忽間近乎垂直地墜落進河道。日落之前,上百只家燕成群結隊,在農田上空高高地翱翔。它們聚集在數十米的高空,仿佛一面面飄動著的旌旗驕傲地迎風展開,不知道什么獵物停留在這樣的位置。
屈原曾說過:“蒼鳥群飛,孰使萃之?”飛燕的部隊自北向南,緩慢而平穩地掃蕩過整個村莊的天空。
一棵樹上的蒙古寒蟬,總以同樣的頻率鳴叫和喘息。它們如何感知這樣的節奏?它們如何區分周圍的同伴是否在同一棵樹上?它們也有耳朵,也有節奏感嗎?如果有,它們嫌吵嗎?
樹林的盡頭,有農民在地面上尋找知了猴。林間蟬蛻隨處可見,如鈴鐺掛在草葉上。出土的知了在地面留下指頭粗的圓潤的深洞。
在林中見到蟬蛻的人,能很輕易地感受到這種昆蟲身上的命運感。在如此平凡而普通的鄉間,居然有這么一種隨處可見的小小生物,在很小的時間尺度上經歷重生、羽化,而又行動遲緩,聲音聒噪,毫不避人。它簡直是大自然特意捏出來給農人看的一個微縮寓言。
我在密林中行走,世界被蟬鳴聲包裹。搖撼一棵小樹,驚飛十幾只蟬。蟬在飛起之前,喜歡排空腹中的樹汁,只見它們嗡嗡振翅懸停,同時從屁股淋出一股股汁水,四面八方的液體襲來,我招架不住。噼里啪啦,樹林里發生了一場小型降雨,我的眼鏡蒙上一層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