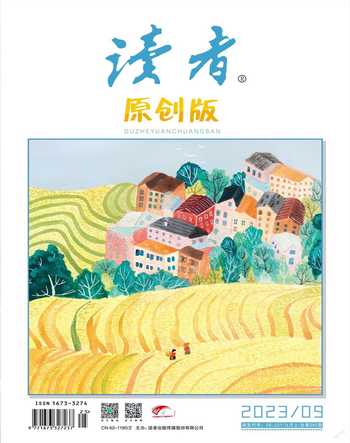下館子
蟠桃叔
1998年秋,我從老家淳化來西安讀書。來的時候是個瘦子,一兩年時間就像吹氣球一樣把自己吃胖了。老家人見了我,贊嘆說西安的水土好,養人。我臊得不行。我知道,是我饞,管不住嘴。
我就讀的西北大學在城墻的西南角,周邊繁華熱鬧,餐飲店一家挨一家;加上當時學校跟前的太白路上還有夜市,煙熏火燎地吹著香風,不由得就敞開肚皮了。
當然,窮學生,口袋里錢不多,一般都是去蒼蠅館子打打牙祭。好吃就行了,不考慮別的。
西大附近原來有家餐廳叫“將進酒”,名氣很大。我去吃過一次,飯菜質量一般,我能記住它,完全是因為它叫“將進酒”。李白的詩,我愛讀。
“魏家涼皮”的老店在西大跟前的大學南路,這兒算是它的“龍興之地”。當年看著普普通通的一個賣涼皮的小館子,誰能想到后來竟能發展成那么大的連鎖餐飲店呢?我不愛吃涼皮,當年沒在這家店吃過飯,所以說它跟我關系也不大。
讓我念念不忘的是太白路上的一家岐山面館,主賣酸香酸香的岐山臊子面,當然也少不了岐山肉臊子夾饃,還有炒菜。我去了一般不吃面,不吃夾饃,會點他們家的回鍋肉,就沖這個來的。
我以前在淳化老家時沒吃過回鍋肉。偶爾有同學帶我在這家吃飯,點了幾個菜,其中就有回鍋肉:那么大的肥肉片子,油汪汪的。我心想,這么肥,一定膩,我可不要吃它。
同學熱情,勸我嘗嘗,拗不過,勉為其難吃了一口。我的天,咋能這么好吃啊!香得我渾身抖了一抖,趕緊多夾了兩筷子。那天我吃得滿嘴流油,米飯都吃了3碗。從此就愛上回鍋肉了,至今情有獨鐘。
我第一次吃回鍋肉是在岐山面館,就覺得這里的是最正宗的,回鍋肉就應該是這味兒。后來我去成都,吃了當地的回鍋肉,隱隱覺得,好吃是好吃,但和那家岐山面館的比,好像差那么點兒意思。可惜那家面館后來升級了,裝修上檔次了,廚師好像也換了,做出來的回鍋肉就不是那個味兒了。只能到別的菜館碰運氣,有時驚喜,有時“踩雷”。后來我畢業獨立生活了,趕緊置辦鍋灶,割上3斤肉,提了一捆蒜苗,一番整治,實現“回鍋肉自由”。
其實說來說去,我還是對“陜北王二羊肉面”感情最深。“王二”最早就是一個路邊攤,后來生意越來越好,才開始租賃店面,店面隨后越擴越大,成了一家名店。來吃飯的基本都是西北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的學生娃,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個比一個能吃。我親眼見過籃球隊的幾個人高馬大的男生在這里一人點一碗羊肉面、一份洋芋擦擦,還要再來一根燉羊蹄,嚇死個人。這要是我的娃,這么吃,我估計都養不活。
“王二”的菜品量大。洋芋擦擦盛出來就是滿滿當當小山樣的一大盤,用花椒粒和干辣椒炒得香香的,就著蒜瓣吃,很過癮。
宿舍聚餐,去“王二”比較多。一份洋芋擦擦可以幾個人分著吃,再來一份涼拌羊雜,酸辣口的,多放蒜末和香菜。一人再來一碗熱騰騰的羊肉面或者燴粉,就是一頓好飯。
常去,就跟老板娘學了幾句并不地道的陜北話。老板娘濃眉大眼,骨架也大,是個典型的陜北俊俏婆姨。20年過去,送走了多少屆學生,她竟然絲毫不見老。她家的洋芋擦擦一直那么好吃,真不容易。
今年6月份,路過“王二”,想去看看—當時剛吃過飯,就為去看看。結果遠遠看見店似乎關了,心里一緊,走近一瞧,玻璃窗上貼了一張告示:“30年老店換新址,請朝北移步300米。”
我朝北尋了過去,尋到了,不過不是300米,1000米都有了。沒關系,管它幾百米,反正在西安城里。我心里這才踏實了些。
可是一想,換新址了,其實就等于把“王二”的過往一刀斬斷了。我們當年的那個“王二”已經煙消云散了。想到這里,心里一陣悵然。
“王二”往南原來有個小店,以包飯聞名。生意奇好,一到飯點,全是來吃飯的大學生。我就曾在這里包過一個月的午飯。
小店做的是蓋澆飯,因為是包飯,做啥你吃啥。米飯敞開吃,菜嘛,全是下米飯的菜,今天是宮保雞丁,明天是紅燒茄子,后天就是爆炒豬肝,熬一大桶綠豆湯或者紫菜湯,放那兒自己舀。他們家最受歡迎的菜是魚香雞蛋,重油,使勁倒生抽,倒醋,撒白糖和胡椒面,成品后撒大量蔥花,再裝盤。這么一番操作,吃的主要是調料的味道。
在這兒吃了一個月我就不吃了—以前可是頓頓吃午飯時就要出校門往那邊走,生怕誤過飯點。關鍵是他家的飯菜真的不值得人這么緊趕慢趕,想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學生娃撲著往里進。后來經歷多了,也就明白了,你紅火并不代表你強、你棒,你只是紅火而已。李白在《將進酒》里都說了,古來圣賢還皆寂寞呢。
其實我主要還是在學校食堂吃飯。如果沒記錯,西北大學當年有4個食堂。有次我生病了,沒胃口,端個洋瓷盆去學校的大食堂吃飯,轉來轉去不知道吃啥,最后要了一碗酸湯面。說實話,那碗酸湯面是我在西北大學吃過的最好吃的一頓飯。吃得我渾身舒暢,病都好了。
那年頭兒的大學食堂,米飯又硬又糙,啥菜都一個味兒,就算有好吃的,打飯師傅勺子一抖,到碗里也沒多少了。天天吃難免膩歪,所以需要出學校到街上下館子調劑調劑。遇到好吃的小飯館,同學之間也會互相宣傳介紹。
宿舍小張的女朋友大橘子給我推薦了大學南路上的一家東北菜,讓我一定要去嘗嘗。在那里,鍋包肉和地三鮮輕而易舉地把我征服了。
大橘子問我用餐體驗如何,我實話實說:“好吃得要命!要是經濟條件允許,我都想天天去吃,頓頓去吃。”
大橘子很有成就感,又給我推薦了邊家村的一家油潑面。這家店提供整根的黃瓜,來這兒吃面的人個個拿著根黃瓜,咔嚓一口黃瓜,吸溜一口面,也是一景。
回來,大橘子又問我好吃不。我說,吃完面,筷子我一根一根都舔了;我又給碗里倒了面湯,搖了搖,連面湯都喝干凈了。大橘子一聽,捂嘴直笑。
后來大橘子和小張有矛盾,分手了,她還不忘給我推薦美食,說邊家村十字的大盤雞吃起來美得很,里面的洋芋比雞肉好吃,倒一份白皮面進去,拌一拌,醬汁一裹,香得人哇哇叫。
我受了蠱惑,準備去時,小張知道了,讓我站穩立場,不要去吃那個負心女推薦的大盤雞。我批評了小張的幼稚和狹隘,不但去了,還拉著小張一起去。小張表示堅決不去,我說:“大橘子也去呢,你去不?”小張扭捏了一下,去了。一頓大盤雞,他倆你幫我挑花椒,我給你夾面,很快沒有了隔夜仇,又和好啦。
中學同學老樊跟我關系好,我們同來西安讀書。一到周末,不是他來找我,就是我去找他。他來找我,我們多半會去附近的“德福祥”吃泡饃。點兩份牛肉泡饃,一人倆饃,慢慢掰,一邊掰一邊諞,天南海北地扯一扯,簡直太安逸了。那時候的人不玩手機,掰饃就認真掰饃,說話就認真說話,聽也認真聽。
現在回憶當年吃泡饃的情景,歷歷在目。清晰到筷子的木紋和碗邊的磕角,還有老樊眼鏡片后的多層眼皮,都仿佛就在眼前。
長安路上曾經有一家“九月餐廳”,我和老樊當年也常去。他家在當時顯得很特別,雖然是小館子,卻精致又清爽。老板氣質沉靜,年紀不大,像個知識分子。餐廳為什么叫“九月”呢?我和老樊都覺得這其中一定有故事。
“九月餐廳”做的都是家常菜,但是用心,有一道豆角紅燒肉是我們必點的。入味,燒夠時間了,但是豆角的形還在,擺了盤整整齊齊的。不像有些店,燉得亂七八糟的。
后來老樊考研、讀研,開始忙忙碌碌,我們就很少見面了。再后來,老樊去了上海,進了一家大醫院,就徹底見不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漸行漸遠。
老樊離開西安后,我一個人去“九月餐廳”吃飯,點一道豆角紅燒肉、一碗米飯就夠了。肉汁和米飯拌在一起,用勺子挖著吃。好吃是好吃,孤獨也是真孤獨。
“九月餐廳”的北面還開過“小六湯包”的分店。我和小九在這里吃過,當時我們還只是普通朋友。當時她跟我聊她的故鄉江南,我的腦子一幀一幀出圖畫。湯包是好吃的,不過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吃上。我還是第一次發現,有人吃東西也能吃得那么好看。后來這家餐廳消失了。
“九月餐廳”附近還有一個“天香樓”,裝修得古香古色的,靠近紅專路口。我剛上班時,我媽來西安看我,我帶她在這里吃飯。我媽一看菜單,說點個土豆絲吧。我對我媽說,下館子就是要點讓人膽固醇升高的菜呢。后來這家餐廳也消失了。
還有一家,好像是賣什么魚的,店名實在想不起來了。我在這家店請過一個中學同學吃飯。她在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所以就近選了這家。那頓飯吃得尷尬。雖然是老同學,但是出了社會,走上不同的路,也便沒有什么共同語言了。那頓飯后,我們再無聯系。后來這家餐廳照例也消失了。
再后來,“九月餐廳”消失了。這些我都沒有告訴老樊。
20年很快就過去了。
這時光啊,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這城市啊,也真是個變形怪物,時時刻刻都在變化。反正我那些年吃過的那些館子,或關門,或搬家,如今統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