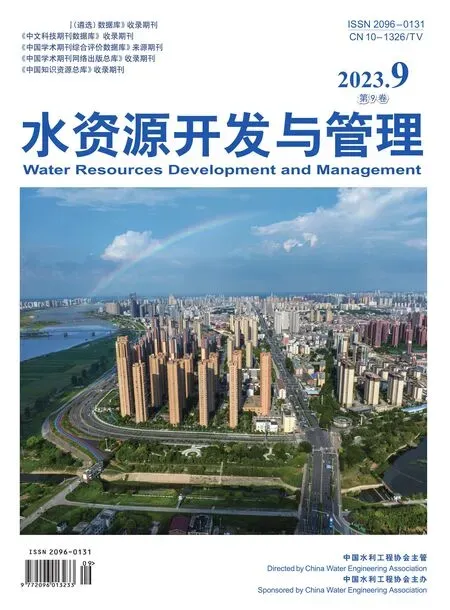龍祠水源地高濃度硫酸根離子來源分析
張芳齊
(太原理工大學(xué)建筑設(shè)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24)

1 龍祠水源地概述
1.1 水源地形成原因
龍祠水源地位于臨汾市堯都區(qū)西南13km西山山前的龍祠、晉掌村一帶,是在龍子祠泉域巖性地層、地質(zhì)構(gòu)造和地形條件共同影響下,灰?guī)r裸露區(qū)大氣降水得以入滲補給,通過巖溶水系統(tǒng)的地下徑流匯集,在向東部盆地運動過程中,受到山前大斷層的阻擋,地下水橫向受阻后便沿斷層順向運動,由于龍子祠一帶地形最低,成為東部阻水邊界的缺口,斷層的東側(cè)坡洪積物厚約35m,下部為石炭二疊系,因而下部阻水,上部部分透水,使巖溶水溢流成泉,從而形成地下水型飲用水水源地,見圖1。
泉水出露區(qū)1956—2000年多年實測流量為5.19m3/s[7],水源地于1988年投產(chǎn)使用,設(shè)計年供水量為2518.5萬m3,現(xiàn)狀實際年供水量約為2000萬m3,供水范圍為臨汾市市區(qū),用于城鎮(zhèn)生活和農(nóng)業(yè)灌溉,供水服務(wù)人口約47.5萬。
1.2 泉域水文地質(zhì)條件
1.2.1 含水巖組
泉域內(nèi)主要含水巖組有寒武—奧陶碳酸鹽巖含水巖組、石炭系碎屑巖夾碳酸鹽巖巖溶裂隙含水巖組、二疊系碎屑巖裂隙水含水巖組和第四系松散層孔隙含水層。
1.2.2 補給、徑流泄水條件
a.補給條件。碳酸鹽巖裸露區(qū)直接接受大氣降水入滲補給、石炭~二疊系碎屑巖類接受大氣降水入滲后,通過斷裂、陷落柱或順巖層傾向,向深部奧陶系巖溶水補給。
b.徑流條件。受地質(zhì)構(gòu)造及水動力條件的控制,區(qū)內(nèi)巖溶水形成了主徑流帶的運移方式[8],在向斜南端龍祠村形成最低的匯水點。主要徑流方向有:復(fù)向斜東翼灰?guī)r裸露區(qū)在降水入滲后,由北向南經(jīng)羅云山斷裂向龍子祠泉匯流;向斜西翼及北部灰?guī)r裸露區(qū)在降水入滲后自北向南經(jīng)向斜軸部的深循環(huán)后,向龍子祠泉匯集;泉域南部灰?guī)r裸露區(qū)在接受大氣降水入滲后,自南西向北東方向徑流,匯入龍祠主徑流帶,流向龍子祠泉。
c.泄水條件。泉水溢流排泄,通過羅云山斷裂的透水段以側(cè)向徑流的方式補給山前洪積扇地下水及人工開采排泄。


圖2 龍子祠泉水硫酸根離子濃度歷年變化趨勢
3 成因分析
泉水中硫酸鹽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巖溶巖系中石膏的溶解;二是煤系地層中硫和硫化物氧化生成硫酸與硫酸鹽。前者為地層沉積環(huán)境下水巖相互作用的原生產(chǎn)物,后者則是由于煤礦開采改變了硫鐵礦的賦存環(huán)境,發(fā)生的化學(xué)反應(yīng)導(dǎo)致離子溶解濃度增加。
3.1 石膏層
臨汾一帶在中奧陶世各期早期為一個小的膏鹽湖沉積區(qū)(圖3),分別在上、下馬家溝組和峰峰組底部沉積有石膏層,其原始沉積為一套澙湖相泥晶白云巖-泥質(zhì)碳酸鹽巖-石膏及硬石膏巖混合體,由于近代巖溶作用的破壞,地表及淺層部位的石膏已經(jīng)少見,常見的是溶蝕后的石膏結(jié)晶和大量層次不清的膏溶角礫巖,石膏多為層狀和似層狀,受構(gòu)造擠壓后在部分地段呈透鏡狀,同一石膏層沿走向常迅速尖滅。

圖3 中奧陶世鄂爾多斯盆地-臨汾巖相古地理圖
石膏(主要成分為CaSO4)的溶解速度是石灰?guī)r和白云巖的約5~10倍[9],不同組織結(jié)構(gòu)及巖性石膏的溶解度為57~332mg/L,比石灰?guī)r和白云巖高5~20倍,因此,夾于碳酸鹽巖中的石膏總是最先溶解,并導(dǎo)致碳酸鹽巖層的一系列破壞。
3.2 煤系地層硫鐵礦
龍子祠泉域內(nèi)分布有59座煤礦,設(shè)計原煤年生產(chǎn)能力合計4740萬t,井田面積合計574.3km2,煤礦現(xiàn)狀主要開采2~11號煤層。煤系地層中常含有較多的硫化礦物,一般含有0.3%~5%的硫,主要以黃鐵礦形式存在,約占煤含硫量的2/3,區(qū)內(nèi)特別是下組煤9號、10號、11號、12號煤多為中—高硫煤。在自然狀態(tài)下,硫化礦物一般分布在煤層和相對隔水層之中,深部地下水含氧量甚少,而且硫化物與地下水接觸機會也少,不易氧化。

由于多年的歷史欠賬不能完全實現(xiàn)所有企業(yè)礦坑水達標排放或零排放。煤礦停采后,產(chǎn)生的采空區(qū)逐步蓄積成為“地下水庫”,形成“老窯水”,它的化學(xué)成分更加復(fù)雜多變,對泉域巖溶地下水水質(zhì)構(gòu)成的潛在隱蔽危害不容忽視。
3.3 地質(zhì)結(jié)構(gòu)模式
龍子祠泉域為“單斜逆置型”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具有如下特點[10]:?地層傾向與巖溶地下水流向相反;?煤系地層處于上游、碳酸鹽巖滲漏段處于河流下游;?主體河流分散,滲漏段長度較長。大面積裸露可溶巖分布在泉域下游,“含煤體”分布在泉域上游。上游煤炭開采破壞了煤系含水層,礦坑排水及城市污水排放經(jīng)過可溶巖河谷時,產(chǎn)生滲漏,給巖溶水的污染提供了路徑。
4 來源定量分析
硫在自然界中有32S、33S、34S、36S 4種穩(wěn)定同位素,由于不同來源硫在各自特定的演化過程中形成硫同位素的分餾,因而造成了硫同位素的差別,利用這一差別,可判別它的來源。
煤中硫鐵礦是在泥炭化及成煤期,在還原環(huán)境中還原細菌(英文縮寫SRB)作用下,將海水中硫酸鹽還原成H2S,與陸相黏土中鐵反應(yīng)形成的。SRB更青睞原子半徑小的32S[11],故32S 優(yōu)先參與反應(yīng),即硫鐵礦中相對富集32S,而34S值很低,中國北方煤總硫的δ34S值平均為3.68‰[12]。有關(guān)學(xué)者對在娘子關(guān)泉域以及北方其他地方獲得的一些中奧陶系中石膏所做的測定結(jié)果δ34S值都在23‰以上[13-14]。

水樣δ34S 值測定在中國地質(zhì)調(diào)查局武漢地質(zhì)調(diào)查中心實驗室完成,δ34S值采用IsoPrime質(zhì)譜儀進行測定,δ34S值采用CDT ( Canyon Diablo Meteorite) 標準,測試精度優(yōu)于±0.1‰。




表1 龍子祠泉水中34S硫同位素測定值及占總濃度比例
5 結(jié) 論
通過上述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結(jié)論:
a.龍子祠水源地水質(zhì)中硫酸根離子濃度自20世紀80年代就呈超標狀態(tài),并有增長趨勢,超標1.2~1.8倍。
b.高濃度的硫酸根主要來源于中奧陶系的石膏層和煤系地層硫鐵礦的氧化,以及特殊的“單斜逆置型”地質(zhì)結(jié)構(gòu)。水源地水質(zhì)δ34S 值大小取決于石膏和煤系硫鐵礦來源的混合比,受煤系硫鐵礦影響大時δ34S 值就偏小。
c.中奧陶統(tǒng)石膏的溶解是硫酸根高濃度的主要原因,占比在75%以上;但煤礦開采導(dǎo)致的硫鐵礦氧化溶解卻是加劇總濃度波動變化的直接顯性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