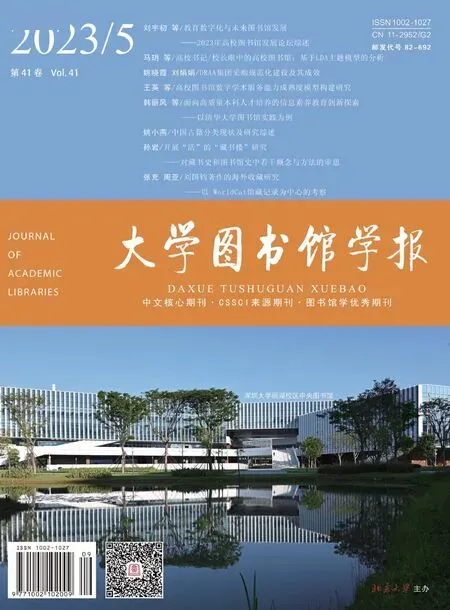中國古籍分類現狀及研究綜述
□姚小燕
古籍分類是我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大難題。從我國古籍分類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編撰分類目錄《七略》以來,雖然隨著《中經新簿》《晉元帝四部書目》《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的編制,逐步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基本次序,但從本質上講,這些都屬于書目分類,并不是獨立的、專門的古籍分類法。鮑國強曾指出,迄今為止古籍分類目錄種類繁多,古籍分類法理念眾說紛紜,比較權威的古籍分類法并非沒有,卻始終沒有出現國標層面的古籍分類法,極大地制約了古籍編目工作的標準化[1]。
那么目前國內外各古籍存藏機構使用的是何種古籍分類法,為何至今沒有產生一部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呢?筆者借助問卷調查及相關文獻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并擬從發展現狀及社會需求等角度出發,提出對于編制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的看法,敬祈方家教正。
1 國內外古籍分類現狀調研
2022年12月7日,天津師范大學古籍編目研習中心舉辦了中心成立報告會暨古籍編目專家講座,來自國內外的90余名專家、學者及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研究生線上出席了此次會議。該校研究生黎冬瑤同學向海內外參會嘉賓發放了關于古籍編目現狀的調查問卷,經過參會人員發散傳播后最終得到274份調查問卷。本研究所使用的國內外相關機構古籍分類現狀數據即來自本次調查回收的問卷。
1.1 數據分析
對所回收問卷的數據進行基本處理后,筆者共得到國內外233所機構使用的古籍分類法數據(1)本次調研后統計所得《國內外各古籍存藏機構古籍分類統計表》,讀者如有需求可發郵件向作者索取。。據統計,呼和浩特市圖書館等31所機構使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類分古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等107所機構使用“四部分類法”類分古籍。北京大學圖書館等6所機構使用的是十進分類法,復旦大學圖書館等12所機構使用的是自編分類法,中國國家圖書館等13所機構使用的是劉國鈞《中文普通線裝書分類表》等其他分類法。此外,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等27所機構同時使用了兩種分類法,福建省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同時使用了三種分類法,還有33所機構未對所藏古籍進行分類。
如圖1所示,總體來看,“四部分類法”是國內外各機構使用最多的古籍分類法,也有一部分圖書館在20世紀70年代改用了《中圖法》。其他圖書館則或使用民國時期編制的圖書分類法,如劉國鈞《中文普通線裝書分類表》、皮高品《中國十進分類法》、杜定友《世界圖書分類法》等,或自編古籍分類法,如《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分類法》《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等,情況頗為復雜。

圖1 國內外被調查古籍存藏機構使用的古籍分類法的現狀
1.2 現狀成因分析
鑒于古籍的形制、數量和保存問題,館藏古籍的分類體系往往一經排架分類便不會輕易更改。因此,現在不少圖書館仍在沿用民國以來所使用的古籍分類方式。筆者通過實地考察及文獻調研后,認為造成目前古籍分類紛繁復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
1.2.1 “四部分類法”是編目人員最為熟知的古籍分類法
清代以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權威地位,使之成為使用最為廣泛、也最為大家熟知的古籍分類法。盡管民國時期誕生了不少借鑒西方圖書分類理論和技術的圖書分類方法,但“四部分類法”仍然是使用最為便捷,也是最適合微調的古籍分類法。正如劉國鈞所言:“此種辦法之優點,即故能不需處處學習特別之分類法,故能有整齊統一之效,而亦可省翻閱之勞。我國用分類法目錄如許之久,而不覺其缺點者,習慣亦其一因[2]。”因此不少圖書館截至今日,仍然在沿用“四部分類法”類分古籍。
1.2.2 民國時期誕生了一些可供使用的圖書分類法
民國時期,一些目錄學、圖書館學專家所研制的較為成熟的圖書分類方法,在圖書館界廣為流行。這些分類法大多受到《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影響,按照學科類分中國古籍,為當時各館古籍分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圖書館使用。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最初采用“四部分類法”類分古籍,1934年皮高品編制的《中國十進分類法》出版后,便改用了皮氏分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3]。又如寧波市立圖書館和舊溫屬聯立籀園圖書館(即今溫州市圖書館)在1930年分別改用王云五《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杜定友《世界圖書分類法》后,也一直沿用至今[4]。
此外,也有一些館藏較為豐富的大型公共圖書館和高校圖書館,以該館館藏為主要分類對象,自行編制了古籍分類法。如清華大學圖書館曾在不同時期分別編制了戴志騫分類法、查修《杜威書目十進法補編》和施廷鏞《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分類法》(也稱為八大類法)[5]。
1.2.3 《中圖法》分類理念新穎、技術先進
《中圖法》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由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公布的《中小型圖書館分類表草案》。后來在中央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主持下,成立了圖書分類法編輯組,并于1975年10月由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圖法》第一版。《中圖法》采用混合編碼、復分、仿分、參見、注釋等分類技術,將古今中外圖書分為22個基本大類,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和推廣。因此一些圖書館便嘗試利用《中圖法》來類分古籍。
需要指出的是各館選擇古籍分類法的具體原因是十分復雜的,這與民國時期圖書館學專家對古籍分類的探索、該館古籍存藏體系的演變、編目人員的專業素質高低、館領導對古籍分類的重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桂質柏曾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分類大全》序言中寫道:“本館創辦以來已二十余年,于茲庋藏書籍亦近十四萬余冊。歷史不可謂不久,藏書亦不可謂不豐,惟對于圖書分類向取中西之分,劃然為兩,寖成習慣,故本館之中日文圖書分類法乃沿東南大學之舊,以四庫為本,而另增新部仿杜威之十進分類法,但此分類法創始之時,圖書不多亦未詳細分析,嗣后圖書漸增,自二十一年改組后,羅家倫校長蒞任,尤極注意圖書館之搜集,原有分類號碼不敷應用,余承乏此間勉于困難之中,率同館員根據原分類法再為分析,以容納各項圖書,幸賴學校當局之扶植,同人之努力,是以有本書之成也[6]。”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南京大學圖書館至今仍有一部分古籍使用的是桂質柏分類法。而南京大學圖書館還曾在劉國鈞、施廷鏞在任期間分別使用過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和施廷鏞八大類法,由此也就造成了該館目前使用3種古籍分類法的現狀。
概言之,一方面由于統一的、作為標準的古籍分類法的缺位,各館只能根據館藏的實際情況選用或自編較為合適的古籍分類方式,并隨著西學的輸入、書籍的增加、館員的轉聘等進行調整或改用他法;另一方面各館結合實際的館藏數量和建設需求而選用現成的四部分類法或《中圖法》來類分古籍,也就導致了目前國內外古籍分類五花八門、各行其是的現狀。
2 20世紀以來古籍分類研究概況
近代以來在國內圖書館館藏西學書籍劇增,而傳統的分類法不能滿足分類編目要求的情況下,四部分類法的權威地位不復存在。受到《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影響,國內古籍的分類方式也隨之產生巨大轉變。為了更全面地了解20世紀以來的古籍分類研究現狀,筆者在中國知網、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等數據庫中以“古籍分類”“古代圖書分類”“中文書目分類”等作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后,發現對于古籍分類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其一為20世紀20、30年代,其二為20世紀80年代至今。
2.1 20世紀20、30年代的古籍分類研究
自宣統二年(1910年)孫毓修撰文介紹《杜威十進分類法》以來,國內受到西方圖書分類理論熏陶,又具有中國傳統目錄學知識背景的圖書館學專家、學者逐漸開始關注中國古籍與西式圖書的分類問題,由此掀起當時古籍分類的研究熱潮。但這一時期學界并未使用“古籍分類”一詞進行單獨討論,而大多使用“中文書籍分類”“中國圖書分類”“舊書分類”等詞探討適用于中國古籍的分類方式,并試圖以新舊圖書統一分類為前提來研制圖書分類法。
最早借鑒西方圖書分類理論與技術編制圖書分類法的是沈祖榮和胡慶生。二人在杜威分類體系的影響下研制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法《中國書目十類法》,將古今中外圖書統一分為10類,打破了經、史、子、集的傳統分類體系,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開始就中國古籍分類該何去何從進行探討,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
(1)梳理及分析中國古籍的分類歷程,如劉國鈞《四庫分類法之研究》[7]、蔣復璁《中國圖書分類問題之商榷(附表)》[8]、蔣元卿《中國圖書分類的起源》[9]等以及一些目錄學經典著作如蔣元卿《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10]、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11]等。這些研究深入探討了我國古代書目分類的發展變遷、各書目分類的具體特點、四部分類法的不足等,實現了對我國傳統古籍分類的歷史梳理和理論闡釋,有助于學界進一步開展統一的適用于古籍的圖書分類法的研究。
(2)專注于某一類古籍的分類研究,如杜定友《中國史地圖書分類商榷》[12]、王著寰《佛學分類法芻議》[13]、傅振倫《中國史籍分類之沿革及其得失》[14]等。這些研究或旨在梳理某一類古籍在歷史上的分類概況,或主張利用《杜威十進分類法》來類分某一專題的古籍。
(3)探討傳統古籍與西式新書該如何分類。如吳敬軒《對于中文舊書分類的感想》[15]、查修《中文書籍分類法商榷》[16]、傅振倫《編制中文書目之管見》[17]等。他們基本上持有兩種意見,其一主張根據書籍的內容和體例,將傳統古籍與西式新書各自劃分分類標準;其二主張用西方先進的圖書分類理論和技術,從實用角度來統一劃分新舊書籍(或修改四部法以容納西式新書,或增補杜威法以容納中國古籍)。
正是基于以上對中國古籍分類的思考,學者們編制了不少圖書分類法和圖書館藏書目錄,開啟了古籍分類研究的黃金時代。而自20世紀30年代后期開始,國內局勢因日寇的全面侵華而日趨動蕩,古籍分類的研究工作遂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滯之中。
2.2 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古籍分類研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圖書分類法的編制工作。在中央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主持下,北京圖書館(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牽頭召集有關專家、學者成立了圖書分類法編輯組,集體編制了《中圖法》。由于當時社會各界旨在容納新書而不改造體系[18],因此沒有對古籍的分類情況單獨討論。
直到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的編纂提上日程,學者們開始重新關注古籍的分類問題。1979年,楊殿珣首次使用“古籍分類”一詞,探討古籍分類的沿革及當時對四部分類法的修訂[19]。廖延唐進一步總結新分類法類分古籍的優點和需要解決的問題[20],由此學界針對古籍分類應該沿用“四部分類法”還是《中圖法》進行了廣泛討論。而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提出,亦使得古籍分類的相關問題再次引起學界關注。結合相關文獻的調研,筆者歸納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古籍分類研究的5個主要方面。
2.2.1 古籍分類法的選擇與編制研究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合作編寫的《圖書館古籍編目》[21]和廖延唐、曹之合撰的《圖書館古籍整理》[22]率先比較分析了使用“四部分類法”和《中圖法》類分古籍應該注意的問題,之后學者們就古籍分類法的選擇與編制各抒己見。
一部分學者主張使用《中圖法》類分古籍。他們認為《中圖法》符合現代人的檢索方式,能夠實現古今圖書的統一分類,從思想性、實用性和科學性角度而言都優于四部分類法[23—28],還研究了利用《中圖法》類分經、史、子、集四部古籍的可行方式[29—32]。
一部分學者主張以四部分類法為基礎編制古籍分類法。他們認為使用四部法能反映當時社會學術思想的本來面貌,體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傳統,且具有可行性[33—37]。而之所以不贊成使用《中圖法》類分古籍,則主要是因為《中圖法》受到以《杜威十進分類法》為代表的西方等級分類體系的影響,無法彰顯古籍本身的分類體系[38]。
還有一部分學者提出其他類分古籍的建議與看法,如嚴代荃建議采用雙軌制,即館藏古籍按經、史、子、集編目,同時又按照學科分類的思想加以改進[39]。崔建英認為應該新編一部中國古籍總結性目錄作為古籍分類法[40]。吳國繁則建議直接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來類分古籍[41]。
在相關研究中,最早對編制新的古籍分類法提出初步構想的是姚伯岳。1993年,他對古籍分類的歷史走向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設想了編制《中國古籍分類法》的基本思路[42]。在此之后,林基鴻、孫榮和陳愛華、姚江河、韓錫鐸等人均各自提出編制《中國古籍分類法》的有關設想。他們或宏觀論述《中國古籍分類法》的傳統與技術[43],或微觀闡明具體的編制思路[44—45]、分類表的制定細則[46]等,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古籍分類法的編制進程。
2.2.2 古籍分類的歷史源流、概念辨析等理論研究
在20世紀80、90年代這場有關古籍分類該何去何從的“學術大討論”中,學者們還從理論角度探討了古籍分類的歷史源流、概念辨析、思想基礎等。如王國強[47]、羅平和趙薇[48]、鄒振環[49]、柳申林[50]、Liu[51]等由古及今地梳理了我國圖書分類法的嬗變軌跡,探討和分析了古籍分類的思想演變過程及原因。黃建國[52—53]、張小慰[54]、門庭[55]、王勇[56]等人重點研究了四部分類法的形成過程、指導思想、歷史成因等。柯平[57]、李嚴[58]、劉延章[59]等人辨析學術分類、書目分類和圖書分類三者之間的關系,指出學術分類與圖書分類是書目分類的基礎。左玉河[60]、袁曦臨[61]等人著眼于近代以來的學術轉型,研究古籍分類體系演變的規律和原因。
此外,亦有一些專著如劉簡所著的《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62]、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現為信息管理系)所編寫的《圖書分類》[63]、程千帆、徐有富合撰《校讎廣義·目錄編》[64]等系統梳理了古代圖書分類法的演變沿革。袁曦臨也在《學科的迷思》一書中述及古代典籍的學術源流及近代以來所面臨的分類困境等[65]。
2.2.3 傳統書目分類研究
在目錄學研究領域,有不少學者對書目分類的有關內容進行梳理和探討,主要涉及《七略》《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書目答問》等。如胡安蓮、鄒賀分別揭示《七略》首創圖書六分法的意義[66]和劉歆編制《七略》的原因[67]。薛璞和景浩[68]、侯延香[69]、王潔[70]等人針對《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沿革、思想基礎和歷史作用等進行論述。程磊[71]、周汝英[72]、門庭[73]等人著重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體例、分類思想、學術價值及存在的問題。杜澤遜具體指出《書目答問》在“古史”“地理”“譜錄”“別集”等類目方面設置不太合理[74]。此外,還有學者對詩文評類[75]、政書類[76—77]、儒家類[78]、類書類[79]以及古代戲曲目錄[80]等的歷史發展和演變規律展開論述。
2.2.4 對現當代各種古籍分類法的評判研究
民國以來誕生了一批相對成熟的圖書分類法,有學者從古籍的分類角度對其進行評判和分析研究。如黃建年、胡唐明、侯漢清等人對劉國鈞《中文普通線裝書分類表》進行研究,并揭示其對于線裝古籍編目的適用性及其在圖書館學與目錄學中的重要價值[81]。王小蘋[82]、周余姣[83]撰文分析裘開明圖書分類學思想的源流與編纂《漢和圖書分類法》的時代背景、分類思想、編纂體例等。戴建國[84]、李寒光[85]等人基于《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善本古籍書目》對“四部分類法”予以修訂。以及劉英潔[86]、韓春平[87]等人綜合評析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制定的《漢文古籍分類表》,并針對其所存在的子目遺漏、立類粗略和選詞不當等問題提出解決對策。
2.2.5 其他相關研究
在古籍分類的數字化研究方面,鄭貴宇[88]、秦淑貞[89]、劉劼[90]等建議可以結合《中圖法》和《四庫法》類分古籍從而實現古籍的計算機編目。在少數民族古籍的分類方面,有的學者建議采用吳肅民編制的民族古籍分類法[91],有的學者建議使用《中圖法》[92],還有學者建議借鑒“四部分類法”[93—94]。中醫古籍的分類方面,陳星和馬程功[95]、孟凡紅和尚文玲[96]等人梳理了中醫古籍分類體系的流變。蔡永敏、孫大鵬結合古代醫籍的分類結果構建了較為合理的中醫古籍知識分類體系[97]。劉培生、張偉娜等人則重點分析了《中醫古籍分類表》的研制及應用[98]。
3 為何至今沒有誕生一部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
綜合研究和分析百余年來有關中國古籍分類的研究進展,發現學者們盡管較好地完成了古籍分類的歷史梳理和微觀闡釋,也研制出一些較為成熟的圖書分類法。但從古籍分類法的統一化角度而言,卻仍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經過思考后筆者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
3.1 理論層面缺乏深入思考
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學界針對古籍分類開展的研究工作,旨在引起當時社會各界對圖書分類法研究的重視,而沒有深入到理論研究的內核。因此,在“四部分類法”無法類分全部書籍的迫切形勢下,實用性是當時圖書分類最為重要的評估標準之一。所謂“夫圖書分類者,明義為先,辨體為次,而以致用為歸宿”[99]。而20世紀80、90年代以來,雖然學界曾對古籍的分類問題進行較為廣泛的探討,并編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和《全國古籍普查平臺分類表》等古籍分類表。但這些分類表也是從實踐角度出發,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而編制的僅供臨時使用的古籍分類表,并非正式的古籍分類法。當時學者對于古籍分類的討論也僅僅停留在分類法的選擇、梳理等方面,沒有深入理論層面去探討古籍分類法的類例體系與編制原理等。
3.2 學界之間缺乏通力合作
欲編一完善之分類法,當先徹底改革原有之中籍分類使舊學者無所借口,但徹底改革非個人所可為,應通力合作、群策群力,乃克有濟[8]。民國時期雖然我國圖書館學專家、學者以《杜威十進分類法》為藍本研制了數十種圖書分類法,但由于當時學界對于圖書分類技術、中文古籍的歸置情況等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因此學者們在編制圖書分類法時往往各自為政,沒能合力解決我國古籍的分類問題。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又陷入人為制造的“非《中圖法》即《四庫法》”的邏輯困境[42],未能客觀、冷靜分析古籍分類現狀,攜手共商古籍分類法編制的未來,也就間接影響了中國古籍分類法的編制。
3.3 偏向于新舊書籍統一分類
“新舊并行制,窒礙殊多,而統一制則較為便利”[2],這幾乎是民國時期圖書館界的研究共識。因此當時編制的圖書分類法多以新舊書籍統一分類為前提,試圖將中國傳統古籍融入西方學科分類體系。事實上,利用西方學科分類體系來類分中國古籍存在很多弊病,既無法彰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古代分類傳統,也有牽強附會,“以中國學術強就西方學理之‘范’”之嫌。正如傅榮賢所言:“在‘學’或‘學術’的意義上重組傳統典籍和傳統知識,固然有助于中西對話,并成為傳統學術現代化的重要路徑;然而‘學’或‘學術’理念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產物,以此為據分類傳統典籍和重建傳統知識體系,難免‘據西論中’‘以今律古’[100]。”這也同樣解釋了為什么在1975年《中圖法》編制成功之后,卻沒有從國家層面成為統一的古籍分類標準。
4 編制一部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仍有必要
編制一部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是新時代開展古籍編目工作的重要內容。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每一次大型古籍編目工作的展開,都會引發業界、學界對古籍分類問題的全國性討論。如果沒有一部統一的古籍分類法,古籍編目工作將需要不斷耗費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探討和研究古籍分類問題。尤其對于很多中小型圖書館而言,大部分館藏古籍被隨意堆放,沒有進行分類整理工作,而這正是目前亟須推進和完善的。此外,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而言,正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實現了對古籍的統一分類才能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古籍的內容與性質,理解學術的傳承與嬗變,這是新時代進行古籍傳承性保護的題中應有之義。更為重要的是,在當今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未來實現對古籍書目數據庫的分類檢索也需要這樣一部統一的中國古籍分類法。只有古籍書目數據庫具備部次甲乙、部類別居的作用,才能滿足讀者“即類求書,因書求學”的檢索需求。而古籍分類法的統一也將為今后各種古籍目錄的編制、書目數據庫的建設和古籍資源的共建共享等帶來相應的便利。
據筆者調查,1993年與2004年,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曾各自立項研究中國古籍分類法。遺憾的是,在編制成功后都沒有進行下一步的系統完善和宣傳推進。事到如今,重新編制一部新的中國古籍分類法,雖然較難改變目前各機構的古籍分類現狀,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部統一的古籍分類法。在當下社會大力推動古籍保護事業的時代背景下[101—102],古籍存藏現狀已基本摸清的現實前提下,從國家層面組織專家合力編纂一部統一的具有時代意義、實踐意義和指導意義的中國古籍分類法,以作為今后統一古籍分類方式的重要依據,無疑仍是我們作為新一代古籍保護工作者應該承擔的歷史使命,也是我們不可推卸、不容推卸的時代重任。
致謝:感謝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黎冬瑤為本文的撰寫提供初始問卷調研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