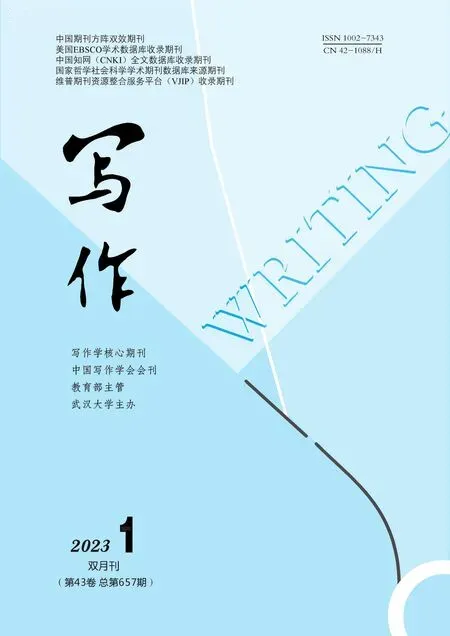《洛希爾的提琴》與契訶夫的人生密碼
周予恬
偉大的“短篇小說之王”契訶夫一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之作,但鮮為人知的《洛希爾的提琴》卻是我極其鐘愛的一篇,我覺得也是最能表達契訶夫對人生感悟的一篇。
《洛希爾的提琴》寫于1894年,此時契訶夫已進入他的“成熟的晚期創作”①童道明在《契訶夫的小說創作》中寫道:“1890年以后契訶夫創作走向成熟”,見[俄]契訶夫:《契訶夫小說全集》第1卷“代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頁。:1892年他寫下了震驚世界的《第六病室》,表達了對俄羅斯社會的深刻洞察,同時也發展了一種創作方式,即隱喻和象征手法的運用。這間充滿病態和絕望的“第六病室”,正是病入膏肓的俄羅斯社會的整體隱喻。而稍后寫作的《洛希爾的提琴》②《洛希爾的提琴》最初發表在《俄羅斯新聞》1894年2月6日,收錄于[俄]契訶夫:《契訶夫小說全集》第9卷,汝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212頁。以下《洛希爾的提琴》引文皆出自該書,不再逐一注明。,將這種手法運用得更為嫻熟而不動聲色,在一種契訶夫式的日常細節的敘寫中,表達的是契訶夫的人生觀。通過細讀這篇小說,分析其中幾個關鍵的情節和物象,我們可以解鎖這一人生密碼。
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亞科甫,又名青銅,他是一個待人刻薄、內心充滿怨恨的人。他的主業是制作棺材,棺材是為死人準備的,是要埋到地底下的,它代表的就是一種“損失”——死亡首先是一種損失,而棺材更是這種損失的具體表征。亞科甫幾十年不間斷地做棺材,可以說,他一生都在與“損失”打交道。這也與小說塑造的角色形象相對應。我們看到在亞科甫作為制棺人的時候,他總是在抱怨和不滿。小說一開始就說明他所住的小城鎮不足以讓他這個職業發達,因為“住在這個小城里的幾乎只有老頭子,這些老頭子卻難得死掉,簡直惹人氣惱。醫院里和監牢里需要的棺材也很少。一句話,生意壞透了”。而第二次講述他的不滿時就更加負面,他幾乎是盼著人死,還得死在城里,“警官害癆病,病了兩年,亞科甫焦急地盼著他死,可是警官動身到省城去就醫,不料就死在那兒了。這又是損失,至少也有十個盧布,因為那口棺材一定很貴,而且蓋上錦緞。”諸如此類的關于損失的表達比比皆是。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他的妻子瑪爾法去世之前,亞科甫完全被“棺材”所籠罩,不論是對自己的妻子,還是拉琴的同伴,他都極其刻薄,甚至虐待他們。但小說并不止于外在,而是細膩地揭示了這一兇狠外表下內心的痛苦和無望,“不管你往哪兒轉,到處都只有損失,別的什么都沒有。”小說顯示出一種頹廢、不耐煩、毫無希望的氛圍,甚至與之相對的“提琴”的意象都被籠罩在了其陰影之下。
但這個制棺人還有一個業余特長:拉提琴。“提琴”的象征顯然是與“棺材”相對的。提琴作為樂器,總是和音樂聯系在一起,而且作者在一開篇就給它定了性:亞科甫通常是會去婚禮上拉琴的,提琴所對應的婚禮與棺材所對應的葬禮形成一個鮮明的反差。如果棺材象征損失,那么婚禮上的提琴就代表了一種希望與獲得(亞科甫在婚禮上的收入也是一種獲得)。提琴具體的象征意義也許不如棺材那么明顯,但其總體來說是更加美好,富有希望,可以給人慰藉的。具體表現在亞科甫被損失攪擾地心神不寧時,“他就觸動琴弦,提琴就在黑暗里發出聲音,他心里才覺得輕松一點。”或許提琴就代表著生活中除開遺憾和損失以外那些容易讓人忽略卻真實存在的美好。在小說前半部分,提琴出現的頻率雖然并不高,或許在亞科甫生活在一堆棺材中時,他覺得提琴所帶來的慰藉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他離開他狹小的、布滿棺材的房子里時,才發現與提琴相聯系的另一種生活才是更好的。
這一轉折發生在亞科甫的妻子馬爾法得病去世的過程中。當妻子小聲喊出“我要死了”的時候,亞科甫突然意識到,“他這一輩子似乎從沒跟她親熱過一次,從沒疼過她,也沒有想過給她買一塊頭巾……卻光是對她叫嚷,為了損失而罵她,捏著拳頭向她撲過去……。”他帶著她去看病,等待她走向死亡,埋葬她,這個看來鐵石心腸的人終于感到“非常難受”,“他不明白事情怎么會弄到這一步,……為什么人們總是妨礙彼此的生活呢?要知道,這造成多大的損失!多么可怕的損失呀!要是沒有憎恨和惡意,人們彼此之間就會得到很大的好處了。”他終于醒悟,他這一生最大的損失不是金錢上的,而是心中的憎恨和惡意!
亞科甫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他也將不久于人世,此時唯有提琴,這象征了生命美好一面的提琴,讓他一看見“心就揪緊,他舍不得死了”。“他一面想他那白白糟蹋掉、充滿損失的一生,一面拉那把提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拉什么曲子,可是曲調悲涼而動人。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流下來。他想得越深,提琴的音調也就越悲涼。”
他對人生的全部醒悟與悔改,體現在臨終前將這把貴重的好琴,送給了他一直欺負的猶太樂手洛希爾。這象征著他徹底放下了憎恨,而想要將生與愛的希望寄托在另一個人身上吧。這也是小說命名為《洛希爾的提琴》的深意所在。
整篇小說,從棺材—損失開始,漸漸地,提琴—愛與希望出現的頻率逐漸增大,文章的后半部分幾乎沒有出現棺材,這非常形象地展現了亞科甫的內心轉變。同時亞科甫對于希望發現得實在太晚,導致有可能實現更好生活的希望變成了遺憾,也帶來了一種無奈。這正是典型的契訶夫式情調,但不是絕望:對于生之愛與希望,作者一直沒有放棄,只是這希望里,也含著太多的痛苦。也許,這就是契訶夫想要傳達給我們的人生密碼:人生充滿損失和痛苦,但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轉向善良和愛,因為最大的損失就是善良和愛的缺乏。這素樸但深刻的人生洞察,甚至亞科甫整個的一生,都濃縮在提琴和棺材兩個鮮明的意象中,展現出契訶夫短篇小說世界獨特而雋永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