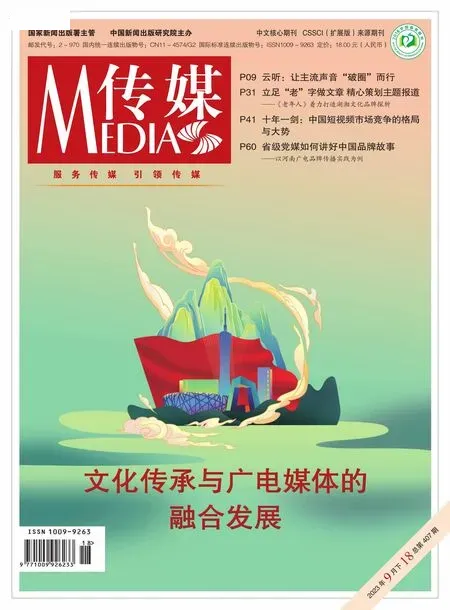構建與嬗變:國產兒童電影中兒童銀幕形象的更迭研究
文/范小玲 王艷芝
兒童電影是一種電影題材,也是一種電影類型,兒童電影中的兒童形象作為電影藝術表現的重要對象與核心,其角色塑造與表現手法,在不同的時期體現出富有特色的藝術形態,也映襯出時代的烙印。
隨著時代的變化,國產兒童電影中兒童銀幕傳播形象不斷更迭,成為特定時代的一種記憶。從時間軸線來看,兒童電影整體朝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兒童銀幕形象從較為單一的色彩演變為“五顏六色”,兒童銀幕形象塑造與呈現,在不同時期有著鮮明的特征,歸納起來看又帶有明顯的共性。
一、作為底層苦難記憶的見證者:社會道德教化與價值引領
國產電影真正將兒童作為主要銀幕形象表現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確立了“彰顯兒童本位、塑造兒童經典”的創作觀。隨著社會追求個性解放、人格獨立、自由、平等、博愛等新思想的涌現,兒童作為獨立的生命體,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由家庭本位的附屬且被忽視的對象,發展為“兒童本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最痛恨舊時代、舊傳統對少年兒童的壓榨與傷害,在作品中疾呼“救救孩子”,彰顯了其對兒童的重視與期望。
由此,從文學到電影出現了一批把兒童作為主要表現對象的作品,塑造了多種兒童藝術形象。1922年,由上海影戲公司拍攝的《頑童》成為中國兒童電影的萌芽。“《頑童》是一部無聲的黑白短片,表現一個6歲的孩子在花園里玩耍的片段。有情節,由演員扮演,表現兒童情趣,是有故事色彩的影片。從兒童故事片的角度看,《頑童》算是中國第一部兒童電影短故事片”。

圖1 電影《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
中國電影從起步之初就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實現教化社會的目的,以寫實主義影像風格揭示城市底層流浪兒童生活之艱辛,電影中的兒童形象大多是苦難社會的受害者。他們大多生來不幸,沒有任何選擇地被迫生活在社會底層。兒童電影通過真實刻畫孩子們的生活境遇與艱辛,展示的是當時悲慘的社會圖景。
1923年,明星公司出品了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第一部長故事片《孤兒救祖記》,這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兒童片。電影不僅再次將焦點放到兒童身上,而且塑造了余璞單純、善良的典型形象,為同時期兒童銀幕形象塑造奠定了整體基調。余璞一出生就被迫失去父愛,被人排斥,艱難地生活著。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下,余璞是不被人接受的苦命孩子,但是他最后挺身而出救下祖父,展現的是一個可憐兒童經歷苦難后的成長。電影觸及社會實際,揭示當時的社會矛盾,將新思想與傳奇故事結合起來,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內涵,最后三代人圓滿結局也起到了道德宣教的作用。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苦兒弱女》(1924年)描述了小慧賣身葬母,有容賣身還債,孩子們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展現了黑暗社會中殘喘生存的孩童所經歷的磨難。張石川導演的《好哥哥》(1925年)表現了在社會動蕩背景下,作為孤兒的大寶背著二寶受苦受難的故事,電影首次塑造流浪兒的形象,是當時紛亂社會的真實寫照,表達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控訴。另外,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電影《小朋友》(1926年)塑造了流浪兒唐小棠的電影形象,他被叔父遺棄,后被喬氏夫婦為還賭債賣給劇團被迫賣藝,揭露了當時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傷害。之后由蔡楚生導演的《迷途的羔羊》(1936年)延續了這類受難者兒童形象,影片成功塑造了小三子這位孤兒形象。小三子失去了父母,被收養又遭拋棄,流浪成為他的宿命,揭露對舊社會制度的強烈不滿。
電影《三毛流浪記》(1949年)根據張樂平創作的同名漫畫改編,通過孤兒三毛在舊上海的悲慘遭遇與苦難掙扎,展現了舊社會廣大城市底層兒童的不幸命運。電影塑造了三毛倔強、正直、機智活潑的形象。三毛雖無衣無食,但不貪戀富貴,雖到處碰壁,但不灰心喪氣,他不向黑惡勢力低頭,頑強地生活著。電影拍攝跨越上海解放前后,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公映的國產故事片,關注度與影響力極高。導演趙明、嚴恭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拍攝這部電影,用喜劇的風格演繹悲劇的人生,用喜劇作為揭露黑暗、針砭社會落后現象的有力武器,讓觀眾含著眼淚笑。三毛富有特點的人物造型以及從社會現實中提煉的行為動作,成為載入史冊的經典銀幕形象。
電影工作者接連塑造出兒童電影中最觸動人心的流浪兒、孤兒等兒童形象群體,成為最能體現社會底層的形象。這些苦難社會的受害者除了成為藝術典型之外,還承擔著教化社會的作用,也成為兒童銀幕形象的最初形態。

圖2 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
二、作為肩負革命重任的小英雄:主流意識形態個性化表達
新中國成立后,國內迎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十七年時期”的電影描寫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成為當時的主要題材之一。兒童電影順應主流意識形態,塑造了一系列小英雄形象。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不僅表現兒童自身的悲慘遭遇,還展現了關于兒童在戰爭危難下的成長與變化。這類題材中的兒童形象年齡大小不同,身份不一,但他們都是戰爭背景下肩負重任的小英雄。這些小英雄的藝術形象或來自真實事件中的真實人物,或通過藝術創作形成的人物形象,都十分典型生動,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石揮導演的《雞毛信》(1954年)中,小海娃經歷重重磨難,最終成功地將雞毛信送到了八路軍手里。電影塑造了抗戰背景下兒童電影中第一個有血有肉的小英雄形象。電影對小海娃心理活動的刻畫,既豐富了人物形象,也增加了戲劇張力。“影片根據兒童特有的思想感情、語言行為刻畫人物,從內容到形式都富有兒童情趣,淺顯易懂,易為小觀眾接受。片中扮演小主人公的蔡元元,將海娃的機靈勇敢塑造得十分生動。繼三毛之后,海娃成為中國少年兒童心目中的又一難以忘懷的形象。”
這個時期有一批兒童電影突出地塑造了許多肩負革命重擔“小英雄”形象。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小兵張嘎》(1963年)作為極具歷史意義的兒童影片,成為久演不衰的經典作品,“嘎子”這一兒童形象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少年英雄。影片中的“嘎子”雖然是一名抗日小英雄,但并沒有因此被神化。影片通過大量的細節塑造人物,分別展現了在敵我斗爭中嘎子經歷的一系列波折,穿插“三次咬人,四次落淚”等經典情節,最后擺脫危險成長為小英雄,電影將嘎子這個形象真實生動地表現出來,人物形象也比較豐滿。
說到兒童形象不得不提《閃閃的紅星》(1974年),這是“十七年”后到改革開放初,這個階段較有影響力的一部電影。電影塑造了“潘冬子”這個家喻戶曉的兒童人物形象。帶著滿腔仇恨的潘冬子“一夜長大”,他懷揣爸爸留下的紅星,肩負起游擊隊交給的革命任務:籌鹽、搞情報、破壞搜山計劃,最后成長為一名紅軍戰士。很顯然,電影兒童形象的塑造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
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大多與戰爭題材結合,這些影片塑造的兒童形象多是肩負重擔的小英雄,他們在戰爭的環境中歷練成長,展現了兒童敢于抗爭的精神,具有一定的歷史教育意義,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圖3 電影《我的九月》中的安建軍
三、作為“叛逆者”,在尋求自我中成長:時代特征的彰顯與濃縮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的成立,兒童電影節的舉辦以及中外電影交流的日益增多,為國產兒童電影生產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在寬松的環境下,人們的主體意識開始復蘇,兒童銀幕形象由原來集體主義基調下產生的小英雄形象逐漸轉化成了關注個體命運,他們找尋自我突破。電影表達了他們從依賴到獨立,從懵懂躁動到身心成長的歷程。
電影《蘇小三》(1981年),塑造了抗戰時期,在江南水鄉一個叫蘇小三的孤兒不甘束縛從雜技班逃離,在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電影賦予蘇小三能變魔術會耍雜技的技能,這樣不僅增加電影娛樂性、觀賞性,也使得人物的行為以及情節發展具有合理性。
電影《大虎》(1981年)刻畫了調皮、頑劣的李大虎在陳娟老師耐心細致地教育下,成為愛學習、守紀律、敢于向壞人壞事做斗爭的好孩子。電影《候補隊員》(1983年)的主角劉可子是小學四年級學生,他生性好動,喜愛武術,自稱“姿三四郎”,學習成績不好,又不守紀律,進不了校武術隊。后來,在黃教練的悉心教導和幫助下,成為一名正式隊員。電影由孩子身上體現出的問題,引起觀眾對學校、社會、家庭教育的反思。《扶我上戰馬的人》(1983年)中塑造以狗娃領頭的人稱“八大金剛”的野娃娃們,為實現騎上高頭大馬的愿望,由原來的“野”孩子,而轉化為認真讀書,積極上進的好孩子。
《多夢時節》(1988年)中小主人公羅菲剛步入青春朦朧期,陷入少女的遐思與幻想。電影對她的個性、理想進行了細致的刻畫,尤其十分到位地把握了她的心理特征。電影片頭電子音樂如夢如幻、朦朦朧朧的氣氛,奠定電影基調與風格。象征意味鮮明,掛滿鳥籠子的大樹下,羅菲與夢中老人的對話,揭示出羅菲精神世界、生活狀態以及成長的煩惱。《霹靂貝貝》(1988年)是第一部國產兒童科幻片,手上帶電的小男孩貝貝與眾不同,生來具有“超能力”。貝貝欲擺脫孤獨、尋求友愛和理解,甘愿放棄“神奇力量”,渴望能夠融入集體,與家人和小朋友能夠親密接觸。
電影《我的九月》(1990年)貼近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電影以北京亞運會到來為背景,表現了生活在北京普通家庭的小學生安建軍從膽小害羞到自強獨立的成長變化。安建軍不善言辭,被人稱為“傻子”。電影通過發生在他身邊的事情,折射出兒童性格的差異,提出家庭和社會對孩子成長影響的深層思考。
另外,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也面臨著新的社會問題,其中涉及兒童以及青少年的問題也有許多,如犯罪,早戀等。此時的少年兒童在找尋自我中更多地充當“叛逆者”的角色,試圖在與社會的對抗中確認自己的地位,表達自己的思想,電影不僅將這個時期少年兒童的個性與訴求進行了細致的刻畫,同時也真實自然地表現了他們的心理特征,使得其銀幕形象更加多維立體,電影也具有了更加深遠的社會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兒童電影中的兒童形象逐步體現了強烈的時代性、明顯的主體意識和鮮明的個性特征。他們或是個性迥異,堅持自我;或是嘗試突破,隨性不羈。在塑造這些兒童銀幕形象時,電影既做到貼合時代背景,也遵從兒童心理發展的規律,銀幕上的兒童形象也給觀眾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引導作用。
四、作為渴望家庭關愛的留守者:鄉愁的表達與同情效應的闡釋
進入新世紀后,農村留守兒童成為兒童電影關注的焦點,涌現出了大量的留守兒童題材的電影。這些影片重在展現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無論是他們貧乏的生活條件還是渴望能得到關愛的內心世界,都使得留守兒童作為弱勢群體,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國產兒童電影的兒童形象也再一次地結合社會實際更迭到留守兒童的身上。
在刻畫留守兒童這一形象時,有很多不同的側重角度,有部分電影著重描述他們的生存狀況,表現了由于父母長期不在家,留守兒童無人看管教育變成了“問題孩子”。比如,《留守孩子》(2006年)中的王小福、杜小葦和月月等留守兒童,他們合伙偷錢去網吧玩游戲,因搶占座位跟別人發生沖突,多次被帶到派出所,體現出了孩子們因缺失家庭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春風化雨》(2009年)中,十歲男孩藍金宇和八歲女孩金悅等一群性格各異的留守兒童打架逃學,在別人的教唆下闖下不少禍。
電影對于留守兒童的表現更多地還是聚焦于呼喚“缺失的愛”的回歸。《空巢里的孩子》(2009年)中父母寄回來的信件成了留守兒童的精神寄托。電影中,孩子們沒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代號:北京、青島、深圳、廣州、蘇州。片尾“北京”全身貼滿收集來的郵票,站在郵筒邊,想把自己寄給父母,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電影最后一個鏡頭推到大樹上的鳥巢,隱喻意義明顯。《天堂的禮物》(2010年)中,小虎的父親外出務工身亡,母親離家出走。為了不讓孩子的心靈遭受打擊,村長給他找了一位臨時媽媽,并且隱瞞真相,大家共同編織善良的謊言,定期會有一本小虎喜歡的《哈利·波特》書郵寄到家里當作爸爸送他的禮物。電影表現了性格孤僻的留守兒童小虎對父母的思念。
《空火車》(2012年)中小女孩月月,時常跑到山坡上遠望駛過的火車,期盼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過年,在她身上反映出大山里留守兒童寂寞、孤獨、敏感的內心世界和時刻盼望與父母團聚的美好心愿。電影《早安!小樹》(2013年)刻畫了五年級學生李小樹所遭遇的困境,三次尋找父親,表面是找錢,實質上是尋找愛,表現了孩子們對于愛的期盼。
《千里送鶴》(2022年)中多杰和格桑幼年喪母,跟父親情感疏離、有隔閡,和奶奶一起生活。他倆救助了一只因受傷又失去父母呵護而無法遷徙越冬的小黑頸鶴,決定將小黑頸鶴從青海草原送到云南香格里拉過冬。善良的姐弟倆跨越千里送鶴,最終盼來了父愛的回歸與陪伴。
一般而言,兒童和老人作為社會弱勢群體,把他們作為表現對象能夠喚起觀眾較大的共鳴,特別是兒童具有天真、稚嫩的特點,能夠獲得觀眾較多的“同情度”。兒童電影將留守兒童作為重要的關注對象,不僅表現孩子們的生活狀態,更多在于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留守兒童銀幕形象的塑造,無論是豐富電影內容、傳遞世間真情,還是呼喚社會關注都具有現實意義。

圖4 電影《早安!小樹》中的李小樹
五、結語
國產兒童電影走過百年歷程,兒童身份與處境的轉變,透過銀幕形象廣泛地傳播,體現出社會的現實狀況,折射出時代的發展變革,也反映出電影藝術創作觀念的轉變。
曾經一段時間,面對種類繁多的娛樂形式,特別是動畫片井噴式的發展,傳統兒童電影受到空前的挑戰。盡管當下兒童電影創作從題材、手法和風格都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態勢,兒童電影數量也不斷增長,但是影院中卻存在高品質兒童電影缺席的尷尬局面。兒童電影面臨著市場份額占有率低和社會影響力偏弱的現狀,如何實現藝術、商業、教育的有機結合,是電影從業者必須再思考的問題。
當今,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電影觀眾,他們對通過影像與聲音傳遞信息、表達思想情感這種形式,有著與生俱來的挑剔,這給電影創作者提出更大的挑戰。兒童銀幕形象的塑造應捕捉凝練現實生活中兒童富有“童趣”的行為和言語,情節發展要符合兒童的思維邏輯。兒童電影創作也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歷史傳統,敏銳捕捉時代變化氣息,結合新時代語境,拓展探索兒童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廣度,以滿足觀眾的審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