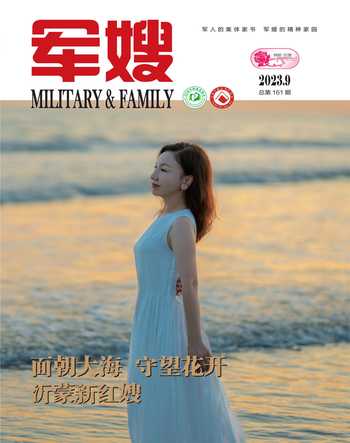為家護航
朱德華
“我們什么時候結婚的呢?大概是2009年底吧。”王娟很忙,忙到猛一問和丈夫結婚的日子,她好像都有點“蒙圈”了。
王娟忙,主要是因為兒子杜戰。每天,她要陪他做數個小時的康復訓練;提前幫他預習功課,和他一起讀讀寫寫;陪他在家看看電影;就寢前,再給他按摩、推拿……
2011年8月,在安徽省蕭縣老家養胎的王娟,足月順產下一個健康的大胖小子,一家人歡天喜地。那時候,丈夫杜凱正在執行遠洋演訓任務。杜戰出生第二天,王娟就辦理了出院手續。
到家那天下午,杜戰的哭鬧聲將王娟驚醒。生產的那幾天,她身體疼得幾晝夜沒睡一個囫圇覺。好不容易回家了,婆婆便把杜戰抱到二樓照看,讓她在一樓能夠好好補覺。
天氣悶熱,杜戰因高溫缺水渾身滾燙發紅,此時,前來串門的熱心鄰居也拿來體溫表,一量體溫竟有40℃多。
從家到最近的兒童醫院一路堵車。2個小時的車程里,王娟不停跟杜戰說話,不停地拍打不讓他睡著。可到醫院時,杜戰已無呼吸、無知覺,被診斷為新生兒肺炎,醫生當即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病危,搶救;病危,搶救;病危,搶救……如此反復12天,杜戰轉危為安。
2個月后,王娟帶著杜戰去醫院復查,診斷結果如同晴天霹靂:因之前高燒導致大運動發育落后,免疫機能弱化。醫生說,若沒有奇跡發生,這個孩子或許終身走不了路、上不了學。
一紙診斷,險些將王娟砸倒。她沒有將消息告訴遠航的丈夫,行船三分險,她不想讓杜凱分心。
王娟相信現代醫療技術。杜戰未滿百日,她就在專家的建議下,制訂了詳細的超早期康復治療計劃:輸營養液、做高壓氧、針灸、按摩、推拿、做康復訓練。
10天一個療程,休息10天后,再進行下一個療程……輸液、針灸,針扎在杜戰頭上,痛在王娟心尖。孩子哭,她卻不能哭,咬牙堅持。而這些,遠在大洋上演訓的杜凱卻毫不知情,他還沉浸在初為人父的喜悅中。
直到杜戰4個月大時,杜凱遠航歸來才得知一切。望著孩子小腦袋上密密麻麻的針孔和疲憊憔悴的妻子,杜凱禁不住雙淚長流。
這么小的孩子,動不動就去醫院,身邊的人不理解,說王娟有些過度緊張、小題大做,甚至有人建議給孩子“驅驅邪”,或者改個名。
夫妻倆相信科學,不為所動。王娟把家中的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用在杜戰身上,即便自己腰肌勞損,有時疼得直不起身來,也舍不得花錢治療。她為孩子所做的努力,感動了一位軍嫂醫學專家,在給孩子做治療的同時,也免費給王娟治療。
10個療程結束,醫院見杜戰恢復得不錯,就停止了輸液,但其他治療項目在門診繼續。為了就醫方便,王娟在醫院附近租了一間房子,每天兩點一線,吃最簡單的飯菜,持續了700多個日子。
和同齡人相比,杜戰肌張力高,腰腹力量弱,翻不了身,王娟就不厭其煩地每天數百次幫他翻身、拉伸四肢。
杜戰1歲半時,學會了說話;3歲時,能下地走路;4歲時,會寫自己名字……發生在兒子身上的一個個奇跡,極大地鼓勵著王娟。
可困難接踵而至。杜戰3歲時,被診斷為弱視,康復訓練中又加了弱視訓練一項。這一練,又是8年。
3歲之前,杜戰大多數時間在醫院度過,與外界接觸少,為了讓兒子融入社會,王娟特意報了一個親子班。在班里,別人都是全家齊上陣,可杜戰只有媽媽陪同。一天,杜戰傷心地問王娟:“我是不是沒有爸爸?”
杜凱一直在艦上服役,每年近300天的出海時長。為了讓兒子相信自己“也有爸爸”,那一次,他專程請了3天假回來陪孩子。

王娟一家近影。攝影/李翰臣

王娟漢族,安徽蕭縣人,1984年1月出生。2010年2月結婚。丈夫杜凱,副艦長。
那3天,是一家三口最幸福的時光,他們一起去上課、一起做游戲。
杜戰上幼兒園后,因為運動功能弱,王娟不得不全程陪護。幼兒園戶外活動時,她進園陪孩子;幼兒園上室內課,她就在大門外等候。
雖然命運不公,但杜戰性格開朗,懂得自我保護。上小學一年級時,有一次因為要上三個臺階,他還主動開口請求路過的校長幫助自己。
杜戰孝順。上小學時,中午學校里有什么好吃的,他都會留一點在飯盒里,帶回家給媽媽吃。
母子相伴12年,雖然經受過很多挫折,但他們相互溫暖、相互治愈。
杜戰曾經寫過一篇作文《我的媽媽》,其中寫道:“我從媽媽身上學到了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堅持,再難的事情只要堅持到一定的時間,就會成功。”
漫長的康復訓練,將會伴隨杜戰一生,但他說“我不怕”。王娟也不怕。
2023年8月1日晚,參加“強軍當先鋒、鮮花獻軍嫂”活動后,忙碌幾天的王娟本想好好睡一覺,結果卻失眠了。她說:“12年來,我心中只有一個目標,為丈夫的事業、兒子的健康,一路護航。”
編輯/吳萍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