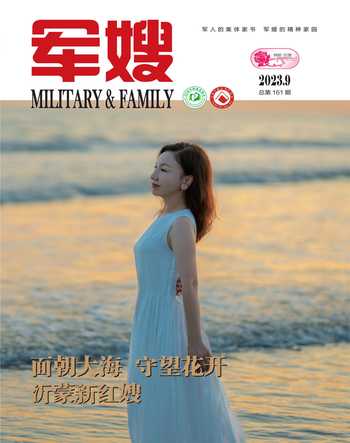戰友“陳大爺”
李香君
“老李,謝謝你寄來的海棠花標本!”“陳大爺”給我打來視頻電話,讓我不由得懷念當兵的日子。
“陳大爺”并非真的大爺,她姓陳名舒雅,山東泰安人。2017年秋,我和她分別從山東農業大學、山東外事翻譯學院應征入伍,在河北涿州參加新訓——兩個完全陌生的人,從此有了一生的交集。
訓練的日子無疑艱苦且難熬,但也歡樂多多——我倆就貢獻了不少笑料。
齊步訓練時,受平時走路習慣影響,我和陳舒雅在隊伍里格外顯眼。我平時走路大搖大擺,腳尖外開,訓練時為避免這個問題,就刻意把腳尖合攏一點,不料卻產生了更奇怪的效果——遠遠看去像是以前裹小腳的大媽在走路,因而被打趣為“李大媽”。
而陳舒雅呢,擺臂時,胳膊外展,身體晃動的幅度很大,有種北京老大爺晨起遛鳥的感覺。多次糾正無果后,班長著急地沖她喊道:“你走路怎么跟個大爺一樣!是吧,陳大爺?”
因此,我和“陳大爺”,經常被單拎出來加強訓練。看著我倆各自扭著奇怪的步伐搖搖晃晃地走著,班長欲哭無淚:“李大媽、陳大爺,你倆能不能好好走啊?”
不久后的某個晚上,我突然“悟了”,很快就摘掉“李大媽”的帽子。但“陳大爺”依然故我,走路依舊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我也就沒改稱呼,一直這樣叫她。
其實,一個人的行走方式、寫字形態、穿衣搭配等細節,都是他(她)真實的側寫。“陳大爺”如她走路的方式一樣,灑脫直爽、不拘小節,心里真實的想法都寫在臉上。從小就敏感多思的我,就很羨慕她。
2017年底,我和“陳大爺”都被分配到武漢某單位,還由一個班長帶著。平時忙于訓練、學習,唯有午飯后的半個小時,按要求在俱樂部整理被子,是大家最放松、自由的時刻,常常一起說笑、鬧個不停。
我喜靜,享受獨處,不愛熱鬧,大多數時候會避開人群,在一邊做自己的事。“陳大爺”很有原則,不喜歡強行融入自己不感興趣的圈子。
俱樂部不大,我倆拎著小馬扎,挨得近近地壓各自的被子,一邊忙活,一邊有一搭無一搭地聊天。
慢慢地,我們發現彼此的價值觀等契合度很高,性格也有很多地方互補。那時,班長對新兵各方面要求很嚴格,我倆常因無法達到標準而挨批評。久而久之,我倆積累下來的委屈和苦惱,都會向對方訴說。
3個月之后,我和“陳大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到了分班的時候,我被分在了一排,“陳大爺”去了二排。雖說只是樓上樓下的距離,但因為兩個排有各自的業務與工作安排,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之又少,更別提能在一起開心地聊天了。于是,傳紙條成了我們交流的主要方式。
在列隊準備前往機房時,一個人影經常會冷不丁地躥到我身邊,手心被匆忙塞入一張紙條后,人影迅速撤離。
不必回頭,我都知道是誰。我不動聲色地將紙條滑進褲兜,裝作無事發生一般,然后找到合適機會,再展開細讀。
“老李,你最近怎么樣?我的師傅人很好,對我也很好……”
“前幾天值班日記寫錯了,班長罰我抄一整本,累死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寫錯了……”
“老李,明天我可以外出半天購買生活用品,你有啥要帶的嗎?我給你買,到時候塞你柜子里……”
…………
每次收到的紙條,我都會整整齊齊地夾在日記本里,等允許使用手機時,再給它們拍照“存檔”。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果不其然,沒多久,我倆“通信”的事情就被班長發現了。雖說沒有明文規定不能傳遞紙條,但為了讓我倆安心學習業務,班長還是把我們叫去單獨談話,讓我們處理好紙條,并保證下不為例!
我拿著那些紙條,看著上面“陳大爺”熟悉的筆跡,不舍和難受涌上心頭——那上面的一字一句,記錄的都是我們新兵生活的點點滴滴。但最后,我還是把它們扔進了下水道。按下沖水鍵的那一刻,我很慶幸手機里還有“備份”的紙條照片。
之后,我們開始了單獨值勤。因表現不錯,班長不再事無巨細地過問。休息時間里,我和“陳大爺”終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一起聊天、看書、散步……
2019年3月,武漢春光滿園,遍地都是黃色的鴉蔥。一個周六上午,我和戰友們到操場上跑步,回連隊的途中,摘了一朵開得最好的鴉蔥帶回去。那時,“陳大爺”在一樓當文書,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我拿著那朵鴉蔥,興高采烈地對她說:“陳大爺,你快看,我把武漢的春天給你帶回來了!”
“陳大爺”上來就是一頓“熊抱”:“老李,你對我太好了……”
2019年8月,我退役返回泰安,在山東農業大學繼續讀書;“陳大爺”回到威海,在山東外事翻譯學院繼續學習。退役后這幾年,只要她回到泰安,我們都要聚一聚。

戰友情深。攝影/徐偉
現在,我嫁給了一名軍人,成了軍嫂,也完成學業將走上工作崗位。“陳大爺”已經就業,嫁給了一名退役軍人,隨丈夫定居在浙江寧波。
“老李,這是我們家的主臥、客廳、嬰兒房,對了,我還特意給你留了一個房間呢,你看……”視頻里,“陳大爺”興奮地向我展示完她的新家后,又幽幽地來了一句,“老李,我想你了……”
看著視頻那頭的“陳大爺”,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陣發酸:“‘陳大爺,我也想你……”
(作者為退役軍人、軍嫂)
編輯/吳萍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