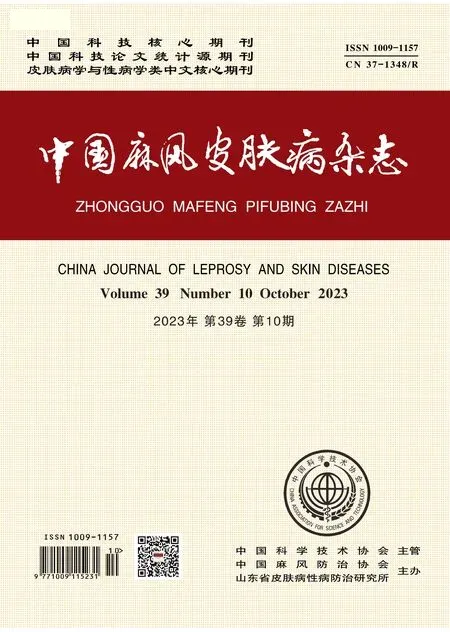特應性皮炎患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的差異性分析
吳卓璇 李 蒙 陳金波 胡 楓 王向東 覃 莉
武漢市第一醫(yī)院皮膚科,湖北武漢,430022
特應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以濕疹樣皮損為臨床表現(xiàn),伴有劇烈瘙癢的慢性炎癥性皮膚病。大多數AD患者在嬰幼兒時期發(fā)病,并持續(xù)到青春期甚至成年期[1-3]。早期發(fā)病是影響AD過敏性進程和發(fā)展為中重度AD的高危因素。近來研究表明,嬰兒腸道早期菌群紊亂與機體特應性、IgE相關濕疹和哮喘發(fā)展之間具有關聯(lián)性[4],推測腸道菌群可能在AD的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本研究將探討AD嬰兒和健康嬰兒腸道菌群在組成以及屬、種方面的差異性,對今后AD治療提供指導意義。
1 對象和方法
1.1 病例來源 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到武漢市第一醫(yī)院皮膚科門診就診的1~12個月齡AD患兒。病例納入標準①符合Hanifin和Rajka診斷AD標準[5,6];②1~12個月齡足月產嬰兒;③無其他皮膚疾病;④無其他系統(tǒng)性疾病(除外過敏性結膜炎、過敏性鼻炎、過敏性哮喘、過敏性胃腸炎);⑤無精神疾病、殘疾、智力障礙;⑥近1個月未使用抗生素;⑦未服用含益生菌等微生物制劑。對照組來自武漢市1~12個月齡,無皮膚及其他系統(tǒng)疾病,未服用抗生素和益生菌的健康足月產嬰兒。
符合納入標準的AD組患兒,男21例,女12例,平均年齡(7.55±3.01)個月;對照組,男17例;女13例,平均年齡(8.06±3.25)個月。2組入選者年齡、性別、分娩方式、喂養(yǎng)方式、家族史、生活環(huán)境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本研究獲得武漢市第一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研究對象的家長或監(jiān)護人均知情同意。
1.2 樣本采集 取受試者糞便標本(>1 g)儲存于-80℃冰箱。干冰運至武漢百易匯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檢測與測序分析。
1.3 實驗方法 糞便樣本提取總DNA后采用Nanodrop對DNA進行定量,并通過0.8%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DNA提取質量。采用兩步PCR的方法進行擴增,擴增區(qū)域是V1-V9,引物是27F: AGRGTTYGATYMTGGCTCAG和1492R:RGYTACCTTGTTACGACTT,同時對擴增結果進行質控。應用武漢希望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PacBio Sequel測序儀對研究對象糞便細菌的16SrRNA基因V1-V9區(qū)進行高通量測序及分析。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α多樣性主要分析菌群的豐富度和多樣性,其中Chao1和Observed species指數表示豐富度,Shannon和Simpson指數表示多樣性,Faith’s PD 指數表示基于進化的多樣性,Pielou’s evenness 指數表示均勻度,Good’s coverage指數表示覆蓋度;β多樣性使用PCoA圖,其中距離算法是Bray-Curtis分析;LEfSe (LDA Effect Size)分析是一種非參數統(tǒng)計方法,同時使用了Kruskal-Wallis以及Wilcoxon秩和檢驗,結合線性判別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在兩組中在豐度上有顯著差異的物種,LDA值代表了顯著差異物種的影響大小,LDA效應量>2且P<0.05為有統(tǒng)計學差異。
2 結果
2.1 兩組嬰兒腸道菌群在門和屬水平上的組成 兩組腸道菌群在門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排列前5位的菌門為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厚壁菌門(Firmicu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疣微菌門(Verrucomicrobia),見圖1。兩組腸道菌群在屬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排列前5位的菌屬為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擬桿菌屬(Bacteroides)、梭狀芽孢桿菌屬(Clostridium)、韋永氏球菌屬(Veillonella)、埃希氏桿菌屬(Escherichia),見圖2。

圖1 特應性皮炎嬰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在門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 圖2 嬰兒期特應性皮炎患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在屬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
2.2 α多樣性指數 研究環(huán)境中微生物的多樣性,通過alpha多樣性分析能較全面地評估菌群落的豐度及多樣性,其中Observed species指數和Shannon指數,這兩組指數顯示AD組較對照組豐度、多樣性、均勻度中位數偏低,Good coverage值表示AD組覆蓋度偏高,但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圖3。

每對箱線圖對應一種α多樣性指數,在其頂端灰色區(qū)域標識。每個箱線圖中,橫坐標為分組標簽,縱坐標為相應α多樣性指數的值。箱線圖中,各符號含義如下:箱的上下端線,上下四分位數(Interquartile range,IQR);中位線,中位數;上下邊緣,最大最小內圍值(1.5倍的IQR);在上下邊緣的外部的點,表示異常值。多樣性指數標簽下的數字為Kruskal-Wallis檢驗的P值。AD組:特應性皮炎嬰兒;對照組:健康嬰兒圖3 嬰兒期特應性皮炎患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的α多樣性指數
2.3 β多樣性分析 研究不同生境間多樣性的比較,從圖中可以看出,兩組之間有明顯的不一致性,使用PERMANOVA檢驗(P=0.032),提示兩組間菌落有顯著性差異,見圖4。

圖4 嬰兒期特應性皮炎患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的PCoA圖 圖中每個點代表一個樣本,不同顏色的點指示不同的組。坐標軸括號中的百分比代表了對應的坐標軸所能解釋的樣本差異數據(距離矩陣)的比例。兩點在坐標軸上的投影距離越近,表明這兩個樣本在相應維度中的群落組成越相似。橢圓形虛線圈為95%置信橢圓。AD:特應性皮炎嬰兒;對照組:健康嬰兒 圖5 嬰兒期特應性皮炎患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的LEfSe圖 縱坐標為組間具有顯著差異的分類單元,橫坐標則以條形圖直觀地展示各分類單元的LDA分析對數得分值。分類單元按照得分值大小進行排序,以此描述它們在樣本分組中的特異性。長度越長表明該分類單元的差異越顯著,條形圖的顏色指示了該分類單元所對應的豐度最高的樣本分組。AD組:嬰兒期特應性皮炎患兒;對照組:健康嬰兒
2.4 LEfSe分析 采用LEfSe分析發(fā)現(xiàn)AD組腸道菌群中,弗氏檸檬酸桿菌(LDA=2.430)、產酸克雷伯菌(LDA=2.211)顯著性增加,對照組鏈球菌屬(LDA=4.517)、韋榮氏球菌屬(LDA=4.311)、巨球形菌屬(LDA=3.592)、唾液乳酸桿菌(LDA=3.510)、副流感嗜血桿菌(LDA=3.108)、埃格特菌屬(LDA=2.871)、第三梭狀芽胞桿菌(LDA=2.850)、肺炎鏈球菌(LDA=2.651)、共生梭菌(LDA=2.588)、無害芽胞梭菌(LDA=2.262)、小韋榮氏球菌(LDA=2.260)顯著高于AD組,見圖5。
3 討論
約有45%的AD發(fā)生在嬰兒期前6個月,研究表明AD嬰兒腸道菌群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具有差異性,提示嬰兒腸道菌群定植在AD的發(fā)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7-8]。嬰幼兒早期腸道微生物組的組成、功能和代謝產物與AD的自然進程有關[9-10]。腸道中豐富的胎糞代謝組與菌群組成可以減少過敏性疾病發(fā)生的風險,且菌群結構和過敏表型之間具有顯著關系[11-12]。嬰兒期腸道菌群的不平衡可能是特應性病程發(fā)展的重要條件[13]。
目前,國內關于AD嬰兒腸道菌群定植的報道甚少。本研究通過16S rRNA測序、α多樣性指數、β多樣性及LEfSe分析,比較患有AD的嬰兒與健康嬰兒腸道菌群的差異性。研究結果顯示,兩組腸道菌群在門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排列前5位的分別是放線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變形菌門、疣微菌門;在屬水平上的物種相對豐度排列前5位的有雙歧桿菌屬、擬桿菌屬、梭狀芽孢桿菌屬、韋永氏球菌屬、埃希氏桿菌屬,與國外研究一致[11,13]。兩組腸道菌群在組成結構上有顯著性差異(P=0.032);AD組的菌群物種豐度和均勻度指數較對照組偏低,但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采用LEfSe分析方法發(fā)現(xiàn)在屬和種水平上,AD組中弗氏檸檬酸桿菌、產酸克雷伯菌較對照組顯著性增加,對照組中鏈球菌屬、韋榮氏球菌屬、巨球形菌屬、唾液乳酸桿菌、副流感嗜血桿菌、埃格特菌屬、第三梭狀芽胞桿菌、肺炎鏈球菌、共生梭菌、無害芽胞梭菌、小韋榮氏球菌較AD組有顯著性增加。上述結果表明,健康對照組嬰兒腸道中益生菌與致病菌以共生形式存在,其菌群多樣性較AD組明顯增多,而AD組嬰兒腸道菌群較為單一,這可能是引發(fā)AD的原因。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AD患兒腸道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梭狀芽孢桿菌的比例升高[7,14,15],而本研究中AD組嬰兒腸道中弗氏檸檬酸桿菌、產酸克雷伯菌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提示上述兩種菌可能在AD發(fā)生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有研究報道發(fā)現(xiàn),經剖宮產出生嬰兒的腸道菌群中弗氏檸檬酸桿菌、產酸克雷伯菌等定植顯著相關,推測可能是哮喘和過敏患病率增加的原因[16]。克雷伯氏菌在腸道定植發(fā)生在生命早期,作為腸道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共生菌群在機會條件下致病,在3個月齡濕疹嬰兒的腸道中發(fā)現(xiàn)明顯富集,炎癥性腸病小鼠模型研究中也描述了克雷伯氏菌和嬰兒腸道早期炎癥的發(fā)生有關[17]。特應性濕疹嬰兒的微生物組和代謝組進行了分析通過肺炎克雷伯菌的富集,與糞便增加相關d-葡萄糖濃度和相關毒力因子基因表達增加有關[18]。
綜上所述,AD嬰兒腸道菌群相對豐度及生物多樣性與正常嬰兒存在差異性。腸道菌群的組成和比例差異與AD的發(fā)展相關,腸道菌群可通過免疫、代謝和神經內分泌途徑促進AD的發(fā)展,影響其持續(xù)性和嚴重性[19]。因此,關注AD嬰兒早期腸道菌群定植,對AD預防和治療具有重要意義,但因腸道菌群受地域、環(huán)境、飲食等諸多因素影響而發(fā)生變化,其對疾病和過敏進程的影響還需進行更深入地前瞻性研究加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