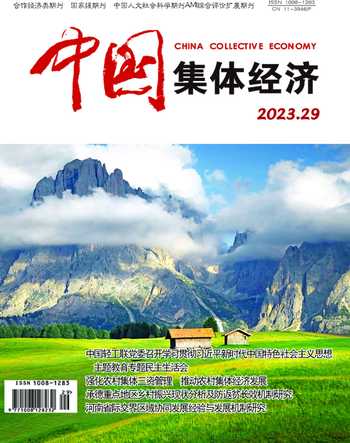研發投入、政府補助和企業績效
徐慧蘭
摘要:文章以2017-2019年科創板367家企業為樣本,通過固定效應的研究方法,就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研發投入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作用,同時政府補貼有正向調節作用。對公司規模進行異質性研究,結果顯示,政府補助對規模較大的企業調節作用更顯著。文章為國家進一步加大研發補助、鼓勵企業創新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研發投入;企業績效;政府補助
一、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謀創新就是謀未來。黨的十八大明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幾年來,國家高度重視微觀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相繼出臺各項政策鼓勵企業創新,包括國家政府補助的政策。近年來,國家向企業發放政府補助已逐漸作為政府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研發投入作為創新活動的基礎,是否能為促進企業績效而服務,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的關注熱點。從學術界研究現狀來看,仍存在一些需要補充之處,為國家進一步推動企業創新提供微觀翔實的證據。本篇論文的主要貢獻:第一,在研究樣本選取上,首先,選擇了合適的技術創新策略的科技公司,因為這類公司比較注重突破核心技術,并且其產品市場知名度也較高,因此具備了相當的市場代表性;其次,深入研究政府政策補貼的調節作用,在對公司業績的主要影響因素中,進一步探討政府研發投資和公司業績之間的相互影響機理;最后,對不同規模的企業進行異質性分析,以便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為進一步推動創新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目前,關于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的研究成果顯著。在公司業績方面,Soriano等人對澳大利亞的制造公司展開了系統化研究,并得出結論:公司的研究投入程度對公司的產品銷售產生一定影響,而產品銷售又對公司的財務績效產生一定影響,而梁萊歆等也指出研究投入程度和利潤率間的正相關關系是很短期的,低研發投資導致相應的低利潤率,從而影響企業業績。程宏偉對96家上市公司進行了調研,發現雖然研發投入與業績成正相關性,但產生的經濟效益卻在總銷售收入過程中所占有份額相對較小,這就可能存在滯后問題,而陳守明等以2007-2009年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發現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與企業當年及之后一年的企業價值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并且研發投入企業業績的提升效應持續穩定,但是這種效應逐年遞減。
不過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之間也會存在中介變量,學者對這個中介變量進行了探索。程華、邵波等以266家浙江民營企業為研究樣本,他們提出R&D的提高既能提升公司的科技水平,又能提升公司業績,于是又把研究關注點放在了技術能力方面,并著重探討技術能力如何作為中間變量,實驗結果證明,雖然研究投資對公司業績沒有直接顯著作用,但在研究投資中技術能力卻發揮重要作用,技術能力在總體上也對公司業績發揮重要作用,并由此證明了技術能力還發揮著中介功能;也有研究者利用實證分析方法發現一些其他中介變量,如科技創新,通過篩選312個浙江省的制造業公司,發現研究投入對公司科技創新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研究的產出數量與發明專利獲得數也具有部分中介意義,對其中的機制研究仍任重道遠。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高新科技企業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根據權變理論,這些公司要明白以不變應萬變的道理,尤其對決策層來說,要意識到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關鍵因素。尤其是在疫情時期,形勢瞬息萬變。提升核心競爭力的主要途徑是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創新需要資金支持和前期投入,因此,加大研發投入是企業進行創新的基礎和源泉。對于企業領導來說,應該強調鼓勵部門進行研發創新,生產新產品或者改進產品性能,研發部門在企業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是企業綜合實力提升的主要依托,還可以降低無效工作的成本費用,使企業健康穩定發展。因此,根據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設1。
假設1:研發投入會明顯改善企業績效。
宏觀環境的影響是企業發展中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方面,財政對項目的補貼有利于中小企業降低開發項目的風險,極大地提高中小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能力,這樣才能促進產品開發的順利進行。但是,政府補貼實質上是行政性的手段。而財政方面,中央政府給企業發展資金補貼主要基于國家層面考慮,能夠推動宏觀經濟增長,同時還能夠增強社會的總體實力,但企業收到財政直接補貼,也意味著需要擔負一定的責任。如通過有效監管來保證被補助的研究企業取得研發成果,所以財政獎勵也能對研究投資和績效之間的聯系產生正向調節作用。根據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設2。
假設2:政府補助對研發投入和企業績效起到正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2017-2019年的科創板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樣本,剔除未披露相關數據的公司,最終確定有效樣本為367家高新技術企業。數據來源于wind金融終端,數據用Stata17.0進行處理。
(二)變量選取
1. 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指標。根據以往文獻,本文選擇能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營業收入(income)這一指標,并將其取對數。
2. 解釋變量:研發投入(RD),本文選用研發費用的對數來衡量;政府補助(subsidy)指企業從政府機構中所獲得的無償的補貼,一般以其自然對數來衡量政府補助的強度。
3. 控制變量:選擇企業規模(size)、企業的償債能力即資產負債率(ALR)、股權集中度即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行業(industry)作為控制變量。
(三)模型構建
本文選取回歸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建立模型。
模型1:incomei,t=β0+β0RDi,t+β2ALRi,t+β3TOP1i,t+β4industryi,t+ui+εi,t
模型2:incomei,t=β0+β1RDi,t+β2subsidyi,t+β3RDi,t×subsidyi,t+β4TOP1i,t+β5industryi,t+ui+εi,t
上式中下角標i代表上市公司,t代表年份,u代表企業的個體效應,ε為誤差項。模型1用來檢驗假設1,模型2用來檢驗假設2。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對樣本中的367家企業3年的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各個變量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從表2可知,研發投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9.44和16.15,這意味著由于企業發展、經營等差異,公司對創新研發的投入也會有所差別;從政府補助的規模來看,不同企業受到的補貼也不一樣;資產負債率的最大值為76.59%,最小值為9.44%,可見科創板的企業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差別很大,就股權集中度而言,最大值為完全控制,均值為42.54%,整體呈現較高的股權集中度。
(二)回歸分析
本文模型采用固定效應,回歸顯示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可得: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在1%水平上顯著,其比率系數為0.9,表明公司研究投資較高,業績將得到改善,證明了本文假設1。之后本文根據溫忠麟等的研究思路,將研發投入和政府補助中心化后做交乘項,再進行回歸。結果如模型(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系數顯著且為正,說明政府補助在此兩者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即政府給到企業的補助越多,企業研發和績效之間的關系會越緊密,因此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
(三)異質性分析
為探討這些因素在大小不同的公司間存在的差異,將公司按規模的中位數進行分類,超過中位數的為大型組,反之為小型組進行分類回歸,結論如表4所示。政府補助對研究投入和公司業績的調節作用在不同規模的公司中體現差異。在規模較大的公司中調節作用最明顯,調整系數為0.326,表示對于規模較大的公司,政府補助將加大研發投入對公司業績的影響。
為了檢驗本文假設的穩健性,本文將凈利潤作為被解釋變量加到原模型中回歸,從而判斷該模型的穩健性,結果顯示模型p值顯著,說明原假設成立,證明前述結論的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2017-2019年科創企業為樣本,用固定效應模型展開研究,得到如下結果:科創企業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政府財政補貼的規模可以對研發投入與績效產生正面調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企業的研究創新活動;政府補助的調節作用對大規模企業更大,大規模企業由于自身能力較強,得到政府補助,研發投入資金增多后,績效會出現顯著提升。
(二)政策建議
第一,對國家補助項目要加強監督,敦促企業進行有效研發投入。必須健全補償管理體系,特別是關于補償資金的事后管理和監測,完善考核評價體系。引導企業嚴格規范、科學管理,增強企業和社會的競爭力,企業應該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真正做到將政府補助都用在研發上,提升社會乃至國家的競爭力,為國家突破核心技術作出貢獻;
第二,政府應結合企業異質性及其他特征制定相應的補助政策和補助額度,合理分配財政資源。政府應該大力支持行業龍頭企業或者有條件的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鼓勵與中小企業組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將補助強度嚴格控制在最優區間范圍內,避免造成國家財政資源浪費。
參考文獻:
[1]淳正杰,譚書敏.R&D投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綜述[J].天府新論,2014(05):90-95.
[2]Sorina D,Huarng K.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knowledge industri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10):1964-1969.
[3]梁萊歆,張永榜.我國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與績效現狀調查分析[J].研究與發展管理,2006(01):47-51.
[4]程宏偉,張永海,常勇.公司R&D投入與業績相關性的實證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06,24(03):110-113.
[5]陳守明,冉毅,陶興慧.R&D強度與企業價值——股權性質和兩職合一的調節作用[J].科學學研究,2012,30(03):441-448.
[6]杜興強,曾泉,王亞男.尋租、R&D投資與公司業績——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投資研究,2012,31(01):57-70.
[7]程華,邵波,徐阿進.企業R&D投入、技術能力與績效關系——基于浙江企業的實證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2,30(05):109-112.
[8]廖中舉.R&D投入、技術創新能力與企業經濟績效間關系的實證分析[J].技術經濟,2013,32(01):19-23.
[9]董明放,韓先鋒.研發投入強度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績效[J].統計研究,2016,33(01):45-53.
[10]楊洋,魏江,羅來軍.誰在利用政府補貼進行創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場扭曲的聯合調節效應[J].管理世界,2015(01):75-86+98+188.
[11]張小紅,逯宇鐸.政府補貼對企業 R&D 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15):204-209.
[12]仲東亭,任浩.高新技術企業績效影響因素實證分析——基于上海全樣本數據[J].中國科技論壇,2021(05):90-98.
[13]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心理學報,2005(02):268-274.
(作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