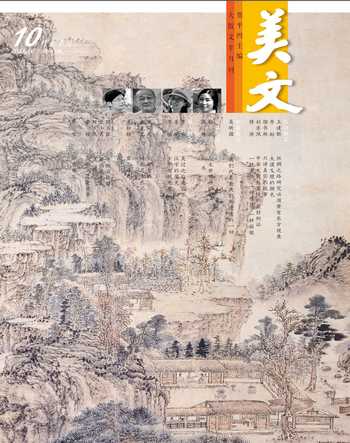淇河
五十七
當每一個早晨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淇河已在我的生命里汩汩涌動,特別是在我投向遠方的目光里,我已聽到清澈的流動之聲。
當每一個夜晚進入夢鄉的時候,鼾聲四起的呼嚕聲仿佛淇河的波濤,長久地回響在深夜的意境里,就像生命的琴弦撥響千萬年的沉寂,靜靜地給人以久遠的回聲。
因此,這方面的文學作品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是能夠永遠屹立于太行山脈的不朽之作。
文字里的綠色元素一旦播撒在這片古老又年輕的土地上,世世代代都會綻放出樹木花草的生機和馨香。
在這里,處處可以看到淇河的騰飛之羽,時時可以聽到清澈的奔流之聲。如果有人想更深入地了解這方面的內容,淇河的回答是不加思考的、是響亮的。
這樣的回答也是清澈的、也是奔放的。
淇河就像童話里的一個美麗傳說。這個傳說仿佛是一滴晶瑩的露珠演變過來的,仿佛是從一片葉子上滾落下來的,仿佛是露珠里的陽光生長出來的……
五十八
我常常從寫作的角度審視淇河。假如淇河是一滴晶瑩露珠的話,那么櫻城鶴壁就應該是從露珠里成長起來的一座城市,是從童話故事里走出來的一座城市。
故而,童話和露珠應該是這座城市的兩張金名片,是否妥當?我相信時間會證明這一切是正確的。
無論別人是什么樣的看法,這對于我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無足輕重的。
一個長期從事文旅生態創作的寫作者,其看法和眼光是與眾不同的。為此,我不會猶豫不決,更不會郁郁寡歡。同時,我更相信筆墨所到之處是銳利的,完全可以洞察一切。
先人一步的眼光和智慧一旦抵達淇河,映現在文字里的春意已經成為櫻城鶴壁的一處可觀之景。步步為意,字字為境,句句是自古以來的美好存在。
假如走在每年4月中旬的櫻花大道上,櫻花的馨香就會主動召喚前來的客人,并成為他們的引導員。那個時候清賞櫻花,仿佛櫻城鶴壁的另一個側面已經完全映現在淇河里。
在我看來,一個都不能少。
五十九
對于淇河的寫作,文字必須是有靈性的,仿佛河流里無數的魚兒成群結隊向我游來,最后聚集在記憶深處。
《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2010年1月18日刊發出來的一首詩歌作品《淇河在成長》即是如此,原詩如下:
“淇河在成長,仿佛岸邊的樹/仿佛樹上掛滿的星星和月亮/仿佛這樣的景致只有一個答案/淇河之水來自我的內心深處/淇河在歌唱,仿佛天籟之音/仿佛水里流動的魚兒和太陽/仿佛這樣的造訪只有一個主張/鶴壁之聲當然是鮮花和夢的宣言。”
在這首詩里,淇河就是岸邊的樹,就是夜晚倒映在河流里的星星和月亮,就是河流里流動的魚兒和太陽。
我之所以這樣贊揚它,因為淇河畢竟是我從小到大非常熟悉的一條河流,是生命里常常流動的一條河流,奔騰在血液里的一條河流……
我對于淇河的關注一天都沒有停止過,有關淇河的一切消息都在我的視線之內。淇河也從未脫離過我的視線,從未脫離過我的思念。
當淇河的水流把我雕刻成一滴清澈的水珠時,我的感覺里依然能夠映現出有關它的全貌,甚至岸邊的一棵櫻花大樹、一株小草、一朵花瓣及一片草葉。
六十
淇河在我生命里漲姿勢的時候,它是沿著我的手臂飛揚起來的。
看到這一切,我已經從固步自封的思念狀態中走了出來,心情猶如鳥兒的翅膀,在湛藍的天空上放松了下來。
即使從一萬米的高空俯視,淇河依然那么清晰可見。
陽光下碧藍碧藍的河流和波濤,令人十分舒暢。這是天賜的自然與生態環境,哪怕一片草葉認可了我,或多或少,對于我來說都是一種來自故鄉的安慰。
這樣的感覺重復的時間長了,思念就會愈來愈濃,迫不及待。
在這種情景下,淇河當然是引發文學創作的一場風暴,字里行間,俯首皆是。
此時此刻,唯有淇河兒女的心里才會響起它的河流之聲,才會視它為精神上的好作品、大作品,幾乎可以碾壓天下的任何一條河流。
六十一
淇河在我的意念里,已經超越河流這個概念,一種嶄新的理念似乎已經遍布淇河的肌體。
淇河不僅僅意味著是一條干凈、純凈的河流,這種理念實際上已經超越傳統的認知。
淇河更有助于加深對于天空的理解,若換一個角度來審視,它其實就是藍天的表情。
湛藍湛藍的表情綻放在河流里,仿佛這樣的感覺已經讓淇河完成了它作為一條河流的使命。
清澈意味著責任和擔當,河流里所有的生命從此開始充實起來。
這么好的水質,河流里的魚兒游來游去,心情是多么愜意。水草在水流中來回擺動,反反復復的興奮勁兒,一眼便知。
櫻花的馨香,毫無顧忌地穿梭在那一片片蘆葦蕩中,美好的情景在這里沒有任何保留。
面對風霜雨雪、狂風暴雨,蘆葦蕩三千多年的沉默積淀于此。面對驕陽似火,浩浩蕩蕩的蘆葦蕩始終是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
看到這樣的場景,就連鳥兒們都激動不已,嘰嘰喳喳,歌聲不斷。
鳥兒們已經完全沉醉于此了,仿佛它們的生命與此相關,命運與河流休戚相連、生生不息。
或者說冥冥之中,淇河之水始終孕育著鳥兒們的期待。
一群鳥兒貼著河面在飛翔,激流之處或漩渦里,似乎到處都可以看到鳥兒們的英姿。此時,如果有人感到驚訝的話,那是他的腳步尚未涉入河流。
佇立河岸,眺望遠方,從小就在淇河邊長大的我,已經驚詫于淇河的深刻變化了,而且是持續不斷的變化。
類似這樣的觀察,不用放眼全部,一個不會引人注目的細節或側面,就足以掌握它的全部。
淇河的這種潛移默化的變化并非偶然,但謎一樣的神秘莫測似乎談不上。
在我看來,淇河的清澈早已注定如此。沒有一棵樹可以否定它的變化,沒有一株草可以淡漠這些觀察,沒有一朵花兒為此草草地衰敗。
這是大自然的愿望,淇河早就懂得這些道理,淇河兒女更有深刻的感受和體會。
六十二
哪怕是一條波紋出現在河面上,無論是在哪個季節,淇河都知道這波紋之中的時過境遷。
稍微晚一些的春之感覺,遲早都會映現在人們的視線里。若是夜晚,一顆流星劃過激流,只會讓淇河次第花開的容顏在清澈之中更加鮮艷、更加靚麗。
無論歲月多么長久,無論燦爛多么持久,淇河清澈的標志,從來沒有成為生態的憂患。
不過,有些向好的變化是逐步展開的,有些則是淇河醞釀已久的,甚至是骨髓里的質的變化。
當然了,也有一些是姍姍來遲的,只要仔細觀察,一片草葉足可以顯示出來。
六十三
多少年以后,當我出于一種寫作習慣,反復思考已經閃現出來的變化時,淡淡的波紋十分清晰地灌溉著這篇文章的每一個漢字。
變化一定是在隱蔽之處形成的,而后漸漸地浮現出來。
就像國家濕地公園里的鳥鳴,時刻都會喚醒那些失眠的浪花睜開眼睛。就像鳥兒的喙,早已把我的思念輕輕地啄開。
當我從記憶里搜尋出來這樣的深刻時,淇河一定會在我的生命里遍布存在。
就是這么一條河流,竟然見證了我的大半人生。命運遭受苦難和坎坷之時,是淇河的一次次挽留和安慰,我的腳步才會植根于此。
多少次難以言說的苦痛,淇河都是默默地浸透其中,化解我的痛苦。
如果把人生的經歷和腳步都當做風景來看,那么,有誰能從我的表情里觀望出淇河?波濤洶涌的河面上,幾朵浪花仍然停留在目光里。
遠方的太行山屋脊,是否支撐著一個人的生命高度?俯瞰山崖之下的蜿蜒小道,似乎讓我更加堅信自己的選擇和追求。
六十四
淇河始終托舉著一種人生信念,就像托舉著一種新生事物。這種事物因淇河的完美而完美,因淇河的完善而改變。
但我并沒有因此而停下自己的腳步,因為這樣的事物是在淇河無與倫比的變化中產生的。
大美的形成完全取決于淇河沿岸的生態,由于這里的生態與淇河有著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自然關系,所以大自然的這種平衡性始終沒有被打破過。
認識是否到位,這依然很重要,這是生態形成的重要元素。
大千世界里,每一種物體本身都有極限性,但這種極限性在淇河沿岸體現出來的,并非一味地終止、死亡。
春風吹來綠又生,這個時候人們會突然發現,樹木花草的許多渴望里又長出了新芽。
許多熟悉的面孔,在經歷了生死的涅槃之后,又被春天托舉了出來。
再多的苦痛也無法攫住它們對春天的向往,眾多的樹木花草沒有一種拔節的聲音會對春天表達出不滿的訴求,沒有一種鮮艷的色彩會把春風拒之于千里之外。
這就是說,任何一種生命,只要向著大自然,向著陽光而生,它的生命呈現給春天的,一定會是綠色的期冀,一定是大自然調和性的平衡感覺。
矛盾自然是會有的,但來自于大自然的這種公平和公道,就像正義的使者,能夠承受住一切艱難困苦。
六十五
未必燦爛,也未必繽紛,但肯定會是韌性的色彩。否則,無論是怎樣的鮮艷和變化,其生命的內部一定會醞釀出大量的毒液和毒性。
當淇河轉過身的那一刻,從側面看,它清澈的面頰就像一位安靜的母親,坐在那里觀看著什么。
它的面孔是那么慈祥,它的眼神是那么富有善意。
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記住了這張面孔。
光陰荏苒,歲月輪回,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我再次見到它時,它依然向我展示出最閃亮的風采。
淇河是動態的,緩緩的河流下,時有激情和波動;淇河又是安靜的,像一位矜持的少女,優美的流向宛如恬靜的處子。
透過清澈的河流,隱隱約約、忽隱忽現,不安靜的思念走向每一株小草。
思念猶如風中搖曳的葉子,沉默之中眺望遠方,又仿佛剛剛從睡夢中醒來一樣,嘩嘩地流動著、流動著……
那久遠的歲月已經從它的額頭上掠了過去,宛如夜晚的流星一閃而過。
深夜的寂靜并沒有什么可怕的,就連星光都這么認為。
星光下的燦爛之處,那波光粼粼就是動態之中的思念嗎?仿佛隨時都會遭遇解體或破碎。
所有這一切,完全都是夢幻的作用。
大自然賦予淇河優美的姿態,這里的每一種生命又賦予淇河堅韌的詩性。對此,魚兒是深信不疑的。
對于這樣的自然和生態藝術,完全沒有必要來詮釋什么。就像淇河的激流,無論遇到什么樣的險灘暗礁,躲避或停止在它看來都是沒有必要的,這就是它勇往直前的力量之所在。
六十六
其實,淇河對于我來說,本身就是久遠的詩化藝術。對于這樣的認知,古人早已在《詩經》里間接地告訴了后人。
淇河就像夢里的一個倩影,深夜的我,仿佛以流動的姿態走向了它,融入了它。
淇河的河流之聲,似乎已經被思念吹向了遠方。
似風,那種撲面而來的遼闊,鑄就大自然的永恒。似霧,那種隱隱約約、時隱時現的思念,就像一尊熟悉的雕像,以靜止的親切吸引著我。即使是千里之外的一株小草,或三千多年的朝歌故都,都是一樣的感覺。
當然了,還有劉莊、辛莊等這一區域的文化遺存。
看似這些文化遺存是靜止不動的,其實,那些遠古的祭祀禮節并未消失。
它們在泥土的抑制之下,以沉默的姿態誦讀著生機勃勃的浩瀚場面。
同時,它們又以不安靜的姿態渴望著浮出土面。就像魚兒從水中探出頭來,大口大口地吮吸陽光、氧氣和靚麗的景色。
即使是激烈地穿過山體的河流,即使是大山下面的縫隙和黑暗里,依然會有流動的聲音和好奇。
盡管伸手不見五指,但彼此之間還是觸摸到了對方的呼吸。
而從河流里生長出來的某一棵樹,仿佛從河流下的石縫里噴發出來似的,優美的姿態挺立在空中,或倒映在水里,其周身上下都充滿了波紋和波動。淇河生態的真正意義,簡單地說就在于此。
六十七
水質清澈了,又是動態的,況且與大自然的生長規律又不相悖,永遠都會順從于大自然、適用于大自然。
反過來看,大自然就是這樣來修復原生態的生長規律和變化的。而那些人為的、無休無止破壞性的、違背大自然生長規律的,用不了多久就會在靜止狀態中自生自滅。
大自然的這種修復功能可以說是天生的。一旦產生作用,其本身就具有這種生命的調節功能,用來抑制異狀生長狀態,并以此來達到原有的平衡狀態。
那些圍繞淇河而生長的樹木花草完全處于一種自然狀態,而非依靠其他。
如果說淇河沿岸就像城墻一樣宛如古代的城市,那么,城墻以內的居民就是河流里的魚兒、蝦兒、蛙兒等等。
它們并不是永遠沉醉于水下,偶而沖出水面,就為換一口新鮮的氧氣。
自遠古以來,它們從來沒有改變過這樣的生活狀態,也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即使在今天的陽光下,依然如此。
六十八
人也是一樣,永遠不能違悖大自然的生長規律,生存或生活環境也是如此,相似之中有類似的,但也是有界限的。
一旦越出界限,各種各樣的災難就會相繼而生,相繼而來。
比如水災、火災、瘟疫,應該說這些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生存超越界限的報復。
或者說是與人類的生存環境有著極大的關系,也可謂是人類不適應于大自然而遭受的滅頂之災。
人類的生存只要一超越這個界限,大自然就會有所預警,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警告人類,若再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發生。
這就看人類是站在怎樣的角度,如何來解讀或破解這些現象了。
沒有任何期待可以化解這些現象,唯有適應于大自然,或順從于大自然才可能化解。
大自然的胸懷永遠是敞開著的。
六十九
一條河的生態至關重要,不管它是大河還是小河,不管它是動態的還是靜態的,不管它的規模有多大還是有多小,不管它是來自于天空還是產生于地下。
即使是從遠方而來,人們首先關注的應該是河流的水質問題,而非其他。
河流問題必須回歸到水質本身上來,清澈與否,事關當地的自然和生態。
比如淇河,它并非已完全脫離世俗紅塵,深夜里的河流,漸漸地忘卻了白天的喧鬧和繁華,依然嘩嘩地流淌不止。
七十
淇河存在于各個時代的文字里,存在于三千多年的詩詞之中,當地人對它喜愛有加。
樹木花草以及鳥兒們都承認它,都認可它。
淇河的清澈,就存在于淇河對生態的渴望之中,始終是堅韌不拔的、全神貫注的,或者說這就是大自然賦予河流的一種重要意義。
清澈可不是隨意就能夠向大自然表白的,在大自然的形成過程中,對于河流的生態要求是極其嚴格的,不容任何舉動和方式褻瀆。
話又說過來,淇河是否清澈,這跟當地的生存和生活環境有著極大的關系,是唇齒相依的關系。唇亡齒寒。
七十一
春秋時期的許穆夫人對此早就有所觀察和認識,并多次賦寫詩詞以接近淇河的生態。
收集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里的《竹竿》《泉水》《載馳》3篇抒情詩,相傳,都是許穆夫人的深刻感悟和體會。
比如《竹竿》這首詩中,許穆夫人盡情地描寫出了自己少女時代對淇河(古稱淇水)生態的認識和留戀。
許穆夫人時常涉足于山水之間,特別是她遠嫁許國以后,時常懷念淇河之水。
猶如懷念父母的養育之恩,那清凌凌的淇河之水是她的思鄉之情啊!
在《泉水》這首詩中,許穆夫人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寫出了她為拯救衛國而四處奔走呼吁的哀號之情,并以此寄托著她的許多憂思。
而在《載馳》這首詩中,則抒發出了許穆夫人的迫切還鄉之情。
她歸心似箭,沖破重重阻力,終于佇立在淇河沿岸,并攜手父老鄉親,奮力抗擊北狄侵略的斗爭。該詩以此表達出她不顧個人安危,誓死捍衛家鄉的信心和決心。
她勇往直前,矢志不渝,為此從來沒有后退過一步。
這些詩詞即使今天讀來,依然可以感受到許穆夫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感情,字字句句,叩擊心扉,不忍釋手。
七十二
淇河之水宛如櫻城鶴壁的臉面,在清澈與櫻花之間,仿佛它們已經過漫長歲月的洗禮,許多回憶在我心里都掀起了波瀾,盡管有些看起來是很平靜的。
我與櫻城鶴壁,我與淇河的種種關聯,就像各個門類的藝術,看似毫無關聯,其實這些都是相通的,而且這種紐帶的關系似乎更加牢固。
這在久遠的時代依然如此,今天也是一樣。
偉大與渺小對于淇河而言,并不算什么負擔。就像背負著沉重的思念,我無論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放下。
如今對故鄉的思念,已經化作一對羽翼,扇動著飛向遠方的藍天。
因為,在離開家鄉的那一段時間,我的感受就是思念,多少年以后,我依然認同這種感受。
對故鄉的思念并非其他,日夜所思所想,今天想起來依然感同身受,而且這種欲望始終非常強烈。
這些都是來自于故鄉的情感元素,淇河的浪花奔騰在我的生命里,反反復復地出現,重重疊疊地推送,從來沒有出現過斷檔的時候。
作為淇河兒女,遙望著太行山,我確實還是有所牽掛的。
七十三
在我創作的許多文學作品里,幾乎隨時都可以看到有關淇河的內容,特別是淇河的自然面貌。
例如《奔騰的淇河是一匹駿馬》。
“奔騰的淇河是一匹駿馬/水的流動是馬的呼吸/魚兒的穿梭是馬的心跳/我的駿馬馳騁的地方,萬鶴翱翔/我的駿馬嘶鳴的地方,關山太行/這里山水富饒/這里綠樹掩映/藍天和鮮花融入歌唱/笑容和夢想不斷生長”
在這首描寫淇河生態的詩歌里,我并沒有直接去寫淇河的生態和水質問題,而是采用了一些意象,從側面勾勒出淇河的無限生機。比如馬、呼吸、心跳等這些鮮活的意象,直接把讀者的想象調動起來,讓讀者用想象來填補文字的留白之處。
這時的淇河,在讀者心里就仿佛一匹駿馬,直奔心靈深處而來。于是,這首詩歌的主題就鮮明起來、就鮮活起來,達到了一首詩歌的完整性、完美性。
淇河可以說是“清澈的太陽之神”,這個稱呼并非過譽之詞。
就我個人而言,認為淇河的真正價值與人類是密不可分的、是自然的、是天然的、是生態的,并非后天所為。如何保護淇河,與人類有著直接的關系,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當然,這必須有和諧的和科學的價值觀融入。
淇河宛如大自然的一尊生態雕像,在它流域內的任何一個河段,生命力都是茂盛的、充沛的、茁壯的以及充滿無限生機的。
而且,這樣的生機,似乎都已把淇河的生態性提高到了完美的高度。關于這一點,仔細審視淇河的方方面面均是存在的。
七十四
同樣存在的,還有一種清澈的對淇河的深刻感悟和領悟。
這些靜悄悄的變化,淇河沿岸的樹木花草都是我很熟悉的。它們身上的任何一個部位,都會留下真實的記錄。
換一個角度而言,這些樹木花草生命生長的記錄或細節,仿佛是大自然以一種生態方式告誡人類的語言。
魚兒的眼睛在河流里從來沒有混沌過,不清晰、不確切的地方,在它看來都不會影響什么,不會產生什么障礙或阻礙,或者說什么都不會發生。
它的魚鱗漲滿渴望,它的尾巴在左右擺動之中,始終把握著前進的方向。仿佛大自然的一種神秘力量,已儲蓄在魚兒的血脈里。
七十五
花兒的色彩是否這么繽紛過?春天的腳步是否這么燦爛過?
即使春天的腳步姍姍來遲,依然不會影響花兒的到來。最燦爛的綻放,最馨香的繽紛。
每一朵花瓣都是春天最美麗的問候,人們在冬天的寒冷里期待已久,十分迫切。
花兒一旦綻放,人們寒意濃濃的笑臉,就會脫胎重生,就會得到陽光暖暖的第一縷撫摸和撫慰。
草兒的葉片在風中搖曳的時候,這難道是它對春天的呼喚?
葉片上的露珠在陽光下是那么晶瑩,是那么通透。仿佛春天的微笑遺落在淇河沿岸,遺落在清澈的波紋里。仿佛滴落的鳥鳴滾動在葉片上,融化在一縷縷陽光里。仿佛風姑娘的倩影時隱時現,仿佛綠色的田野里大片大片的麥子閃亮登場,忘我成長。
一棵棵櫻花樹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河流里,成為春天一幅幅美麗的剪影。
驚奇悅動,目光亂飛,并非收獲季節,淇河沿岸就已結出豐碩的旅游成果。
喜悅隱藏在花香背后,櫻城鶴壁的審美品位正在逐步提升。此時,河面上一排排柳樹的枝條仍在風中來回擺動著春天的心情……
七十六
若從某種意義上來審視的話,櫻城鶴壁更需要自己的生態雕像,這對于一個有品位的旅游城市而言是極其重要的。
雕像的誕生就像淇河的姿態一樣是逐步完成的,自然的生長發展到今天的生態規模,這是夢想家的力量,這是順勢而為的碩果。
生態就像河流一樣在這里生長,并不斷地擴大。
當淇河從遠古時代的混沌之中一覺醒來的時候,它的姿態似乎已經成熟,盡管這種姿態還屬于幼年期。
幾千年一路走過來,遙遠的征途上,淇河的生態就像大自然的一個側影。
多少個世紀之后,它的浪漫之途仍然會超出人類的想象和認知。
當淇河的腳步跨入這個新時代,一排排櫻花樹高高舉起的臂膀上,始終挺立著生態的色彩。
除了櫻花的馨香,在淇河的記憶深處映現出多少歷史朝代?輝耀著多少燦爛的歷史文明?盡管最后都已沉入泥土和夢鄉。
七十七
歷史上的這些朝代頭枕著淇河入睡,可它們萬萬沒有想到今天的淇河生態,經過三千多年的養精蓄銳之后,已經遍布生態的顏色。
看那浩浩蕩蕩的蘆葦蕩,別看它們在風中搖曳不止,但它們的認知卻是上千年的。
為此,它們已經準備好了無數個日日夜夜。
當我的腳步一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期待已久的感覺就像春天的小草露出來一星半點的嫩芽。
這些跡象的顯現,無疑是我跨入生命里春天的第一步,久久等候的第一步。
七十八
關于故鄉的淇河,我可以這么說,它就像血脈里的一條有溫度的河流,日夜奔騰在我的生命里。
它有時會以思想的方式激勵著我,有時會以意志的風暴沖擊著我,有時會以靈感的方式讓我平靜下來,漸漸地創作出許多有關淇河的文學作品或思念故鄉的詩歌。
例如詩歌《淇河邊的山妞兒》。
“那個黃昏在淇河邊兒/山妞兒簡直應了一句古諺/她的目光癡立在巖石上/暴風雨多次勸她回去/但她依然執拗地在等待/遠方的林子讓她倍感孤單/美麗的倩影映入河流的清澈/寂靜聽得清楚/手帕撫摸著淚水說太涼/那個黃昏在淇河邊兒/山妞兒向著遠方眺望/期待猶如河流里/一朵搖曳的荷花那么耀眼/像流水,像含情的垂柳/她的臉頰貼著柔波的耳邊/悄悄地訴說著/酒窩里莫名的惶惑/思念激起的漣漪/讓靜靜的月光/親手交給模樣很俊的淇河”
千里之外,時常可以看到身后故鄉的影子。
故鄉向我走來的時候,腳步是那么堅定,堅定之中透著清澈的自信,宛如淇河考驗著我、關切著我。
櫻花林灼痛了我,太行上托舉著我,鶴鳴湖映照著我,古靈山上聳立著我,云夢山回應著我,大伾山深刻了我,五巖山醫治著我,阿斗寨想起了我,金線河思念著我……
七十九
在異鄉,思念猶如餓狼,折磨著我的許多過往。
一切思念都沉醉于淇河,就像饑渴的人突然看到了生命之泉。于是,我的堅持挺立了起來,我的生命堅強了起來。
在我消瘦的生命里,淇河依然茁壯生長,以至于跨出去的每一步都像淇河的波浪,始終處于奔騰狀態。
沿著河岸走啊走啊,行走之中的軀體里不時傳來淇河的水流之聲。
河流在我的軀體里,猶如一個生態的世界,讓我成長起來,就像思念把我推送到了遠方。
淇河在我的思念里流啊流啊,以至于我的手臂伸出來的時候,淇河之水就沿著這個方向,向前流著、流著。
盛開的手指猶如它的浪花,更像水流之聲。因為,它已經把我引領到一個廣闊的靈魂深處。
(責任編輯:孫婷)
田萬里 1963年生,河南鶴壁人,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4 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河南日報》《中國作家》等數十家報刊。曾獲“中國當代散文獎”“當代最佳散文創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