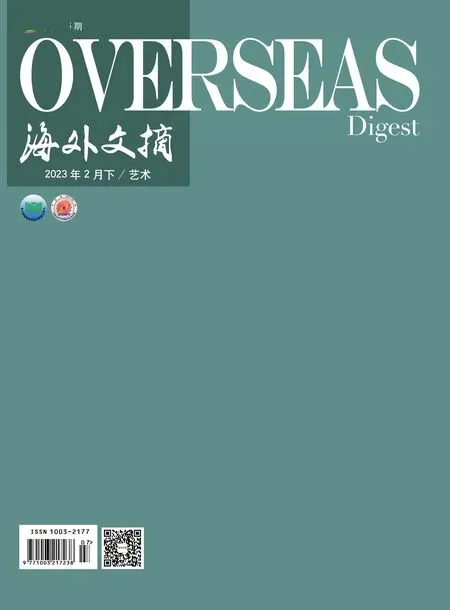論中俄形象學與印象學的歷時比較與鏡鑒
□李明達 王丹/文
形象學從西方傳入中國和俄羅斯。印象學不同于形象學,是由俄羅斯創立的一門新興學科。形象學作為一門科學,是研究歷史形成的動態自然的異國文化形象。印象學則是基于某目的人為地創造的形象。我國缺少對俄羅斯印象學的研究,而是引入西方形象學理論進行研究,西方形象學理論也在國內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我國形象學主要以研究對象、學科界限、中國形象在異國文學的研究、異國形象在中國文化的研究四個維度展開。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厘清真實的、非人為塑造的國家形象,是對我國國家形象提升的鏡鑒。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形象學”和“印象學”作為兩門獨立學科在中國和俄羅斯的歷時發展進程,指出各自理論的源起,各時期中俄學者對學科的理解,概念的異同及其發展特點。
1 研究意義
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一直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中俄兩國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正值中俄建交70周年之際,雙方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21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中俄雙方對該條約予以延期。雙方在政治外交、經濟合作、軍事演習、歷史交流、文化互動等多領域建立合作關系。當前,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對全球戰略結構的變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際的背景下,確立國家形象及其定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尤其對我國而言,認識俄羅斯形象,消除對俄羅斯的刻板印象是加深兩國友好交往,全新、全面、客觀認識俄羅斯的前提,吸收國家形象、國家印象的養分也是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有利鏡鑒。目前,國家形象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話題,但對國家形象、國家印象概念的誤解,往往造成對異國形象的認識偏差。因此,科學地解讀國家形象、國家印象,將其上升到學科領域,從認識中俄兩國形象學、印象學的基本概念出發,認清學科在語義和各階段歷時發展的變化,在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的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2 俄羅斯形象學、印象學的歷時研究
西方學者對“形象學”“印象學”的起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20世紀50年代的歷史比較文學研究中,形象學(имагология)的創始人是法國學者瑪麗·卡雷和M·F·基亞。他們認為不再需要關注一種文學對另一種文學的虛幻影響,而要試圖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的虛幻神話是如何在個人或集體意識中發展演變的。他們試圖將學者們的注意力,從文學問題轉向對“異國”的接受問題。
西方學者之后,俄羅斯學者對形象學的概念進行了詳細且深入的研究。
霍雷瓦(2005)指出,形象學的任務是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生活的真假認識,研究社會意識中對國家起源、發展模式、社會角色存在的偏見和刻板印象[1]。博爾多瓦(2006)寫道,形象學是自我認同的論述,同時是認識異國的話術[2]。保爾科夫(2008)認為,形象學具有歷史特點,其任務是分析其他民族形象的源起、內涵及歷史變異[3]。埃戈羅瓦(2008)指出,形象學研究的是主要大國間的相互博弈:俄羅斯-美國,俄羅斯-西歐國家,廣義上講,是 “東-西”的對峙,在彼此關系中存在寬容的可能性[4]。季莫申科(2012)強調形象學在學理上填補了對國家、民族形象預估不足的空白,為國家領導實施外交策略提供依據和預判[5]。
在當代社會,形象學不再完全依賴文學研究,而是逐漸涵蓋其他人文學科領域,出現了跨學科研究。一些俄羅斯和外國學者從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角度從事形象學研究,并重新定義了形象學的概念。亞森科(1999)將形象學視為文學研究框架下的理論,是歷史-文學學科,被定義為“形象學說”。諾依曼(2001)將形象學作為文化學或社會學研究的分支,認為形象學是對參與群體間文化對話的認識。梅津(2010)將形象學作為歷史學科的分支,旨在探索某一歷史階段在某國家的社會意識中形成的對另一國家或民族的認識[6]。總而言之,形象學在長期的發展中沖破了文學研究的框架。
形象學的基本原則是以認識異國形象為開端,再看自己(本國形象),以促進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的認識。其主要特征是,在不同人文社科領域構建異國形象的演變過程。換句話說,形象學研究的是如何理解和分析異國形象的社會文化起源。
除了來自西方的形象學,在俄羅斯學界還有另外一門人文社會學科,被稱為“印象學”(имиджелогия)。印象學的發展離不開俄語詞根“印象”(имидж)的概念。印象廣義上是有目的地形成個人、現象、物體的形象,以產生對某人情感或心理上的影響,通過推廣、宣傳獲得持續的認可及威信。因此,“印象”是印象學的核心基礎。“印象”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最初用于廣告宣傳中。20世紀60年代,這個術語再次出現在營銷活動領域,作為對消費者心理影響的主要手段。
印象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俄羅斯,此前都沒有這樣的學科和應用方向,它被認為是俄羅斯的學術產物,對印象學而言,研究印象形成的機制不僅是理論需要,也具有應用型特點。謝普被認為是俄羅斯印象學的創始人。1994年他出版專著《印象學:個人魅力的秘密》,提出了印象學的術語概念,形成科學研究的新領域,并將其引入俄羅斯的日常生活中。
印象學是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建立特定的、具體的甚至是對某人某物故意虛構的形象。波切普佐夫(2001)提出印象學是體現大眾傳播現象的學科[7]。彼得羅瓦(2004)認為印象學應該研究人、組織、商標、物品、服務形象的形成規律、功能及管理模式[8]。帕納修克 (2007)將印象學定義為形成(個人、組織、商品)形象的理論、實踐學說,旨在為職場環境重塑形象,推出科學的方法依據及實施方向[9]。貝科娃(2014)指出,印象形成的歷史條件,促進了印象學作為當代人文學科的迅速傳播[10]。綜上可見,印象學研究的是印象塑造的過程及規律。
如今,印象學的概念廣泛應用于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衛生領域等。2002年, 俄羅斯成立了印象學研究院,印象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受到普遍重現。很多大學通識教育和職業教育院校成立形象學系,開展教學。印象學作為高校的必修科目,主要培養文化工作者及公共關系專業人才。
科茲洛夫(2015)指出,一些學者認為形象學是一種創建印象的學科,實則并沒搞清“形象學”和“印象學”的差異。印象學的詞根是印象而非形象,印象學在“培養個人魅力”和“創建和塑造實用型綜合印象”兩個方向得到應用和發展[11]。其實兩門學科有所不同,有必要區分開來。
“形象學”“印象學”是在本國文化里研究異國形象及其文化的基礎。他們的異同在于:
(1)形象學的研究對象是“異國”文化、民族、國家的形象,是在接受者文化中自然形成的動態過程;而印象學的研究對象是專門塑造某人或某物正面形象的過程和方式。
(2)印象學是對各個群體(個人、組織、社會和整個國家)形象的構建與重構;而形象學不能用來研究個人形象。
(3)形象學作為一門學科,研究歷史形成的動態的、真實的、自然的異國文化形象,本質上是研究文化的歷史,以“他-我”二元對立原則為基礎,通過研究異國形象,映射本國文化的形象,以促進跨文化交流及相互理解;印象學研究某人或某事被塑造的人為的、有目的的形象,借助多元化的宣傳,以廣告、大眾媒體、公共關系等手段,獲得持續的認可和權威。
3 中國形象學、印象學的歷時研究
在20世紀90年代,形象學逐漸傳入中國,近年來在中國迅速發展,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形象學基于比較文學在中國出現,其傳播、發展離不開我國學者孟華的貢獻,她在其著作《比較文學形象學》中提出的形象學概念,在中國學術界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孟華(2000)強調,形象學在“本國與異國”語境中(根據二元對立原則)很少關注文學與文化的關系[12]。 以比較文學為出發點研究他國形象不夠充分,逐漸被新學科形象學取代。基于形象學研究異國形象在我國得到積極發展,在我國形象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個方面:研究對象的問題、學科界限的問題、中國形象在異國文學的研究、異國形象在中國文化的研究。
3.1 研究對象問題
形象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是異國異族形象,即他者的形象。形象學始終研究的是對“我”與“他者”間文學、文化關系的關注。姜智芹(2008)從跨文化的角度認為,一個民族在他國所呈現出來的形象類型并不在于它是否與現實相符合,而在于它能否引起各民族間一系列的刺激、反應或互動,是否誘發了有意義的變革,并對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13]。趙穎(2011)指出,通過自身文化與他者的文化比較、交流、詮釋形成的“他者形象”深藏了本土對異族或異國文化的整體看法、態度、觀點和立場,而“他者”的“形象”也映射出某種對本土的文化的態度、看法以及觀點和立場[14]。由于不同國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它并不要求從史實和現實統計資料出發原樣復制異國形象,而只是一個幻象,一個虛影。作者對他者的曲解、夸飾和想象是必然的。彭偉(2014)認為異國形象呈現兩種類型:烏托邦形象和意識形態[15]。烏托邦化的形象質疑本國社會秩序,趨向于對異國形象的美化。意識形態指作家在依據本國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范式表現異國,對異國文明持貶斥否定態度認同和顛覆都是相對的,很難截然分開。
3.2 學科界限問題
中國學者擴展了學科界限,形象學已不再局限于文學領域,從文學形象轉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形成了跨文化形象學這一開放性的研究領域。周寧教授率先提出了跨文化形象學這一概念。從跨文化的角度關注不同文化體系中的異國形象。跨文化形象學超出了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范圍。從虛構的文學文本延伸到其他不同類型的文本,諸如游記、傳教報告、日志、外交文件著作等,拓展了異國形象研究的取材范圍和研究對象。隨著當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電影、電視、報紙、雜志等媒介上的異國形象更值得研究。
鄧繁榮、鐘帆(2012)認為,形象學與其他學科聯系,有助于更充分地了解異國形象,更深入地揭示在不同文化群體間對異國文化結果的想象[16]。可以說,形象學的貢獻在于,它為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平臺。
3.3 中國形象在異國文學的研究
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已有涉及。陳受頤先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形象的論文,如《18世紀歐洲文學里的趙氏孤兒》《魯濱遜的中國觀點》《18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等。1929年,作家鄭振鐸寫了一篇題為《西方人所見的東方》文章,批評了西方語境中的中國形象。他認為中國形象被西方人曲解了。他寫道:“東方離西方真的很遠,對西方而言的東方處在被西方人制造的濃霧之中。[17]”
規模較大的要數周寧等編著的《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學苑出版社,2004年出版),該系列叢書探討自馬可·波羅時代以來7個多世紀西方對中國形象認識的演變過程,觀察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由此可見,中國的形象研究多存在于文學研究領域,以具體的文學作品研讀實踐形式面世,但理論探討不多。
3.4 異國形象在中國文化的研究
與異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相對, 研究中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也是形象學的重要領域。然而,目前的研究形式卻呈現不平衡性。中國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研究異質文化的“本我描述”,關于異國文學的中國形象專著與論文較多,研究中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則相對較少。而實際上研究本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同樣也是形象學的傳統課題,只是仍處在探索、起步階段[18]。目前異國形象在中國文化的典型專著有姜智芹的《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姜源的《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我國學者認為,異國形象在中國文化的研究對了解他者形象、加強文化交流有著巨大的作用。
研究中國的俄羅斯形象始于1996年發布的一項題為《俄羅斯形象在中國》的問卷調查。潘德禮、吳偉(2007,2008)發布的兩項社會調查《中俄兩國良好關系的印證——“中國人眼中的俄羅斯”》《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日益親近是中俄關系不斷發展的基石——2008年度“中國民眾的國際觀”國情調查俄羅斯部分》,成為中國學界解讀俄羅斯形象的重要嘗試。柯惠新、鄭春麗、吳彥(2007)在《中國媒體中的俄羅斯國家形象——以對〈中國青年報〉的內容分析為例》的文章中,分析了《中國青年報》建立的俄羅斯形象。李隨安探尋了異國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認同、誤讀、過濾等現象,揭示了這些現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動機,闡釋了不同文化中異國形象的復雜性和多元性。2012年他出版的專著《中國的俄羅斯形象》,首次詳細地研究1949—2009年間中國的俄羅斯形象,書中根據友好、對抗、正常化的歷史分期,將俄羅斯形象分為正面、負面、客觀形象三個階段。
4 結語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需要對各國國家形象及國家印象進行辨識。“形象學”“印象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在我國及俄羅斯發展迅速,我國從西方引入形象學,并借鑒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四大研究方向。我國沒有引入俄羅斯的新興學科——印象學。俄羅斯學界對國家形象主要有兩種研究方向:其一,沿襲西方傳統學科的形象學,其二,派生出具有俄羅斯特色的產物——印象學,兩門學科存在本質不同,在不同階段發揮各自作用,并形成跨學科多領域研究視角。對我國而言,通過形象學理論及衍生的俄羅斯印象學觀點,厘清形象學-印象學之間的異同及發展特點,理解在我國文化、民族意識中認識的是歷史上形成的客觀、自然、動態的俄羅斯形象,而非人為的被塑造的俄羅斯形象(俄羅斯印象),以促進中俄兩國各領域的深入了解和發展。■
引用
[1] Хорев,В.А.Польша и поляки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литераторов: имаголог.Очерки[M].М.: Индрик, 2005.
[2] Болдова, Т.А.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ская и м а г о л о г и я [J].В е с т н и к В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6(14):114-115.
[3] Поляков,О.Ю.магология в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м науч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J].В естник В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8(4):8-10.
[4] Егорова, Л.П.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й имагологии[C].//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авказ: сб.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уч.-практ.конф.Сочи, 2008.:7-11.
[5] Тимошенко, О.А.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заимо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и и Норвегии в XX веке: образы и стереотипы[J].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2012(6):28-32.
[6] Ощепков А.Р.Имагология [J].Знание.Понимание.Умение.2010(1): 251-253.
[7] Почепцов, Г.Г.Имиджелогия[M].М.:Рефл-бук; Киев: Ваклер, 2001.
[8] Петрова, Е.А.Имиджелогия: проблемное поле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J].PR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и.2004(1):36-38.
[9] Панасюк, А.Ю.Имидж: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M].М.: РИПОЛ классик, 2007.
[10] Быкова, Е.Е.Имидж как реклама лич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J].Вестник НГТУ им.Р.Е.Алексеева.Сер.: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с о ц и а л ь н ы х с и с т е м а х.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2014(4): 66-73.
[11] Козлова, А.А.Имаг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 е т о д в и с с л е д о в а н и я х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ы[J].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2015(3):114-118.
[12] 孟華.形象學研究要注重總體性與綜合性[J].中國比較文學,2000(4):1-20.
[13] 姜智芹.中國:英國的典范:17-18世紀英國文人眼中的中國[J].國外文學, 2008(3): 58—63.
[14] 趙穎.略論當下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四組爭議[J].世界文學評論,2011(2):265-268.
[15] 彭威.跨文化形象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及存在的問題[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14(3):308-311.
[16] 鄧繁榮,鐘帆.國內外形象學研究的現狀分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33(S1):195-197.
[17] 鄭振鐸.西方人所見的東方[J].小說月報,1929(1):20.
[18] 伍依蘭.形象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前景[J].社會科學論壇,2009(6)1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