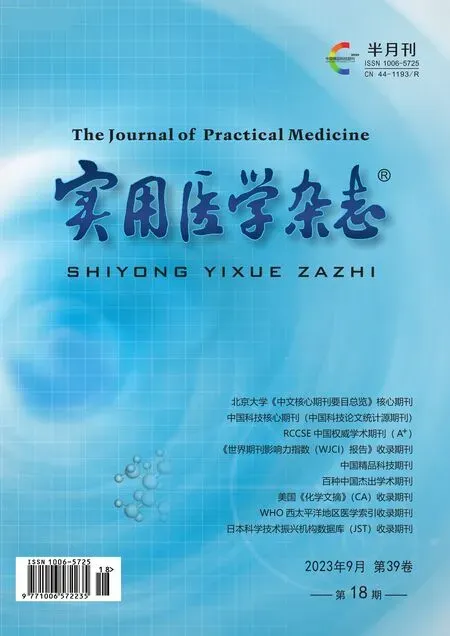尿石素在精神疾病中的神經調節作用及應用前景
黃正元 趙麗蓉 張珂璇 王高華 周本宏,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 1精神衛生中心,2藥學部 (武漢 430060);3武漢大學藥學院 (武漢 430062)
精神類疾病是復雜的疾病,與遺傳、神經發育、感染等因素有關,同時還受到社會和心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是生物-心理-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1]。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療藥物非常有限,在新藥的開發上暫無大的突破,因此,開發有效預防和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尤為迫切[2]。鞣花酸是廣泛分布于石榴、草莓及胡桃等水果或堅果中的天然多酚類化合物,其在自然界中主要以縮合形式的鞣花單寧存在,而鞣花單寧和鞣花酸的生物利用度極低,部分未被吸收的鞣花酸則在哺乳動物胃腸道菌群的作用下代謝成更易吸收的尿石素類物質[3]。研究發現,尿石素類物質是鞣花單寧和鞣花酸在體內發揮生物活性的物質基礎[4]。近年來,有關尿石素生物活性、體內代謝過程與組織分布以及神經系統調節作用機制吸引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并在神經系統保護作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已經證實尿石素可以通過血腦屏障在多種神經疾病中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凋亡的潛力發揮有效的神經調節活性[5]。目前,尿石素應用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尚未見相關報道,關于尿石素在精神疾病中的神經保護作用知之甚少。
盡管目前的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但尿石素作為一種天然的生物活性物質,發揮著強大的神經調節作用,對于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癥狀和促進康復可能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前景,有潛力成為精神疾病預防和治療的新型策略之一。因此,本文對尿石素的結構分類以及尿石素的生物活性及在精神疾病中的可能調節機制進行總結,以期為尿石素在精神疾病中的進一步的研究和臨床藥物開發及靶點應用提供新思路。
1 尿石素的結構和分類
天然尿石素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見,但作為鞣花單寧或鞣花酸的代謝產物卻廣泛分布于哺乳動物的尿液、糞便和膽汁中[6]。GARCíA 教授采用腸道微生物體外代謝實驗技術首次證實尿石素是由鞣花單寧和鞣花酸的代謝產物,鞣花酸在腸道菌群內酯酶作用下失去一個內酯結構,然后從不同位置連續失去多個酚羥基之后逐漸形成至今已發現的尿石素A、B、C 等10 余種代謝產物。鞣花酸失掉內酯環后首先得到尿石素M-5,然后在不同位置脫羥基后生成尿石素D、尿石素E 和尿石素M-6 等幾種四羥基尿石素異構體,隨后的修飾導致四羥基尿石素失掉一個羥基后得到尿石素C、尿石素M-7 等三羥基尿石素,再失掉一個羥基得到尿石素A(Urolithin A,UA)及其異構體,最后在結腸微生物的作用下得到單羥基的尿石素B(Urolithin B,UB)[7]。鞣花單寧和鞣花酸的腸道微生物代謝途徑,見圖1。

圖1 鞣花單寧和鞣花酸的腸道微生物代謝途徑[7]Fig.1 illustrates the metabolic pathways of tannins and gallic acid by gut microbiota
2 尿石素的生物活性及在精神疾病中的可能調節機制
近年來,尿石素豐富的生物活性引起了廣泛關注,主要集中在其抗炎、抗氧化應激、抗凋亡、調節腸道菌群以及調節線粒體自噬功能上,并已驗證尿石素在神經精神疾病中具有有效的神經調節作用[8-9]。
2.1 抗神經炎性損傷 神經炎性損傷主要是存在于中樞神經系統中由多種病理損傷。研究發現,UA 和UB 可降低由脂多糖誘導后小膠質細胞的一氧化氮水平,通過抑制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磷脂酰肌醇3 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信號通路的激活來抑制促炎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表達,發揮抗神經炎性損傷作用[10]。此外,UA 可以調節腸道變形菌的分布和重塑來調節炎性因子白細胞介素-10、白細胞介素-17 的平衡和轉化生長因子-β 的的釋放,在神經細胞炎癥反應調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1]。研究[12]發現,神經炎性損傷與抑郁癥密切相關,抑郁癥的患者血清中IL-1β、IL-6 和TNF-α 等表達增高,在尸檢報告中這些促炎癥因子同樣表現出高水平表達。同樣,精神分裂癥患者腦脊液中促炎癥因子水平明顯升高,而這一過程依賴于小膠質細胞的活化[13-14]。研究發現,UA 可通過降低IL-6 和TNF-α 濃度,抑制人類神經母細胞瘤細胞和BV2 小鼠小膠質細胞的神經炎癥,通過防止神經炎癥途徑來增強神經元細胞活力,從而防止小膠質細胞的過度活化。還有研究發現,UA 可以通過激活AhR-Nrf2 依賴途徑來改善TNF-α 和IL-6 的生物合成,上調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預防炎癥的發生[15]。另外,UA 還可減少表現出阿爾茨海默病病理生理學的APP/PS1 轉基因雌性小鼠的神經炎癥,防止學習和記憶缺陷,并減輕斑塊產生和Aβ 水平和反應性膠質增生[16]。由此可見,小膠質細胞本身就是中樞神經系統中對抗外來損傷和病原體的重要防線,中樞神經系統過度的炎癥反應能激活小膠質細胞從而導致促進促炎細胞因子和神經毒性因子的釋放,進而引發神經炎癥。而尿石素類化合物,可以抑制小膠質細胞促進促炎細胞因子和增加抑炎因子的分泌,緩解因炎癥帶來的神經損傷,具有潛在的神經調節作用和應用前景,可為精神疾病炎性損傷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思路。
2.2 抗氧化應激 氧化應激失衡是生物體內氧化與還原反應作用失衡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使線粒體功能出現障礙,產生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ROS 可作用于中樞神經系統誘導神經元變性死亡,從而影響神經細胞間的信息傳遞和修復功能,加劇學習和記憶的缺陷[17]。研究[18]發現,UA 能提高氧化應激下小鼠腦神經瘤(mouse brain tumor cells; neuro-2a,Neuro-2a)細胞的過氧化氫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清除Neuro-2a 細胞中產生過量的ROS,保護神經元免受氧化應激損傷。氧化應激在抑郁癥的發病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它導致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神經組織損傷以及神經可塑性下降,進而導致認知功能障礙[19]。在一項患有與年齡相關記憶問題的老年受試者中,連續4 周飲用8 盎司石榴汁的個體表現出血漿中UA 代謝物水平和視覺記憶的顯著改善[20]。研究[21]還發現,UA 通過調節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蛋白的核轉位,從而抑制氧化應激并給予小鼠腦神經瘤細胞神經保護作用。同樣,精神分裂癥患者早期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與認知障礙呈正相關[22],這說明氧化應激和線粒體功能障礙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的早期信號。研究發現,在D-半乳糖處理的衰老小鼠中,UB 阻止了ROS 促進的腸道免疫反應,調節NADPH 氧化酶亞單位和血紅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 1,HO-1)表達抑制活性氧生成,顯示出抗氧化作用[23]。氧化還原狀態的改變是由自由基生成和抗氧化劑防御機制之間的不平衡引起的,在精神疾病患者中這種不平衡加速了神經元變性和凋亡的生理功能。因此,保護神經元免受氧化應激損傷是治療精神疾病的一種有效手段,而鞣花單寧的腸道微生物轉化產物尿石素類化合物可作為一種有效的抗氧化劑,可減緩ROS 引起的精神疾病神經元氧化應激反應,這可能是其發揮神經調節作用的原因之一。
2.3 抗細胞凋亡 細胞凋亡是一個主動的由基因決定的程序性死亡過程,與細胞色素C、p53、TNF-α 等有關,同時促凋亡蛋白(Bax、Bad、Caspase-3)與抗凋亡蛋白(Bcl-2)之間的平衡在細胞死亡/存活的調節中起重要作用[24-25]。慢性應激會導致抑郁癥患者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下調,而BDNF 是發育成熟的神經元功能的調控因子和神經元受損的存活和促進再生的必須因子[26-27]。研究[28]發現,鞣花酸可能通過調節5-羥色胺能系統和BDNF之間的相互作用,引起抗凋亡蛋白Bcl-2 的激活,從而發揮抗凋亡作用。另外,與蛋白激酶B 磷酸化相關的Bad 磷酸化在D-半乳糖誘導的衰老小鼠中被UB 顯著上調,而Bad 可通過的PI3K/Akt 途徑和神經元中(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介導的死亡途徑之間的信息整合,作為存活和凋亡信號的分子開關,維持神經細胞和組織的穩態[29-30]。同時,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的腦細胞改變與大腦細胞凋亡的形態學特征相似,細胞凋亡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發病機制中的重要環節之一[31-32]。研究[33]發現,在D-半乳糖暴露的衰老模型小鼠腦老化過程中,海馬和大腦皮層中TUNEL陽性細胞總數增加,D-半乳糖促進Caspase-3的激活誘導凋亡途徑,對其使用UB后,發現TUNEL陽性細胞的數量下降,Caspase-3 的激活也被抑制,起到神經保護作用。還有研究[34]發現,UB 可明顯阻斷D-半乳糖衰老小鼠腦組織中膠質纖維酸性蛋白的激活和表達,減少神經細胞的凋亡,起到神經保護作用。越來越多的數據支持神經元細胞凋亡可能是導致精神疾病進展的有利證據,因此,防止神經元細胞凋亡也是治療精神疾病的一種有效手段,尿石素類化合物可靶向作用于凋亡相關蛋白如細胞色素C、Bad 和Caspase-3 等來抑制細胞凋亡,這可能是尿石素類化合物改善精神疾病神經元活性的潛在方法。
2.4 調節腸道菌群 腸道菌群參與宿主代謝、能量調節、免疫發育等各項人體生命活動,在調節腸-腦通信中起重要作用,由此,“微生物-腸-腦軸”的概念應運而生。近年來,隨著對精神疾病發病機制和腸道菌群穩態的深入探索,發現大部分神經精神疾病與腸道菌群的組分和結構穩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腸道微生物通過微生物-腸-腦軸對宿主的應激反應、情緒和認知功能產生重要影響,對腦功能、神經發育有重要意義[35]。研究表明,UA 通過上調重組與合成蛋白(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依賴性上皮細胞連接蛋白來增強腸上皮細胞的屏障功能,直接調節腦活動[36]。另外,UB 可以調節腸道菌群組成,削弱衰老小鼠的腸道免疫功能,重塑腸道微生物群落來調節腸道微生物平衡,調節各種神經遞質分泌,起到神經保護作用[37]。還有研究[38]發現,UA 還可以抑制p53 介導的腸道微生物的重塑來起到神經保護作用。因此,調節微生物-腸-腦軸,可作為精神疾病防治的新方法。尿石素可以調節腸道菌群的組成和平衡,增強腸道黏膜的完整性和屏障功能,防止有害物質通過腸道黏膜進入血液循環,防止炎癥反應和神經系統的異常激活,維護腸腦軸的正常功能。同時,還可以調節腸道免疫系統的活性,促進免疫細胞的平衡和功能,調節神經遞質的合成和釋放,改善情緒、認知和行為。這些為深入理解腸腦軸的調控機制,并探索精神疾病的治療策略提供了新的視角。
2.5 調節線粒體自噬功能 線粒體自噬是線粒體在受損或應激后通過選擇性的靶向清除多余或受損線粒體來維持動態平衡的過程[39]。當激活有絲分裂的蛋白水平降低時,線粒體選擇性自噬的啟動受到損害,導致功能障礙的線粒體聚集[40]。電鏡下可見抑郁癥表現出線粒體數目減少和形態結構異常,包括腫脹、空泡性變、內嵴排列紊亂,甚至溶解消失等[41]。研究[5]發現,UA 通過SIRT1-PGC-1α 信號通路維持大鼠腎上腺髓質嗜鉻細胞瘤克隆化的細胞株(pheochromocytoma cells,PC12)細胞和多巴胺能神經元的線粒體形態,誘導線粒體生物合成來恢復線粒體功能發揮神經保護作用。此外,RYU 等[42]發現UA 能通過激活秀麗隱桿線蟲線粒體自噬功能,減緩神經精神性疾病發生發展,進而延長其生命周期。研究[5]發現,線粒體功能障礙是阿爾茨海默病早期中最上游的標志性病理的缺陷,而UA 通過激活自噬和沉默調節蛋白1(sirtuin 1,Sirt-1)有效抑制NF-κB 乙酰化和Aβ 產生。另外,在D-半乳糖誘導的衰老小鼠模型中報道了UA 可通過激活Sirt1/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號通路,誘導海馬自噬來預防腦相關認知缺陷[43-44]。由此可見,中樞神經系統中線粒體功能障礙或相關蛋白缺失后會影響線粒體轉運,誘導神經元線粒體缺失導致神經傳導障礙,而尿石素通過調節自噬過程,促進自噬的誘導、平衡自噬通路、保護神經元免受損傷,使自噬的活性與途徑的選擇保持適當的平衡,這有助于神經細胞對特定的損傷或應激作出適當的自噬反應,維持細胞穩態,從而改善神經精神疾病的發展和進程。因此,改善線粒體功能障礙可作為前期干預精神疾病的重要突破點,這為開發尿石素在精神疾病中基于自噬調節的治療策略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潛力。
3 展望
隨著“精神藥理學3.0”時代的到來,人們把研究重點放在了精神藥理學機制的研究上[6,45]。尿石素是一類在神經系統具有明確生物活性的天然代謝小分子化合物,可通過特有的神經調節功能發揮神經保護活性,但因其在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可利用的結論不夠充分,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在藥理學方面尿石素神經相關活性與其化學基團的關系尚未有研究,目前對于尿石素的研究僅僅是停留在其生物功能上,其結構生物活性同樣值得深入探究,因此,對尿石素有效的結構成分以及神經精神疾病方面的活性潛力進行深入的研究,能為精神疾病的藥理作用機制研究提供新方向。其次,尿石素的生物學活性可在多種疾病模型中發揮作用,涉及神經、腫瘤、血管等多個系統,但其確切的作用靶點和通路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在神經系統中,其進入腦內作用的分子靶點及神經環路作用機制不明,仍需大量實驗研究來發掘。另外,尿石素系列化合物水溶性差的問題需要解決,雖然目前正在開發一種可生物降解的膠囊納米顆粒來包裹尿石素以增加生物利用度的靶向治療方法,在提高存活率和減輕氧化應激方面顯示出有希望的結果[47],然而,這些對于尿石素的臨床精神藥理學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人體中進一步測試,才能了解轉化的意義。ANDREUX 教授首次對UA進行了基于人體的藥物安全研究,在對健康的老年人進行了為期4 周的單劑量或多劑量UA 給藥后,結果發現UA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用500 mg/d和1 000 mg/d 劑量的UA 治療4 周后,老年人的血漿酰基肉堿和骨骼肌線粒體基因表達得到調節。這些結果[48-49]表明,在人類定期口服UA 后,可誘導改善線粒體和細胞健康的分子特征。在后續的研究中,尿石素的臨床藥理學研究應該提上日程,將基礎與臨床結合起來,綜合評估尿石作為藥物的安全功效,有利于尿石素在精神疾病預防和治療中的藥物臨床轉化及科學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尿石素是一類結構和功能相似的天然活性物質,其代謝產物有十余種,但其神經調節作用研究的重點也是參差不齊,大部分是圍繞在抗炎、抗氧化應激、抗凋亡等生物活性展開研究,這樣使得尿石素的生物學功能的研究趨于碎片化,不利于發現和總結尿石素的全部活性,綜合來看,尿石素的神經調節功能并不是某種生物活性單獨在起作用,而是表現出多個活性相互促進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尿石素是否還存在其他更好潛在活性和功能可應用于精神疾病的神經調節過程,也是目前需要思考和驗證的課題,進一步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以深入了解尿石素的作用機制和臨床應用前景,為精神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的可能。
【Author contributions】HUANG Zhengyuan wrote the article.ZHAO Lirong and ZHANG Kexuan drew the figure.WANG Gaohua reviewed the article.ZHOU Benhong funded and revised the article.All authors read and approved the final manuscript as submit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