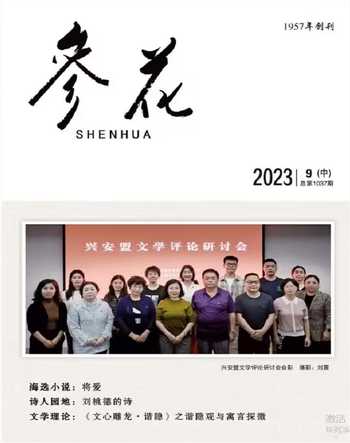溫暖淳樸的鄉(xiāng)情表述
散文的妙處,因人而異。九歌的散文《鄉(xiāng)村土宴》充滿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和時代色彩,展示了一幅原汁原味的北方鄉(xiāng)村生活畫卷。
文貴有情,真情實感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動力。《鄉(xiāng)村土宴》飽含九歌對家鄉(xiāng)的深情厚誼,圍繞二哥的娶親婚宴展開,籌備采買、送親迎親、喝酒吃菜,寫出了鄉(xiāng)村土宴喜慶熱鬧的氛圍,鄉(xiāng)情、鄉(xiāng)俗、鄉(xiāng)音,構(gòu)成了其散文的審美特質(zhì)。
北方民俗文化、鄉(xiāng)土氣息是《鄉(xiāng)村土宴》的敘事底色。
所謂鄉(xiāng)村土宴,就是鄉(xiāng)村的流水酒席,它不同于城市宴席的豪華排場,也不僅僅是把一群親朋好友請來吃個飯那么簡單。主家賓客、大人孩子、酒肉菜譜,處處有講究,每一處細節(jié)都透露著鄉(xiāng)民為人處世的世俗哲學(xué),也折射出鄉(xiāng)民樸素的智慧和鄰里間的人情百態(tài)。
鄉(xiāng)村土宴是父母為二哥娶親而準備的一場隆重?zé)狒[的結(jié)婚盛宴,買酒買菜、殺豬宰雞,掌勺的、落忙的、燒火的、做飯的、端盤子的,準備齊整,喜氣洋洋,披紅掛彩的二哥迎來了披紅掛彩的二嫂,按照婚禮儀程:坐福、點煙、開席,全屯子的老老少少熱熱鬧鬧地赴一場鄉(xiāng)村土宴。
鄉(xiāng)村土宴的特點是場面大、人多、熱鬧。場地是自己家開放的院子,家里的桌椅板凳、杯碗瓢盆當(dāng)然不夠用,所以都是借來的,款式不一、五花八門;條桌、炕桌、四仙桌、八仙桌,各具形態(tài),所有桌子“是從東西兩院前后街臨時借的,帶著各家的飯味菜湯水兒”;盅盤碟碗也是借來的,大小不一、雜花樣兒,各家的“盤子們”和主人們一樣待遇,“也能湊到一個桌上”,全屯子人隨禮湊份子,一悠、兩悠、三悠,流水席,吃完一撥人,再來一撥人。流水席雖然簡單,但是其中的傳統(tǒng)儀式和禮數(shù)還一直在,人們熱鬧著,也默默遵循著這些禮儀,如婚禮的過程“坐福”,紅布裹著的斧子塞進被褥里,巧妙借用“斧子”——福字的諧音,新娘子坐一坐,沾了福氣,幸福一輩子,這種習(xí)俗流傳至今,仍代代沿用;“清蒸白條雞壓在桌心,成了壓桌菜。桌長不發(fā)話不能吃,年老的不動筷不能吃,不到最后不能吃”。婚姻是人生大事,鄉(xiāng)民們一起見證著二哥二嫂的幸福時刻,連長生天也“罩著這屬于人間貧俗小民難得的喜樂”。在作者的審美觀念中,在平凡的敘述中,北方婚宴的習(xí)俗文化、鄉(xiāng)村淳樸的民風(fēng)展現(xiàn)了一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文化意蘊。
鄉(xiāng)村土宴的菜系說不上歸屬,但婚宴上的標準規(guī)格是不能簡省的。菜單子早就“劃拉”好了,四六八碟、煎炒烹炸、燜熘汆燉,南北薈萃,雞是整雞,魚是全魚,清蒸白條雞壓桌,然后紅燒鯉魚、獅子頭、紅燒肉、過油炸馃、掛漿蘋果一一上桌。獅子頭本是淮揚名菜,是將有肥有瘦的豬肉剁碎,配上荸薺、香菇等材料做成丸子,然后先炸后煮,配上翠綠青菜掩映,色彩誘人、香味撲鼻,是無法抵擋的美食。
但是在北方,獅子頭卻不叫獅子頭,叫肉丸子,“汆丸子,炸丸子,四喜丸子”。在大馬勺的工序里,“丸子出鍋,掌勺的拿筷子中間來一下,大小不管,人人有份兒就得。丸子餡趕上啥算啥,遇上材料不足,豆腐渣芡粉面子,倒油摶和,炸出來一模樣。”這完全是改良版的“獅子頭”,透著當(dāng)?shù)厝穗S機應(yīng)變的靈活與淳樸的智慧。鄉(xiāng)村土宴上,紅燒肉也不叫紅燒肉,叫老虎肉上席,非常具有地域性特色,之所以叫“老虎肉”,并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有引申含義,說明這是一道硬菜,全是肉,肉多,扛吃。鄉(xiāng)村土宴上多美食,這里有南北飲食文化的交融,更有鄉(xiāng)土風(fēng)俗文化的底蘊滋養(yǎng),雅俗共存、魅力無窮。
品讀《鄉(xiāng)村土宴》,有時代記憶,也有生活氣息。
好的散文是發(fā)自內(nèi)心、真實平淡的。汪曾祺曾說:“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鄉(xiāng)村土宴》記錄了真實平淡的現(xiàn)實生活,是社會發(fā)展到某一階段的縮影創(chuàng)作。
鄉(xiāng)村土宴流行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九歌熟悉熱愛這一片土地、山水、人情,截取鄉(xiāng)村生活的一個側(cè)面,真實反映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遷。他描寫了一場鄉(xiāng)村土宴中的流水席,鄉(xiāng)里鄉(xiāng)親、豬肉老酒、土生土長、原汁原味,院子里支起鐵鍋,煎炒烹炸燉,香飄十里八村,讓人不禁重溫舊日往事。
《鄉(xiāng)村土宴》開場就出現(xiàn)了一個重要人物——大馬勺,是二哥婚宴上幫襯做菜的,他的故事貫穿全文始終。大馬勺并不姓馬,真實的姓名不待考證,作者用了最具有職業(yè)特點的名字。大馬勺即“屯子里擺席掌勺的”,他們一家子都和餐飲有點瓜葛,回勺是大馬勺的兄弟,是他哥的幫手,小勺子是大馬勺的兒子,后來接了他爸的班。
歲月流逝,大馬勺老了,兒子小勺子接了他的班。小勺子腦袋瓜機靈,接過家傳手藝,與時俱進,“想著法變著樣地捯飭”,招兵買馬壯大了父親的事業(yè),專門做起了婚宴生意。兩千多一場,雇了一個上灶師傅、兩個配菜的小工、三個服務(wù)員,置辦了喜棚桌凳、盤子碗,大馬勺做了知賓,全家組成一套班子,鄉(xiāng)村土宴“升級”了。時過境遷,世事變化,從大馬勺親自上灶掌勺,到小勺子當(dāng)上小老板,鄉(xiāng)村土宴的經(jīng)營理念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改變,鄉(xiāng)人的生活也越來越富裕,曾經(jīng)的“鄉(xiāng)村土宴”早已不能與“升級”的婚宴相比,此例足以看出時代的發(fā)展進步。情由心生,筆隨意馳,作者關(guān)注現(xiàn)實、關(guān)注鄉(xiāng)村生活,生活與藝術(shù)合而為一,從瑣碎平常的世俗生活中,自然流露出作者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和家國情懷。
如今的大馬勺不愁吃喝、安閑自在,“街上走走,暖地坐坐”。電視里美食烹飪節(jié)目的新鮮玩意“沙爹醬烤培根”讓他覺著有意思,也是他生活里不多的那一點意思了。大馬勺時常自言自語、顛來倒去地感慨“生的不是時候不是地兒”,否則“也能在大飯店子里弄個廚主還是主廚當(dāng)當(dāng)”,這成了他活下去的理由。冬去春來,日復(fù)一日,對著北方的風(fēng)雪,對著高藍的春天,對著一日三餐,對著空了的酒杯和滿了的茶杯,自然的輪回與生命的逝去如此沉重感傷,支撐大馬勺晚年生活的那些話,熾熱真誠,烘烤著日月,烘烤著他的余生,那是大馬勺一生的執(zhí)著,字里行間無不滲透著作者對生命的感悟和悲憫情懷。
《鄉(xiāng)村土宴》凸顯出了鮮活的人物形象,也顯露了作者的語言功底。
多年來,九歌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獨特個性的創(chuàng)作之路,形成了適合自己的敘述方法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鄉(xiāng)村土宴》直抒胸臆,開頭即寫人物,語言流暢簡練,絕不拖泥帶水。從審美感性視角出發(fā),描寫了勤勞儉樸的父母,幫襯做菜的大馬勺,落頭忙的劉鐵嘴兒,碎嘴的西院王大娘,熱情的賣菜老張頭,還有掌勺的、燒火的、做飯的、端盤子的、送親的、迎親的、車老板子、接暖壺的、端洗臉盆的、繃大鏡子的……這些人物紛紛亮相,既呈現(xiàn)了鄉(xiāng)村婚禮上的熱鬧場面,也彰顯了鄉(xiāng)民們的質(zhì)樸熱情以及鄰里間友好相助的和諧關(guān)系。
作者描寫人物有獨特的視角,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刻畫形象,選用極為簡練樸素的文字,不重渲染烘托,也不重辭藻修飾,而是依據(jù)人物出身、環(huán)境、地位,三言兩語地描摹出人物的外貌、神態(tài)及心理活動,使讀者如見其人。如寫大馬勺,“小個兒,像個瘦猴兒”,與人們心里肥頭大耳、脖頸子流油式的廚師偏差太遠,他一邊“跳馬猴似的忙活著”,一邊嘴里也不閑著,和他一個拐彎兒親家調(diào)侃打著嘴架。寫他弟弟,“回勺的個子不高,橫粗,車軸漢子。”抓住人物外貌、語言、動作,惟妙惟肖,簡單幾筆,特征顯露,盡傳神態(tài)。鄉(xiāng)村土宴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串聯(lián)起一個個性格迥異的人物,展現(xiàn)了北方鄉(xiāng)村人民熱情善良、樂觀幽默的性格。
作者寫人敘事,言簡意賅、線條明晰,展現(xiàn)了北方鄉(xiāng)村普通人的生活狀態(tài)。寫喜宴上的人們,喜宴上的菜譜,甚至寫到桌子底下的豬兒、狗兒、雞兒、貓兒,濃厚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豬喝著槽子里的油泔水,狗站在墻角啃骨頭,貓趴在炕腳底下嚼魚刺,大公雞也領(lǐng)一群母雞在當(dāng)院里撒著歡找食兒。”這是在鄉(xiāng)村生活才能看得見的真實場景,畫面淳樸、動態(tài)十足,充滿溫情脈脈的煙火氣。
散文語言是較能表現(xiàn)作家個性的因素之一,作家審美情趣不同,語言風(fēng)格亦不同。“散文的語言,以清楚、明暢、自然有致為其本來面目。”(李廣田)在多年的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中,九歌追求散文語言的通俗曉暢之美、樸素自然之美,使外在語言與內(nèi)心情感相契合,呈現(xiàn)出一種通俗質(zhì)樸、自然淡遠的語言風(fēng)格。他描寫北方淳樸民風(fēng),描寫親情鄉(xiāng)情,彰顯著生命的真實與頑強,溫暖蘊藉、自然生動。
九歌善于使用東北方言,呈現(xiàn)鮮明地域特色。如作品中另一個人物——落頭忙的劉鐵嘴兒。“落頭忙”是東北方言,指村子里幫忙張羅事的人,能說會道,頗懂人情世故、禮尚往來,在北方鄉(xiāng)村里被人們戲稱為“大明白”“小諸葛”或“屯不錯”。這些名字、俗語方言,自有東北黑土地的詼諧幽默。作家鄉(xiāng)音難改情切切,方言俗語信手拈來,如“踅摸個筆頭兒”“劃拉菜單子”,踅摸、劃拉都是動詞,指尋找、潦草書寫等動作;“日頭兒冒嘴”指太陽從地平線上露出頭,充滿動態(tài)感和畫面感;還有“筍雞上不了架”“二伏蘿卜球蛋蛋”“窗戶外頭連天遍野的大煙兒炮”,都是人們?nèi)粘V械馁邓子谜Z,彌漫著淳樸的鄉(xiāng)土氣息,呈現(xiàn)了口語話、通俗化、形象化的語言特質(zhì)。
九歌善于錘煉語言,巧妙使用修辭手法,抓住準確的詞語,反映人物性格和事物特征。文字看似平淡質(zhì)樸,但淡而有味,于平淡中寄予真情理趣。如文中結(jié)尾寫勞碌了一輩子的大馬勺,老了之后還是有苦惱遺憾,念念不忘如果能夠重新活一回,也能再次人生輝煌:弄個主廚當(dāng)當(dāng)。在永恒的時間面前,人的生命無法回頭,大馬勺的人生感嘆正是蕓蕓眾生的迷茫困惑,文思含蓄、耐人尋味。
梁實秋說,“文調(diào)的美純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妙處。”《鄉(xiāng)村土宴》書寫北方淳樸的鄉(xiāng)風(fēng)民俗,書寫鄉(xiāng)村普通人的生活狀態(tài),融入了作者對故鄉(xiāng)土地的深情眷戀,融入了對時代變遷和人們命運的關(guān)注,字里行間流露出生命的思考和生存的智慧,也讓讀者在平凡的歲月中,對平凡的生活抱有溫情與想念。
作者簡介:張芳,女,有多篇小說評論、散文評論、詩歌評論及戲劇評論文章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