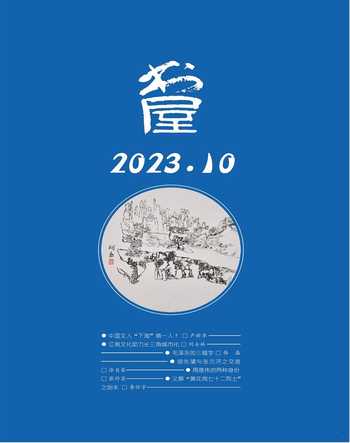江淮亦濟舟
鄺啟漳
清朝末年,雖有李鴻章、張之洞等主張西學,但仍然以中學為主,西學為用。有人以為,櫛沐過歐風美雨的中國學人,一定會放眼世界,注重西學。但是,并不盡然。出生于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辜鴻銘,十歲就到蘇格蘭公學接受啟蒙,后又到德國萊比錫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留學,獲得文、哲、理、工、神等多個學位,精通英、法、德、俄、日等多種文字和拉丁、希臘兩門古語。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寫成,而著作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對西方讀者尤有吸引力。可這位精通西學的老兄最服膺的卻是儒學。戊戌政變后,伊藤博文由北京南下來到武昌慕名拜會辜鴻銘,在談到儒學時,辜推崇中華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兩人不歡而散。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已開始意識到要平等地研究中西學問。我在追尋我的老師、英美文學研究家周其勛足跡的過程中,發(fā)現我國以南京為中心的學人,曾掀起過一陣中外文化交流的熱潮,而周其勛教授就是其中非常活躍的一位參與者。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時任東北大學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周其勛先生攜妻女從沈陽逃回上海,再赴南京。周先生受聘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主任,還兼任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教授。其妻倪翰芳先生也在吳貽芳任校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英文教授。周先生當時三十四歲,風華正茂、血氣方剛,在教學、翻譯和寫作之余,并不囿于五尺講臺和明窗凈幾,積極參與在南京的各種學術活動和對外文化交流。
上海《申報》1934年11月17日報道中意文化協(xié)會的籌備:
中意兩國,為亞歐兩大古國,足稱為東西文化之代表。中國所代表之東方文化,其得以傳播于歐陸者,厥賴馬可波羅創(chuàng)始之力為多。近年以來,中意關系,日臻密切……近日復有兩國使館升格,及羅馬東方學院請中國政府派送留學生之舉,兩國交換教授,亦正在進行之中。羅馬中意協(xié)會(Ligna Italo-Cinese)在三年前已告成立,是中意關系,日在進展之中,兩國文化溝通,實有更積極組織之必要。京中學術界人士蔣復璁、徐悲鴻、蔣碧薇、陳可忠、謝壽康、伍叔儻、郭有守、滕固、厲家祥、辛樹幟、楊公達、趙士卿、劉奇峰、高廷梓、李景泌、商承祖、于斌、潘玉良、沈剛伯、周其勛、唐學詠、岑德彰、陳耀東、蔣兆和、張梁任、樓光來、曹汝匡、呂斯百、何兆清、朱庭祜等三十余人有鑒于此,特發(fā)起組織中意文化協(xié)會。
這份名單幾乎囊括了南京的名流,都是當時的精英人物,除了于斌,其他人主要來自國立中央大學和教育部以及教育部所屬的國立編譯館。毋庸置疑,這些人士無一不與意大利淵源深厚:于斌神父,1924年赴意大利留學,先后獲神學、哲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擔任梵蒂岡教廷駐華代表公署兼中國公教進行會總監(jiān)督。我們知道,梵蒂岡教廷就在羅馬,所以于斌無疑是中意交流的紐帶。蔣復璁,自1932年從柏林大學畢業(yè)歸來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時候起,便多方奔走,與世界各國建立交換關系,使館藏外文書刊得以大量增加,當然也對意大利文化感興趣。地質系教授朱庭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地下水研究組主任,而古羅馬帝國的地下水系統(tǒng)是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跡之一,這個龐大復雜的灌溉工程雖經千年而不廢,朱教授自然對其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外文系樓光來和周其勛等英美文學研究家對作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發(fā)源地的意大利以及文藝復興三巨星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素來推崇備至。藝術系的西洋畫派畫家們,諸如徐悲鴻、滕固、潘玉良、蔣兆和與呂斯百,都無一不把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三大畫家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奉為仰慕、學習和臨摹的模范。早在協(xié)會成立之前,女畫家潘玉良的作品就曾陳列于羅馬美術展覽會,她本人也曾獲意大利政府美術獎金。藝術系的音樂家唐學詠十分鐘情意大利歌劇。
周其勛先生漫長的教學生涯也處處與意大利文化相關。據《文匯報》2015年7月3日《錢鍾書在牛津大學》一文,錢鍾書1935年參加出國留英考試時,周其勛和樓光來是英國文學專門科目的命題者與閱卷者。他們共同命題的歐洲文學史試題包括:1.古希臘悲劇與莎士比亞悲劇這兩種戲劇藝術的主要區(qū)別是什么?試舉例以說明之。2.就以下題目作出簡要評論:a.《新生》和《神曲》中的貝雅特麗齊(Beatrice);b.但丁《地獄篇》中的維吉爾詩風;c.但丁的冥府三界之旅。這里,兩位先生的試題要作些解釋。《新生》是但丁的第一部作品,詩人把幾年來寫給戀人貝雅特麗齊的三十一首情詩用散文連綴而成;《神曲》則是但丁在被放逐期間所寫的長詩,包括《地獄》《煉獄》《天堂》三部,描寫但丁先是在他崇拜的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帶領下游歷了地獄和煉獄,把所見所聞所感呈現出來,讓讀者體驗到地獄的罪惡煎熬、煉獄的苦難折磨,然后又在戀人貝雅特麗齊的帶領下到達壯麗華美的天堂,這就是上述試題所謂的“但丁冥府三界之旅”。
意大利與古希臘羅馬文明淵源深厚,而周先生對古希臘悲劇情有獨鐘,他教英國文學,莎士比亞悲劇就脫胎于古希臘悲劇。上海電影制片廠著名編劇沈寂(1924—2016)曾深情回憶起周其勛先生在上海孤島時期的復旦大學教他們古希臘悲劇課程的情景:“我們系里有位教授叫周其勛……他對希臘悲劇很有研究,很想開‘希臘悲劇這門課。然而,第一年沒有學生報名,沒開成。第二年,他還想開這門課,我聽到消息后就去報名,為了怕人太少,我就拉了一個叫慎儀的同學一起去報名……但是兩個學生還不能開課。周教授就說,他有個學生不是復旦大學的,是旁聽生,按學校規(guī)定,三個學生就可以開課了。‘不過,他又說,‘三個學生坐在教室里不太像樣,到我家去上課。我們都同意去他家上課。”
周老師告訴他們,古希臘悲劇有三大代表作家。他只教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古希臘悲劇有個特點,前面是合唱,歌頌命運。莎士比亞的幾部杰作如《哈姆雷特》等就脫胎于古希臘悲劇。周教授一面講課,一面表演,非常生動,引起學生對戲劇的很大興趣。
其實,周教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教我們時也談到過古希臘悲劇。我記得他說,古希臘悲劇是一種假面劇,演員都戴著類似我們京戲臉譜的面罩。《俄狄浦斯王》是希臘藝術完美結構的典范。該劇第一次通過“倒敘”的手法,講述了俄狄浦斯王到頭來發(fā)現自己就是“弒父戀母”的罪魁禍首,悔恨之余戳瞎自己的雙眼,所以,后來弗洛伊德把“戀母情結”稱為“俄狄浦斯情結”,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哈姆雷特就有這種情結。
半年以后中意文化協(xié)會成立時名單擴大了許多。隨著諸多高官的加入,協(xié)會的規(guī)格提升為國家級的人民團體。上海《申報》1935年4月3日報道:
中意文化協(xié)會,由中意兩國聞人發(fā)起組織,已經推員籌備,起草會章,不久即將開會正式成立……以研究及宣揚中意兩國文化及促進其友誼為宗旨。業(yè)于上年11月19日舉行第一次籌備會,通過會章草案,票選郭有守、伍叔儻、徐悲鴻、楊公達、樓光來、謝壽康六人為籌備員。并決定待駐華意大使羅亞谷諾來華時,正式成立……借謀兩國文化事業(yè)之發(fā)展……發(fā)起人名單:于斌(公教進行會總監(jiān)督)、王世杰、伍叔儻、厲家祥、朱家驊、朱庭祜、呂斯百、何兆清、辛樹幟、李熙謀、李景泌、沈剛伯、沈覲扆、汪延熙、宋春舫、岑德彰、周其勛、周還、唐學詠、徐悲鴻、徐公肅、翁率平、陳劍翛、陳可忠、郭有守、郭心崧、商承祖、盛成、黃宗孝、高廷梓、曹汝匡、程滄波、張志遠、張道藩、張梁任、楊公達、楊振聲、葉楚傖、蔣復璁、蔣兆和、蔣碧薇、樓光來、趙士卿、滕固、潘玉良、劉奇峰、劉師舜、戴季陶、謝壽康、謝冠生、瞿常(以上中國發(fā)起人)。巴內地、克法理絡克立德(以上意人在中國郵政總局任要職)、賴班亞(意人任司法院顧問)等五十五人。
雖然有諸多國民政府高官加入,但本質上還是文人雅士的交流,通過私誼而自由結社。高官們也是由他們的摯友們拉來作大旗振聲威以便取得經費的,其中以朱家驊的人脈最廣。國立編譯館三子(館長辛樹幟、人文組主任周其勛、自然科學組主任陳可忠)是朱家驊的左膀右臂。伍叔儻是其連襟,郭心崧、沈剛伯是其密友。著名畫家徐悲鴻,與蔣碧薇是夫婦,與呂斯百是師生,與音樂家唐學詠是同事兼摯友。在巴黎留學期間,徐與上述名單中的郭有守、謝壽康和張道藩等過從甚密,一起組織了名為“天狗會”的文藝團體。在南京,女畫家潘玉良舉行畫展時,徐和“南京文藝俱樂部”成員謝壽康、周其勛、唐學詠、呂斯百、商承祖等每展必到以示支持,因為潘玉良畫的是裸女,為當時的世俗所不容。
其實,在中意文化協(xié)會之前,還有中波文化協(xié)會和中英文化協(xié)會的建立。上海《申報》1933年6月2日報道:中波文化協(xié)會發(fā)起人現有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朱家驊、段錫朋、宗白華、張炯、張歆海、許念曾、陳立夫、黃建中、厲家祥、王世杰、羅家倫、程其保、黃侃、徐謨、李熙謀、楊銓、沈鵬飛、胡適、敖京斯基、汪東、謝壽康、楊廉、蔣夢麟、劉瑞恒、陳和銑、褚民誼、陳劍翛、杭立武、溫登濤、林東海、郭有守、傅秉常、辛樹幟、周其勛、劉英士、傅斯年、張道藩、伍叔儻、韓湘眉、張維楨等四十余人。該會5月開籌備會時,曾推舉中波兩國籌備委員,并議定章程草案。該會定于6月8日開成立大會。這個協(xié)會的層次極高,超越了文化領域而達到兩國全方位、多功能的交流合作,因為名單包含了南北兩京的文化高官和學術大家,以及駐外使節(jié)或外語教授而兼駐外使節(jié)的雙棲人才。除此之外,還有國聯顧問、公路工程專家敖京斯基。他是波蘭人,當時正為幫助我國修筑川陜公路而跋涉在峻嶺綿延、壁立千仞的秦嶺劍門關一帶。
上述名單中的溫登濤其實是見諸當年報端的波蘭駐華公使魏登濤(或稱魏登濤夫人)。中波文化協(xié)會1933年6月28日成立時,她和謝諾舒斯基等五人被選為名譽會長;陳立夫、褚民誼、謝壽康、陳劍翛、郭有守、李熙謀、敖京斯基七人為理事。魏登濤夫人熱心中波友誼,常奔走各地演講。她的演講,包括那篇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講的《波蘭女子在本國歷史文化上之貢獻》一文,1935年由中波文化協(xié)會結集出版,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署名雖是協(xié)會,但我相信周先生很可能參與了翻譯,因為他作為國立編譯館的編審、人文組主任、譯界名流,又名列協(xié)會發(fā)起人,參與翻譯此演講集責無旁貸。
在這一系列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由杭立武1933年創(chuàng)辦的中英文化協(xié)會最為人稱道。他促成了一件對后世意義深遠的盛事,即在英國倫敦舉辦了一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讓中國文物出國展覽成了一場傳奇。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英糾紛層出不窮。就在兩國矛盾余音未了之時,英國以敦睦中英邦交、慶祝新王愛華德八世加冕為由,通過中英文化協(xié)會邀請中方合作,在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中英文化協(xié)會的成員相當于半個南京政府,他們代表國民政府欣然接受了來自英方的邀請,不遠萬里,將七百多件(一說三千件)來自故宮博物院及其他機構的文物送到倫敦。展品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專家負責甄選和鑒定,先在上海展覽四周。隨后由英國海軍重巡洋艦“薩福克”號運往英國。在此期間,國立編譯館以周其勛為首的英語專才,均受命與博物專家全力合作為展覽準備所有的英文解說和背景材料。編譯館并派出編審唐惜芬為隨團翻譯。
1935年11月28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倫敦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百靈頓堂隆重開幕,時任英國博物館東方藝術部副主任、詩人勞倫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主持了開幕式并在英國報紙上撰文宣揚。展覽持續(xù)至1936年3月7日結束,觀眾達四十二萬人次。為答謝這位東方藝術學家和詩人對中國藝術展覽會的支持,也為了表達對在淞滬戰(zhàn)爭中為國捐軀的將士的悼念,周先生譯了一首勞倫斯·比尼恩的詩《悼戰(zhàn)死者》(For the Fallen),發(fā)表在南京《是非公論》1936年第七期上。周先生在譯注中說道:“當代英國詩人L.Binyon……現任英國博物館東方藝術部副主任,對于藝術,研究有素。曾于1929年到日本演講,其近著Landscape in English Poetry and Art即系彼在東京帝大之演講。此次我國古物陳列倫敦,Binyon撰文宣揚,尤為我國人所應感謝者也。”
周先生不僅積極參加各種對外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活動,而且身體力行,以文字和語言促進中外文學和文化的交流與溝通。1936年7月,他以教育部播音講師的身份,通過當時的“中央廣播公司”,向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和各地的“民眾教育館”播講了《中國詩對于西洋詩之貢獻》。播講一開始就指出:“現今,英、美、法、德的詩人,都以熱烈欣賞的態(tài)度,在研究——那遠自荷馬以前直到現在——一統(tǒng)相傳,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詩學。”接著,他又說:
中國詩影響西洋詩者,大略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講;西洋詩人受中國詩影響者,也可分作兩派來說:一派代表舊派的,作者以為以東方的遼遠神秘,足可為幻想之題材,把此種材料置于詩中,必定可以作為奮興讀者的一種資料,但是他們不能深切懂得中國詩人的旨趣與方法;另一派的詩人,是來從未見過中國,他們但憑靈感或技巧,或者在詩題或意境方面,來顯示他們所得到的影響,像艾梅羅威(Amy Lowell),福乞兒(Mr. Flatcher),弗得利克彼得森(Dr. Frederick Petcon),愛拉旁的(Ezra Pound)等,都屬于這派的,他們都極力研究關于中國的一切,在他們的寫作中,他們竭盡他們的能力來應用他們所學習到的一切,他們這種意象派詩人所最顯著的特點,幾乎全系含有中國意味,他們的詩的風格形式,雖然都屬無心的摹擬,但仍然有若干地方,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是仿效中國詩的作法。
Ezra Pound(現譯埃茲拉·龐德,1885—1972)與上述的Amy Lowell(現譯艾米·洛威爾)以及中國讀者所熟悉的艾略特和海明威關系很深。在倫敦,他們過從甚密,后面這三位都視前一位為師。艾略特先是將長詩《荒原》原稿寄給龐德然后又到倫敦與他切磋,而后者則將原稿大刪大削,最后只剩下一半。海明威夫婦到倫敦,與龐德夫婦住在同一條街上,在別人的介紹下與后者相識,兩家一起去喝茶和旅游,龐德將海明威介紹給他的朋友圈,而海明威則教龐德學拳擊。由于龐德比海明威大十四歲,所以海明威以小學生求教的姿態(tài)請龐德修改他的短篇小說。不過,二戰(zhàn)以后,艾略特和海明威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洛威爾亦在戰(zhàn)前獲得了普利策詩歌獎,反而是他們的老師龐德聲名逐漸冷清。
盡管龐德與諾獎無緣,但作為英美“意象派”領袖和因與中國的淵源而成為比較文學的開山鼻祖,其成就并不亞于某些諾獎得主。正如周先生在演講中所說的,龐德從未到過中國,不懂中文。那么,他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翻譯了那么多中國古典詩詞的呢?那是在艾略特和海明威到倫敦前的那幾年,龐德幾乎天天到大英博物館和周先生提到過的,曾熱心協(xié)助中國在倫敦舉辦文物展覽的東方藝術專家、詩人勞倫斯·比尼恩見面。比尼恩則把龐德介紹給一位曾經到過日本、長期研究東方哲學和藝術的Ernest Fenollosa(今譯范諾羅莎,1853—1908)。
范諾羅莎是一位出身哈佛的美國教授,于1878—1890年和1897—1901年兩度(總共十五年)到日本,一面教授西方哲學一面研究東方的藝術和詩歌,并把研究的過程和發(fā)現都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也是通過比尼恩的推薦,范諾羅莎的遺孀瑪麗·范諾羅莎認定龐德才是丈夫遺愿的執(zhí)行人。她于1913年秋跟龐德見了面,把先夫的筆記即“范諾羅莎的寶貝”送給他,允許他利用這本筆記出一本中國詩集、一本日本能劇集和一篇有關中國人性格的論文。
“范諾羅莎的寶貝”是一疊逐字翻譯中國古詩的手稿。每句詩行之下是逐字的音譯(transcription);不過,音譯是按日語的五十音圖來加注,所以在我們看來很不準確。音譯下面則是逐字的意譯,然后才是其他注解。
讀著這些手抄筆記,龐德覺得中國詩的境界與他的意象主義和旋旋主義運動不謀而合。龐德的意象主義詩學向來主張“對事物直接處理,不用多余的陳述”,“自然物就是足夠的意象”。這些主張其實和中國詩的意境說異曲同工。也就是說,中國詩超脫西方時間觀的限制,用一系列的自然物作為意象符號,來展現一幅鮮明的圖景,這是英美詩人所做不到的。
臺灣的比較文學名家葉維廉博士在《龐德與瀟湘八景》一書中指出,(中文)文言可以超脫英文那類定詞性、定物位、定動向的指義元素而成句,而英文就不可以。他說:“中國詩拒絕一般西方的邏輯思維及文法的分析。詩中‘連接媒介明顯的省略,譬如動詞、前置詞及介系詞的省略,加上無需語格變化、時態(tài)變化(但這些卻是文言的特長),使得所有的意象在同一平面上互相并不發(fā)生關系地獨立存在。這種因為缺乏‘連接媒介而構成似是而非的‘無關聯性,立刻造成一種氣氛,而能在短短四行詩中放射出好幾層的暗示力……”龐德一眼就看中了中國詩中的蒙太奇效果,從范諾羅莎的遺稿中選譯了二十五首中國古詩,并于1915年以Cathay命名結集出版。
Cathay是歐洲人對中國的別稱,源自契丹(Khitan)。后來又演變成一個詩意的名詞,仍指中國,可譯為“國泰”“華夏”或“神州”。現在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的英文名就是Cathay,所以龐德的這本譯詩集通常都被稱為《華夏集》。
《華夏集》在英國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成為英美現代詩歌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僅促進了英美意象派詩歌的發(fā)展,而且為中西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經典個案。諾獎得主艾略特盛贊龐德是“我們時代中國詩的發(fā)明人”。這里,艾略特的意思是說,龐德把中國詩翻譯活了。《華夏集》里的詩,無論是譯詩還是原作都是上乘佳作,深受讀者的喜愛。與此同時,由于龐德與中國的淵源關系越來越為研究者所重視,周先生這篇登在南京《廣播周報》1936年第一百零二期上的論文,后被收入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編的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成為經典,歷久彌新。
總而言之,隨著1933年中英和中波、1934年的中意等文化協(xié)會的成立,南京的對外交流活動蔚然成風,此后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協(xié)會亦相繼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