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樂作品中的中國
方迪
一個終其一生對音樂創(chuàng)作保持審慎態(tài)度的英國現(xiàn)代主義作曲家,在他八十三年的跌宕生涯中,曾經兩次奔赴戰(zhàn)場,歷經殘酷的生死考驗,卻絲毫不減生命的溫柔底色,亞瑟·布利斯(Arthur Bliss)以其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不變的浪漫情懷和極高的歷史使命感,為英國音樂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架起橋梁。
一個仗劍天涯、放蕩不羈,秀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的“謫仙人”,在他六十一年的起伏人生中,曾讓“力士脫靴”“貴妃研墨”,為后人留下無數(shù)迤邐華章。“詩仙”李白以其狂妄不羈、雄奇飄逸的風格,將盛唐浪漫主義文學推向高峰。

兩位在時代、地域、身份、專業(yè)上相去甚遠的大家,以詩樂對話,引得聽眾無限遐想。1923年,在紐約莫霍克湖邊度假的布利斯,偶得日本學者大田重吉所譯的《李白集》,便依據(jù)其中《越女詞》篇的五首五言絕句,創(chuàng)作了室內樂歌曲《越女詞》(The Women of Yueh)。布利斯以極為流暢詩意的手筆譜寫了五首清麗雋永、令人悵懷的女聲與室內樂作品。
《越女詞》五首其一:“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音樂伊始,在弦樂四重奏纏綿地奏響主題后,長笛柔亮的顫音模擬出一片江南湖水蕩漾的粼粼波光。女聲緩緩地唱出詩句,一詠三嘆,雖是英文歌詞,但旋律走向上居然也如同中文吟詠般抑揚頓挫。作曲家仿佛駐足荷塘岸上,不知是遠觀荷塘春色,還是看那正在泛舟的年輕姑娘。
樂風一轉,歡快的節(jié)奏律動刻畫了一幅生動的蓮間嬉戲圖:“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管樂與弦樂的應答唱和讓音樂的氣氛瞬間熱鬧起來。活潑俏皮的長笛,仿佛姑娘嬌羞百媚的笑語。不時點綴其間的鋼片琴(俄羅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芭蕾舞劇《胡桃夾子》的“糖果仙人舞曲”中使用鋼片琴的片段最為著名),其明亮清脆的音色給樂曲增添了甜美而夢幻的色彩。想來,“笑”應該是這首詩歌的詩眼。
“耶溪采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樂曲在各個聲部三拍子的舞曲韻律中展開,已分不清是采蓮女手中的雙槳在搖曳,還是她心中的春波在蕩漾。她一會兒唱著歌、劃著船出來,一會兒又說說笑笑地劃進荷花叢躲起來。采蓮女的害羞生澀、欲罷不能的矛盾心理與繾綣之情被音樂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聽罷此曲,不禁令人想起法國作曲家福雷的《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組曲》(Op. 80)第三樂章中的《西西里舞曲》。論此情此景,倒也是頗為相像。
不詳?shù)囊粽{伴隨沉重的步伐緩緩靠近,弦樂組單調地重復拉奏,制造出一股強大的阻力橫亙其中。凄切的女聲唱出:“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全曲唯有尾聲的管樂組奏出一長串較緩的顫音透出微光,但那也只是鏡花水月的幻影罷了。曲終的幾個音聽起來極為晦暗不和諧,道出有情人天各一方,難以終成眷屬的結局。
李白怎甘心以此哀傷情調收尾,正可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鏡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當詩人游至鏡湖,望見明凈的湖水與相貌姣好的女子,那水的靈動與女子姣好的身姿交相輝映。“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詩人重新燃起追求美好愛情與自由生活的熱情。

布利斯創(chuàng)作的這一套樂曲,以速度上的快慢、色彩上的明暗、情感上的喜憂對比交錯展開,將中國特色的五聲音階融入多調性的和聲寫作中,配器上并不復雜,人聲與器樂的邊界也被有意模糊。音樂短小精悍,單曲不過一兩分鐘,整套下來也不過十分鐘,一氣呵成,五首歌曲具有很強的統(tǒng)一性。這是作曲家少有的異國題材作品,是其早期對現(xiàn)代主義音樂語言拓展的嘗試,但無論如何,也很難讓人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場上擔任皇家燧發(fā)槍團的軍官,與中國浪漫主義唐詩《越女詞》聯(lián)系到一起。這份浪漫主義情懷究竟從何而來?只要追溯作曲家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育經歷,便不難發(fā)現(xiàn)個中緣由。
布利斯出生于倫敦郊區(qū)的巴恩斯,是家中長子。他幼年喪母,慈愛的父親獨自撫養(yǎng)三個兒子,并有意培養(yǎng)他們對文學藝術的興趣。可能是父親別有用心,希望通過文藝的滋養(yǎng),彌補孩子們母愛的缺失。聰明的布利斯沒有讓父親失望,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同時學習古典文學和古典音樂,之后又進入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進修。
在大學校園里,他結識了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Edward Elgar),并在音樂上受其啟發(fā)良多,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還與拉爾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古斯塔夫·霍爾斯特(Gustav Holst)、赫伯特·豪威爾斯(Herbert H o w e l l s)、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亞瑟·本杰明(Arthur Benjamin)成為摯友,他們在日后都成為了英國重要的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指揮家。今天,我們可以在這個二十世紀初英國作曲家群體的音樂中,發(fā)現(xiàn)一些共性語匯。無論是埃爾加的《威風凜凜進行曲》、威廉姆斯的《綠袖子幻想曲》,還是霍爾斯特的《行星組曲》、豪威爾斯的《挽歌》,都具有盛大慶典音樂般莊嚴、雄壯的氣勢,擅長以英國傳統(tǒng)民風曲調與廣泛的抒情旋律渲染浪漫主義色彩,配器上呈現(xiàn)出簡化趨勢。雖然我們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前輩作曲家的影子,如馬勒、施特勞斯等,但在尤金·古森斯和亞瑟·本杰明的音樂里,已經可以聽到印象主義轉向,布利斯也從德彪西、拉威爾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等現(xiàn)代作曲家的音樂中汲取靈感。

1942年,布利斯主動請纓擔任BBC音樂總監(jiān),推出了戰(zhàn)后的新音樂節(jié)目,以推廣英國作曲家的新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他在英國文化協(xié)會音樂委員會任職,戰(zhàn)后曾多次代表英國音樂家出訪。或許正是世界大戰(zhàn)的腥風血雨,塑造了布利斯極強的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他的藝術關懷也上升到國家層面,乃至全人類共同命運的范疇。在此期間,他為許多芭蕾舞劇和電影創(chuàng)作了音樂。1950年,布利斯被封為“爵士”,同時還獲得了“女王音樂大師”的榮譽稱號,正式擔任創(chuàng)作國家級場合所需要的儀式音樂的創(chuàng)作工作。布利斯深厚的作曲功底和熟練的技術運用讓他對這些工作駕輕就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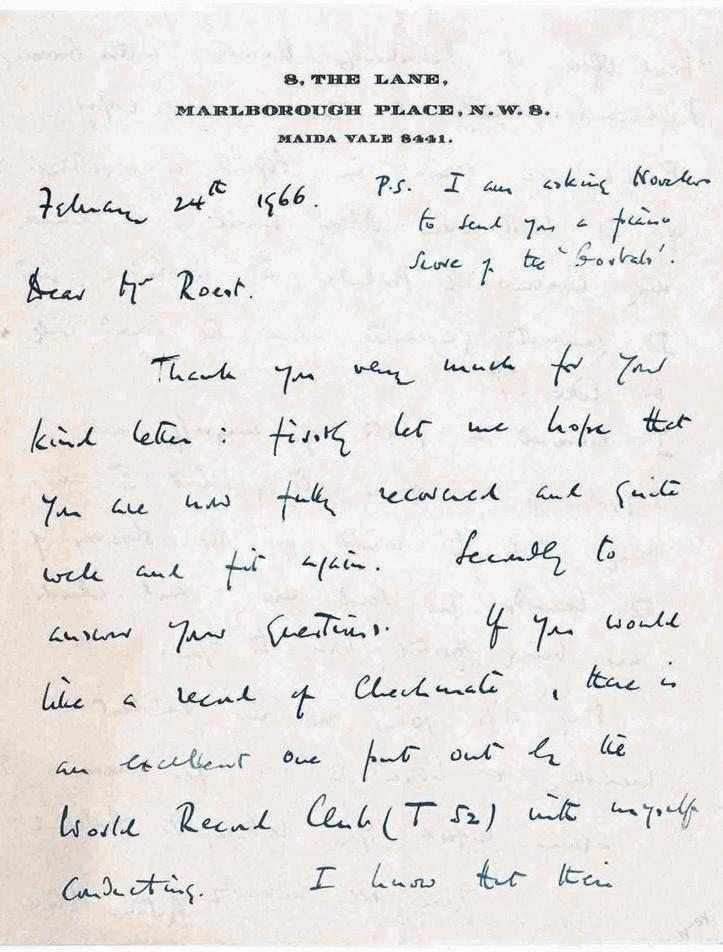
無論是為皇家和官方所創(chuàng)作的音樂,還是更具個性化的寫作,布利斯都獲得了社會面的廣泛好評,并使他在今天的英國音樂界仍享有很高的聲譽。在戰(zhàn)場上,他是沖鋒陷陣的戰(zhàn)士;在和平年代,他則以音樂譜寫生命華章,撫慰戰(zhàn)后人們受傷的心靈。亞瑟·布利斯選擇了李白的《越女詞》,展現(xiàn)出他對遙遠東方風土人情的向往。誰的心里不渴望這樣一片江南水鄉(xiāng)呢?這片唯美凈土,是作曲家一生不變的浪漫主義底色,更是植根于人類捍衛(wèi)并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是歷經劫難仍堅韌不屈的生命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