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回聲·逍遙游
李鵬程
“絲綢之路”上的音樂是永恒流動的河川。這無形的聲音匯入文人的詩詞里、藏經洞的壁畫上、音樂家的歌聲中。在當今世界各地,很多音樂家依舊傳唱著關于絲路的音樂,以開放的姿態跨越古今、東西、雅俗之間的藩籬,源自不同地域的聲音就這樣神奇地融入各類當代音樂風格。
我的腳步和耳朵曾一次次在陌生的世界流連忘返,故于此“絲路回聲”專欄分享所見所聞,在“逍遙游”“樂人談”“十問”三個板塊中,見證“絲綢之路”的精神和聲音在當代的無限延伸。這一抹新鮮的色彩和你處于同一時空,或許在未來某個奇妙的時刻,你會在地球的某個角落聽見他們在永恒歌唱。
翻過高加索
縱覽西方音樂史教科書中的作曲家“萬神殿”,哪一位最東方?
從地理位置看,當屬生長于格魯吉亞的亞美尼亞人阿拉姆·哈恰圖良(Aram Khachaturian),他的父母生長在阿塞拜疆地區。依照現今版圖,他算是亞洲人。
高加索山脈橫亙在里海與黑海之間,北邊是俄羅斯,南邊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南高加索三國是歐亞交通走廊,也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這三國被稱為“火藥桶”,既有宗教信仰原因(格魯吉亞是東正教,亞美尼亞是基督教,阿塞拜疆是伊斯蘭教),也有蘇聯解體后領土紛爭的遺留問題。現在假如你想走遍這三國,第一站可不能先到格魯吉亞,因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邊境是關閉的。
不過,這三國的人們都將哈恰圖良視為本土音樂的驕傲。一方面,這三國的音樂文化非常接近;另一方面,蘇聯的一體化制度讓哈恰圖良得以汲取南高加索各個地區的音樂素材。我聽過許多這里的民間歌舞,才明白哈恰圖良的獨特旋律來自何處。
中國聽眾熟知的“指揮沙皇”捷杰耶夫極其看重自己的高加索身份:“我是奧塞梯人,我成長于高加索,與車臣和格魯吉亞相鄰。高加索由多重民族與國家構成,有著迥異的民族精神和性格。”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大舉向東擴張,將大片中亞地區納入俄國版圖,于是有了“強力集團”的“東游記”。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推開了基輔的大門;鮑羅丁的《在中亞細亞草原上》是為慶賀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作,《伊戈爾王》則是借基輔君主征伐東蠻的史詩贊頌當朝圣上;巴拉基列夫的《塔瑪拉》直接以十二世紀前后的格魯吉亞女王作為標題;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天方夜譚》則將西方作曲家對東方的音樂想象推向了極致。而哈恰圖良走的路線與他們相反。
哈恰圖良在二十世紀初高加索地區最大的城市第比利斯郊區長大,而在蘇聯建立之初,南高加索三國屬于同一個行政區域,所以各民族的流行曲調成為他天然的音樂養料。“我在充滿民間音樂的氛圍中長大:節日、儀式、歡樂和悲傷的事件,在人們的生活中總是伴隨著音樂,民間游吟詩人和音樂家演奏的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歌曲以及舞蹈的生動旋律——這些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里。”
十八歲時,哈恰圖良移居莫斯科,開始學習專業音樂,與此同時,也開啟了大起大落的人生。
像哈恰圖良這樣的少數民族作曲家,真正能躋身主流的寥寥無幾,但他卻成功地在蘇聯文化體制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樣生長于第比利斯的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實現了權力集中,并試圖將文藝界與國家意識形態相統一。蘇聯希望作曲家們能夠延續“強力集團”的民族主義風格,于是自帶民族音樂屬性的哈恰圖良自然成了組織的希望。1939年,哈恰圖良開始擔任蘇聯作曲家協會的副主席一職,并于1943年入黨。次年,他寫出了《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歌》。
何止一首《馬刀舞曲》
1939年,哈恰圖良在亞美尼亞采風半年,并為亞美尼亞藝術節寫出首部芭蕾舞劇《幸福》。三年后,這部作品被改編為芭蕾舞劇《加雅涅》(Gayane),由基洛夫芭蕾舞團(如今的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首演。哈恰圖良憑借這部作品獲得斯大林獎,他請求用這筆錢為紅軍造一輛坦克。
《加雅涅》的階級斗爭劇情是特殊時代的“特產”:亞美尼亞女主加雅涅勸告丈夫不要走私,丈夫燒了集體農莊倉庫并在逃跑過程中刺傷了加雅涅,邊防軍指揮官將她的丈夫繩之以法,并對加雅涅悉心照料,一年后在新建倉庫典禮上,兩人舉辦了婚禮。
雖然劇情早已過時,但其中的音樂被編為組曲后保持著極高的上演率。其中的《馬刀舞曲》通過手風琴傳遍中國大江南北,它出現在央視《曲苑雜壇》藏族小伙兒洛桑的口技表演中,出現在動畫片《麥兜當當伴我心》的童聲合唱中……這支“神曲”為什么會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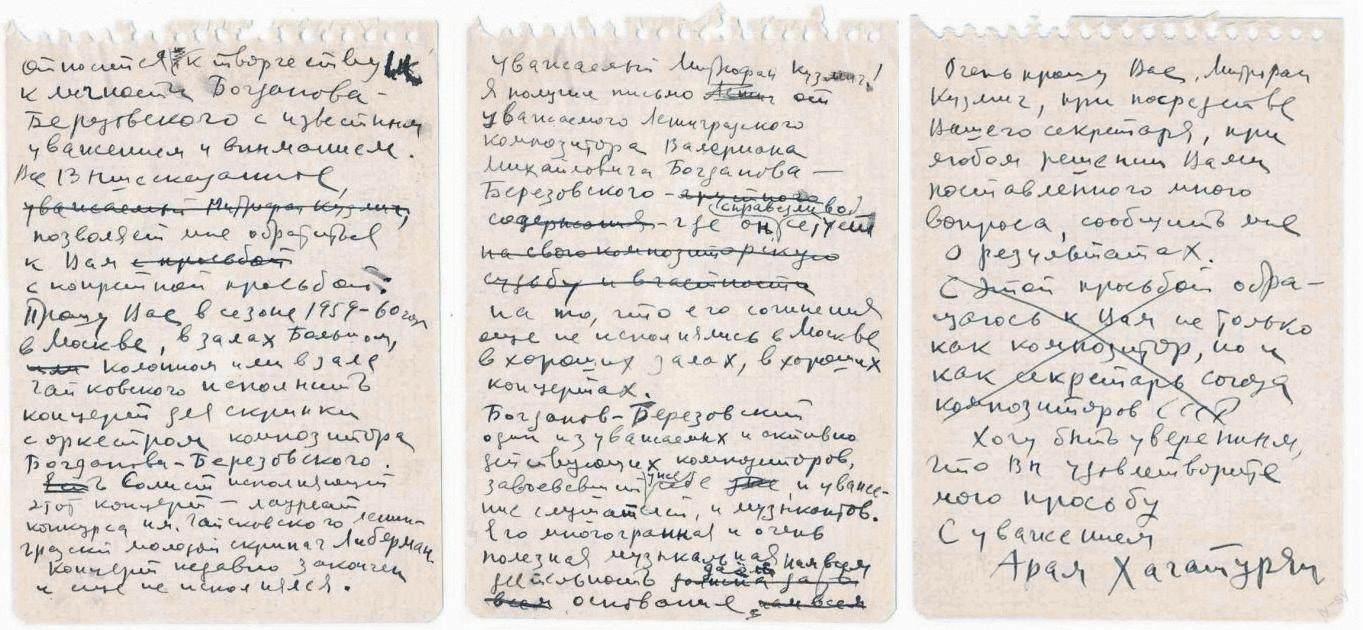
急板粗礪的重復音、野性詼諧的滑奏、圍繞第一個主音進行裝飾和半音階下移,在典雅而深刻的交響樂世界實為罕見。舞臺上的庫爾德小伙子揮舞著馬刀盡顯戰斗民族本色,顛覆了從柴科夫斯基到普羅科菲耶夫一脈相承的芭蕾形象。《馬刀舞曲》的中段是對亞美尼亞婚禮舞曲的變形,與之對應的竟然是薩克斯管吹奏的一段爵士樂風格的旋律——要知道蘇聯是長期排斥美國爵士樂的,以往交響音樂中也極少出現薩克斯管。尾聲的終止句還要在持續主音上方,“跑調”出另一個調的五聲音階。短短兩分多鐘的小曲,涵蓋了哈恰圖良音樂的所有特征——粗野的旋律、奔放的節奏、多民族風格融合、不合常理的雙調性對置,以及與之相配的民間舞蹈動作。
哈恰圖良有著“神曲”音樂家的共同煩惱:《馬刀舞曲》風頭太盛,以致于多數人忽視了他還有不少迷人的作品,如《加雅涅》中的《阿耶莎之舞》(Ayeshas Dance)。該曲由散板引入,短笛獨奏帶有即興意味的異域曲調,圍繞骨干音轉出無數個小三度螺旋的旋法是俄羅斯音樂中常見的,但由于這里的裝飾音型在游移不定的調式中打轉,從而帶有更濃郁的中亞音樂特色。舞曲主題在三拍子基礎上加入大量切分節奏,六次變奏保留原調和旋律框架,僅靠層層疊加新的旋律和樂器就足夠新鮮。這些創作特征濃縮在哈恰圖良的《兒童曲集》(Album for Children,1947)第十首《民間風格曲調》中,可以聽到持續主音的伴奏與脫離主調的旋律,這種現代化民族曲調的手法顯然來自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
《加雅涅》還有多個迷人的段落,最后的《列茲金卡》(Lezginka)是高加索地區的特色舞曲,當所有人以為是哈恰圖良直接編配了民間音樂時,他卻說自己從不照搬任何已有旋律。當高加索民歌潛入哈恰圖良的內心聽覺時,他自然就擁有了無與倫比的旋律天賦,這是無數作曲家哪怕通過長時間的學習與訓練也難以企及的。
柔板—故鄉
人們將哈恰圖良與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并稱為蘇聯音樂“三巨頭”,但如今更多人是從他們那張著名的合影里才看到哈恰圖良的模樣。奇怪的是,無論是歷史評價還是上演率,哈恰圖良明顯不及另外兩位同行,到底是為什么?
在二十世紀西方音樂史的書寫中,具有創新精神的先鋒作曲家被視為孤勇者。普羅科菲耶夫與肖斯塔科維奇的創作本質上是現代主義的,蘇聯厭惡這種遠離群眾審美的“形式主義”傾向,卻又不得不借助他們的國際聲譽。他們像斯特拉文斯基那樣是“精神層面的流亡者”,這也是他們在西方樂界備受推崇的主要原因。此外,相比另外兩位同行作品中的悲劇性和崇高性,哈恰圖良的音樂多少顯得不夠深度。

按理說,雅俗共賞的哈恰圖良應該被蘇聯官方當作盡善盡美的樣板,可1948年的那次大批判卻讓他跌入谷底。由日丹諾夫主導、赫連尼科夫代言的大會點名批判為“形式主義”的作曲家有七位,哈恰圖良最冤,“躺槍”的原因大概與他的作曲家協會副主席身份有一定關系。在此之后,赫連尼科夫成為協會的最高領導人直至1991年。
費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一書中感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藝術家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肩負起道徳領袖和民族先知的重擔,而國家對他們的恐懼和迫害又是如此之甚。”在嚴厲的譴責之下,哈恰圖良做了大量自我批評。作為常規的懲罰,他被派往對常人來說是邊疆的亞美尼亞,但這里恰恰是他夢中的故鄉。余生三十年,哈恰圖良主要從事教學和指揮,創作方面的重頭戲是舞劇音樂《斯巴達克斯》(Spartacus),這部英雄悲劇是作曲家挺過人生至暗時刻的產物。

《斯巴達克斯》的柔板是哈恰圖良另一廣受喜愛的名曲,不少西方導演將它作為影視配樂,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BBC電臺歷史劇《旺定航線》、電影《冰川時代2:融冰之災》(Ice Age 2: The Meltdown)等。擅用古典音樂的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1968年的電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借用了《加雅涅》中的柔板,作為空間站宇宙航行的配樂。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導演的《異形2》(Aliens 2)開場的宇宙航行配樂,用的是同一段柔板。誰說哈恰圖良的音樂像鮑羅丁那樣“土”?他的柔板甚至成了科幻太空場景的標配。從這點來看,哈恰圖良和拉赫瑪尼諾夫有著類似的待遇——學術界看不上,好萊塢當成寶。
無論如何,中亞作曲家們還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受到哈恰圖良的影響,如阿塞拜疆作曲家菲克列特·阿米洛夫(Fikret Amirov),他創作了許多基于本土素材的交響樂,其中《阿塞拜疆隨想曲》(Azerbaijan Capriccio)的主題與哈恰圖良《小提琴協奏曲》的主題如出一轍。生命末年,哈恰圖良重游南高加索三國。他想創作一部反映亞美尼亞人民苦難的歌劇,可惜未能完成。病逝于莫斯科之后,他的遺體被運回亞美尼亞的首都埃里溫,前來送葬的人擠滿了整個市中心。在哈恰圖良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這位西方音樂史上的東方作曲家依舊值得我們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