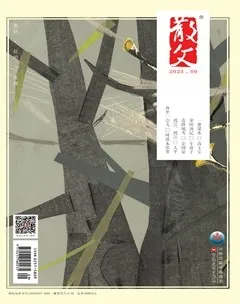裁縫鋪
韓嘉川
裁縫師傅的穿著,無論新舊總是板正干凈,一條皮尺掛在脖子上,人不離三尺臺案,眼睛與耳朵卻觀六路聽八方。看他貌似不經意,手不離巴掌大的南泥小茶壺,目光越過人的頭頂,從櫥窗望出去,像在看街面上的人來人往,其實他留意的是人們穿戴的流行款式與質料效果。人道木匠的眼光有分寸,而裁縫更是如此,無論男女老少,他一打眼就能判斷出身高胖瘦和三圍尺寸,且根據人的氣度,換算出需用多少布料,適合什么款式。
這是童子功,打十幾歲就到鋪子里學徒,雖然開始幾年與裁剪縫制的臺案沾不上邊,干的多是跑腿的營生。到老主顧家里取布料送成衣,鍛煉的是記憶。夫人小姐姨太太試穿衣服時,所說任何話都要點滴不漏地聽到心里。女人在穿衣服方面的啰唆是天性,絮絮叨叨說了一大篇后,常常回問道:我剛才說的什么,你聽到了嗎?小學徒要馬上一字不落地將要點復述一遍,讓她們放心。回來揀出其中要緊的說給師傅,譬如腰圍要縮二分,肩頭下半分。師傅聽了皺起眉,抖開帶回來的衣服,伸開手摩挲一遍,又低頭伏在上面聞聞,說知道了掛起來吧。徒弟便用衣架撐起衣服,要掛進旁邊的櫥子里,師傅正在喝水,趕緊騰出嘴來道:不,掛到上面去。鋪子門面的上空橫著一根根竹竿,常年一件緊挨一件地掛著做好的衣服。徒弟記著,沒看到師傅再把那件衣服做什么處理,過幾天讓他原樣又包好送去,而這次姨太太一上身就說,看看,這一改,就合適了吧!
一看二摸三聞味兒,是裁縫師傅的看家本領:看的是尺寸,人體的間架結構;摸的是面料的質地;聞的是染料成分。有的人胖瘦不顯,哪里該緊致哪里該放開,是根據顧客的審美需要決定的。姨太太的衣服要亮麗,買的是鮮艷的洋布,染料也多是化工品,雖然布料縮水輕,在竹竿上掛兩天,衣服還是能抻出半分,染料的銳色也減了分毫,看上去就不再那么刺眼了。
那記憶是禁得起檢驗的。我把取衣服的單子遞過去,早就由學徒變成師傅的裁縫,不慌不忙地拿起一根頭上有一對鐵彎鉤的竹竿,在密密麻麻懸掛在半空中的衣服中,準確地將我的衣服拿下來,抖了抖,像欣賞一件藝術品,讓我穿給他看,穿上后的效果都在預料中。他站立的位置離兩面大鏡子不遠,示意讓我自己對著鏡子看看。那時我對衣服的審美沒有標準與要求,看不出好壞,倒是從鏡子里能看到他衣服的可體與整潔。
那間鋪面在市場樓北門的右手側,連著三個頂部弧形的落地櫥窗里,以前有穿旗袍女裝模特,后來貼了“講衛生、除四害”等標語。鋪面里原來只有兩臺德國百福縫紉機,是他的師傅與師母使用的,到他能上機以后,師傅就專做量體剪裁接生意的事。后來這間門面改成了被服廠的門市部,機器也換成了六臺本地產的鷹輪牌縫紉機,令整個鋪面總處于此起彼伏的轟響中。他出師開始量體接生意后,不僅繼承了師傅高超的手藝、嚴謹和藹的行事風格,也繼承了師傅的生活習慣,譬如喝茶。只不過他不用南泥壺,用的是時興的搪瓷茶缸,每天一上班就泡上茉莉花茶,那種香味可以持續得比較久;持續比較久的還有茶缸內壁長年累月形成的“茶山”,據說是不能洗刷掉的,哪天不放茶只倒白開水在里面,依然會有茶的味道。
他家在市場樓的西邊樓上,一條長長的胡同,兩側住滿了人家。嫌樓道里黑漆漆的,不刮風下雨天氣好的時候,他多是從市場樓外面的街道走到西門再上樓。在門市部里眼睛向外望出很遠,而在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穿行,他卻總是低著頭,腳步很輕頻率很快,保持了學徒時的習慣。
他的老婆坐在敞開的門外干加工活,是將被服廠的下腳布料拆成線,一斤五毛錢。見他進了胡同,便對正做飯的大女兒秋英喊:可了不得,你爹回來了,飯還沒做好?裁縫并不多話,進門坐了床沿上,看十一二歲的閨女忙活。在家里他說得最多的話就是:“鼻子大起頭,鼻子大起頭!”這是跟老婆盤算每個月的開銷與收入對比,生活所需的花費比收入高的意思,因而不得不舉債。那時很多單位都有大大小小的互助組,即十幾個人一個組,每人拿出十塊錢,每月可以給困難職工提供一定的幫助,可借用一二十塊錢,下月發工資時還上,若還需要就再借。往復循環的,是無盡的惆悵。
烤火費還未發下來,母親就開始盤算給我做衣服的事。我長得比較冒進,比同齡的孩子多出一兩寸,又特別調皮,費衣服,每年做一套新衣即便打補丁也穿不到年底。母親下班后一趟趟去百貨公司看布料,去的次數多了,與布匹柜臺的營業員都熟了:華達呢、卡其布,寶藍色,以及尺寸價錢精打細算,在營業員的聯合參謀中,決斷買下了布料,接下來由我抱著去排隊量體裁衣。
貼著櫥窗的位置是一條長凳,排隊的人緊挨著坐著,屁股下面的凳子面寬且光滑,坐在上面很舒服。鋪面中間的地板上有一米見方的鐵板,四周是半人高的圍欄,里面一只不大但熱量不低的爐子給人以足夠盎然的暖意。有的人趁熱打起了瞌睡。爐子上方是一個大大的方形爐罩,用來遮擋向上飄動的飛塵,以保護懸掛著的衣服。櫥窗外有賣糖球的戴著氈帽扛著草把子的中年人,凍得紅紅的臉上掛著兩條清鼻涕;街角賣糖炒栗子的炒鍋散發出甜膩的白色熱氣,賣栗子的人一邊用方頭鐵锨在鍋里翻炒一邊叫喊:糖炒熱栗子!曲調像在唱歌。
挨到我的時候,往往已經到了掌燈時分,裁縫師傅依然極有耐心。量過尺寸,他并不往小本子上記,以至于我會有他是否已經忘掉的擔心。然后他將布料在案子上鋪開,一邊摩挲一邊說布料會縮水多少,并上下打量我的身體,顯然是在為我的成長留出一定的預期。問是否帶了口袋布,見我茫然以對,便用商量的口吻說:到百貨公司買兩方手帕,就可以了。后來理解,這是為了用口袋布襯出布料,用在面子上。人們對于里子與面子,往往覺得里子質料差一點沒關系,可以代替,而面子一定要符合一致的審美觀。我匆匆跑回家讓母親去買方手帕……
走出門市部的時候,街上已經飄起了雪花,人們縮著脖子在走。市場樓的北門沖著新華池澡堂,那里的方形氣窗冒出白色的霧氣。臨近年關了,人們紛紛前去一洗塵芥,干干凈凈地迎新年。
我同學的父親也是從蓬萊農村來城市學裁縫的,學了沒幾年就到一家針織廠的成衣車間做了工人,依然在裁剪案子上工作。那時還用大剪刀,先將布料一層層疊放整齊,然后比照模板畫線,再用大剪刀咔哧咔哧裁剪。常年裁剪那幾款針織服裝,每一個細節都爛熟于胸。后來廠子里成立技術科,他屬于自幼學藝的“科班出身”,又多年將裁剪技術發揮得游刃有余,就被調去做技術員,從理論到實踐,對廠子里的產品開發進行研究與指導。
又到冬天,母親再度為我的新年衣服犯愁。市場樓北門外的門市部不再接來料加工的生意了,據說有了更重要的給軍隊做被服的生產計劃。同學來我家玩時,自告奮勇地說讓他父親給我做。母親喜出望外之際,也有一個疑問說不出口,那就是他的手藝如何?同學的父親是一個慷慨豁達、有求必應的人。他接過布料,一遍遍地向空中抖開鋪展在他家的床板上,再疊起。他的拇指留有挺長的指甲,用來在布面上劃出橫豎的壓痕,想必他是以此來考慮裁剪尺寸的分毫,至于什么時候用粉餅畫線剪裁,就要看他的興致了。
總是在緊傍年根了才拿到他熬夜做出的衣服,可穿到身上,總覺得領子與兩肩之間皺巴巴的,也不知道哪里不對勁。春節穿了去他家拜年,他看到后,又用長長的指甲在衣服上劃來劃去,然后說脫下來我給你改一下。修改后的衣服看上去好一些了,但領子與兩肩之間總有一些褶子,于是便懷念起北門外門市部的裁縫師傅。他裁剪的衣服總是板板正正沒有絲毫皺褶,他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是沒有任何皺褶的,與身體融合在一起,看上去挺拔有神。
成年以后,街上有了時裝與流行色。有一年發現家里還有一塊布料,于是就滿街尋找承接來料加工的裁縫鋪。經朋友帶領,在一片居民樓里七拐八拐地來到一間叫“紅袖”的裁縫鋪。滿屋子中年婦女圍著一位扎小辮的男子,他的背帶褲外面是開懷的西裝皮背心,里面是難以掩飾的大肚子。他瞥我一眼,稱不接男裝活兒。朋友趕緊上前賠著笑臉說:我們不是說好的嗎?哦,是你呀,那就等著吧。等終于將那些婦女打發得差不多了,他開始給我量身體尺寸,再仔細地記在小本子上。看他把收下的布料扔進一大堆里,我提醒道:這塊布料會有盈余,你看……他回答:放心吧,用不了我會退給你的。按約定的日期去取衣服的時候,他的屋子里依然擠滿了人,依然大都是中年婦女。他費了好大的勁找到我的衣服,塞過來,讓我回去試,有什么不合適的地方回來找他。我覺得還是當面試試才好,便穿上了。沒想到衣服做得太大,下襟快接近膝蓋了。他自己也看著不像樣,說:你給我的布料太多了,你放這兒吧,我再給你改改……我不快地拿著衣服離開了,想再找家鋪子,讓做事認真的裁縫給改一下,改到能穿即可。走到半途,我想:這樣的鋪子與師傅,現在還能到哪里去找啊?
于是再度想起市場樓北門外的裁縫師傅。聽說,后來他做了領導,且不在被服廠了。市場樓拆掉了,他的家肯定也搬了,如果人還在的話,得有九十歲了。
責任編輯: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