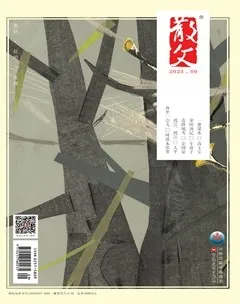在交河故城
秦嶺
每次來吐魯番,我總要登上交河故城。小心翼翼地從南城門高聳的豁口探進去:十米、三百米、一千六百米……我屏息靜氣,盡量避免腳步、氣息和全身衣物的窸窣之聲驚擾這巨大的、無邊的、深邃的沉默。但我作為一個活物的一言一行,還是不小心制造出聲音來了,這聲音在沉默中反彈回來,像是對我發出警示:這是一座沒有主人的城市,但你已走進了主人的故鄉。沉默,蓄滿了面積達四十三萬平方米的城堡群廢墟,適應并融入沉默最好的辦法,是給眼睛以自由。映入眼簾的,是完全裸露的高高低低的土堡、大大小小的土墩、寬寬窄窄的土壑、長長短短的土柱……不見一只鳥,不見一棵樹,不見一滴水,不見一根草。這綿延不絕的土的凹凸、土的起伏和土的組合,讓我變得像一個放肆冒失的闖入者,以至于當唐代詩人李頎的詩句“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從腦海里閃現出來時,那種極富視覺、聽覺沖擊力的畫面感和代入感,讓我忽然踟躕不前,頻頻環顧四周,心中的惆悵,如大漠孤煙,直直的,不知直向何方;如長河落日,圓圓的,不知圓成甚樣。
沒人知道當年李白是否蒞臨交河城,他在《搗衣篇》中寫道:
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
萬里交河水北流,愿為雙燕泛中洲。
詩中那玉手,那狂夫,那雙燕,真是物我兩忘、如泣如歌,而“雙燕泛中洲”傳遞的情感信息似乎是:那癡癡的期許,那悠悠的祈愿,那盈盈的執念,正在水一方。
先賢的吟詠幻影般消失,仿佛搭載著歲月的回音匆匆而來,又捎帶著歷史的挽歌匆匆而去,它留下了可觸可摸的沉默,卻又空空如也。
陪伴我的維吾爾族朋友艾比布拉問我:“交河故城像不像一條不沉的船?”
“可我,怎么覺得像海市蜃樓呢?”我當然不認為這是海市蜃樓,但我實在沒有勇氣承認眼前實實在在的真切。
與不遠處繁華熱鬧的吐魯番相比,交河故城虛幻般的沉默令人心悸,真擔心這份沉默也會瞬間隨風遠逝。
交河故城距吐魯番市只有十多公里,雄踞在雅爾乃孜溝兩道河床之間一個高達三十米的黃土臺子上,河水從臺地北面一分為二,又在臺地南面合二為一,這使交河故城像極了一個巨大的河心島。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里就是新疆早期人類生活的重要區域,后來成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車師國的都城,是當時的吐魯番地區的首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漢書·西域傳》說:“車師前國,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稱交河。”按建筑學家的說法,當年的交河城完全是先民們采取原始而智慧的“減地留墻”之法“挖”出來的一座城市:挖出城郭,然后夯筑塔樓;挖出墻體,然后坯砌屋頂;挖出街巷,然后鋪墊路道;挖出廣場,然后壘造寺院……于是,鱗次櫛比的官署、作坊、店鋪、民居拔“地”而起,布局有致的演兵場、藏兵壕、鐘鼓樓“土”落石出。長達千米的“南北大道”兩側,明道暗隧縱橫交錯,地上地下連貫統一,空中樓臺彼此呼應。考古顯示,這里,僅是寺院內的佛塔,就多達一百零一座。駱賓王詩云:“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
“可知的這種建城之法,在全世界僅此一處。”艾比布拉說,“交河故城,是世界上唯一的生土建筑城市。”
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座雕刻出來的城市。換個說法便是:這是城市建筑的工藝品。它像一次平地而生的隆起,也像一次從天而降的降落。又因此,它誰也不像,而誰也別指望像它。它,就是它自己。
如今,這一切真的像海市蜃樓一樣飄逝于歲月。什么叫城市?地理學給城市的定義是:地處交通方便環境且覆蓋有一定面積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結合體。也就是說,人間從來沒有沉默的城市,是交河故城把所有城市的沉默收藏、儲存了起來。這樣的沉默,反而讓每個到訪者的內心都無法平靜和安寧。說什么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這視野里的天,一定還是當年的天;云,一定還是當年的云;風,也一定還是當年的風,而腳下這一尺尺、一寸寸、一厘厘的土,又何嘗不是當年的土呢?恍惚間,我分明是和萬萬千千曾經在這里生活過的車師、匈奴、鮮卑、粟特、突厥、回鶻、蒙古人在歲月里重逢了,相聚了。那一圈圈土墩,是強壯、英武的古車師人正載歌載舞嗎?那一排排土埂,是漢代西域都護府即將出行的駝隊和馬車嗎?那一樁樁土柱,是南北朝時期居民家中升起的裊裊炊煙嗎?那一處處土丘,是沿著絲綢之路抵達這里的唐朝使者和商人們剛剛卸下的商品嗎?而我,可能是漢代、唐代,或者宋代的某個旅人,在市井徜徉,在店鋪購物,在客棧痛飲,或者,在觀摩一場什么賽事。我還聽到了寺院的鐘聲和樂坊傳出的十二木卡姆的演奏聲,聞到了客廳里葡萄美酒的味道,看到了將士手中夜光杯發出的光芒……
“現在,你想到哪里了?”艾比布拉笑著說,“很多來這里的人,總會說仿佛夢回兩漢、大唐、南北朝什么的,像學生寫作文似的。”
我不由得放聲大笑。我說:“你太厲害了!是這無解的沉默,縱容了我少年時代才有的漫無邊際的大夢。”
“噓。”他提示我,“你的笑聲驚動它了。”
我倆同時復歸于沉默,腳步也停了下來。如果有人從遠處光禿禿的城垛上眺望我們,看到的也許是兩個沉默的小土墩。烈日當空,城堡群的投影長長短短,條條縷縷,與強光覆蓋的地方反差鮮明,仿佛高溫鑄就的黑白對比,醒目,交織融合,宛如古老的黑白幻燈片。我倆的時代身影,就這樣融入投影的沉默之中,古老得不知所終。我們,分明是把自己走丟了。
可歷史的投影,反而愈加清晰起來。除了交河故城,同樣沉默的高昌故城也距離吐魯番不遠。兩座相同命運的城市廢墟相望于大漠,像一對歷史的難兄難弟。在歲月的刀光劍影中,交河城的歸屬曾一再易主,車師、高昌、吐蕃、蒙古先后成為這里的主宰者。十四世紀初,交河城最終凋零在蒙古鐵騎卷起的塵埃中,它在血雨腥風中最后一次見證了大漠落日,同時也見證了吐魯番作為地標名稱的誕生過程。這一過程,和歷史上許多征服者攻城略地的模式一樣,伴隨著戰火、血腥與殺戮。交河、高昌沒了,吐魯番有了。不久,吐魯番在“城頭變換大王旗”后,成為吐魯番汗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多年后,明代西域使者陳誠來到交河城,面對繁華落盡、一片蕭瑟的廢墟,留下了這樣的詩句:“斷壁懸崖多險要,荒臺廢址幾春秋……使節直從西域去,岸花堤草莫相留。”顯赫了兩千多年的交河城,從此被貼上了“故城”的標簽。
我想,陳誠當年一定感受到了這份凝固、冰冷、空曠的沉默。“莫相留”,就是說我留不得,你也留不得:哥們兒!看一眼,莫回頭……走吧!
一個“故”字,讓古老的交河城永遠停留在往昔的盡頭,不再回來。
八年前,這座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項目“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人說這是故城的幸運,但在我看來,當彌足珍貴的幸運脫胎于不可逆轉的不幸,轉而以遺產的方式贏得文化層面的首肯和認同,這樣的幸運實在有些太沉重了。
要說人間最漫長的,莫過于歲月。時間的隧道里,有多少城市生而不滅,又有多少城市滅不復生,有的因之被稱為古城,有的則被稱為故城。古城和故城,共指那些歷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古老城市。前者仍然具有生命的賡續和文化的傳承,而后者,則專指廢棄的、無法重生的遺跡。我曾游歷許多古城,比如大理古城、平遙古城、喀什古城、泰寧古城等,那種古今相聞的震撼與美麗,實在是妙不可言。然而交河故城為什么沒有成為交河古城呢?如此具備地理、交通、人文優勢的前國都,完全可以“春風吹又生”地舊貌換新顏啊!如果此一問成立,這里至少該是現代意義上的交河縣,或交河市。
“你看看那里,也許就知道了。”艾比布拉輕輕抬臂,用手一指。
他指向的那里,有三十多口干涸的古井,每口井里都曾挖掘出大量人體骨架;那里,有四十五座墓葬,里面有大量長睡不醒的逝者;還有那里,對!就在交河故城官署區旁邊,有一個現在看來非常特殊的大型墓葬群,里面是二百多具兒童的骸骨,年齡最大的不過十來歲,最小的則是剛剛出生的嬰兒……
為什么是在井里?為什么會是孩子?今人猜測萬般,杳無解答。
“故城,也有不沉默的時候。”艾比布拉講起了一個流傳已久的說法:半夜三更起風時,常有孩子們的哭喊聲傳來,孩子們的喊聲很絕望,哭聲很悲傷。有些牧民曾循聲進入廢墟一探究竟,卻發現除了風聲在殘垣斷壁之間嗚嗚作響,再無別的聲音。而當牧民從城門口出來,那哭喊聲又傳來了……
明白了,無論事實還是傳言,都是故城凄婉、幽怨的回聲。岑參有詩云:“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岑參所處的唐代,早于交河城徹底廢棄的元代八百年左右,假如岑參當年能預想到這些八百年后孩子們的哭喊聲,夜宿交河,他將作何思何想?而后來慢慢站穩腳跟的吐魯番人,只怕是誰也不忍踩上這片哭泣的土地。
要說是這樣的“不忍”保護了廢墟,也不盡然。假如大自然擁有話語能力,它一定會說:這盛年凋敝的生土之城之所以歷久彌堅,是因為我賦予了它得天獨厚的氣候——我營造干燥呵護它,我避免酸雨侵蝕它,我抵擋冰雪凍僵它。
然而交河終究未能成為浴火重生的古城,沉默,已成為它的固有屬性。
在歷史的風輕云淡中,這樣的沉默更像是人類存亡、去留的佐證和象征。可是,人類的戰爭機器從未放慢帶血的步履,攻城略地一如既往,孩子們的哭喊聲從未停止。此時此刻,隨便打開電視,仍可見不止一座城市炮火不斷,殺聲震天,現代化武器以遠超冷兵器千百倍的毀滅性力量,正在讓一座座城市化為廢墟……
有位從戰火紛飛的國家來到交河故城的外國人說:“這里的沉默,讓我思念家鄉。”
申遺成功之后,交河故城獲得了“世界上最美的廢墟”的美譽。
不知道別人如何欣賞這種美,我個人的理解是:如果它真的是一條船,那么它的美在于,它以廢墟的名義負載了人類無法承受的沉默。它選擇了永遠停泊,而不是在大漠的酷暑、風暴和嚴冬中悄然駛離,遠去,直至在時間的汪洋中沉沒。這種無形的沉默之美才是無與倫比的。如果僅僅是用來獵奇和迷醉,那就不再是交河故城了。
一輪明月從殘垛邊緣緩緩升起。這遍體鱗傷的明月,每晚都把交河故城的沉默輕輕籠起。而交河故城不舍晝夜,沉默地將人間的一切側耳傾聽。
責任編輯: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