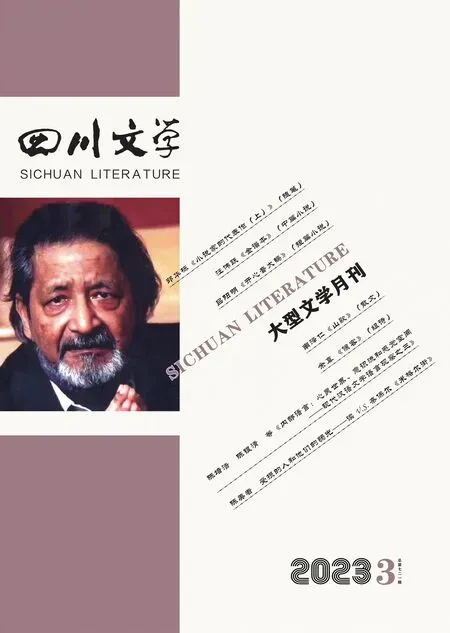仙人仙語
□文/林宕
一
剛走近家門口,小英就聽到了客堂里傳出的說話聲。
她媽說:“她怎么會推他到河里?”
隨即,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阿戇說的。阿戇你說是不是?”
小英的心“噗噗噗”地跳快了。心跳一加快,她的腳步也加快了,她幾乎是一步跨進了她家的客堂里。
她媽美娟、阿戇媽紅桃、阿戇站在客堂的北窗前。透過敞開著的北窗,可以看到屋后美娟搭的那個絲瓜棚已經一片蔥綠,一些高處的藤蔓即便尋不到東西可以攀援了,卻還在向上生長,梢頭倔強地伸向了空中;部分藤蔓的軀干卻已經從架子上長長地耷拉下來。
小英的目光從窗外的絲瓜棚上收回,看著她面前的三個人,說:“是我推他的,推他落水的。”
小英回憶了前天上午的情景。她把阿戇這個戇大推到河里后,這個阿戇竟然“憨人有憨福”——在岸上福氣不好,生了個木瓜腦袋,在水中,他的福氣卻來了,他沉不下去,身體在河水里轉了幾個圈后,緩慢地爬上了岸,然后,渾身水淋淋地重新站在了小英的面前,還嘿嘿地對著小英笑。
小英想不到這個戇大竟然會把這件事說給他媽聽。說了也就說了,說了或許更好,小英就重復了一遍自己剛才說的話。
美娟的眼睛里掠過驚懼的神色,她的眼睛對著小英的眼睛。她發覺小英的目光特別明亮,似乎不能經受這份明亮,美娟快速轉過臉去,然后舉手撩一下額頭上的頭發,眼神安定下來,又轉回臉來,對小英說:“你瞎講啥?發燒把腦子燒壞了?”
美娟知道,是自己在瞎講了,小英的腦子不會壞。可她不瞎講又能怎么樣?她跟紅桃家的親家是好幾年前就攀好了的。剛攀時,阿戇剛從娘肚皮里出來,誰知道他是個戇大呢?知道他是個戇大后,美娟覺得也不能反悔,她不想讓村里人戳背脊骨。
阿戇一步跨近小英,喉嚨口發著“嘶嘶”的氣流聲,臉上露著歡喜神情。當他的身體差不多要貼上小英時,他媽一把拉住了他,把他拉開了。
這一拉,讓小英的眼睛里有啥東西閃了一下。她的目光更明亮了。
小英說:“我沒有發燒,是我把阿戇推到河里的。”
小英注視著阿戇媽紅桃,紅桃也注視著她。兩道目光絞在了一道,它們像是在角力,在角力的過程中誰也不愿意服輸。片刻間,時間像是凝固了,很快,時間又突然化開了——紅桃的眼睛首先移開了,臉上居然還露出了笑。她似乎醒過來了,說:“隨你哪能說,你都是阿戇沒有過門的媳婦。你再惹毛我,你也不要想變了這個身份。”
紅桃笑嘻嘻地把臉轉向美娟,說:“你說呢,美娟?”
美娟點頭說:“對的,這小貨色是在瞎嚼舌頭呢。”
美娟又對小英說:“你肚皮里幾條蛔蟲,紅桃嬸娘一清二楚呢。”
小英漲紅了臉,好像自己心里的啥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了她媽和紅桃面前。她微微張嘴,吁出一股悠長的氣息。小英像大人了,有話不脫口而出,有話會把它們變成一股悠長的氣。她確實是大人了,她不是大人的話,怎么會主動惹毛紅桃呢?惹毛紅桃是一個心機呢——紅桃和美娟幾乎同時在這么認為了。
阿戇是戇大,他的好多話是沒頭沒腦的啊,他的話好多是顛三倒四的啊。說不定他那樣對紅桃說,還是小英教的呢,小英如果真想下毒手,阿戇現在還能立在這里嗎——紅桃和美娟也同時這樣認為了。
紅桃和美娟的臉上都露出笑了。
紅桃對阿戇說:“你以后不能再瞎三話四了。”
阿戇呵呵笑。他這樣笑,看上去是在承認自己之前的瞎三話四了。
其實,阿戇瞎三話四是正常的,可以原諒,他本來就叫阿戇啊。可小英瞎三話四就不正常,不能原諒了——紅桃和美娟又一次同時這樣認為了。
這樣認為后,紅桃和美娟都收住了臉上的笑,她們對小英板起了面孔。美娟還跨前一步,伸手捩了捩小英的臂膀,說:“以后再瞎講,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小英的嘴巴扯動了一下,像是真被她媽用手撕了一下。
二
小英在路上碰到了紅桃。紅桃一副走親眷的樣子,左胳膊里挎著一只籃頭,籃頭上遮著一條羽襟。恍惚間,小英以為紅桃是要來她家,可旋即,小英看出不是的,紅桃并不是往她家的方向走的。
小英想躲開紅桃,可已來不及了,紅桃叫住了她,隨后把她往一旁的雜木林里拉。紅桃的手感到了小英的不情愿,就說:“又不是要強奸你,怕啥?”
紅桃又說:“以前,你爸泉榮倒想在這林子里強奸我呢。”
紅桃臉上露出笑。小英也笑了,然后她的胳膊和身體柔軟下來,跟著紅桃往林子里走。
這時候,紅桃的腦子里則浮現出這樣的一些情景。這些情景發生在她剛出嫁到這里時。
剛嫁到橫涇村時,紅桃以為自己會與別的剛嫁到這里的新娘子一樣,被男人們“吃豆腐”——這是這里的一個風俗。可吃新娘子“豆腐”大家也是遵守著一個度的。過度了,這里的老人們是不同意的。因為有著這么一個風俗,嫁過來時,紅桃的內心有些惶恐,不過,令她想不到的是,她嫁過來后沒人吃她“豆腐”。就在她暗自慶幸時,她得知:有一類新娘子,男人們是不去吃她們的“豆腐”的,那就是壞腳壞手們和戇大們討進的新娘子,而在村里人的眼中,紅桃的男人阿偉是一個戇大。其實,阿偉也就是啞子一樣不愿開口說話,可他并不是真正的啞子。他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啞子,卻連著一周不說一句話,這不是腦子壞了的戇大,還是什么?村里人的這個判斷后來被證實了,被紅桃后來生出的兒子阿戇證實了,阿戇這個真正的戇大證明了自己的父親確實是一名戇大。當紅桃明白別人不吃她這名新娘子“豆腐”的原因時,盡管她內心的惶恐沒有了,可她心里不爽了,她心里憋屈了。她后來在路上碰到泉榮時,就問泉榮,你也不吃我“豆腐”嗎?
紅桃娘家所在的村莊和泉榮所在的橫涇村,也是夫家所在的橫涇村就隔著一條河,所以,紅桃與泉榮從小就認得的。當泉榮聽到了紅桃的這句問話后,他搔了搔頭皮,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紅桃看著泉榮那張英氣的臉,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說不清的感受。當時的泉榮還沒有處對象,看年輕女性的眼睛里,就難免有一種特別的神色,這特別的神色就是一種既膽怯又勇敢的神色,這神色像是一種年輕而又生猛的火焰,點燃了新娘子紅桃的血液。她又向泉榮開口了,說,你吃我“豆腐”吧?說著,她挺著胸脯朝泉榮跨近了一步。
他們的身邊是一片雜木林。泉榮朝雜木林瞥一眼,說,現在又不是在公眾場合,單獨碰著,不能吃的。
泉榮說的是一個當地人吃新娘子“豆腐”的規矩。可紅桃的血液已經被泉榮眼睛里的火焰點燃了,她似乎不理會這個規矩了,說,那我們就不要讓人看到,不要讓人看到你吃我“豆腐”時不在公眾場合。
紅桃的腳步朝雜木林里移動了。泉榮在遲疑,可很快他跟進了雜木林里。他們在雜木林驚動了一群麻鳥,麻鳥們飛走后,他們就在兩棵榆樹間站住了。泉榮的雙眼里盡管像著火了,可他不知道該干什么。紅桃就把自己的胸脯挺到了泉榮的胸脯上——這哪像是男人在吃新娘子“豆腐”,分明是新娘子在吃別人豆腐了啊。這似乎讓泉榮感到不好意思了,感到自己對不住男人這個稱謂了。他一把抱住了紅桃,很快又放倒了紅桃。在地上,他要進一步動作時,紅桃掙扎起來。紅桃一掙扎,泉榮的動作變大了,他的動作一變大,紅桃就叫起來,還一口咬在了泉榮的肩膀上。泉榮叫了一聲,然后慌忙從地上爬起。片刻后,兩人面對面站著了,都呼哧呼哧地喘著氣。泉榮說,是你讓我進來的,要我這樣的。紅桃說,你這樣不是“吃豆腐”。泉榮說,我說過“吃豆腐”要在公眾場合,可你偏要領我進來。紅桃似乎吃癟了,說不出話了。她轉過身來,快速走出了雜木林。
雜木林還是以前那個雜木林。可進入雜木林的兩個人已經不同了。
紅桃繼續想著以前的那段時光,她和泉榮進雜木林的時光。
紅桃想徹底離開夫家、回娘家——她的這一企圖后來沒有實現,在夫家的家族勢力以及強大的某種村俗前,她的這種企圖最后被粉碎了。在她的這個企圖剛成形時,她悄悄地把泉榮再次約到了雜木林里。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泉榮起先是不答應的,可紅桃用堅決的口吻告訴泉榮,她是有“要緊事”跟他說。泉榮說,有“要緊事”說也用不著進雜木林。紅桃說,沒人規定雜木林里不能說“要緊事”。歇一口氣,紅桃又說,放心吧,我不會在那里吃了你。看著紅桃像剛摘的鮮桃一樣粉嫩的臉,又覺得她都那么說了,泉榮的腳步就動了,就跟著紅桃進了雜木林。
紅桃還是在兩棵榆樹間立停了,一立停,她就坐了下來。她扯一下泉榮的褲管,要泉榮也坐下,泉榮的屁股也就落到了地上厚厚的枯葉上。紅桃把手放到泉榮的膝蓋上,泉榮一動不動。紅桃的手開始撫動,泉榮還是一動不動。泉榮覺得自己變了,覺得自己已不是上次來這里時的泉榮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啦,好像肚皮里正涌動著一股委屈。見泉榮一動不動,紅桃真的開始跟泉榮說“要緊事”了,她的話讓泉榮吃驚。她說,我要離開這里,我要離開阿偉。泉榮瞪大眼睛看著紅桃。紅桃問泉榮,你說阿偉是戇大嗎?泉榮搖搖頭。紅桃說,你認為不是?泉榮又點頭。紅桃說,所以,我離開他,不是因為他是戇大,他不是戇大。他不是戇大,可他讓我變成戇大,變成腦子有病的人了。紅桃轉臉四顧,似乎在擔憂有人突然闖到他們身邊。她又說,我說的事,你千萬不能說出去的。泉榮點頭。她接著說,我為什么想離開,還有……她咽一口唾沫,似在猶豫,就在她重新抿上嘴巴的時候,樹林里響起了幾聲明麗的鳥叫,像是在替代紅桃說話。不過它講的是啥,泉榮聽不懂。
泉榮抬頭,頭頂上是濃密的枝葉,不見鳥的蹤影。它一定是隱藏在哪片寬大樹葉的背后,在窺視著密林中的兩個人。當紅桃欲言又止時,它終于忍不住,替她講了幾句。
泉榮想起身,紅桃一把拉住他。她把他的手往自己身上拉。她又說,我不能白來這里一次,我不能白做一次新娘子……她對泉榮繼續囁嚅道,你曉得嗎?出嫁后,再帶著囫圇的身體回娘家,后半生過不太平的……泉榮心里驚嘆一聲,再次瞪大眼睛。
紅桃的另一只手在自己身上動了。泉榮的手立刻縮回,他想站起來。可他站不起來。紅桃又伸手拉泉榮,泉榮的身體終于倒在了紅桃的身體上。
三
十多年后的一天上晝,小英在路上碰到了紅桃,紅桃一副走親眷的樣子,左胳膊里挎著一只籃頭。紅桃讓小英跟著她進了雜木林。
進了雜木林后,紅桃打量起身周的樹木。雜木林確實還是原來的雜木林,里頭的樹木仍舊是有的挺拔有的彎曲,它們的枝葉仍舊是蔥蔥綠綠的,它們分泌出的樹脂的氣味仍舊是那個味道,有點清香有點甜。紅桃還覺得,即使與不同的人進去,在里頭圍繞著他們的那股詭秘氣氛還在。沒辦法,進這個雜木林,好像就是要做一些詭秘事情的。
紅桃立停在一棵厚殼樹邊。這里,地上的落葉不多,還都是些新鮮落葉,所以地上顯得還干凈。紅桃把籃頭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下。見小英還立著,她伸手拉小英,小英幾乎是跌坐到了地上。
紅桃拿掉籃頭上的羽襟,抓出一只醬煨蛋。醬煨蛋的味道讓小英的舌根處一酸。可她不接紅桃遞過來的醬煨蛋,別過頭去,把舌根處的酸水咽了下去。
紅桃放回醬煨蛋,又從籃頭摸出一塊蔥餅,遞給小英——紅桃拉小英進雜木林好像就是為要了給她吃東西。吃東西又不是件需要遮人耳目的事,用得著把她拉進雜木林?小英感到有點好笑,又有點可氣,就想從地上立起來,可紅桃還是拉住了小英,另一只拿著蔥餅的手縮回到了籃口邊。
紅桃說:“我本來想回娘家去的。”
“那你去吧。”
“等一等吧。”
“那你早點去吧。”
小英說著又要立起來,紅桃也再次拉住了她。
小英說:“你領我進樹林里,就是想讓我吃東西?”
“不是。你不吃就不吃吧。”
“那是為了強奸我?”
小英說著“噗嗤”一聲笑出聲來,紅桃也笑了。小英想不到自己能夠在紅桃面前說出這樣的話來。兩人這樣笑,當然是把這句話當成笑料了。這樣笑,還說明了一點:兩人其實把紅桃先前說的那句話也是當做笑料的,那句話就是:以前,你爸泉榮倒想在這里強奸我呢。
既然拉小英進樹林不是為了給她吃東西,也不是要強奸她,那么還坐在這里做啥呢?小英就說:“那么好吧,既然沒有別的事,我們就出去吧。”
紅桃卻再次一把拉住小英的臂膀。
紅桃說:“不,我有事,我有事要問你。”
“那也用不著進樹林問啊。”
“進樹林就是因為有事要問你。”
“你就問吧。”
紅桃的嘴唇皮掀動了一下,卻沒有一下子出聲。片刻后,她終于囁嚅道:“那天阿戇落水,是你推的,是嗎?”
小英不接嘴。有了上次她家客堂里的經歷,小英覺得自己沒必要像上次那樣說了。說了,也會從紅桃的嘴里得到同樣的應答。
紅桃又說:“上次在你家里,我那樣說了后,你怎么不吱聲了呢?你應該反駁我,反駁你媽。是你推的,你就要咬牢。”
和上次一樣,小英的臉又漲紅了。好像她做的錯事被紅桃發現了。不過她還是沒有吱聲。
“你應該咬牢啊。”紅桃舔一下嘴唇,“是你做的事,你為啥不咬牢呢?”
紅桃伸出手來。這一次,她伸手不是為了遞吃的東西給小英了,她的手直接放在了小英的臂膀上,兩根手指捩了一下小英。小英沒有反應。紅桃的兩根手指在小英臂膀上再次用力捩起來。
小英尖叫一聲,晃動臂膀,晃掉了紅桃的手指。然后,她的身體沒有了進一步的行動,她沒有試圖從地上立起來,一動不動地坐著。紅桃的聲音則再次響起來:“小貨色,我當時是盼著你咬牢的啊。你怎么說了一聲就不再說下去了啊。”
小英臉上的紅色已徹底褪去,不但如此,她的面孔還泛白了。她沒有看紅桃,蒼白的面孔正對著前面的一棵雞爪槭。
接下來的片刻,兩人都沒有聲音,一片寂靜包圍了她倆。在小英的感覺中,這片寂靜是重的,壓在了她的身上,她的身子更加立不起來了。而在紅桃看來,被她捩了幾下,外加說了幾句后,小英是服帖了,不再犟頭捩腦了。
既然小英不再犟頭捩腦了,紅桃就又開口:“你以為我一定想把你討進我家嗎?我家阿戇一定要你嗎?不,把你討進家里派啥用場?不派用場,只是討進一張吃飯的嘴巴罷了。我家可沒那么多口糧。我只是要你講,阿戇落水是你推的;當然,你是這樣講了,不過你要在你媽和我面前咬牢啊,我以為你要咬牢的。”
紅桃的兩根手指又放在了小英臂膀上。小英的臂膀抖動了一下,可紅桃卻不再捩小英。
小英說:“你不是在說我瞎三話四嗎?”
“你是在瞎三話四嗎?不,你說的是事實,是事實,你就要咬牢,要多說幾遍。”
“不,我沒有推他落水,是他自己落水的。”
紅桃的兩根指頭又在小英臂膀上用力捩起來。小英沒有發聲,也沒有抗爭,不,她抗爭了,她的抗爭集中在了自己的臉上,她臉上的皮肉在扭動,嘴角也扯到了一邊。不過,她的身體不動,僵硬著。紅桃似乎很不滿這僵硬,用力推了她一把,又撲到了她的身上,隨后雙手同時在她身上掐起來。
小英居然還是不出聲,只是身體在扭動,想從紅桃的身下掙脫出來。可她越是掙得厲害,紅桃的雙手掐得越是厲害。于是,她不再動彈。
紅桃繼續掐小英。她不想在小英身上留下看得出的掐痕,所以她不再掐小英露著的臂膀。她現在只掐小英被衣裳遮著的胸脯。她邊掐邊在嘴巴里咕,你非但不咬牢,還否認是你推的!你這樣說,不擔心被雷打嗎?
紅桃不再掐小英,猛地直起上身,從小英身上下來,坐定。喘著氣,她又說:“其實,現在你否認也沒用了,橫涇人都曉得是你推阿戇落水的,都曉得了你不愿來我家。”
小英還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見小英對她的話沒啥反應,紅桃就一把抓住小英的手臂,把她從地上拉起來,還把一口唾沫吐到了小英面孔上,接著,她對小英說了這次見面中的最后一句話:“告訴你,你來我家的話,除了給我家白白增加一個人的口糧,沒其他用場。現在,我家可以不要你了,不過,因為你推阿戇落水了,村里的人會認為是你家不要阿戇的。”
紅桃拎起籃頭,拍了一下屁股,一篷塵煙從她屁股后頭悠悠飄下,飄到了小英的面孔上。小英打了一個噴嚏,也從地上爬起來,尾隨著紅桃,往樹林外走。
四
紅桃又來到了美娟家。她進門時,正在客堂里的小英想轉身往灶頭間走,紅桃叫住她:“做啥要逃?怕我吃你嗎?”
在客堂的一角,美娟正在一只青缸里發豆芽。她把臉從缸口抬起來,直起身,沾滿汗漬的面孔上堆出笑。她甩甩濕漉漉的雙手,向紅桃迎上去。
紅桃還是挎著一只籃頭,上面遮著一塊羽襟。
小英立停在了灶頭和客堂之間的門檻上。恍惚間,她以為紅桃是剛從那個樹林里出來的,她身上被紅桃捩過的地方也立刻疼痛起來。她一步跨進了灶頭間里,走到灶肚后面,在木凳上坐下。她聞著灶肚里草木灰的淡淡香氣,支起耳朵,聽客堂里傳來的聲音。
美娟說:“紅桃,你這是做啥呢?”
紅桃已拿掉籃頭上的羽襟,里頭是方糕和赤豆粽等一些糯食。
紅桃說:“做的時候,多做了幾個。看到我,你家小英做啥逃呢?”
美娟就朝灶頭間里喊小英,沒有回應。
美娟說:“這小貨色,真不識相。”
她又朝灶頭間里喊。小英在灶肚后立起來,不過她沒走進客堂里,而是一步跨出灶頭間連著后院的木門。她感到她身上的疼還在,她像是要逃避這疼似的逃向后院,繞過絲瓜棚,走過一塊小小的菜地,然后來到了隔壁人家的灘涂石上,坐下。她聽不到她家客堂里的聲音了,只聽到面前的河水的細小流動聲,甚至聽到了水草里小鯉魚的唼喋聲。河水的流動聲和小鯉魚的唼喋聲襯得周圍特別寧靜。一歇后,小英似乎有點忍受不了這種靜了,朝她家客堂的方向側轉頭來,支起耳朵。然后,她家客堂里的聲音也真傳來了。這聲音居然也像她面前的河水聲一樣清晰起來。她聽著美娟和紅桃的對話,感覺到自己的命運也像小河河水一樣在向前流動,在流動中被不斷擠壓。她感到美娟和紅桃的聲音就是兩道扭曲的河岸,不斷擠壓著她的命運之河,而她的命運之河在掙扎著往前流動,流向不可知的明天。
紅桃說:“我看算了。”
美娟說:“啥意思?”
“阿戇配不上小英。”
“你不要試探我,我們不會變。”
“還用試探嗎?你看,我一來,小英就躲開。”
“她那是難為情,你也不要再開玩笑了。”
“我這不是試探,也不是開玩笑,我這是實話。我實話對你講吧,其實小英來我家,我家就是多支了一份口糧。”
“紅桃,你越說越豁邊了。你說這個口糧不口糧的豁邊話,說明你就是在試探。我不能上當。”
“不是試探。”
“我如果把你的試探當真了,上你當了,村里的人最后戳的還是我的背脊骨,而不是你的背脊骨。”
“美娟,謝謝你這樣講。”
“紅桃,我只能這樣講。你不要落眼淚,你傷心啥?你不要落眼淚。”
“好,我不落。我不傷心,我開心。你怎么也落淚了?”
“跟你一樣,我這也是開心的眼淚。”
這些話,像是一縷輕風,穿過小英家的后窗,越過屋后院子里的那個絲瓜棚,又經過那塊小小的菜地,然后吹到了隔壁人家的灘涂石的上方,和小河的流動聲、魚兒的唼喋聲匯聚在一起。匯聚在一起后,這縷輕風似乎變強大了,開始撞擊小英。小英的上身微微搖晃起來,這撞擊似乎也讓小英感到疼痛了,也或許感到開心了,她流淚了,和客堂里的那兩個女人一樣流淚了。她也和那兩個女人一樣,說不清自己的眼淚是傷心的眼淚還是開心的眼淚。她低頭,看到河中的水草邊有幾尾鯽魚,嬉戲中的它們顯然是開心的。開心的鯽魚卻讓她臉上的眼淚水流得更多了。
她繼續淚眼朦朧地看著河中的鯽魚,它們還在左右追逐,上下嬉戲。它們的追逐和嬉戲在河面上激起了一道一道波紋,這波紋是它們開心的笑,無聲,可持久。
她也笑了,流著眼淚笑,淚眼里也有一圈一圈閃亮的波紋。她在灘涂石上立起來,也想做一條魚了,也想讓自己的笑化作河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紋。她跨前一步,立在了最后一個臺階上。這個臺階是一塊狹長的黃石,河水的長期浸潤,使它變黑了。不過它還是那么陰涼,陰涼透過她的鞋腳底傳到了她的腳底心,然后又傳遍了她的全身。這是黑的陰涼、水的陰涼、魚的陰涼,也是快樂的陰涼。她站在最后這個潮濕的臺階上,已感受到魚的快樂了。魚的快樂是左右追逐、上下嬉戲的快樂,她也要去追逐它們了,和它們一道嬉戲了。
橫涇河里產生了一聲水響,像有一條大鯉魚躍起后重新撲入了水中。
五
正走在河北岸的春林把小英救了起來。他看到有人在河里掙扎,都忘記了驚呼,立刻跳入河中。
春林第一時間認出了小英。小英已經窒息,臉色像白紙。春林向四周發出幾聲救援般的喚叫聲,可沒有誰應答他,周圍一片寂靜。
把小英抱到河北岸的玉米地里后,春林稍稍鎮定下來。他看到過好幾次別人搶救落水者的情景,現在,他也要這樣做。他在小英的臉上擰了一下,看到被擰過的地方立刻凹下去,又迅速彈回來,他心里就有底了,馬上跪下左腿,弓起右腿,然后把小英背朝上、面朝下地橫擱在自己弓起的右腿上。
午后的陽光灑下來,春林的頭頂感到了陽光的熱辣。他開始不住地顛動弓著的右腿,隨著顛動,小英橫著的身體也在上下顛動。他的右腿感受著小英肚腹的柔軟,眼睛盯著小英的嘴巴,終于,他看到小英的嘴巴里開始掛下一線水流。
在陽光的蒸烤下,玉米葉散發著干澀的氣息,地上的泥土蒸騰起干燥的氣味。春林翕動著鼻翼,繼續顛動右腿。小英嘴角那里流下的水線變粗了,她的喉嚨口發出了一記輕微的聲響,垂向地面的右手似乎還抓摸了一下。
這聲響和抓摸讓春林大腿的顛動舒緩下來,他的目光落在了小英身上,小英濕漉漉的上衣和單褲緊緊貼在身上,身上的曲線就顯現出來。很快,春林又抬頭四顧,目光中帶上了一絲警覺神色。
周圍沒有人。不過春林眼中還是有些許擔憂神色,他又轉臉四顧,然后右腿完全停止顛動,左手向前伸去,像要去半空中抓摸啥。他的左手停在半空,仍帶著一縷擔憂神色的眼睛又朝小英看去。小英嘴角處的那條水線還掛著,不過變細小了;她的臉色在泛紅,身體上的溫度也在上升,春林的大腿已感受到了這體溫。
春林的左手迅速落下,落在了小英圓滾滾的臀部。左手摩挲了幾下后,他放下了小英,把她放到地上,兩只手同時在她身上抓摸起來。可很快,小英的眼睛睜開了。
春林的眼睛第一時間和小英的眼睛對上了,他迅速移開目光,也迅速地把手移開。他單膝跪下,左手重新伸進了小英的胳膊間。
春林說:“你醒轉來了。”
小英卻重新閉上眼睛。
看著小英閉著的眼睛,春林覺得她已經沒有問題。春林注視著小英右眼皮上一粒細小的黑痣,希望她躺在他臂彎里的時間長一點。可小英很快又睜開了眼睛,掙扎著要從春林的臂彎里立起來。春林攙扶著她,讓她立起來,自己也立了起來。剛立停,小英的腿彎打晃了,身體就歪靠在了春林身上。
春林說:“怎么會跌到河里的呢?”
小英不出聲,身體從春林身上移開去,也終于立穩,立穩在了離春林半步遠的地方。
小英說:“春林哥,謝謝你。”
“怎么會跌到河里的呢?”
“在灘涂石上汏腳,滑了。”
春林不再細問。
好了,小英已經完全沒有事了。春林瞥一眼靠在北岸邊的一條鴨頭船,又瞥一眼對岸,說:“上船吧,我送你過去。”
兩人就跨到了鴨頭船上。攬在一棵小樹上的纜繩被春林輕輕一扯,就斷了,也在這時,春林發覺船上沒有撐篙和搖櫓。這是一條棄船。春林讓小英立在艙里不動,自己則立在船艄上,雙腳使一下勁,穩住了鴨頭船,然后向岸上伸出左腳,用力一點,鴨頭船就快速地滑向河心。剛過河心,船的滑速就慢了下來。小英擔憂的目光落在春林的背影上。她看到春林的雙腿似乎又在使勁了,鴨頭船就繼續緩慢地向河的南岸移動。小英目光里的擔憂消失了,她放心了。
看著春林的后背,小英心里突然產生了一股異常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剛才心里的那份擔憂是沖著他的,現在心里的那份放心也是沖著他的。她進而覺得,自己心目中的真正男人就應該是這樣一個男人:既讓她擔憂又讓她放心、安心。
她想到了阿戇。阿戇只會讓她擔憂,不會讓她放心、安心,甚至連擔憂都沒有。她低頭想了一下,發覺自己心里確實不曾對他有過啥擔憂。
鴨頭船靠近了南岸那個灘涂石的東側,船頭輕輕吻上泥岸。春林的一只腳放在船艄,一只腳放在岸上,兩只腳讓鴨頭船定穩在了岸邊。
他對小英說:“上岸吧。”
小英待在船艙里不動,似乎還不想上岸。可當春林伸出手時,她的手立刻迎了上去。春林把她一把拉到了船頭上,然后輕輕托住她的腰,把她推送到了岸上。他自己也上岸了,在跨上岸的一剎那,用腳蹬了一下鴨頭船,鴨頭船在他的身后迅速滑開去,晃晃悠悠地在河心打起轉來。
“纜繩壞了。”
春林好像在為自己的蹬船動作尋借口。而小英并不認為春林把鴨頭船蹬到河心去有啥不好,她覺得就應該讓它自由自在地在河中晃悠,想飄到哪里就飄到哪里。不要用一根繩子去拴住它,不要去當小船的主宰,不給它自由。為什么現在的人都喜歡當主宰?既想當物件的主宰,還想當別人的主宰?
小英回頭看著在朝東漂移的鴨頭船,嘴里小聲嘀咕,你飄吧,隨便飄到哪里,你想飄到哪里就飄到哪里,你是自由的,別人管不著你。
“你怎么像老人,對東西講話了?”春林用疑惑的眼神看著小英,隨后他笑了,“我救你的事你也只好對死東西講,不好對活人講啊。”
春林想到自己剛才那雙不老實的手,舔舔嘴唇,又說:“你回家吧。”
小英抬腳后,春林朝另一個方向走了。沒有走出幾步,他回頭看,目光與小英的目光相遇了。
六
還是有人曉得了春林救小英的事,小英跌進河的事還是傳到她爸媽耳朵里了。美娟想問小英是怎么跌到河里的,可看到小英對她不理不睬的一副樣子,就沒有開口。美娟跟泉榮說起,泉榮就瞪她一眼,說你是阿木林?自己跳的!
美娟一聽,身體當場軟下來,癱坐在了一只竹椅子里,然后放聲哭起來。
泉榮又瞪她一眼,走開了。屋里,就只有美娟一個人了,她就盡情哭。后來,她的哭聲變小了,可哭聲還是顯得委屈、綿長。好多人都聽到了她的哭聲。
對于美娟的哭聲,路過她家門前的大部分人是見怪不怪的,因為經常有女人的哭聲從哪個家門口傳出,夫妻吵架、娘家有難、男人軋姘頭、家里丟東西等等,都是發出哭聲的原因。在橫涇村,女人的哭聲,有時就是這戶人家的一種對外宣示,告訴外人,這家人家或者這個哭著的女人碰到不幸啦,可這不幸是外頭人沒法幫忙的,所以女人的哭聲不是求援,只是一種告知、宣示。這種告知或宣示看上去與家丑不可外揚的古訓相抵觸,其實不,這種哭里沒有具體內容,只有悲傷。這種哭是在把心里的悲傷往外放呢,往外放了,心里的悲傷才會減少,直到消失。站在外頭人的角度看這哭,這哭其實也是平常的,見怪不怪的,哪一戶人家沒有難處、一直能避得開不幸呢?避不開的,橫涇有那么多戶人家,總有不幸降臨其中一戶人家。于是,在橫涇,經常會有哪戶人家屋里傳出女人的哭聲,外頭人一般不去打聽這哭聲背后的故事,就像看到哪戶人家屋頂傳出炊煙后,他們一般不去打聽這戶人家到底燒了啥飯菜一樣。外頭人曉得,家家戶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都有碰到不幸的時候。一旦家遇不幸,男人承受力強,女人往往會承受不住,就要哭,她們會哭得委屈綿長、抑揚頓挫。她們中,會哭出好聽和不好聽兩種味道——有些外頭人路過發出哭聲的人家,有時會立停腳步,聽一歇,像聽歌一樣。這時,在屋里哭的人好像曉得有人在外頭聽,哭得更加抑揚頓挫了,甚至會哭出一股特別的韻味。外頭聽哭的人如果不認得這哭著的人,這時會開始在哭聲里想象哭者的長相、年齡等,他不會揣摩這哭聲所產生的原因,只會揣摩哭者的容貌、年齡等。
現在,美娟的哭聲也是抑揚頓挫的,已經有一股糯糯的韻味在里頭了。她不曉得外頭有沒有人在聽她哭,可她曉得,她的哭既是給外頭人聽的,更像是給她家的不幸舉辦的一種儀式,這儀式是在“超度”她家的不幸呢。
可她家的不幸是啥呢?她的哭似乎是由小英的跳河引發的,不過小英不是由春林救起來了嗎?救起來就是由“不幸”變成了“萬幸”,美娟該高興啊,她怎么哭了呢?——當然,沒有啥人這樣問。不,也許美娟的家人在心里這樣問了,泉榮、小英,甚至紅崗,都這樣問了,盡管他們現在都已離開了家,可美娟的哭聲早已進入了他們的耳朵。他們不是外頭人,他們一定是在心里這么問了,只是沒有問出口。到了夜里,泉榮的一句話終于證實,他確實在心里那樣問了,他還自己回答了自己。
泉榮的這句話是對美娟說的,他說:“我看算了,還是到紅桃家去回掉吧。”
美娟瞪著紅腫的眼睛,說:“啥意思?”
“去回掉,回掉這門親事。”
周圍靜下來,這種靜好像是有重量的,壓在了美娟和泉榮身上,讓他倆的喘氣粗重起來。美娟停了手上的生活——她正在疊衣裳。昏黃的燈光下,她手中已褪色的土布衣裳也泛著一層黃色,像是沒有洗去的塵土。美娟把衣裳放在身左的竹椅上。
美娟說:“我不想讓人戳背脊骨。”
她又說:“憨人有憨福。”
之前,美娟對泉榮說過這兩句話,現在她是在重復,不過這次她說的語氣好像不同了。哭過之后,在說這兩句話時,她語氣堅決,這讓泉榮感到奇怪,也讓泉榮感到灰心。
與美娟相反,泉榮剛才說話的語氣倒比平時輕柔多了,好像不久前放聲大哭的倒是他,倒是他把身上的力氣哭完了,于是他說話的聲氣變軟了。這聲氣其實與他說的那兩句話的內容不符的,所以,就如他驚奇于美娟的話,一開始,他的話也是讓美娟驚奇的——美娟驚奇于他說話的語氣,也驚奇于他所說的話——他還是第一次對美娟說這種話。
泉榮說得比平時輕柔,不等于他是在隨口說,他是一本正經的,他又輕聲而態度堅決地說:
“去跟紅桃說吧,回掉吧。”
“不回。”
“你不回,我去回。”
泉榮轉身,跨出家門。他像是聽到了美娟在背后發出的叫喚聲,可他不管了,繼續朝前走,走上了通向那幢走馬樓的村道。走馬樓是村里的老地主遺留下的一幢老宅,老地主新中國成立前逃到臺灣后,村里的幾戶貧農搬了進去,紅桃的公公家也搬了進去。
村道兩邊,乳白色的霧氣在兩側的田野里升起,帶著一股在白天積聚起的溫熱,飄蕩到了他的身邊。不一會兒,泉榮走到了走馬樓前的場地上,在兩棵青楓樹中間蹲下——此時,他像懷揣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很怕碰到熟人,他甚至想把腦袋埋到兩腿間了。
終于,泉榮還是從兩棵青楓樹間立起來,搖搖晃晃朝前面的黃崗巖門框走去。年輕時,即使在夜里,他也能看清門框上方“高家府邸”那幾個字,此刻,他努力朝門框上方看去,卻已看不清那幾個字了。看不清,要么是風雨已把那幾個字侵蝕得不像樣子,要么就是他的眼睛已經退化,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都說明太多的日腳已經從他身上、從他周邊的東西上碾過,現在的日腳已經不是過去的日腳。
泉榮跨進門廳,聞到了鳶尾花的淡淡香味。他低頭,目光落到門廳墻腳跟的幾叢鳶尾上。門廳里盡管幽暗,可他還是看到了一朵朵的鳶尾花像一只只藍色的蝴蝶,停留在鳶尾葉間,隨時要飛起來的樣子。他立停,走不動了,再次蹲了下來,就如剛才蹲在兩棵青楓樹間一樣。
一歇后,泉榮終究還是立起來了,轉身走離門廳。他明白,他是沒法敲響阿偉家的門的,他是根本無法實現來這里的目標的——實際上,現在來這里的目標到底有沒有,他也不清楚,這個目標或許只是嘴巴上的目標,只是他與美娟爭吵聲里的目標,并沒有存在于他的心里。
泉榮在村道上往回走了,這表明,他和美娟的爭吵已經結束。
爭吵結束了,可泉榮的思緒還不能一下子平復下來,快到家門時,他沒有繼續朝前走,而是在場角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然后,他又想了一遍自己與美娟的那幾句爭吵,笑了。他認為美娟的話是對的,美娟的話其實倒代表了他的意思,而他的話倒沒有代表自己的意思,不,他的話只是代表他當時的意思,沒代表他平時的意思。平時——講到平時,他心頭漫過一股水一樣的東西,既暖又酸,說不清讓他好受還是難受——對阿戇,他心頭一直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感覺讓他在阿戇和小英這門親事上,感到自己像是男方一邊的人。這讓他自責,也讓他自醒:在小英和阿戇這兩個孩子的事情上,應該這樣做,必須這樣做(他心頭有了一個偏向)。很難說,阿戇和小英的這門親事,是不是這種“自醒”的結果,盡管看上去這門親事是阿戇家的人主動攀上來的,可這種“自醒”是否無意中促成了對方的主動呢?在對方主動后,這種“自醒”是否加固了雙方的那份約定?
回想起來,當泉榮心頭發出了“應該這樣做,必須這樣做”的聲音后,再看到小英時,他心里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柔情,一股父親對女兒特有的柔情。他不曉得以前面對小英時,心里是否有過這種柔情,不管怎么樣,他現在有了。他感謝這門親事,讓小英“成為”了他的女兒。當然,有時候他也自責,自責時,他會有一些“反常”的言辭和舉動,比如和美娟的這次爭吵,比如向阿偉家的這次進發。
好了,現在又回到了平時,他的內心也終于平復。他從石頭上立起來,吸一口涼涼的空氣,向屋門走去。
七
對于橫涇村的人來說,時間就像橫涇河里的河水,大多數時候和大多數河段,它看上去是不動的;也像中午時分掛在頭頂心上的太陽,看上去是靜止的。可實際上河水和太陽在一刻不停地動,時間也在看似不動地“動”,泉榮家就在這種“動”中迎來了一件大事。
在這件大事到來前,泉榮和美娟先是發現小英話更少了,不過變溫順了——她不主動跟泉榮和美娟說話,可當泉榮和美娟讓她做啥,她都二話不說地去做,甚至泉榮和美娟沒讓她做啥,只要她覺得他們需要幫手時,她也會默默地上前,做他們的幫手——這完全是一個就要出嫁的姑娘的行派了啊。不是嗎?好多即將出嫁的姑娘都是這樣的,突然間話語變少了,可也突然間變勤快了。她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然覺得自己說不出話了,她們只能用手、用一份勤快和體貼來表達心里的依依惜別之情,也表達對父母多年養育的感恩。大恩無言,她們怎么能用話來表達自己的感恩心情呢?不能的,說出來,這感恩之情就輕就薄了。所以她們不說,只行動。她們中,有人甚至會在半夜里悄悄地爬到她爸媽的床上,蜷縮到她媽的腳跟頭、身體邊或懷里,睡上一夜。她想回到童年,甚至想重新鉆進她媽肚皮里呢。現在,小英盡管沒有在半夜里睡到她爸媽的床上,可毫無疑問,她已經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個。
不過,小英與她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是不同的。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惜別和感恩時,一定還有一份憧憬。而小英心里只有恐懼和厭惡。不過,她把心里的恐懼和厭惡壓制住了,不讓它們流露出來。所以,她現在所表現出來的樣子,就是無數即將出嫁的橫涇姑娘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這樣子讓泉榮和美娟心里難過,真正難過了。尤其是美娟,有一天夜里,落了半夜眼淚。后來,她用枕巾揩干面孔,起身走過間壁墻,躺到了小英床上——倒過來了,美娟倒成了一名就要出嫁的橫涇姑娘,而小英則變成了她媽。其時,小英和紅崗已分開睡了,美娟在原來的那張木床邊給紅崗搭了一張小床。當美娟睡到小英身邊時,睡在小床上的紅崗似乎聽到了動靜,翻了一下身子,嘴巴里嘰咕一聲,又磨了幾下牙,就不再有動靜,重新發出細微的鼾聲。他沒有被驚醒,真正被驚醒的是小英,可她假裝沒有醒轉,假裝還在夢頭里。當她媽的手臂繞到她身上時,她一動不動;當她媽把臉頰貼上她的臉頰時,她還是一動不動。可她媽已經感覺到她醒轉了,小英也曉得了她媽的這感覺。曉得了,她還是裝作沒有醒轉來,裝作還在夢頭里。
美娟也不動了,手臂仍舊繞在小英身上,臉頰仍舊貼著小英的臉頰,好像她也睡著了。美娟側躺著,小英仰躺著,兩人就這樣“睡著”了。這樣的“睡著”能把兩人真正帶進夢鄉嗎?肯定不能,對美娟來說,抱著孩子睡覺已是陳年舊事;對小英來說同樣如此,躺在她媽懷里睡覺不知是哪一年的事了。現在,她們已經不能回到過去,可她們這樣做一定是想回到過去,這樣,她們其實是在與自己過不去了。與自己過不去,只能讓自己難受——兩人不能再裝作睡著了,再裝作睡著,身上的皮肉就一定會酸疼,皮肉一酸疼,兩人只能動。小英先動,她的身體一拱一拱的,既像在撞擊美娟,更像要鉆進美娟的身體里。美娟身上的酸疼感被拱輕了,可還有,她的右手就在小英的后背上輕輕撫摸,撫摸的動作牽動了她渾身的皮肉,她身上的酸疼感就基本消失了。小英身上的酸疼也消失了,不過朝她媽身上拱的動作似乎給她帶來了另一種感覺,她想留住這感覺,甚至想讓這感覺再強一些,就不僅繼續拱,雙手也開始在她媽身上撫摸,不,其實是抓摸。她媽身上像有著啥滑脫脫的東西,需要她一次次抓摸。她的抓摸是輕柔的,這輕柔地抓摸也像落在了她自己身上,讓她心里那股暖暖的酥軟感覺更強了。她把臉貼到了她媽的臉上,就跟她媽剛才做的那樣。她的臉一貼上她媽的臉,她媽的臉就在她的臉上摩挲起來,她感到自己終于在那股暖暖的、酥軟的感覺里融化了,融化進了她媽的身子里。她也就真正進入了夢鄉。
可美娟還是睡不著,她就開始回憶,回憶自己嫁到橫涇后發生的樁樁件件事體,也回憶嫁到橫涇以前發生的樁樁件件事體。這些事體都是她經歷過的,也是讓她難忘的。把這些事體串起來,就是她的一條命運的曲線——在她還是姑娘時,有一次,一位算命先生曾指著她手掌上的一條紋路,說它是她的婚姻線。女人的婚姻線就是她的命運線。因為美娟家窮,給不起“卦金”,這位走村串戶的算命先生不愿意再說下去了,拄著拐杖要走。美娟媽立刻把兩個雞蛋塞到算命先生的口袋里。算命先生就重新開口,對美娟說,你的婚姻大事一定要由你爸媽做主,我只能多說這一句話,不能再說別的了。算命先生多說的這句話是用兩個雞蛋調來的。現在看來,就是當時的兩個雞蛋把美娟最終引到了橫涇——紅桃當時來做介紹時,美娟其實與本村的一個小伙子好上了,可她爸媽是極力反對她嫁給這個小伙子的,而對紅桃提起的這門親事倒是極力支持的。后來,在大人們為小英和阿戇確定那種關系的前后,美娟也曾拿著“卦金”去給小英和阿戇算過命。算命先生的家在十幾公里外,那里有一棵千年白果樹,被人稱做“仙樹”,“仙人”就在“仙樹”下為小英掐算。第一次掐算時,“仙人”居然說:你女兒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讓她爸媽,也就是你與你男人做主。這不由得讓美娟感到驚奇,立刻想到了以前那個拿了她家兩個雞蛋的算命先生。更讓美娟感到驚奇的是,“仙人”又加了一句:這樣,你女兒的婚姻才能順當。美娟就睜大了眼睛,看著“仙人”那張枯瘦的臉,又把目光轉向一旁的白果樹,看著這棵需幾個人合圍才抱得過來的大樹,她很想給它燒根香,她也很想給“仙人”增加點“卦金”。可最后她啥也沒有做,只是懷著一份敬懼回家了。后來,她又去尋“仙樹”下的“仙人”了,這次,她報上了阿戇的生辰八字。“仙人”沉默一歇,然后說,沒人說聰明不好,可實際上,聰明總被聰明誤;沒人對憨人道好,可往往是,憨人總有憨福氣。美娟又一次睜大眼睛,又一次把目光從“仙人”臉上轉到了“仙樹”上。“仙樹”粗糲的樹皮上有一道彎彎的疤痕,它像一只含笑的眼睛,看著美娟。
現在,床上的美娟覺得那只“眼睛”仍含笑看著她。美娟的嘴角處也露出了笑意。她一笑,身體就放松了,身體一放松,一股暖暖的、酥軟的感覺就上身了,這感覺和小英剛才的感覺是一樣的,既是一種酥心的感覺,也是一種瞌睡的感覺。在意識到自己快要睡著時,美娟使勁睜一下眼睛,抬起放在小英脖子上的右手,在半空中抓摸著,像是一只溺水者掙扎在水面上的手。很快,她的右手重新落下,落在了小英的肚腹上。
美娟的右手感覺到了一份異樣,她凝神想了一下,睡意頓時跑掉了一半。她的右手在小英的肚腹上撫摸了幾下,心頭的睡意徹底消失了。
美娟在床上坐起來,側身拉了一下燈繩,然后掀開薄被,借著暈黃的燈光察看起小英的肚皮。
小英睜開了眼睛。
美娟連忙說:“困吧困吧。”
然后,她又側身拉了一下燈繩,周圍重新一片漆黑。
八
美娟后悔告訴泉榮了。泉榮在屋后攔住小英的一剎那,美娟就后悔了,她看到泉榮一把抓住小英的肩膀,低吼:“我還以為你是胖了!”
小英想掙,泉榮把她按在瓜棚邊的石凳上,又低吼:“不要動。”
泉榮還從來沒有這么粗暴地對待過小英,美娟很吃驚。接著發生的事讓她更吃驚了,她見泉榮拿起地上一根細竹竿,開始往小英身上抽打,邊抽打邊說:“說,誰的?”
泉榮把自己的說話聲壓得很低,可在美娟聽來,這聲音還是那么響亮。
和壓低嗓音一樣,泉榮也控制著抽打小英的動作,他似乎沒有狠命抽打,手臂沒完全掄開,只用手腕用力。他眉頭皺緊,嘴角歪斜,臉上顯出了痛苦的表情,好像被他抽打的是自己。
每挨一下抽打,小英的身子就抖動一下,可她不擋不逃,也不叫。
美娟也像受到了挨打,她身體發軟,腿彎打戰,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可她立刻又掙扎著立起來,往前走幾步,把身體擋在了小英的面前。
這時候,如果老天爺的目光投向人間的這個場景,他會看到泉榮拿著竹竿的手遲疑了一下,眼睛里似有亮光一閃,然后,泉榮的手臂再次掄開了,他手中的竹竿落到了美娟身上。美娟的身體震動了一下,還發出了聲響,人,也又一次跌坐下去。這一次,她跌坐在了石凳上。
老天爺聽到了美娟身上發出的聲響,它比剛才小英身上發出的聲響要大。老天爺還看到泉榮的眉頭展開了,嘴角也不再歪斜。
挨了竹竿后,美娟的嘴巴里沒有發出聲響。這一點,她是與小英一樣的。她的嘴巴緊緊抿住,她似乎變成了電影里受到逼供的英雄。她又挨了一竹竿,身體再次震動了一下,雙手的十指緊緊摳住身下的凳沿。
泉榮手中的竹竿落下的頻率密起來,美娟的嘴巴里終于發出聲響了,可她在壓抑這聲響,所以顯得粗糲、喑啞,她試圖把這粗糲、喑啞的聲音壓回到喉嚨口,可失敗了,失敗后,這聲響像是被撕裂了,帶著“嘶嘶”的尾音。這種撕裂感就是她的疼痛。她的疼痛粗糲、喑啞、破裂,可這疼痛讓泉榮眼睛里的光亮更亮了。老天爺看到這光亮一閃一閃的,老天爺認為這一閃一閃的光亮就是快樂。快樂大部分情況下會變成笑,甚至會變成手舞足蹈。如果快樂沒有變成笑,變成手舞足蹈,就會變成快樂者眼睛里一閃一閃的光亮。這樣的情況,老天爺看到的多了。就是在泉榮身上,老天爺以前也看到過這樣的情況,比如他從紅桃那里回來,眼睛里就有一閃一閃的光亮,這種光亮往往要持續大半天或大半夜。老天爺當然曉得每個凡人的快樂是從哪里來的,世間萬事萬物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哪能不曉得呢?他現在就曉得泉榮的快樂是從哪里來的。他看到泉榮發亮的眼睛里映現的美娟不是現在的美娟。好多年前,泉榮沒有用竹竿抽打美娟,現在美娟送上來讓他抽打了,他的手臂就掄過了十六年的時光,讓竹竿落在美娟身上。
紅崗的到來中斷了泉榮的抽打。紅崗沖上來,抱住泉榮,還朝石凳上的兩個人哭喊,你們跑開啊!
泉榮扔掉了手里的竹竿。
盡管受了皮肉之苦,可美娟不恨泉榮。到了晚上,兩人躺在床上時,美娟的身體悄悄貼到泉榮身上,泉榮動一下,微微移開身子。美娟又貼上去,泉榮就不再移開。美娟把手放到泉榮胸膛上,她想撫摸,可手臂和腰身上的疼痛最終沒有讓她做出撫摸的動作。她就貼著泉榮躺著,一動不動,泉榮也一動不動。后來,泉榮終于開口,說:“我要廢了那小子。”
美娟像是沒有聽見,她沒有立刻接嘴。
“不能便宜他。”泉榮又說。
美娟終于說:“他是誰?”
泉榮說:“對,他是誰?”
“我問你呢。”
“這死貨色不肯說,我現在再去問她。”
泉榮要起身,美娟想拉他,可抬手的動作把她渾身的疼痛又都牽出來了,她嘴里呻喚一聲。
泉榮轉臉問:“怎么啦?”
美娟說:“不要去問了,是春林。你沒有覺得?”
“我怎么沒有覺得?打她時,我問管問,肚皮里還是清爽的。我就是想讓她親口說出來。”
“她已經親口對我說了。”美娟聲氣綿軟地說,“她不說,我其實也曉得是誰,我撞到過他們幾次……”
泉榮重新躺到床上。
“我也看到過,可我沒有往那方面想。”
“現在也不要多想了,領著她,悄悄打掉吧。”
“不,不能便宜了春林。”
“對,不能便宜了他家,應該找上門去。”
“你怎么順我了?”
片刻后,一股警覺掠上泉榮心頭。他重新抬起上身,他這次不是為起床,是為了看美娟。他和老天爺一道,在美娟的眼睛里看到了亮光。這亮光曾經在他自己的眼睛里閃過,在自己眼睛里閃時,他沒有看到,只有老天爺看到,現在閃在美娟的眼睛里時,他與老天爺一道看到了。
“黃花閨女能讓人隨隨便便困了?”美娟說。
美娟看著泉榮。泉榮注視著她眼睛里的亮光。
泉榮說:“這事不能聲張,悄悄地領她去打掉。”
“悄悄地領她去打掉也有人會曉得。”
“這不管,這總比鬧騰后讓人曉得好。這事不能鬧騰、不能聲張。”
泉榮又說:“這事不能讓紅桃家曉得。”
美娟說:“要是曉得呢?”
“曉得我們也不承認。”
“曉得,他們也會當做不曉得。”
說罷這話,美娟眼睛里的光亮熄滅了。
九
看到紅桃,泉榮想繞開,可紅桃喊住了他。
紅桃說:“怎么開始躲我了?”
泉榮舔舔干裂的嘴唇,說:“我躲你做啥?我又沒有做啥虧心事。”
后來,他們走進了村道邊上一個廢棄的茶棚,紅桃說:“美娟來尋過我了。”
泉榮呆了呆,隨后,他聽到自己的牙骨發出了響聲。立在他面前的好像是美娟,而不是紅桃,他的眼睛里都有火焰了。他朝地上看去,地上沒有竹竿。不過,他的右手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動了。
紅桃說:“我都沒有激動,你激動啥?”
“我怎么激動啦?我有啥好激動的?”
“好,你不激動就好。我告訴你,隨便發生啥,我家都不會變。”
泉榮的右手不再抖動,他看著紅桃,又舔舔嘴唇,說:“我家也不會變。我家怎么會變呢?”
“可美娟好像要變。”
“笑話,她怎么會變呢!”
“不變就好。”
紅桃轉臉四顧,見周圍沒有啥動靜,就壓低聲音說:“早點作日腳吧。”
“你家作吧,快點作好。”
泉榮再次舔舔嘴唇,想說啥,終于又沒有說,轉身走開了。
三天后,兩人再次碰到,紅桃就把作好的日腳告訴泉榮,說是一家人翻了老皇歷的。日腳作在兩個月后。泉榮抬頭,看到天空像是一塊巨大的藍布,一朵朵白云是釘在上面的一塊塊補丁——他知道自己是高興了,自己一高興,腦子里就產生各種各樣的聯想。
紅桃說:“你朝天上看做啥?天上會落下好東西來?”
“不是落下好東西了?”
紅桃舉手揩一下眼睛,突然哭了,還男人一樣蹲了下來。
泉榮說:“做啥做啥?”
泉榮想不到自己的話會讓紅桃哇的一下哭出了聲來。他去拉她,說:“做啥做啥?”
紅桃揚起臉來,涕淚縱橫的臉上居然露出笑來,她說:“我是高興呢,我高興了就要哭,你又不是不曉得。”
泉榮的喉頭有點發熱,他也想蹲下來,然后抱住紅桃。可他剛想這樣,紅桃就直起身來了,說:“走吧?萬一被人看到。”
“我們又不做啥,怕啥?”
“不怕啥我也要走了。你還有啥話要對我說?”
“看你樣子,倒像還有啥話要對我講。”
“你看出來了。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你說吧。”
這時,紅桃反倒遲疑起來,目光里閃著一絲擔憂神色,似在擔憂自己要說的話會讓泉榮不開心,甚至會讓泉榮光火。不過,遲疑片刻,她還是說了:“你讓小英帶著身子來。”
說罷,紅桃眼睛里擔憂的神色沒有了,她靜靜地看著泉榮。泉榮沒有接嘴,與聽到任何一句極其普通的話一樣,他臉上的表情很平靜。從這表情看,看不出他是不是會照紅桃的意思辦,不過即使他想這么辦的話,小英本人和她媽不一定愿意這么辦——紅桃好像正在這么想了,她在轉身前又說:“你也對美娟和小英說一聲。以前美娟不是也這樣,帶著身子嫁到橫涇村的。”
說罷,紅桃走離了泉榮。
回家后,泉榮沒有對美娟和小英說啥。實際上,他自己也不愿意聽紅桃的話,怎么可能想讓美娟和小英聽她的話呢?他只是一聲不吭地牽住了小英的手,往外走。
小英想犟,他的手就捏緊。小英只得乖乖地跟著他走。后來,泉榮不再牽著小英的手,她也乖乖地跟著泉榮走了,她跟她阿爸上了隊里的拖拉機。拖拉機到了香花集鎮后,他們下來,轉乘上一輛像要散架的公交車。
這是一輛開往江蘇木瀆的公交車,因為一天就兩個班次,所以車廂里很擁擠,根本占不到座位。一歇后,泉榮和小英被陌生乘客隔開了。在車廂的晃動、乘客的擠壓中,泉榮不時通過人體間的縫隙,朝小英看上一眼,有時看到她的半張臉,有時看到她的后腦勺。一路上,車子要停靠好幾個車站,司機是個好心人,逢站都停了。可車里實在擠不進人了,在中途的某個車站上,有人就吊門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舉動,可車子又不能不開,否則車子里的乘客要鬧。司機就盡量往馬路當中開,以免路旁的樹木碰到吊在車門外面的人。后來,吊門的這個小青年終于到站了,還未等車子停穩,就跳下去,拔腿跑了。車廂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氣。
泉榮有個表弟是江蘇木瀆人民醫院的醫生。他帶著小英要去找的人就是他。那時候,鄉下人碰到這樣的事都是這樣的,都去遠方尋找熟人或親戚的,越遠越好,最好出省。這個熟人或親戚是醫生的話最好了。
車子終于到終點站了,停靠在路邊的一塊木牌子邊,木牌子上是五個蒙塵的字:木瀆汽車站。
車門“嘎吱”一聲,車廂里的人都像要撲向那塊木牌子。泉榮是被人撞下車的,差點兒摜倒,好在他在木牌邊及時收住了跌勢,立停,雙腳就一下子感受到了腳下土地的堅實。他又迅速往一旁跨開去,避開人流,目光開始尋找小英。車門口還在擠出乘客,這車門此刻就是一只水壺的窄口,在往外倒的卻不是茶水,而是餃子,這些餃子爭著從壺口出來,顯得既擁擠又急促。在這種擁擠和急促中突然發出了一聲叫喚,有人在車門下摜到了。
泉榮心頭一緊,連忙跨步上前。泉榮的第六感覺是正確的,還沒有等他走近,倒地的小英已經被人從地上攙了起來。泉榮對攙小英的那位老人笑笑,老人也笑笑。老人自己都有點走不穩路了,可那么多人中攙起小英的就是他。泉榮猶豫著自己要不要也去攙扶一下老人,然后陪他走上一段路。最后,他打消了心里的這個念頭,只是走在老人身邊,像是隨時準備著去攙扶要倒下的老人,而小英則跟在他的后面。
乘客們已經四散,泉榮身邊的行人越來越少,最后,那個攙扶過小英的老人也拐進了右邊的岔道。
通往表弟家的泥道上只有泉榮和小英了。泉榮停住腳步,讓走得過于緩慢的小英跟上來。待小英走近時,泉榮在塵土氣息中聞到了一絲腥味,他疑惑的目光落在了小英蒼白的臉上。他的目光開始下移,然后看到小英的褲管在滴水。泉榮的目光像是一只手,推搡了小英幾下,小英終于支持不住,身體一歪,又摜在了地上。
直到這時,泉榮的腦幕上才像是劃過了一道亮光,他醒悟過來:他看到的是血,不是水。他走上前去,在小英的身邊蹲下來。
小英的褲管濕溻溻的,一股腥甜的氣味再次鉆進泉榮的鼻孔里。他想張口說啥,這時一輛拖拉機正巧在他們身邊“突突突”地開過,迎面撲來的塵土讓他嗆了起來。就在他發出咳嗽聲時,小英歪歪扭扭地從地上立了起來。
泉榮也立刻從地上立起來,他一步跨到了小英的面前,轉個身,蹲下來,說:“上來吧。”
泉榮感覺到了小英的遲疑,雙手就向后伸去,反抱住了小英的腿彎,然后身體前傾一下,迅速直起。他馱起了小英,開始往回走了。他曉得已經用不著去尋自己的木瀆表弟了。
泉榮的臉上都是淚水。他心里,也涌動起一股水流,他不曉得是高興的水流還是傷心的水流。
十
這次,美娟是拉著泉榮一道去十幾公里外的那棵千年白果樹邊的,可是,“仙樹”還在,“仙人”卻已不在。白果樹西側的一幢磚木平房里走出一位老婦人,告訴美娟和泉榮,說他走了,半年前走的。
美娟把目光轉向一旁的白果樹,在這棵需幾個人合圍才抱得過來的大樹上,她再次看到了一道彎彎的疤痕,它還是像一只含笑的眼睛,看著美娟。片刻間,這眼睛變成了那位“仙人”的眼睛,仍舊含著笑意。與此同時,似乎有和緩、低沉的聲音也在美娟的耳邊響起。
美娟側臉,問泉榮:“你聽到了嗎?”
泉榮說:“聽到了。”
“聽到他說了什么嗎?”
“聽到了。”
“我也聽到了。”
回家后,泉榮去了田里。美娟沒有去,在客堂里腌起菜來。一會兒后,小英進門。美娟把她叫到身邊,遲疑一下,然后用親切的語氣對她說:“春林是個聰明的小伙子,阿戇呢,也是一個憨人有憨福的人。”
小英不明白她媽說這話的用意,臉上露出茫然神情,不過只一歇,她似乎明白了她媽這句話的用意,臉上換了一種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