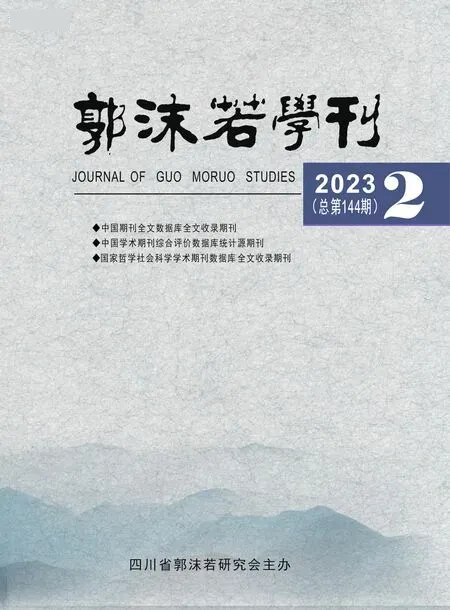郭沫若往事兩題
馮錫剛
(上海印刷出版高等專科學校,上海 200093)
一、1951:關于《撒尼彝語研究》的檢討
1951 年6 月7 日,《人民日報》刊載郭沫若《聯系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一文。僅僅過了三個月,郭沫若又一次公開檢討。事情的起因是中國科學院出版的學術著作《撒尼彝語研究》,遭致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批評,認為作者的序文存在立場問題,遂于7 月22 日致信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及相關人員:
郭院長并轉常培先生:
中國科學院出版的語言學專刊第二種《撒尼彝語研究》的序文,對法國神甫鄧明德的敘述,立場是錯誤的。為了加強中國科學院出版物的嚴肅性,提議考慮具體辦法,予以補救。今后中國科學院的出版工作中,亦希能有具體辦法,使此類政治性的錯誤不致發生。如何望示。
敬禮!
陸定一 七月二十二日①本節所引,均刊載于《科學通報》1951 年第10 期。
郭沫若接信后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次日即致函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
莘田先生:
附上陸副主任信,閱后請擲還。關于本書具體補救辦法,我擬了幾條:
(1)凡本院編譯局、語言研究所贈送者全體收回;(2)通知商務印書館立即暫行停售,發售以來已售多少,將確數見告;凡已售出之件,可能收回者亦一律收回;(3)該書必須將序文除掉,由馬君改寫,并將全體內容整飭一遍,再考慮繼續出版。以上諸點,我將以回復陸副主任,至于中國科學院出版工作的一般具體辦法,當另行商議。
敬禮!
郭沫若 七月二十三日
據此,中科院及時采取了補救措施,除處理已經出版的書籍外,7 月26 日,還做出《關于〈撒尼彝語研究〉的檢討》,指出“我們作為科學工作者的‘買辦的思想’不僅未能肅清,反而在加以‘發展’,這確是值得我們深刻地檢討的”。并強調此事“責任不限于作者馬學良,科學院的各位負責人,科學院編譯局及語言研究所的負責人,都有同樣的責任。我們希望有關的負責同志們能深切誠懇地作一番自我檢討,這樣來加強科學院出版工作的嚴肅性,并加強全中國科學出版事業的嚴肅性”。作為院長的郭沫若,自然要身體力行,《科學通報》1951 年第10 期《關于〈撒尼彝語研究〉的檢討·結語》即出自其手。《結語》開篇即承擔責任:
《撒尼彝語研究》所犯的政治性的錯誤,首先是應該由我負責來自行檢討的。書在未印出之前,我沒有親自審查,在既印出之后我也沒有細加核閱,這樣的疏忽實在是萬不應該。
接著具體陳述各項補救措施,對陸定一所作“對法國神甫鄧明德的敘述,立場是錯誤的”定性,作了詳盡的闡發。對于著作者,郭沫若說了這樣一番話:
國內少數民族的語文研究者不多,像馬學良同志這樣對于少數民族語文有素養的學者,我們是應該珍惜的。這次所犯下的錯誤,主要是由于我們負行政領導責任的人幫助不夠,但馬學良同志卻能夠認真檢討,接受批評,為我們的學術界樹立了一個良好的作風,我們認為是難能可貴的。
引用兩段毛澤東語錄來總結教訓:
毛主席說過:“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我們在這次檢討中,可以說,是實踐了毛主席的這個寶貴的指示。但“改正”得是否“徹底”,還要看我們今后大家的努力如何。要肅清舊時代的思想,是一項很艱巨的斗爭任務。“錯誤要求犯得少一點”,非是經常不斷地進行刻苦的自我斗爭,養成高度的警惕性和銳敏的感受性,是不容易得到保障的。這一真理,我們在這一次的書面檢討中也得到了一項事實上的證明。
毛主席的《實踐論》告訴我們:“認識從實踐開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也就是整個學習過程的繼續。
郭沫若以這樣一句話結束了這篇長達三千字的檢討:
讓我們共同努力吧,為爭取政治性錯誤的徹底消滅而奮斗!
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在接到副主任陸定一的信件之后,迅速而周到地處理這一事件,足以見出自我定位的準確。大規模的武訓批判事件發生之后,在中國科學院和編譯局及馬學良本人的檢討中,都提到武訓批判一事。郭沫若本人則因曾經贊揚武訓而先后兩次在《人民日報》公開檢討。將郭沫若因武訓問題所做的檢討和因“序文”事件所做的檢討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在領導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同時,郭沫若面臨著怎樣的思想壓力。
二、1954:《〈侈靡篇〉研究》之前后
1954 年前后,郭沫若以相當的精力,從事《管子》集校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事由的遠因可以追溯到1951 年的兩次檢討。1952 年2 月上旬,郭沫若收到從無交往的知名學者邵祖平教授的一封求助信。時隔半月,政務繁忙的郭沫若親筆回復,以少有的坦誠,直陳心事——
祖平先生:
二月二日給我的信,我拜讀了。魯迅先生確是不可及的。以他的年齡和所處的時代,象他那樣跟著時代前進,一直站在最前頭的人,實在少有。從發展的過程上來看,他自然也有些可訾議處。我的《莊子與魯迅》,便是采取那樣的角度來看的。魯迅受過莊子的影響,但他在思想上已經超越了莊子。和韓非的思想更是立在兩絕端的。只要是實事求是的研究,我覺得不算是失敬。
足下對我,評價過高,實毫無成就。拿文學來說,沒有一篇作品可以滿意。拿研究來說,根柢也不踏實。特別在解放以后,覺得空虛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樹,著述研究也完全拋荒了,對著突飛猛進的時代,不免瞠然自失。我倒很羨慕教學工作,時常能與青年接近,并能作育青年,立人立己,達人達己,兩得其利。這事業是值得終身以之的。望足下不要輕視它。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長,重慶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師。
科學院無文學研究機構。丁玲所主持的研究院,以創作為主,年青人多,和先生的希望不符。我希望您仍然打起精神,為西南文化建設服務。學習馬列主義,隨處都可,不必北來。
此致
敬禮!
郭沫若
二月十七日①《文藝報》1979 年第5 期。
邵祖平是民國時期成名的舊體詩詞的作家,于詩學造詣深湛,1940 年代執教于四川各大學。1950 年代前期,邵因故欲辭去重慶大學的教職,求助于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欲謀北京高校執教。郭沫若復信首先談到對魯迅的評價,緣于邵早年以《學衡》而與魯迅有齟齬,且在1951 年紀念魯迅70 誕辰時發表過有違主流意識的言論,受到公開批評。想來邵在信中談及此事,作了解釋。對此,郭沫若以過來人相似的情感經歷表示充分的理解,并以寫于1940 年代的《莊子與魯迅》為例,強調“只要是實事求是的研究,我覺得不算是失敬”。1956 年,在編輯《沫若文集》時,有人建議將《創造十年·發端》刪去,因內中對魯迅多有嘲諷。郭沫若堅持保留,只是添加了題解,表示“無改于對魯迅先生的尊敬”。郭沫若既明確表示“魯迅在世也要聽從黨的安排”,那么對于涉及魯迅的有關歷史,自然也敢于在與現實政治并無沖突的前提下堅持保留真相。這分寸的拿捏十分精確。
這封信最堪回味的是這樣幾句:“特別在解放以后,覺得空虛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樹,著述研究也完全拋荒了,對著突飛猛進的時代,不免瞠然自失。”郭沫若既是卓有成就的學術家,又是具有強烈事功意識的政治活動家。鼎革之后,郭沫若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并兼文教委員會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長。在世人的心目中,確是活躍于政壇的國務活動家。然而,難為世人知曉的是,這位看來日理萬機的國務活動家,居然“覺得空虛得很”,學術與事功竟兩頭脫落。說“著述研究也完全拋荒了”,事實上1952 年出版過一本《奴隸制時代》,作者認為是“《十批判書》的補充”,較之1940 年代的學術研究自然是相形見絀。但說“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樹”,實在是出人意外的肺腑之語。(因為吐露這樣的隱衷,這封信是否實寄,是個問題。此信的原件藏于郭沫若故居,1979 年6 月,為紀念作者逝世周年,由故居紀念館提供墨跡予以公布。)
這年9 月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郭沫若由副總理移位,擔任人大副委員長。能者在職,賢者在位,郭沫若焉能不察。1955 年3 月,郭沫若應邀參加中國科學院中共黨組擴大會議,當著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陳毅的面,就加強科學院黨的領導,說了這樣一番話:“請中央派一位更高級的、真正有領導能力的同志擔任院長職務,只有如此,才可以和政府有關各部有機聯系,也可以統籌規劃科學工作。我在這里不是說客氣話,讓我多寫兩篇文章比當兩三年院長更有好處。請陳毅同志把這個意見向中央轉達一下,不然,我見了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是要提的。請中央不要把我當成統戰對象看待,讓我領導科學院的工作,確實值得考慮。”②方黑虎:《握手之間——郭沫若的中國科大情懷》,《郭沫若學刊》2019 年第4 期。就其政治抱負來說,隔三差五在世界和平大會上發表演說,無所謂建樹,而領導科學院則又覺難以伸展,故“多寫兩篇文章比當兩三年院長更有好處”實在是明智之言。
這就有了1954 年春撰寫的《〈侈靡篇〉的研究》這樣一篇長達近三萬字的論文。寫作的緣起為1953 年11 月接手的《管子集校》。許維遹、聞一多于三四十年代先后著手整理該書,原名《管子校釋》,至1951 年許氏去世,遺稿近40 萬字。郭認為“許聞舊稿僅屬草創,嚴格言之,離成書階段甚遠”,故擱置甚久。次年9 月下旬,郭沫若撰《〈管子集校〉敘錄》。①1956 年3 月北京的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輯入《敘錄》與《校畢書后》。以下摘引該文,可知其學術追求:
整理工作費時凡十閱月,中因出國,曾中輟者兩月,其余則大抵集中力量而為之。
此項工作,驟視之實覺冗贅,然欲研究中國古史,非先事資料之整理,即無從入手。《管子》書乃戰國秦漢時代文字之總匯,其中多有關于哲學史、經濟學說史之資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陰陽家者言、農家者言、輕重家者言,雜盛于一籃,而文字復舛誤岐出,如不加以整理,則此大批資料聽其作為化石而埋沒,殊為可惜。前人已費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釋,但復散見群書,如不為摘要匯集,讀者亦難周覽。有見及此,故不惜時力而為此冗贅之舉。
許氏余所不識,聞氏生前則曾兩次見面,并曾有文字往還。二氏同系清華大學教授,二氏之合作,其時在抗日戰爭期間,其地在昆明。為物質條件所限,二氏所參考之書籍不多,……。
凡在整理過程中,對《管子》原書不能不反復通讀,于諸家校釋亦不能不反復校量,故于原文疑難處之通曉亦得時有弋獲。因此使整理后之稿本增至一百三十萬字以上,比許聞原稿已增加三倍。
1955 年11 月,郭沫若寫《校畢書后》,“本書之增訂,計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接受許聞初稿加以整理,至今二校校畢為止,費時整整二年。行有余力,大抵集中于此”。在陳述了種種“令人難以滿意者”之后,以欣慰的心情告白:
本書如上所述,且有種種疵病,然于歷來《管子》校勘工作,已為之作一初步總結。此一工作,于今后有志研究《管子》者,當不無裨補。此書之作,專為供研究者參考之用耳。使用此書時或不免有龐然淆雜之感,然如耐心讀之,披沙可以揀金,較之自行漁獵,獺祭群書,省時撙力多多矣。
至余整理此書,亦復時有弋獲。《管子》一書乃戰國秦漢文字總匯,秦漢之際法家學說尤多匯集于此。……故欲研究秦漢之際之學說思想,《管子》實為一重要源泉。余久有意加以徹底研究,而文字奧衍,簡篇淆亂,苦難理解。今得此機會,能將原書反復通讀,鑿通渾沌,已為此后研究奠定基礎。二年之光陰,亦非純然虛費也。
《〈侈靡篇〉的研究》正是集校過程中的研究成果。該文論證《侈靡篇》的制作年代為漢初“呂后專政時代”,論斷其“基本上是一篇經濟論文”,并論述其政法文教、軍事國防之主張,分析作者的“階級立場與思想背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探究侈靡學說衰頹的原因。以“余久有意加以徹底研究,而文字奧衍,簡篇淆亂,苦難理解。今得此機會,能將原書反復通讀,鑿通渾沌,已為此后研究奠定基礎”的學術自信,假以時日,《管子》研究或將與《十批判書》成并峙雙峰。遺憾的是,《〈侈靡篇〉的研究》既是開篇,亦為終曲。《〈管子集校〉敘錄》的結尾,算是留給后人的托付:
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險,披荊斬棘者縱盡全功,拾級登臨者仍須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勞,焉能享受?關于《管子》全書之進一步研究,將尚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