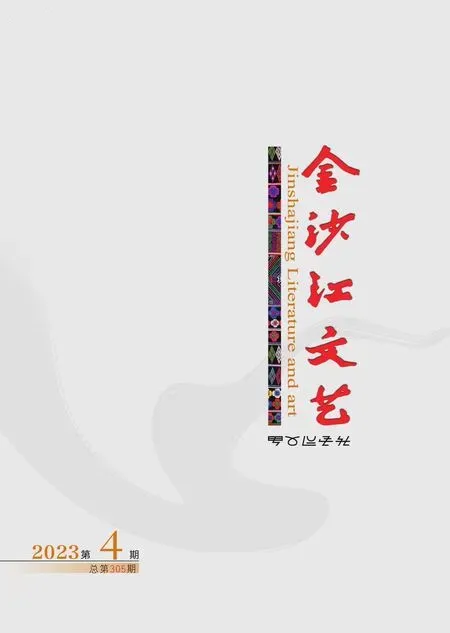雄性河流
◎李成生(彝族)
河流的性別,一直是女性的專利。黃河、長江,詩人們都以“母親”喻之,言其滋養生命,孕育文明。可是在巍山,這種約定俗成的概念被打破——先祖把起源于這里的河流稱為“額骨阿寶”,這是一個彝語名詞,翻譯為漢語就是“一條彎彎曲曲河流的父親”。以這個詞義審視發源于巍山的大河——紅河,讓人的想象闊達廣袤:穿越崇山峻嶺的紅河,它的那些難以計數的支流,像同一血緣的家族譜系,是這個父親的子女,它們也許有溫柔恬靜的一面,但更多屬于奔放、澎湃、勇敢、無畏、豁達以及剽悍,這是男人具有的性格。
當然,紅河有資格承受這樣的稱謂。它在中國境內流經十幾個縣(市),一路向南,越過越南老街、安沛、河內,奔騰1280公里,在太平省投入南太平洋懷抱——北部灣的萬頃波濤,攪動著紅河的激情,沉淀著南高原生生不息的文化氣質,博大的、雄性的河流特質,彰顯著男性百折不回、艱苦卓絕的性格。
把目光聚焦于巍山一隅,我們感慨萬千,同時浮想聯翩。這條大河的起源,聽不到一個雄壯的音符,更像唐人的仕女畫、宋人吟唱的小曲,纖細婉約,波瀾不驚。或者是上蒼的縝密安排,“額骨阿寶”起程的地方名叫龍虎山。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幾乎全部崇拜龍這種被時間虛構的神靈,它大多數時候是水的化身,那個第一次載入古籍的《九隆神話》,神秘地解釋巍山起程的南詔國王族源頭,他們自稱是九隆之后,相信這種只能想象的生物是他們的祖先。至于虎,對于發軔于古代烏蠻的彝族來說,太古歲月里曾經是他們的圖騰。他們以為世界萬物都是一只神虎倒地后變幻而來的,他們自稱 “羅”或“臘羅巴”,就是老虎的意思。這座毫無險峻可言的龍虎山,坐落在巍山縣永建鎮北面的崇山峻嶺中,是哀牢山的一條余脈,饅頭一般的山巒只能算巍峨哀牢山的孫輩,縱然林木蔭翳,鳥唱蟲鳴,但抵不住它的矮小卑微,見過這些“山包”的人大失所望:一條雄壯奔騰的大河,怎么會起源于這樣嬌小的“饅頭”之中呢,它們實在是太小巧玲瓏了,它還敢稱自己是“額骨阿寶”!
當拜訪過紅河源頭的人嘗夠這些饅頭狀山巒的厲害后,大都認為這條大河從此起程,“師出有名”。那是一個上蒼擺下的迷魂陣,如果沒有向導,你進去以后很難找到出來的路。它們相貌相同,網狀的崎嶇山道彼此相連,讓拜訪者終日在山里轉圈,直到你精疲力竭。這個名叫密鹿么村的山民們會告訴你一個秘密:在一個香蒲草長得異常旺盛的地方,挺立著一棵古老蒼勁的麻栗樹,山民稱其為“龍樹”,樹旁有一低矮、簡陋的龍王廟,其間一個淺淺的水洼,就是紅河的源頭。每年農歷正月、四月、七月的某一天,山民會來此祭龍,殺雞宰羊,敬香跪拜,祈求龍王普降甘霖,讓村莊五谷豐登,富足豐腴,然后豪飲踏歌,愉神愉己。神圣從神秘演化而來,以世俗的方式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把龍看成行云播雨的大神,是祖先們靈魂深處的一種企盼,當實在無法戰勝不斷光臨的大旱災難,他們只能想象出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神,膜拜它,驅使它。在這個世界上,迄今為止沒有哪一個人見過龍的尊顏。正如這神秘的大河之源,它的隱藏處秘不示人,它要孕育一條偉大的河流,必須用最晶瑩最圣潔的水滴洗凈塵垢,為千里奔騰作最完美的準備。畢竟,它的目標是遙遠的南海,在不間斷地遠瞻和吸納中,走完充滿挑戰的坎坷旅程。
龍虎山以茂密的森林涵養大河之源的力量。據說,這里的水源即使遇到大旱之年也不會枯竭,一如既往地汩汩涌泉。從那水洼浸出一條涓涓溪流,晶瑩剔透,漸匯成河,然后像孩童一樣牙牙學語,再后便高歌前行,銳不可當。這一段出山的河水,被山民稱為“羊子江”,大概山民善養山羊,因為河岸水草肥美,氣候溫和。成長必經的歷程,大河從這里蹣跚學步,流進狹長的巍山壩子后,它就是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年,蓬勃地奔向遠方。
自然神奇地演繹著雄渾的歷史。古代的陽瓜川如今稱為西河:它總是沿著西山一側前行,從不淌到東面。它是大山的兒子,在尚未遠離故土的時候,緊依魁梧的父親,培養百折不撓的陽剛之氣。這一段旅程雖然只有短短的30多公里,但足以讓這位遠征的兒子積蓄充沛的力氣:東西兩面的大山滋養了一群血性的支流,對稱地兩兩相向,注入主干河流,各20余條支系,把這片土地澆灌成富庶的魚米之鄉。這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家族,它們聚集在高聳的巍寶山下,歷練成一隊神勇的武士,闊步遠征。這個族群更像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王朝,葉脈狀的水系其實就是刻在歷史神經上的族譜,清晰地彰顯著它們的血緣。
自然無聲地召喚著人們的靈魂。唐代,崛起于陽瓜川的一個烏蠻部落,像河流的支脈一樣鐫刻他們的家譜。他們在歷史里流經一個又一個風景,在蒼山洱海之間,在古永昌郡邊陲,在東面的昆川 (昆明),實現著一個個夢想。可無論他們走得有多遠,有一條名叫瓜川的河無法從記憶中抹去。這里是族譜的元點,富饒的原野,成為世代靈魂回歸的圣地,哪怕肉體客死在遙遠的交趾(今越南河內),他們也要乘風尋覓大河的蹤影,讓魂魄飛回夢想起源的地方。不僅僅是那幾個被史書記住的詔王,還有那些各成支系的、自稱 “蒙人”的血親,他們如奔向大海的千千萬萬條支流,扇狀地流淌于崇山峻嶺之中,卻依然遙望來處——森林和鮮花簇擁下那一泓涓流。
雄性的河,翻滾著尚武精神,澎湃向前。西河在離開故土時,與最后一個前來報到的兄弟相會,它叫五道河。一個幾近360度的回旋,是他們對故土深情的回望,是給家鄉父老兄弟的注目禮,是對巍峨大山和平曠原野的叩拜。此后,往南流至南澗東涌后與南澗河、彌渡河交匯,稱禮社江,學名元江。那片被史書記錄為“蒙舍川”的土地,經歷數不盡的腥風血雨,存活下來一種自稱 “彌撒頗”的人,“彌撒”其實就是 “蒙舍”的變音,它是這塊充滿動人故事土地上崛起的第一個政權,名叫“蒙舍詔”,它是一千多年前出現在云南高原上的一個古老王國。這些歷盡磨難的蒙氏后代,用這個曾經的王國稱謂自己,以紀念消弭在這條河畔的無數英靈,讓河流的血性在自己的血管里脈動,生生不已。
禮社江,多么富有文化的稱呼,它是對源頭那個邦國的紀念么?它一路流過水塘、漠沙、元江、紅河、元陽、蔓耗,于河口出中國境流入越南。那是一種怎樣的力量啊,在高原的溝壑中,成千上萬的支流像尋親的族胞,向這條洶涌的大河奔來,帶著高原特有的泥土,把本來清澈的河流染成紅色,這就是紅河——熾烈如日,熱忱似火,在流域的12萬平方公里內,孕育出讓世界炫目的文明。
許多民族在這條古老的河流畔生息、遷徙。傣族從河流中部遷至越南,再從越南遷至老撾、泰國;苗族、瑤族順著這條大河,不斷向南探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現在還定居在越南。而越南,這個南亞富庶的國家,主體民族京族的洪王就發源于紅河岸邊,如今,洪王廟就建在福壽縣的紅河周邊。紅河,越南語為“hongya”,這是這條大河名稱的源頭。
在這條大河的第一流域段,167.6平方公里的巍山壩子演出了河流的第一臺大戲,南詔古國發端于斯,用250余年的輝煌裝點了大唐帝國邊疆的絢爛色彩。向南,向南,文明像岸邊綠色的森林,蔓延到浩瀚的大海邊。一條雄性的河流,把生長于斯的民族滋養成天地精靈,他們雕刻大地,創造了絕世無雙的梯田文化(哈尼族);他們仰望太陽,發明了比瑪雅人更早的十月太陽歷(彝族);他們精耕細作,讓稻作文化的輝光射向四面八方(越南京族)。還有那些從河頭到河尾的城邦,讓宗教和藝術走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感動著不同信仰、膚色、語言的人們。雄性的河流,用它博大的襟懷,養大了一個殊于世界、耀眼奪目的地域文化。
它是接納、融合、交流的象征。因為永不滿足,所以不息奔流;因為渴望成長,所以一直匯集水的力量;因為自知鄙陋,所以朝拜一望無際的海洋。
啟程和抵達,紅河的兩頭講述著一個相似的故事:越南最后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將都城建立在紅河三角洲上,紅河的尾部因而有一個南詔那樣的王都,為此,人們把紅河稱為“雙頭巨龍”。千百年來,這條橫亙在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大河,吟唱著高亢的英雄史詩,一路敲響振聾發聵的鼙鼓,汲天地之靈氣,至今續寫著非凡的篇章。
雄性的河,它的故鄉是額骨阿寶。湛藍的天幕下,那片隱秘的森林,碧綠的草地,令人神往。
一個王朝的出發,像一條大江的策源地那樣,細小而波瀾不驚,多為溪流,然后涓涓流淌,最后匯成驚濤駭浪,澎湃向前。一個王朝的崛起似乎也是這樣的,它不一定依藉平曠的土地,遼闊的疆域,甚至稠密的人煙。這就是蓄勢待發。南詔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做大,很能證明這個推斷:方向決定一切,沒有正確的路徑,只會誤入歧途,斷送前程。這和人生是多么地相像,有的人找到通向彼岸的捷徑,直達目標;有的人一直在錯誤的路上徘徊,至死也無法抵達生命的終途。
對于一千多年前的往事來說,南詔國更像一個神話。絕大多數有價值的史料被湮滅在歷史的深處,至今人們能夠管窺這個國家的資料其實非常有限,不管再多的典籍提到這個傳說中的民族國度,但實際上大多出自一個人的見聞錄,這就是唐人樊綽的《蠻書》。數百年后的明朝,有個被貶的文人楊慎到云南住了很長時間,弄出一部《南詔野史》,為研究南詔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但總的來看,依然顯得撲朔迷離。
有人斷言,南詔的存在一半是史,一半是神話。可我堅信,這個邊陲民族政權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它影響了云南一千多年。
或者那些早已消逝在時間深處的祖先與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不止一次地走進巍山這片神秘蒼茫的土地,試圖讀懂一些歷史的真相。今年秋天再次來到巍山,有一個影像突然躍入眼簾,我的腦袋像被電擊一般,出現了夢幻般的場景。在巍寶山麓的巡山大殿,一個戴黑色包頭、身著羊皮褂的烏蠻漢子雙手抱胸,目光炯炯地注視著遠方。在《南詔圖傳》上我看到過這樣的形象,他是一千年前征戰在陽瓜川里的烏蠻武士,高高的鼻梁,明亮的眼球,黝黑的皮膚,剛毅不屈的表情,透出勇往直前的英武。《蠻書》里描述過一種叫“望苴子蠻”的勇士,他們不穿鞋子,上身披甲,手執長矛,“馳突如飛”,往往沖在陣前,讓敵軍聞風喪膽。我想,有這樣的武士,細奴邏是不需要玩“火燒松明樓”這種把戲的,在門閥和豪強稱雄的晉末,武力征服幾乎是這個時代獲得土地和地位的基本手段,乃至到了唐初,各種門閥勢力依然左右著歷史的進程。在云南,東西兩爨經年征伐,荼毒百姓,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正是南詔的這些武士在詔主率領下統一了云南,結束了數百年的社會動蕩,使民生得以養息,經濟社會得以發展。
從地理位置上看,南詔王朝出發的臺階并不高。這個狹長的壩子雖然富庶,物產豐盈,但畢竟深藏在崇山峻嶺中,很難瞭望遠方。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從細奴邏父子到他們的孫輩皮羅閣,四代詔王在這里堅守了近90年,不斷豐滿羽翼,在等待中兼并了周邊的部落,從經濟和軍事上積蓄了稱雄南天的力量。可是,這一切都還只是這個王朝出發的輔助準備,真正讓他們站到歷史高地上的原因,是他們洞察時勢的政治目光。也就是說,其他部落政權雖然在軍事實力上高于南詔,但他們目光短淺,除了蒼山洱海外,一無所知,更不要說選擇一條寬闊的大道。南詔的王從細奴邏開始,就將視野投向了南國這片廣闊的大地,他們甚至知道長安需要什么,深知欲得整個云南,必須要有強大的后盾。于是,“奉唐為正朔”一直是南詔的政治主張。在其他詔王沉迷于酒色的時光中,南詔的政治理想一天天走向現實。
巍寶山麓的前新村在秋色中并沒有顯現出應有的灰暗,森林只是從春天的翠綠變為深綠。這個群山皺褶中的山寨無疑透露出一些時間的密碼,解釋王者出發前的狀態:這里可以了然大半個陽瓜川,看見河水蜿蜒地流過肥沃土地,在曲折的歷程中變成一條大江。小小山寨承載著歷史的重任,在一千多年前接納了兩父子——舍龍和他的兒子細奴邏。許多民間故事將神話的情節強加給了世俗生活著的人,把歷史變成傳說,迷惑了智商很高的現代人。可是,這寂寥的山寨背靠巍峨的大山,腳踩粼粼波光的河流,賜給父子倆天時地利,使他們的耕牧變成一種精神修煉,滋養了祖先賜予的智慧,他們很快把這一川富庶攬入懷中,踏上了征服南國的途程。這時,安于現狀的洱海周邊部落首領們還在驅使奴隸,享受奢侈生活,不知越過一座名為“草吊”的山頭,亦然是龍盤虎踞的氣象。
蒙舍詔,這是南詔本來的稱謂。這個族姓源于森林茂密、群山如海的哀牢腹地。可以相信一點,舍龍在敗走巍山之前,一定是部落的首領,否則他們父子倆絕不可能擁有治人之術。他們要去一個名垅圩圖的地方,這個山包緊貼著陽瓜江,地形險要,易守難攻,勢為全川鎖鑰。這是他們第一次啟程,不墨守成規,視天下為己廬,顯示了他們的遠大的胸懷。像那條河流一樣,它發源的目的是不想永遠做一條微弱的溪流。王者的宮殿如今已埋在歲月的深處,徒留下一些殘磚斷瓦,但透過這些散碎的遺跡,仍能窺見王城昔日的輝煌景象。那些雍容飽滿的石雕佛像,那幢仍存地宮的佛塔,那些刻寫著工匠名字的瓦片,那座設計精巧的沐池,無不訴說著大唐的余韻、 “南蠻”的好學包容。這種善于學習的精神幾乎貫穿整個南詔時期,以至漢語文學的“清平樂” “菩薩蠻”等詞牌源頭均在南詔,南詔王和大臣們的詩歌創作水平不遜中原,被收入《全唐詩》。建立南詔統一政權后,他們的管理竟然借鑒了唐朝的大部分體制。南詔王室在保持原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時,接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優秀文化,不斷完善自己的智慧,較之其他五詔,他們擁有了更高的出發姿態。
整整90年,幾代人的接力,南詔在公元738年征服了洱海周邊的反抗勢力,修筑太和王宮,結束了滇西地區的割據動蕩,為統一云南打下了堅實基礎。可是,留意這段歷史時,巍山的蟄伏養息仍然是繞不開的話題:一個從深山里走出來的家族,一群曾經靠耕牧養家活口的山民,怎么能登上歷史舞臺,建立一個具有完整政治文化體系的國家呢?
夜色濃時,巍山古城的燈火顯得有些夢幻。拱辰樓被彩燈裝點得輝煌燦爛,潔凈的青石板小街徜徉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游人,美食街的夜市攤人氣爆棚,諸如 “過江餌絲” “一根面”等小吃大受追捧,這深藏大山里的集市,怎么會忽然吸引來如此眾多的異鄉客,他們來到這里難道僅僅是看看古城和品嘗美食?
從一千年前開始,這塊土地上演出過無數精彩的歷史大劇。作為一個王朝的出發地,它涵養的文化精神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一個定居美國的烏蠻后人在巍寶山土主廟修復開光之日,萬里迢迢趕來參加祭祖大典,看到祖先的塑像,老淚縱橫。他們離開故土太久了,他們仰望那段輝煌歷史的機會太少了,他們離祖廟太遠了,他們即使富可敵國,但清除不掉祖先遺留的血脈,他們會在冥冥之中夢見先人的影像,那座遙遠的山,那片蒼翠的森林,那條清澈的河,那個細長的壩子,那些早已模糊的鄉黨面容,牽繞著他們的夢魂,讓他們在漫長的思念中煎熬,他們強烈地向往回歸,回歸進這塊可以安魂的土地。云、貴、川、廣的族人絡繹不絕地來到巍山,只為看一眼這里的物象,哪怕看一看古城中散漫行走著的人群。
其實,每個人都會面臨出發與回歸。2014年夏,一群來自北京的烏蠻后代走進這座古城,在拱辰樓前流連良久,其中一個是大學的博士生導師,他指著那塊“雄魁六詔”的巨匾給同行的族人講述悠遠的歷史。而我則更喜歡另一塊匾:萬里瞻天。祖先們居住在這彈丸之地,卻能看到遙遠的未來,放眼廣闊的世界,他們的出發與回歸,越過了時間概念,閃爍著不朽的靈光。公元800年,一出來自南詔的大戲在長安皇宮麟德殿演出,這出大戲參演人數之多,藝術水平之高,就是現在的演藝團隊也難與比肩,這出大戲的名字叫 《南詔奉圣樂》。演出結束后,《南詔奉圣樂》的曲目被留在宮中,唐德宗讓宮里的“太常工人”傳習演奏,并經常在宮廷內進行表演,“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從此,《南詔奉圣樂》成為唐朝的14部國樂之一。這僅僅是南詔與中原文化學習交流的一個范例,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一個學習的民族,一個接納的民族,必然獲得長足的發展,必然能養育出一代代精英,立于先進之林。而一個深知感恩的民族,一個不忘初心的民族,一個知道回歸的民族,定能傳承善良的美德,普世的襟懷,和美的風尚。
從這里出發的是一個王朝。回歸到這里的是涓涓的文化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