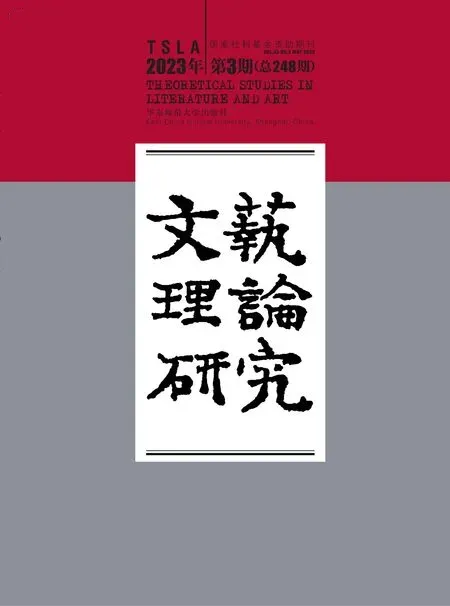用典與駢文的文本形態
李金松
駢文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一個特別的文體,主要是借助偶對、用典、聲律、藻飾這四大修辭手段建構自己的文本,并強化這些修辭手段在文本生成過程中的藝術作用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文本形態。駢文文本形態上顯現出來的獨特的藝術魅力,激發了漢魏以來的文人學士紛紛致力于這一文體的寫作,他們創造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無數膾炙人口的美文經典,不斷地給歷代讀者提供審美享受對象。隨著駢文的傳布日廣,駢文的文本形態也漸漸受到學界的關注,并被學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關于這一方面的討論,自民國早期孫德謙《六朝麗指》以來,最值得注意的是吳興華的《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這篇論文。然而,這篇論文對駢文文本形態的論述雖然有不少精到之論,但囿于對清代常州駢文創作這一主題的討論,因而沒有作更多的展開。因此,本文擬在學界已有的對駢文文本形態研究的基礎上,以當代互文性理論審視駢文文本的形態,拓深我們對駢文文本形態的認識。
一、 互文:駢文文本的生成
駢文的文本是通過偶對、用典、聲律、藻飾這四大修辭手段建構起來的。其中,偶對是駢文最基本的修辭形態,是一篇駢文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一篇文章,即使沒有用典、聲律、藻飾這三大修辭形態,但只要具備了數量相當的偶對句子,就可以被定義為駢文。但是,作家進行駢文文本的建構,不限于使用偶對這一修辭手段,而是往往伴隨著用典、聲律、藻飾這三大修辭手段的錯綜運用。大致說來,駢文所運用的這四大修辭手段,在駢文文本建構過程中承擔的藝術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偶對建構駢文的基本形態,聲律與藻飾只是具有裝飾性的作用;而用典,在很大程度上則是駢文文本的意義與其審美品質的來源。因此,根據典故的有無,駢文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類型:典型性駢文與非典型性駢文。所謂典型性駢文,即含有典故的駢文;而非典型性駢文,即沒有涵具典故的駢文。事實上,雖然有不含典故的非典型性駢文的存在,但是自漢魏以來的駢文,基本上是屬于典型性駢文。駢文的這一藝術事實,決定了其文本的生成一般依賴于對典故的運用與組織。本文中提到的駢文概念,指的是典型性駢文。
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曾這樣定義互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現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薩莫瓦約 3)又說:“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克里斯蒂娃 87)根據她對互文所下的這一定義來考察駢文,我們不難認識到:駢文對典故的運用與組織,其實是此前的其他文本在駢文篇章中的交叉出現,是對其他文本的鑲嵌組合與吸收轉化;而這種其他文本在駢文篇章中交叉出現、鑲嵌組合與吸收轉化,從而使駢文文本呈現出互文性的形態。換言之,駢文文本互文性形態的形成,是互文性發揮作用的結果。那么,典故的組織與運用是怎樣達成了駢文文本的互文性形態呢?
(一) 剪裁拼貼
宋代駢文學者謝伋指出:“四六之工,在于剪裁。”又說:“四六全在編類古語。”(王水照 34)駢文對典故的運用與組織,基本上是采用剪裁拼貼(或鑲嵌)的方式。所謂剪裁,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表達目的,對源自前代文獻中的故事或語句進行處理,刪繁就簡,趨于簡練,使之達到駢文的形式規范。如《北山移文》中“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許梿 137)這兩句,各有出典,前句源出《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司馬遷 2465)后句出自《淮南子·主術訓》:“(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蹝也。”(劉文典 290)《北山移文》中的這兩句,顯然是對《史記》與《淮南子》兩處文字的剪裁,大大地濃縮了前文本的故事性。駢文的剪裁,不僅是針對有故事性的作為事典的前文本,而且也包含作為語典的古代經典中語句的前文本。如駱賓王《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高文 何法周 98)這兩句,前句出自《史記·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司馬遷 2755),后句出自《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朱熹 104)。不可否認,駱賓王對出自前文本的語句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使之符合駢文的形式要求。雖然駱賓王所作的這些加工使語典如鹽著水,幾乎無跡可求,但這兩句出自前文本的語典,還是能夠被理想的讀者辨認出的。另如汪中《哀鹽船文》“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汪中 578)這兩句,前句出自《詩經·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高亨 221),后句出自《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朱熹 90)。前一句是經典成句的剪貼,后一句則是為了表達的需要對經典成句略事剪裁,兩處不同的前文本被汪中在文中拼貼組合在一起,從而生成了一個新文本的一部分。雖然一篇駢文并非全部由包含典故的語句構成,但包含典故的語句在一個駢文文本中往往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即如王勃的《滕王閣序》,全文773字、144句,含事典46個;如果將語典合起來,這些典故涉及的語句,共88句,占全篇句子的61%。可以說,《滕王閣序》全篇文字主要是由典故鑲嵌組合而成,是來自以前的文本,是對以前文學的回憶或表述。這些不同的前文本,在《滕王閣序》中就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如果抽離了這些包含典故的語句或其他文本,《滕王閣序》這一文本不可能以目前我們見到的形式存在,同時也相應地失去了因這些典故或前文本散發出來的美學品質與藝術魅力。可見,一篇駢文對以前文本的剪裁、鑲嵌組合是駢文文本生成的主要方式,即一個駢文文本既由互文而達成,同時又呈現出互文的樣態。也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互文是駢文文本存在的前提,沒有互文,也就沒有駢文文本了。
(二) 意義生產
一個個典故,其實就是一個個意義單位,因而用典對駢文而言,不只是語言表達上的一種修辭現象,像劉勰所言“頗引書以助文”(700),而且,也負載著駢文文本的意義生產,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駢文文本的原初意義。對于用典蘊涵的意義生產功能,現代學者劉永濟就指出:“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別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辭。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證今情也;用成辭者,引彼語以明此義也。”(131)“以少字明多意”,即典故被書寫者運用與組織的表達目的。相較于散體文而言,駢文用典是比較繁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用典而建構起來的。因此,駢文中對典故的運用與組織,不僅僅是建構文本,同時也是在進行文本的意義的生產,就像劉永濟所說的那樣,“援古事以證今情”“引彼語以明此義”。如沈炯《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最后一節:
〔……〕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吊,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凄戀。(許梿 79-80)
要想深入地理解這節文字,有必要了解沈炯寫作《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的歷史背景。據《陳書·沈炯傳》載:“少有雋才……荊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卻掃,無所交游。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姚思廉 253)沈炯寫作《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陳己思歸之意”在文章的最后一節表達得最為顯豁。沈炯對自己“思歸之意”的表達,既有“古事”(事典),也有“成辭”(語典)。“古事”主要有“嚴助東歸”(《漢書·嚴助傳》)、“長卿西返”(《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嚴助、司馬相如二人均善文章,漢武帝一度讓他們分別回到故鄉為官。沈炯由漢武帝的通天臺聯想到漢武帝時代的嚴助與司馬相如,已暗喻了自己的思歸之意。而“雀臺之吊,空愴魏君”,源自陸機《吊魏武帝文》。魏武帝曹操曾從匈奴贖蔡文姬歸漢,對此,沈炯不可能不熟知。而且,陸機此文之末有“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凄傷”(嚴可均 2030)數語,沈炯概括文意,借以表達自己眷戀故鄉而難以返歸的哀痛。沈炯運用在文中的這三個“古事”或事典,具含的意義都指向“思歸”這一主旨,其表達目的乃是“以證今情”,即傳達其當時“思歸”的情感體驗。“成辭”主要有“黍稷非馨”(《尚書·君陳》)、“徼福”(《左傳》僖公四年、文公十二年等篇)這兩個。作為糧食的黍稷,在祭祀神明中往往被用作供品。無論是在《尚書·君陳》中,還是后來被《左傳》所引用,“黍稷非馨”涉及的是祭祀神明,強調的是祭祀者的德行。而沈炯在文中沿用《尚書·君陳》篇的這一“成辭”或語典,雖然文字完全一致,但意義已發生遷轉,獲得了微微有別于原文本的新意義,意謂自己奉上的供品并不貴重。“徼福”,意為求取福報或賜福。沈炯在文中襲用的這一“成辭”,意在祈求漢武帝的神明給予他返鄉的福報。在《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最后一節,沈炯所襲用的兩處“成辭”,與其意欲表達的意旨基本上是契合無間的。顯而易見,無論是“古事”(事典)還是“成辭”(語典), 都是從以前的原文本剪裁而出,并在駢文文本中按照書寫者的某種意圖有序地鑲嵌拼貼的,是以互文的形式存在,都在參與駢文文本的意義生產,建構起駢文文本的意義系統。可以說,用典是以互文的形式參與并建構駢文文本的意義系統。而這一情形并非沈文所獨有,駢文的其他文本如徐陵的《玉臺新詠序》、汪藻的《隆祐太后告天下手書》、汪中的《自序》等,莫不如是。因此,我們可以獲致這樣的一個認識:駢文文本的意義系統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互文而建構起來的,并以互文的形式展現出來。如果沒有對典故的運用與組織而形成的互文性,駢文文本意義的豐富性將會大打折扣,文化意蘊也會顯得很蒼白。
據學界研究,“在所有的文類中,最具互文性的恐怕要數集句了”(李玉平 150)。這一看法無疑是正確的。而在集句之外,最具互文性的文類,我們不得不推駢文了。正是由于大量地運用與組織典故(其他文本片段)而形成的互文性,駢文文本才得以生成并進行意義的生產與輸出。
二、 對話:多個維度的展開
駢文在文本形態上不僅呈現出互文性的特征,而且由于運用與組織大量典故的原因,駢文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各種其他文本片段的交匯處。因此,駢文文本實際上是一個雜聲的世界,可以說是眾聲喧嘩,這從而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這種對話關系的表現不是俄國文論家巴赫金所揭示的“雙聲”和“復調”,而是“在各種價值相等、意義平等的意識之間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董小英 18),是被剪輯、鑲嵌到駢文文本中其他文本片段彼此之間的對話與融合,以及在此語境基礎上形成的歷時與共時的對話。而這種對話在駢文文本中,主要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
其一,不同文本片段的對話、交流。一篇駢文的文本系由包含典故的語句與沒有包含典故的語句這兩部分構成。沒有包含典故的語句姑且不論,而這些包含典故的語句,在形式上呈現為濃縮或未經濃縮的文本片段。如為大家熟悉的《聊齋志異》卷首蒲松齡所作的《自序》,是一篇膾炙人口的駢體之作,全篇用典是非常繁密的,基本上是由包含典故的語句鑲嵌、編織而成,這些典故在文本中以文本片段的形式存在。《自序》雖然不算長,但為了節省篇幅,我們還是截取其第一段予以討論: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中省46字)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斷發之鄉;睫在眼前,怪有過于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盧耶?(蒲松齡 6)
不過二十來句,但幾乎每一句都包含了典故。就典源而言,這些典故或文本片段來自《楚辭》、杜牧的《李賀集序》、李商隱的《李長吉小傳》《莊子》《詩經》《左傳》《后漢書》《晉書》《世說新語》《國語》《南史》《列子》《史記》《酉陽雜俎》、王勃的《滕王閣序》和《禮記》等。無論是作為事典還是語典,這些來自不同典籍的文本片段匯聚在一起,盡管經過了蒲松齡的剪輯、拼貼,但猶如不同的聲部在進行對話,有層次地述說著意脈相關的主題。如此文的第一聯,“披蘿帶荔”,對非理想讀者而言,可能沒有多少感覺,但對于理想讀者而言,很容易使之聯想到屈原在《山鬼》中刻畫的山鬼形象;而“牛鬼蛇神”,則是杜牧描繪的李賀詩歌中陰森而又恐怖的意境。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自序》中的這一聯,剪裁自《楚辭·山鬼》與杜牧《李賀集序》、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以及李賀詩歌藝術意境。這些文本片段被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在文本中構成了相互映射的對話關系,是以鬼怪為主題的對話。而通過彼此之間的對話,這些被組織的文本片段陳述了自古以來人們喜歡描述或談論關于鬼怪的事情。在這一聯之后的三句,是一聯單句對與一奇句組成,是來自三個以前的文本片段,即《莊子·齊物論》“地籟則眾竅是已……敢問天籟”(郭慶藩 49)、《詩經·匪風》“懷之好音” (高亨 191)與《左傳·哀公七年》“有由然也”(楊伯峻 1641),在四部中分屬子、經。這些文本片段經過蒲松齡的剪輯、拼接,在《聊齋志異·自序》中珠聯璧合地被整合在一起。這些來源于不同典籍的文本片段,擁有不同的語調,屬于不同的話語;而它們被蒲松齡創構的新文本《自序》吸收與轉化,其實是在這個新文本提供的平臺上進行對話、交流。在對話、交流中,這些文本片段一方面在參與文本的生成,一方面與那些沒有包含典故的語句一起,共同進行著意義的生產與輸出。所以,來源不同的其他文本片段被駢文書寫者吸收、整合到文本中,這意味著駢文文本是“各式表述片段的交匯處”(薩莫瓦約 6)。其他文本或表述片段在駢文文本中的交匯,雖然是以形式層面的存在,但實質上是它們彼此之間的對話,而且是跨文本的對話。因此,駢文文本對于這些濃縮或未經濃縮的其他文本片段而言,不過是一個對話空間。
其二,駢文文本創構者與前文本的對話。創構駢文文本,一般是要運用典故的。典故在駢文文本中,是以其他文本片段的形式存在的。被吸收、整合到駢文文本中的其他文本片段,不是隨意拼湊的,而是經過了駢文創構者深思熟慮的遴選。駢文創構者對這些其他文本片段的遴選,無疑是由其個人的文學記憶決定的。這種文學記憶,就是駢文創構者對文學史上出現過且自己閱讀過的文學作品不斷地進行回憶,并將回憶到的一些文本片段組織到新的駢文文本中。文本學者蒂費納·薩莫瓦約指出“文學作品總是在和它自己的歷史進行對話”(薩莫瓦約 10),就是針對文學創作中的這種現象所作的概括。駢文創構者進行駢文寫作,選擇典故或其他文本片段創構駢文文本,其實是與前文本亦即文學自己的歷史進行對話。不過,蒂費納·薩莫瓦約所說的文學作品與自己的歷史進行對話,包含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這包括了進行文學書寫時對以前文學作品的題材、體裁、風格、意象、辭采的選擇。而與一般文學書寫不同的是,由于駢文文本的創構需要編織大量的典故或其他文本片段,因而駢文文本創構者與文學的歷史進行對話,相比較而言,更具典型性。如庾信《小園賦》中的這一聯:
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于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于鐘鼓。(庾信 20)
雖然只有四句,但每一句都是有出處的。對于這四句,清初的倪璠一一找出它們的出處,作了比較詳細的注釋:“《左傳》閔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江淹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庾信 21)倪璠所作的注釋,盡管頗有省略,但基本上再現了《小園賦》創構者庾信寫作此聯時對文學的歷史的記憶。然而,將《小園賦》中這一聯同其出處的諸多文字進行比較,我們即可發現庾信對這些文字作了藝術處理,使之簡約為一個個文本片段,并將這些文本片段組織成一個在意義上符合自己表達需要的新文本。而庾信對這些前文本文字的藝術處理,實際上是他同這些前文本進行對話。這是因為:第一,庾信通過這些前文本的閱讀,已與這些前文本之間,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這猶如一個說話者、一個傾聽者,這些前文本向他輸出文學的歷史信息,而他作為傾聽者接收這些前文本提供的文學的歷史信息。第二,庾信接收到的這些前文本提供的文學的歷史信息,在其記憶里并不是有秩序、分門別類地排列的,而是雜亂無章的。庾信在進行駢文創構時,對于所獲取的文學的歷史信息,通過回憶、甄別,選擇最適宜體現自己意圖的文本片段。對《小園賦》的創構,庾信無疑回憶到了貯存在記憶中的《左傳》《國語》以及江淹《雜體詩》中的文本片段。對前文本片段的回憶,正是現在與往昔的對話,基本上已具對話特征。第三,對自己記憶中的前文本片段,庾信在創構駢文文本時,不是一字不改地完全抄襲或引用,而是進行一定程度的解構,改造或引而申之,或正用,或反用,使解構后的文本片段與自己的思想意識或情感體驗契合;將上舉《小園賦》中的一聯與倪璠注釋作個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庾信對前文本所作的解構。而庾信對記憶中前文本片段進行解構,是與前文本對話的延伸,依然是對話,而且是更具深度的對話,因為它為駢文文本的創構提供了語匯與意義的材料。駢文文本創構者與前文本的這種對話,當然不局限于《小園賦》中的這一聯,《小園賦》全篇,浩如煙海的駢文文本基本上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妨這么認為:如果沒有駢文文本創構者對以往的文學的回憶,及其與前文本進行的對話,駢文文本基本上不可能被創構出來。在這一意義上,駢文文本可以說是駢文創構者與前文本對話的紋路。通過這個紋路,我們可以獲取駢文文本創構者與前文本對話的基本信息。
其三,讀者與作者的對話。按照一般的理解,讀者與作者的對話屬于文學接受的范疇,是屬于文學活動中的接受過程。然而,對于駢文而言,其文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作者與讀者對話的產物,具有對話性,這是因為典故或前文本片段在駢文文本中的大量存在。駢文文本中所嵌入的典故或前文本片段,猶如堅硬的外殼,對于不合格或非理想讀者而言,是一種在理解接受上難以逾越的障礙,駢文文本的意義世界對于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存在;相反,對于合格或理想讀者而言,駢文文本的意義世界是開放的,他們并不存在理解與接受上的障礙。盡管如此,一篇駢文文本的意義并不全是作者或其創構者賦予的,而是與讀者的對話合作達成的。在駢文文本創構者或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中,其中心就是駢文文本中嵌入的典故或前文本片段。典故或前文本片段由于來自更早的文獻,在融入駢文文本時大多表現為由此及彼、借古喻今,充滿了比喻或暗示,朦朧隱晦,往往給不合格或非理想讀者帶來了理解上的難度,而給在文史素養上與作者比較接近的合格或理想讀者則帶來了聯想活動。這種聯想活動,在作者的特定指引下,自然回憶了作者回憶的相關內容。讀者的這種回憶雖然未必與作者的回憶完全契合,但基本上能還原或者說再創造作者意欲表達的意義,這就是吳興華所說的“讀者在不知不覺當中,也參加了創作”(1—15)。如前舉庾信《小園賦》中的那一聯,庾信回憶到了《左傳》《國語》中的相關文本片段,而倪璠對這一聯進行的注釋,是作為讀者對庾信的回憶進行回憶,他不但將這種回憶落實到具體的文字,而且進一步指出“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于輪軒也。臧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于鐘鼓也。以喻魏、周強欲己仕,而己本無情于祿仕也”(庾信 21),還原或再創造了庾信意欲表達的不愿仕宦北魏、北周的寓意。把握庾信在這一聯中所表達的寓意,前提是必須了解或理解這一聯包含的典故的原義。如果一個讀者不了解或理解這一聯中包含的典故的原義,庾信借助典故表達的寓意只能落空,他所創構的文本片段對這位讀者而言是無意義的。而作為合格或理想讀者的倪璠圍繞這一聯包含的典故,與庾信創構的這一文本片段展開了對話,還原了庾信的回憶內容與其表達的寓意,讓這一文本片段甚或全篇的意義呈現了出來。可見,一篇駢文文本意義的達成,離不開讀者的參與,是在讀者與作者彼此交互的對話中被創造出來的。這是因為:作者創構駢文文本時,由于用典的緣故,已經預設了自己的讀者是那些“具有大體相同的世界觀、道德標準和文化素養”(吳興華 1—15)的對象,王铚在《四六話》中針對用典要求“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王水照 8),就已包含對駢文讀者對象的預設;而只有具備這種文化素養的讀者對象,才會理解領會作者用典所表達的意涵。而作者對讀者對象的這樣預設,影響著作者對駢文文本的創構,可以說,作者預設的讀者對象,自始至終伴隨著駢文文本創構的全過程,在場與作者不斷地進行交流對話。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讀者也參與了駢文文本的創構。誠然,駢文文本創構的這種情形與一般文學文本的創構似乎沒有多大區別,但這種情形唯有在大量用典的駢文文本創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駢文的文本形態。
駢文文本中雖然還存在其他維度的對話類型,但上述三個維度無疑是主要的。法國符號學家朱莉亞·克莉斯蒂娃指出:“結構主義的動態要素就在于‘文學語言’(literary word),它是文本表面的交點而不是單一的點(固定的意義),是多種書寫之間的對話,也就是在寫作者、接受者(或小說人物)和當下或先前的文化語境之間的對話。”(戴阿寶 111)在她看來,所有的文本都是對話。不過,與她所說的這些文本比較起來,大量用典的駢文文本的對話性特征更為鮮明,也更具典型性。因此,從互文性這一角度來觀照駢文文本,駢文文本顯然是一種典型的對話結構的存在。
三、 張力:因差異而形成
互文、對話導致了駢文文本張力的形成。而在互文、對話之外,用典意味著對前文本的解構與重構。然而,一個駢文文本不是所有的文句都包含典故(集句性的駢體之作例外,如黃之雋的《香屑集序》),其中也有不用典故的文句。因此,根據形態、意涵的不同,駢文文本的張力大體可以分為兩組關系。
(一) 解構與重構
如前所述,駢文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互文而生成,并呈現出互文性的樣態。而互文,具體手法則大多是對前文本進行剪裁、組合。因此,創構駢文文本這一文學行為自然就涉及對前文本進行解構與重構。解構,是對前文本的破壞,是將前文本的某一片段從其整體性中切割出來;而重構,則是對被切割出來的來源不同的前文本片段進行整合,進行新的文本的建構。駢文文本創構中的這種解構與重構,前者面向過去,后者面向未來,兩者在駢文文本中的不同向度構成了一種緊張關系,從而構成了駢文文本的張力。如陳維崧《陸懸圃文集序》中此聯:“成言已久,食之慮涉于肥;宿諾難逋,頭也懼來其責。”(陳維崧 335)此聯是前文本經過陳維崧重構后的文本片段。而其前文本或典源分別是《楚辭·離騷》:“初既與予成言兮。”(馬茂元 8)《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楊伯峻 1727)《論語·顏淵》:“子路無宿諾。”(朱熹 137)晉張敏《頭責子羽文·序》:“……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嚴可均 1919)陳維崧《陸懸圃文集序》中此聯運用這些前文本片段或典故,意謂:曾經與陸氏有過約定,為其文集作序。如果食言不為其文集作序,一定招來他的責備或嘲笑。將陳維崧此聯同其前文本或典源進行比較,陳維崧沒有對前文本片段或典故一字不落地照搬,而是進行了解構,將“成言”“宿諾”等文本片段從其前文本中切割出來,稍加變化,重新建構、組合,融而化之,誠如陳維崧在《四六金針》中所說的那樣,“化為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并行不悖”(3),而形成了一個新的文本。就《陸懸圃文集序》此聯中“食之慮涉于肥”一句而言,僅6個字,而與其對應的其前文本片段(不計標點符號)則是58字,這顯然是對其前文本片段切割并加以濃縮,6個字包蘊了58個字的內在含量,這種“內含式拓展,無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內容含量”(莫道才 132)。駢文文本創構中的解構與重構,在文本的結構形式上呈現出來的以少總多,這種少與多之間的差異,前文本與新文本之間的差異,存在著一種張力。而這,還只是因篇幅形式的差異而形成的張力。
此外,駢文文本存在著因意義差異而形成的張力。前文本片段或典故雖然是一個個意義單位,但駢文創構過程中對前文本片段的解構與重構,很多時候并不是同一意義的順承,而是在意義上發生了轉移、衍展甚或折向反義。如庾信《謝趙王賚絲布啟》這一聯:“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庾信 568)其文本片段或典故分別是《古詩·上山采蘼蕪》“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陳祚明 88)與皇甫謐《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18)。庾信用這兩個典故,譬說自己的妻妾接到趙王賞賚的絲布非常高興。原典意謂新婚的妻子擅長織縑,夏桀元妃妹喜喜歡聽裂繒的聲音。將這一聯表達的意涵同原典比較,上聯由原典織縑這一行為的事實描述轉變為喜悅情緒的表達;而下聯的原典是一個君王極力討好女性的故事,而聯語斷章取義,截取其中的前半,表達情緒的喜悅。不難看出,這一聯語表達的意涵與原典是有相當出入的,即原典的意義在聯語中發生了轉移。王勃《滕王閣序》中“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高文、何法周 43),雖然出典分別是《晉書》中吳隱之的故事與《莊子·外物》涸轍之鮒這一寓言,但與原典比較起來,聯語中的“覺爽”“猶歡”這種心理情緒并非原典所有,而是王勃根據自己的意緒補充上去的,是在原典的基礎上進行想象而衍展的,聯語意義與原典意義之間的差異是頗為明顯的。如庾信《哀江南賦序》中這一聯:
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98-99)
上聯用的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藺相如與趙王在澠池同秦王相會的完璧歸趙故事,下聯典出同書《平原君虞卿列傳》,毛遂隨平原君趙勝出使楚國,平原君與楚王久談不決,他按劍而上,說服楚王,捧銅盤與楚王歃血為盟。此兩典中的主人公都完成了使命。而庾信在這一聯中用此兩典,云“見欺”“不定”,改寫了故事的結局,使原典的意義走向了反面。他在此聯中對典故如此書寫,是將自己與典故中的主人公進行比照,喻說自己不但沒有完成出使西魏的使命,反而被迫留在西魏,凸現了自己懊惱、悔恨以及無可奈何的痛苦心境。上述這三種用典類型,都是典面與典義之間存在著意義上的明顯差異。這三種用典類型在駢文文本中雖然只是一定程度的存在,但由此而形成了駢文文本中的藝術張力,使人感覺到駢文文本內涵豐富,耐人尋味。
合而言之,無論是形式差異而形成的張力,還是意義差異而形成的張力,不僅顯現了駢文文本生成過程中解構與重構的互文關系,還展現了駢文創構者創造性的藝術表達。
(二) 用典句與非用典句的錯綜
一個駢文文本,并非全都是由用典的文句組成的,其中也包含了許多不用典的文句,如前舉王勃的《滕王閣序》這篇作品,全篇文句共144句,用典的文句88句,而未用典的文句則有56句,用典的文句與不用典的文句在全篇中錯綜交互、疏密有間、錯落有致。駢文中用典與不用典的文句,思維形式不同,從而在讀者的接受過程中會引發不同的思維活動。不用典的文句由于直致平實,意旨比較單一、顯豁,讀者順著文字逐步展現的駢文創構者的邏輯思路,把握其意旨,不需要太多的思維上的聯想活動。也就是說,不用典文句展現的駢文創構者的思維基本上是線性的,而讀者在接受過程中產生的思維活動也是線性的。相反,用典的文句包含的典故是駢文創構者對前文本的回憶與剪裁,在藝術表達上往往是由此及彼、借古喻今,其意旨與不用典的文句比較起來,更為豐厚、曲折、隱晦,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必須展開思維上的聯想活動,回憶駢文創構者回憶的前文本(尤其其中的事典,則往往伴隨著一幅或一組畫面)。只有這樣,讀者的理解才有可能與駢文創構者在文本中所要表達的意旨契合,不至于發生謬誤。換言之,用典的文句在思維上是橫向的蔓衍,并借助典故中包含的故事而呈現出一幅或一組生動的畫面。因此,駢文文本中不用典的文句是以線性的思維形式存在的,用典的文句則是以畫面的思維形式存在的。這樣,直與曲、顯與隱、線與面,這兩種不同思維形式的文句在駢文文本中交錯,彼此相形,建構著藝術張力。如庾信《哀江南賦序》中的這一節:
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94-95)
在此節文字中,前面四句,沒有用典,明白顯豁,庾信簡要地概括了自己從中年到暮年的劫后余生。讀者對這四句的理解,基本上不需要思維上的聯想活動。而自此節文字的第五句到最后一句,除“追為此賦”一句未用典外,其余十五句,都涉及典事,只不過最后三句用的是語典。語典是古典文獻中的成語,如前舉劉永濟所言“引彼語以明此義”罷了。而涉及事典的文句,基本上是一幅或一組活躍的畫面,無論是作者進行文本創構,還是讀者的理解,都需要思維上豐富的聯想活動。如“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這一聯,用了四個事典。上聯中“畏南山之雨”這一句,用的是《列女傳》中“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劉向 20)事。雖然典面上的“畏”字,與事典中的“藏而遠害”一語扣合,但這一句包含的畫面有南山、玄豹、霧雨這些物態與藏這一動作行為,畫面顯然不是一幅,而是多幅。“忽踐秦庭”一句,用的是《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赴秦乞師、哭于秦庭的事,此句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個字,但包含的畫面絕不止一幅。至于此聯中的下聯兩句,以及其余諸聯,同樣包含了多幅畫面。可以說,用典的文句是用一幅幅生動的畫面來替代陳述,借以觸發讀者思維上豐富的聯想活動,實現意義的表達。而就《哀江南賦序》中的此節文字來看,用典文句與不用典文句在文本中的組合,其實是線與面的扭合,兩者不同思維形式的相反相成,從而構成了藝術張力。任何一個文本只要用典,就會存在用典的文句與不用典的文句之間彼此相形的藝術張力。駢文由于用典較多,堪稱這種藝術張力的標本。
駢文文本中對前文本或典故的解構與重構,以及用典文句與不用典文句的錯綜,都會因差異而形成藝術表達上的張力。理解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駢文的文本形態。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認識到用典在駢文文本生成及其文本張力塑成中的意義。正是由于用典,駢文的文本形態基本上呈現出互文性、對話性與張力的特征。盡管駢文文本形態的這種特征在其他文本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只有在駢文文本中表現得最為典型、集中。因此,我們認為:在建構駢文文本的四大修辭手段中,偶對、聲律、藻飾這三大修辭手段不過是建構駢文文本外在的形式特征,而用典,則是建構駢文文本內在的形式特征。駢文的文本形態及其本質,更多的是由其文本的內在形式特征即用典所決定的。要想深入研究駢文,必須重視對駢文文本中用典的細致深入探討。否則,駢文研究就失去了它的特性,淪為一般的文學研究了。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陳維崧:《四六金針》,《叢書集成初編》第263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Chen, Weisong.SecretsofWritingParallelProse.CollectedCollectanea,1stSeries.Vol. 263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CollectedWorksofChenWeiso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Chen, Zuoming.AnthologyofEarlyPoemsfromtheHallofPickingBeans.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戴阿寶:《文本革命》。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7年。
[Dai, Abao.RevolutionofText.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董小英:《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Dong, Xiaoying.AscendtheTowerofBabelAgain:BakhtinandHisTheoryofDialogism.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Gao, Heng.ContemporaryAnnotationstoThe Book of Poetry.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高文 何法周:《唐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Gao, Wen, and He Fazhou.SelectedEssaysoftheTangDynasty.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Guo, Qingfan.CollectedAnnotationstoZhuangz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皇甫謐:《帝王世紀》,《叢書集成初編》第370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Huangfu, Mi.AnnalsofEmperorsandKings.CollectedCollectanea,1stSeries.Vol. 370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朱莉亞·克里斯蒂娃:《詞語、對話和小說》,《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83—118。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DesireinLanguage:ASemioticApproachtoLiteratureandArt.Trans. Shi Zhongyi, et al.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83-118.]
李玉平:《互文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Li, Yuping.Intertextuality.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Liu, Wendian.TheVariorumEditionofHuainanz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劉向:《列女傳》,劉曉東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Liu, Xiang.CollectedWomenBiographies.Ed. Liu Xiaodo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劉勰:《文心雕龍注》,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Liu, Xie.Annotated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Liu, Yongji.EmendationsandAnnotationsto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馬茂元:《楚辭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Ma, Maoyuan.TheSongsofChu:ASelection.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莫道才:《駢文通論》。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
[Mo, Daocai.AComprehensiveDiscussiononParallelProse.Jinan: Qilu Press, 2010.]
蒲松齡:《聊齋志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Pu, Songling.StrangeTalesofaChinese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7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Sima, Qian.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Samoyault, Tiphaine.Intertextuality.Trans. Shao We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汪中:《述學校箋》,李金松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Wang, Zhong.InterpretationoftheNarrativeofLearning.Annotated. Li Jins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Wang, Shuizhao, ed.TalksonEssaysofSuccessiveDynasties. Vol.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吳興華:《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文學遺產》4(1988):1—15。
[Wu, Xinghua. “ReadingSelectedParallelProsefromChangzhouintheQingDynasty.”LiteraryHeritage4 (1988): 1-15.]
許梿評選、黎經誥箋注:《六朝文絜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Xu, Lian, and Li Jinggao, eds.SelectionsfromtheSixDynasties:NotesandCommentarie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Yan, Kejun, ed.CollectedProseWritingsofthePre-Qin,Qin,Han,ThreeKingdomandSix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Yang, Bojun.AnnotatedZuo’sCommentarieso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Yao, Silian.BookofChe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2.]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Yu, Xin.AnnotationstoCollected Works of Yu Zishan.Eds. Ni Fan and Xu Yim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Zhu, Xi.CollectedAnnotationstoThe Four Book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