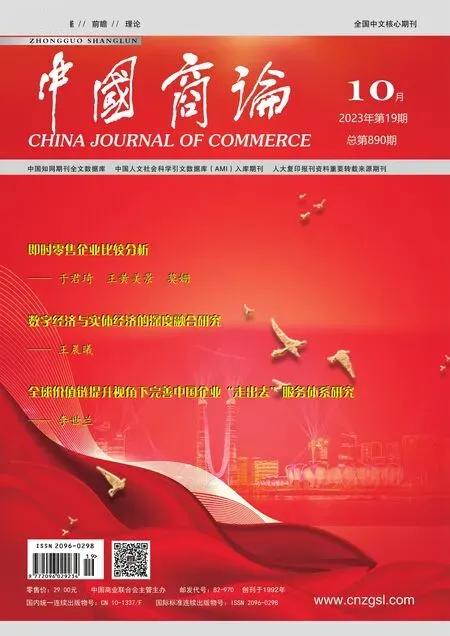中國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的時空演變研究
李彤 石鵬娟(通訊作者)
(青海大學財經學院 青海西寧 810016)
隨著我國互聯網技術的不斷增強,“大數據時代”推動了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其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力。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超過19萬億,達到歷史新高,總量占GDP的比重為18.8%。與此同時,工業化快速進程帶來的環境污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打破了傳統工業高污染、高耗能的經濟增長方式,為綠色經濟發展提供新的著力點。因此,從工業生態效率和數字經濟的內在聯系出發,為推動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建設的轉變提供理論指導。
1 文獻綜述
對于生態效率的研究,隨機前沿函數[1]、數據包括分析方法[2]等測度方法的應用較為廣泛,研究視野則傾向省域[3]、城市群[4]、縣域[5]等層面,并認為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環境規制等因素對生態效率均有影響。數字經濟的研究由起初的概念界定[6]深化為數字經濟對經濟總量[7]、城鄉消費差距[8]、創新效率[9]等社會效應方面。目前,關于數字經濟和生態效率關系的研究,梁琦等(2021)認為數字經濟對生態效率提高具有正向作用[10]。
綜上所述,學者對生態效率和數字經濟分別進行了充分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但缺少數字經濟與工業生態效率的協同效應的研究。因此,本文從時空演變角度對工業生態效率和數字經濟耦合協調進行探究,豐富了此類問題的研究。
2 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2.1.1 工業生態效率的指標體系
工業生態效率的實質是以最小的資源投入產生最大的效益,因此工業生態效率指標體系應包括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在投入指標中,資源投入包括工業用水、工業用電量;人力投入以平均用工人數衡量;資金投入包括工業資產投資額;期望產出為工業增加值,非期望產出為工業固體廢物、氮氧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煙(粉)塵排放量。
2.1.2 數字經濟指標體系
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11]的研究,采用金融普惠指數、互聯網普及率、相關從業人員情況、相關產出情況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對數字經濟水平進行測算,其中后四個指標的含義分別為: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重、人均電信業務總量和百人中移動電話用戶數。
2.2 研究方法
2.2.1 超效率SBM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不僅有效解決了投入產出變量的松弛問題,還處理了多個決策單元同時有效時的區分排序問題。此模型考慮了n個決策單元,每個決策單元有M個投入、S個期望產出和Q個非期望產出,測算方法如下:
式中,ρ為效率值;X、Y、Z分別為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要素;為松弛調整量;μ為權重。
2.2.2 熵值法模型
熵值法是算出多個指標的權重,并對每個指標進行得分,其計算步驟的公式如下:
(1)對各項指標數值進行歸一化,正向指標歸一算法為:
其中,i表示年份;j表示測度指標。
(3)計算數字經濟評價體系第j項指標在第i年占該指標的權重,其中
(4)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0≤ej≤1;信息熵冗余度為:dj=1-ej
2.2.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一詞現廣泛應用于生態環境、經濟發展多個領域,具體的耦合協調度的測算模型建立如下:
式中,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a和b為待定系數,由于工業生態效率和數字經濟同樣重要,故a=b=0.5。根據耦合協調度值,將結果劃分區間為[0.0,0.3)、[0.3,0.5)、[0.5,0.8)、[0.8,1.0],且所對應的耦合協調度等級分別為低度、中度、高度和極度耦合協調。
2.2.4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是一種通過研究要素空間分布的狀況來判斷要素空間分布程度的方法,包括全局和局部莫蘭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I為全局莫蘭指數;Ii為局部莫蘭指數;n為空間單元的個數;yi為空間單元觀測值;wij為空間權重矩陣。
2.3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及各省份統計年報,部分缺失數據用線性插值法填補,本文剔除港澳臺地區,以31個省作為研究樣本。
3 實證分析
3.1 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演變
3.1.1 耦合協調時序演變
由圖1可知,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呈現上升趨勢,且上升較為明顯。2011—2020年,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C值為(0.5,1.0),不存在低度耦合階段,而2011—2010年中國省級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D值為(0.4,0.8),平均值低于0.59,耦合協調度D整體上以高度耦合協調為主要趨勢。從演變趨勢來看,其對應的耦合協調度的類型經歷了中度耦合協調與高度耦合協調兩個過程,協同效應不斷增加。

圖1 2011—2020年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
3.1.2 耦合協調空間格局演化
本文運用Origin軟件繪制出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雷達圖(見圖2),可看出耦合協調度隨著時間的演進呈同心圓中心向外擴張的趨勢,說明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的耦合協調發展正在逐年優化。從空間分布來看,2011年處于低度耦合協調的區間有:西藏、貴州、云南、寧夏、甘肅、貴州,這些省份均位于我國偏遠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處于高度耦合協調的區間有7個地區且均位于我國東部地區,而處于中度耦合協調有19個地區,占全國比重為61.3%。這表明2011年兩系統互相抗衡特征強烈,發展不平衡。2020年,我國31個省(市)的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的耦合協調度等級結構進一步優化,并突破了期初無極度耦合協調等級的狀況。總體來看,2020年耦合協調雖大幅上升,但仍呈“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空間格局。

圖2 2011年、2020年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
3.2 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發展的空間關聯格局
3.2.1 全局空間自相關
本文運用Stata16.0測算2011—2020年中國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的全局莫蘭指數,如表1所示,全局莫蘭指數值均大于0,且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在時間和空間上均具有有效性。從時間上來看,2011—2020年兩系統的全局莫蘭指數呈上下波動狀態,表明我國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在不同年份表現出不同的集聚趨勢;從空間格局上來看,兩系統整體上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鄰近省份的空間集聚特征明顯,表現出耦合協調度較高的省份和耦合協調度較低的省份均趨于集聚。

表1 2011—2020年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全局莫蘭指數
3.2.2 局部空間自相關
通過局部莫蘭指數進一步揭示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的集散情況及演化特征。由圖3可知,在“高-高”集聚區:東部省份超一半位于該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山東等地區,空間集聚態勢逐漸由分散狀態向東部沿海集聚,所占比例從2011年的29%增加到2020年的45%,說明兩系統的空間集聚產生了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低-低”區從2011年的32%減少到2020年的26%,表明隨著數字經濟水平的提升或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型升級,該區域原有的省、市向其他區轉變。總體來看,中國多數省、市均處于第一、三象限,且第二、四象限所占比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波動,在空間上表現為組團式的環狀分布。

圖3 2011年、2020年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Moran散點圖
4 結語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構建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使用空間自相關考察了兩系統耦合協調度時空格局演變特征,得到以下結論:
(1)從時序演變來看,2011—2020年中國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均值整體處于上升趨勢,從中度耦合協調階段向高度耦合協調階段演變,協同效應不斷增加。
(2)從空間演變上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全國各地區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等級空間差異趨向均衡,但整體呈現“東高西低”的不均衡空間分布特征。
(3)從空間相關性上來看,中國工業生態效率與數字經濟耦合協調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具有明顯的“集聚性”和“兩極化”的特征,相關系數不斷波動,其中“低-低”集聚省份以西部地區為主,“高-高”區主要是東部和中部發達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