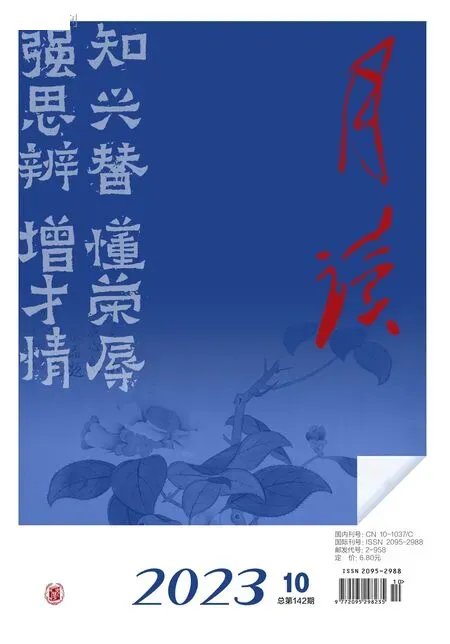從田間到舌尖,從救荒到小康:漫談《齊民要術》
◎ 鐘彥亮
在網絡游戲世界,我們常常會癡迷于開荒種菜,以至于誕生“種菜流”玩法;生活中,只要看見帶點泥土的地方,無論是公用陽臺,還是自家的小花盆、泡沫箱,總忍不住想往里種上點兒蔥、姜、蒜或者其他什么;我國宇航員在太空種菜、維和官兵在非洲種菜、科考隊員在南極種菜等新聞被接連報道,似乎更加印證了我們熱愛種菜、擅長種菜的“天賦”—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沒有我們種不了的。
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國人骨子里仿佛就刻著“耕種基因”。我們很早便深刻認識到農業是百姓衣食之源、國家富強之基,古人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天也常說“手里有糧,心中不慌”。所以我們歷來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經營,并將其中精華總結成為農書,北魏賈思勰撰著的《齊民要術》(以下簡稱《要術》),便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農學巨著。
“簡歷”是個謎:賈思勰到底是誰
賈思勰,謎一般的人,不僅史書沒有他的傳記,而且其他文獻均無只言片語提起過他。目前我們掌握他的確切史料,只有《要術》宋刻殘本及明清各本卷首的作者署名,均題作“后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但就算是這區區十個字,依然存在很大爭議。
“后魏”便是“北魏”,這點倒沒什么疑問。問題出在高陽,這是因為北魏有兩個高陽郡,《魏書·地形志》載,一個是瀛洲高陽郡(今河北高陽),另一個是青州高陽郡(今山東淄博)。賈思勰究竟在哪個高陽郡任職太守,從古至今,學者們做了不少細致考證,“河北說”與“山東說”也各有支持者,只是如今認為他曾是青州高陽郡太守的,逐漸占了上風。
所幸,賈思勰在《要術》中透露了他“朋友圈”的情況,提起了與他同時代的三個人,分別是皇甫吏部、元仆射和劉仁之。其中,劉仁之最值得我們關注,他名姓清楚,《魏書》有傳,為進一步了解賈思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關鍵線索。
賈思勰是在《齊民要術·種谷》中提起劉仁之,夸贊“西兗州刺史劉仁之,老成懿德”,并介紹他以“區田法”耕種的成功經驗。然而《魏書·劉仁之傳》卻說他“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劉仁之表里不一,暫且不論,傳中又說他與馮元興交好。檢《馮元興傳》,馮元興為太子侍讀時,曾與太子侍講賈思伯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元詡讀書。而《賈思伯傳》中,不僅稱賈思伯“與(馮)元興同事,大相友昵”,還提到賈思伯有個弟弟叫賈思同。
如此順藤摸瓜之下,我們不禁大膽推測:既然賈思勰認識劉仁之,而劉仁之與馮元興交好,馮元興又與賈思伯相善,并且思伯、思同與思勰的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似乎同為賈姓的“思”字輩,那么思勰是否與思伯、思同之間有親屬關系,并借著思伯的關系網認識到劉仁之?
在沒有其他更多史料支撐的前提下,根據上述推測并結合書中賈思勰對山東風物的熟悉,很多人推測思勰與思伯、思同之間為同鄉、同族、同宗、同輩的堂兄弟可能性很大。又因賈思伯本傳說他是“齊郡益都人”(今山東壽光),所以我們便順著把思勰的籍貫系在齊郡益都。這就是為什么在一般的介紹資料甚至歷史課本中,會把賈思勰寫成是山東壽光人的主要原因了。同時,這也是為什么在《典籍里的中國》里,有關《齊民要術》的表演中,會出現“賈思伯”這一角色的緣故了。
當然,有人認為賈思勰即賈思同(見欒調甫《〈齊民要術〉考證·〈齊民要術〉作者考》),也有人認為賈思勰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一個叫賈勰的人(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齊民要術》引述吳檢齋先生的說法),等等。
總之,如何寫賈思勰的“簡歷”,這個農學史上的大難題,有待新的史料出現,方可有望得到解決。
資生必備:《要術》是一部怎么樣的書
雖然賈思勰謎團重重,但不妨礙我們閱讀《要術》。書名《齊民要術》,“齊民”猶言“平民”,意思是平民百姓;“要術”,字面意思是重要方法,這里特指謀生的重要方法,合起來的意思便是平民百姓謀生的重要方法。
《要術》何時成書?目前通行說法是公元六世紀三四十年代。不過在《四庫提要辨證·齊民要術》中,余嘉錫先生同意吳檢齋(吳承仕)先生“思勰著書,疑在梁武之末,當東魏武定末”的觀點,稱贊其說“詳密可信”。照此說法,《要術》成書時間最晚要去到六世紀四五十年代。筆者讀了吳先生考證,確感精彩,限于篇幅,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看,在此不多加介紹。
《要術》全書十卷,九十二篇,十一萬五千余字,書中主要反映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生產經營情況,書中常說的“中國”,指的便是該區域。由于賈思勰未曾涉足南方,也沒有去過漠北,書中提到的“漠北寒鄉之羊”和南方作物,只是舉例補充,并不在本書重點描述的范圍之內。
《要術》基本內容與結構安排,則緊扣百姓生產生活。賈思勰在自序中介紹說:“起自耕農,終于醯醢(xīhǎi),資生之業,靡不畢書。”
所謂“起自耕農”,這是因為農業中以農作物的耕種最為基礎,所以書中卷一、卷二先講耕田、收種等農事基本功及常見的水稻、旱稻等谷物作物的種植方法。
膳食以谷物為主,同時應多吃果蔬。《要術》按照從草本植物到木本植物的順序,接著講蔬菜和果子。卷三講種菜,包括葵、蔥、韭、蒜等;卷四講種果樹,包括棗樹、桃樹、李樹、梅樹等;卷五再順著講種植具有其他經濟價值的樹木,包括桑樹(可養蠶)、榆樹(可做木器)、楊樹(可造房子)等。在講完谷物、果蔬和林木等植物種植后,卷六便開始講動物養殖,包括牛、馬、驢、騾、羊、豬、雞、鴨、鵝、魚等古代農村常見的動物。
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不僅可以將富余的糧食加工成為農副產品,還能吃上滿滿一桌盛宴呢!所以卷七、八、九便講酒、醋、醬、糖等農副產品的制作以及各種葷素菜肴的烹飪,這便是“終于醯醢”了(醯是醋,醢是肉醬,醯醢泛指調味料)。
卷十則補充記載“五谷、果蓏(luǒ)、菜茹非中國物產者”,即我國南方熱帶、亞熱帶植物。雖然賈思勰說“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但由于他引用的文獻幾乎都失傳了,所以這卷特別具有農史價值,被譽為我國最早的“南方植物志”。
同時,《要術》尤其注重記載救荒作物,倘若某種作物能救饑賑貧,那么賈思勰在介紹完它的基本情況后,必定會強調其救荒作用,有時甚至會激烈批評不重視救荒作物的現象,如:
芋可以救饑饉,度兇年。今中國多不以此為意。后生有耳目所不聞見者,及水、旱、風、蟲、霜、雹之災,便能餓死滿道,白骨交橫。知而不種,坐致泯滅,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課之哉!
此外,《要術》還有部分內容是講農業致富,集中體現在《貨殖》并散見于其他篇章中。
綜上所述,《要術》在內容上不僅重視救荒作物,而且囊括了農業生產經營中農、林、牧、漁、副所有門類;在結構上“起自耕農,終于醯醢”,符合農業活動中從農作物到農產品的全過程,可謂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編排合理。所以正如他所說“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幫助百姓謀生的重要方法,無不寫在書中了,因此《要術》也被譽為是“中國古代農業百科全書”。
《要術》用百姓話講謀生事,全書語言幾乎沒有南北朝時期常見的駢四儷六,反而通俗易懂,童子能解。賈思勰說:“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要術》材料來源豐富,主要是四個方面:“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
采捃經傳。摘錄古書中有關農業生產經營的資料,以確保來源的權威。據統計,《要術》引書中,有書名可考的有160余種,無書名可考的不下幾十種。明代胡震亨稱贊道:“此特農家書耳……乃援引史、傳、雜記,不下百余種,方言奇字,難復盡通,腹中似有數千卷書者。”
爰及歌謠。連帶收集農諺農謠。書中收集三十多條農諺農謠,如“濕耕澤鋤,不如歸去”“左右通鋤,一萬余株”等,均為百姓在長期農業生產中總結的精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很強的指導作用。
詢之老成。向富有農業生產經驗的老農或在生產上具有一技之長的前輩請教,吸收他們寶貴經驗,如書中記有皇甫吏部和元仆射釀酒的“家法”。
驗之行事。賈思勰親自觀察或親身實踐。如他發現并州產的豌豆種至井陘口以東,太行山以東的谷子種至山西壺關、上黨,均“苗而無實”,就是徒長莖葉而不結實,“皆余目所親見,非信傳疑”。
除去“采捃經傳”,其他材料均源于百姓(包括賈思勰自己)的實踐經驗,真實可信,可靠管用,所以此書受到歷代百姓的信任和喜愛。
《要術》在中國農學文獻中地位很高。雖然《要術》之前也有農書,如西漢氾勝之的《氾勝之》十八篇(即《氾勝之書》)、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等,但大多都失傳了,《要術》保存了它們部分片段,從輯佚情況來看,此前農書涵蓋的農業范圍遠不及《要術》廣大。而《要術》之后的四部大型農書,即元代《農桑輯要》、王禎《農書》,明代徐光啟《農政全書》及清代《授時通考》,均受《要術》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農桑輯要》便說“大致以《齊民要術》為藍本”。因此《要術》不僅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農書,更是承前啟后、影響最為深遠的農書。
為民愛民:賈思勰為什么要寫《要術》
如上所述,《要術》無論從宗旨、內容、結構、語言還是材料等方面,均來源于百姓、服務于百姓,賈思勰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接地氣”的著作?我們從《要術》中他自述的兩件事,便能知他良苦用心所在。
從社會背景看,賈思勰親歷“杜葛之亂”。北魏孝昌元年(525),杜洛周、葛榮等人不滿北魏統治,相繼起事,轉戰河北,燒殺擄掠;永安元年(528),二人先后兵敗身死,史稱“杜葛之亂”。
杜葛之亂沉重地打擊了北魏的社會經濟,導致連年饑荒,百姓食不果腹。賈思勰在《種桑柘》寫道“故杜葛亂后,饑饉薦臻”,幸好黃河以北的百姓平時懂得儲藏桑葚干,大戶人家藏有百石,少的也有數十斛,百姓便靠著吃桑葚干活命,“數州之內,民死而生者,干椹之力也”。《魏書·崔孝暐傳》也有類似的記載:孝莊帝初年(約528),崔孝暐擔任趙郡(今河北趙縣)太守,當地“罹經葛榮離亂之后,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恰逢“夏椹大熟”,崔太守同樣認識到桑葚是救荒作物,可以活命,便“勸民多收之”,以備不時之需;郡內沒有耕牛,又“教其人種”,全力恢復農業生產。
兩相合看之下,我們便知在杜葛之亂后,重視儲藏救荒作物,教授百姓耕種技術,讓生產生活盡快重回正軌,正是百姓所盼,社會所需,由此我們也能明白為何本書尤其強調救荒作物了;并且與崔孝暐不同的是,賈思勰還鼓勵發展多種農業經營,甚至描繪“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養魚,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亦無貲之利也”等因農而富的場景,讓百姓務農信心更足,選擇余地更大。
外因需要內因才能起到作用。從個人經歷看,賈思勰曾有養羊失敗的經歷。他在《養羊》提到,自己養過二百頭羊,但“一歲之中,餓死過半”,活著的大多滿身疥瘡、瘦弱疲倦,“與死不殊”,而且羊毛稀疏短淺、毫無光澤。最初他以為是自家不適合養羊,后來又懷疑遇上了瘟疫。經過多次反思后,才回過神來,僅僅是因為自己準備的飼料少了,導致羊群餓死、病弱,“乃饑餓所致,無他故也”。
吃一塹,長一智。這次慘痛的教訓讓他摸索出養羊的正確方法,并深刻體會到“三折肱為良醫”“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的道理,感慨“世事略皆如此,安可不存意哉!”若百姓不懂務農方法,大概率會損失慘重,自己踩了坑,卻想為別人指條路,存了這樣的念頭,所以賈思勰想教百姓正確的謀生方法。
假如說《要術》明線結構是從耕農至醯醢,那么暗線則是講活命之本、謀生之道和富家之術,幫助百姓在亂世之中活下去,并以正確的方法吃得飽、吃得好和富起來,而這正是賈思勰撰著《要術》的重要原因。
借鑒農學思想:今天如何讀《要術》(一)
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鎮居民日益增多,農業農村人口也隨之下降。同時,得益于我國農業科技快速發展,大機械、高科技的現代化農業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農業。在此背景下,普通讀者還能從一部一千多年前的古老農書獲益否?
答案是肯定的。《要術》不僅蘊含了豐富的農學知識,取得很高的農學成就,而且還體現了深刻的農學思想。
據農學史家總結,《要術》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系統總結了黃河中下游旱作農業區以保墑防旱為中心的精耕細作技術,種子處理和選種、育種、良種培育等技術,播種技術、輪作和間混套種技術,植物的壓條、嫁接、保護技術,動物的飼養、防治疾病技術,對微生物所產生的酶的廣泛利用以及農副產品加工等多個方面。
《要術》記載的農業技術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其中的農學思想,同樣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堅持以農為本。書中處處體現著“農本”思想,自序不僅引用許多書目中關于重農的論述,還舉了黃霸、龔遂、召信臣等“良二千石”大力發展農業,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美談,有力地證明治國理家均需以農為本。
尊重自然規律。書中一方面指出農業生產需要尊重自然規律,“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若尊重規律,那么“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若“任情返道”,隨心所欲,就會“勞而無獲”。
破除生產迷信。古人受生產力及認識水平所限,為了有個好收成,在農業生產時往往摻雜著迷信。比如《要術》引《氾勝之書》說:“凡九谷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賈思勰對此便頗不以為然,毫不留情地反駁道:“《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從之。’”又引用諺語“以時及澤,為上策”,意思是播種哪里有什么忌日,趕上時令,趁地里有水分,趕緊種上,就是上策。對于釀酒中的繁瑣儀式,則直截了當地說“其糠瀋雜用,一切無忌”。
強調積極勞動。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自序便道“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古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若想在農事中有所收獲,變得富足,那么必須參加勞動。
合理安排財富。自序點出“財貨之生,既艱難矣”,但“凡人之性,好懶惰矣”,倘若四體不勤,揮霍無度,又碰上“政令失所,水旱為災”,那么脆弱的小農經濟極易崩潰;但在“年谷豐穰”的好年景時,人們往往“忽于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于施與”。為了避免“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所以平時要“用之以節”,合理安排財富的使用。
農業也可致富。雖然自序說“商賈之事,闕而不錄”,但書中也有《貨殖》一章。不僅講了很多靠農業經營而使家庭豐實的故事,而且還常引述被視作財富象征的陶朱公的“致富秘訣”,在《養羊》便引道“陶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又在《養魚》中引用《陶朱公養魚經》,夸張地描述養魚的獲利情況。所以賈思勰并不反對通過農業獲利致富,反對的僅是“舍本逐末”的商業投機行為,所以他才批評“舍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
時過境遷,現代農學知識發展程度,已經超過《要術》所載,但書中的農學思想,在“三農”工作、鄉村振興及勞動教育等方面,依然能給予我們深刻的啟迪。
不止是農書:今天如何讀《要術》(二)
同時,《要術》保存了漢晉及北魏時期社會生活和風俗信仰的歷史文化信息,為我們了解古代百姓的煙火日常提供了一個親切的觀察窗口。
《要術》是一部古代農家菜大全。我們知道,賈思勰渴盼百姓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所以《要術》不僅在七、八、九卷專卷專篇介紹各種烹調手法以及不同調味料和葷素菜式的制作,并且會在講解動植物的篇章中順帶介紹其吃法。
具體來看,光是烹調手法,《要術》便載有羹、臛、蒸、缹、腤、煎、炙等不下十幾種;其他菜式更是花樣繁多、不勝枚舉,這里不妨稍作“報菜名”:比如主食就有粟飧、菰米飯、胡飯、杏酪粥等,葷菜則有蒸肥雞、煎鴨子、炙乳豬等,素菜則有蔥韭羹、瓠羹、膏煎紫菜等,小吃、點心則有粽子、細環餅、截餅等。
《要術》還會貼心地提示烹飪成敗的關鍵所在,比如烹調茄子時,提醒我們要用“竹刀、骨刀”破開茄子,假如“用鐵(刀)則渝黑”(茄子含有單寧,遇鐵會變黑)。
當然,《要術》所載之美味或許已不盡符合現代人口味,但我們依然能從中感受到古代農家溫馨的“煙火氣”。倘若我們能從中汲取烹飪靈感,結合現代工藝,將《要術》部分美食復原出來,也是美事一樁。
《要術》還是一部古代農家民俗寶典,記載了古代農村生活民俗和農業生產行業習俗,今天讀來饒有趣味。
單看生活民俗,就已是五花八門。若想驅邪避疫,則要“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發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敕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若冀求富貴,就得“埋蠶沙于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大吉,致財千萬”或“埋牛蹄著宅四角,令人大富”;若要驅除鼠害,不僅要在“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還要念上一段咒語,“付敕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
行業習俗更是讓人眼花繚亂,尤其是在釀酒業。比如,假如我們要做三斛麥曲,就得經過一套冗長的流程:日子得選在七月的“中寅日”,人員則是穿著青衣的童子,制作前的準備工作,則規定要在“日未出時”,讓童子們面向“殺地”的方位,汲回來二十斛水。經過一番準備之后,讓童子還是面向“殺地”的方位做“和曲”“團曲”的工作,“團曲”當天就得做完,不能隔夜。這還沒完,下來還要畫地布曲、假置“曲王”、選出主祭人,主祭人還要上供、念祝禱文等。回看《要術》,倘若我們能將書中的民風民俗加以合理轉化,與古為新,難道這些古老的材料不會煥發出別樣的光彩嗎?《要術》,是農書,卻不止于農書,筆者想,這正是這部古老的農書之于今天的價值所在。
從田間到舌尖,從救荒到小康,《要術》為百姓謀生計,為農業謀發展,而賈思勰拳拳仁愛之心,款款叮嚀之意,也充溢在《要術》的字里行間,千載之下,依然熠熠生輝,縱使賈思勰史書無傳,但他和《要術》,將永遠活在百姓心中。
齊民要術
叢書名: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
譯注者:石聲漢 譯注 石定枎 譚光萬 補注
定價:100.00元
出版方: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