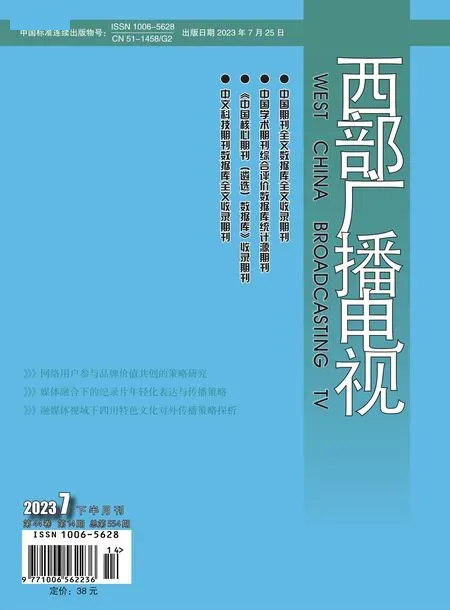鏡像理論視域下《奇跡·笨小孩》的敘事解讀
李僡倫
(作者單位:東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
繼《我不是藥神》火爆銀幕之后,青年導(dǎo)演文牧野再次推出現(xiàn)實(shí)主義力作《奇跡·笨小孩》,引發(fā)社會(huì)廣泛關(guān)注。該片于2022 年春節(jié)上映,由易烊千璽、田雨、陳哈琳、齊溪等人出演。貓眼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22 年10 月7 日累計(jì)票房13.79 億。影片融合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與類(lèi)型片元素,記錄了以景浩為代表的新時(shí)代普通人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他們?cè)诖蟪鞘欣锍粮。门?chuàng)造奇跡,爭(zhēng)取幸福。該片是中央宣傳部國(guó)家電影局2021 年重點(diǎn)影片項(xiàng)目,入選2021 年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100 周年重點(diǎn)獻(xiàn)禮影片,呈現(xiàn)出新時(shí)代中國(guó)電影的創(chuàng)作訴求和審美焦點(diǎn),講述了10 年前深圳年輕人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是打造新主流電影的重要范例。文牧野導(dǎo)演對(duì)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充滿(mǎn)溫情的人文關(guān)懷,使得這部電影在佳片如云的春節(jié)檔收獲了良好口碑。
1 觀(guān)影心理的對(duì)鏡建構(gòu)
在觀(guān)影者觀(guān)看的早期階段,觀(guān)影者對(duì)銀幕中的形象會(huì)產(chǎn)生自戀式的認(rèn)同,將其視為與自己同一的存在[1],從而進(jìn)入想象界,這被拉康稱(chēng)為一次同化。影片兩分半的片頭交代了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及主人公的家庭情況。導(dǎo)演通過(guò)輕快的音樂(lè)、溫暖的色調(diào)、簡(jiǎn)短的對(duì)話(huà)、溫情自然的動(dòng)作,展現(xiàn)了景浩送妹妹上學(xué)的生活樣貌,迅速將觀(guān)影者代入導(dǎo)演所架構(gòu)的故事情境當(dāng)中。拉康認(rèn)為,鏡像階段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們可以找到自己,構(gòu)建自己。“他者”除了現(xiàn)實(shí)中的他人,還包括鏡像中的“他者”,即在鏡子、屏幕上出現(xiàn)的其他人。一方面,觀(guān)影者會(huì)通過(guò)鏡頭,尋找片中角色與自己的共性,代入“他者”的表演中,從而產(chǎn)生情感共鳴。比如《奇跡·笨小孩》中拼命籌齊醫(yī)療費(fèi)、無(wú)力償還房租、房東催租的電話(huà)和紙條、投資過(guò)程中市場(chǎng)環(huán)境突變、求職時(shí)面對(duì)的冷臉和不公等細(xì)節(jié),展示景浩也經(jīng)歷著普通人的經(jīng)歷,此時(shí)的觀(guān)影者與劇中人物融為一體。
觀(guān)影者在觀(guān)看一段時(shí)間后,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存在于正在凝視的銀幕上,意識(shí)到電影只是將虛構(gòu)的故事搬上了銀幕,從而進(jìn)入理性的象征界。在觀(guān)影過(guò)程中觀(guān)影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干擾或因劇情的代入感不強(qiáng)導(dǎo)致缺席電影。景浩不顧傷痛,拼死趕到高鐵站與趙振昌談判,最終竟然順利獲得一次與老總談話(huà)的機(jī)會(huì),這一段緊張激烈的交叉蒙太奇配上積極向上的歌詞與激情澎湃的編曲,勾勒出大城市打工人的奇跡故事。反觀(guān)在場(chǎng)觀(guān)影者,其并不能擁有片中景浩同樣的勇氣和振奮人心的機(jī)會(huì),便會(huì)抽離于情節(jié)。但導(dǎo)演在視聽(tīng)層面的嫻熟技法與敘事技巧的靈活運(yùn)用,讓觀(guān)影者沉浸其中,滿(mǎn)足內(nèi)心期待,此時(shí)觀(guān)影者又作為看與聽(tīng)的主體而在場(chǎng),“縫隙”由此存在。
敘事的情感滲透、細(xì)節(jié)的刻畫(huà),再次將觀(guān)影者代入電影中,并與其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幻想銀幕中的“我們”即將發(fā)生的故事,此時(shí)裂縫被縫合。“觀(guān)眾在攝像機(jī)的連續(xù)調(diào)動(dòng)下,不斷調(diào)整自己去認(rèn)同被設(shè)計(jì)和被組織后的形象,隨后陷入到一種由雙鏡頭所建造的虛構(gòu)的陳述中,達(dá)到‘相信’影像內(nèi)容真實(shí)的幻覺(jué)狀態(tài)。”[2]
羅伯特·麥基在其著作《故事》中提到:“故事是生活的隱喻。”很多學(xué)業(yè)未完成就被迫謀生或者沒(méi)有受過(guò)名校教育的觀(guān)影者,都會(huì)自動(dòng)代入這種身份,與影片中的角色共情,如同照鏡子一般窺視自己在片中的表演行為,讓觀(guān)影者擁有兩個(gè)人的視角。景浩在艱難困苦中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夢(mèng)想,取得了成功,為妹妹掙夠了醫(yī)療費(fèi),還回到大學(xué)完成學(xué)業(yè),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公司。成功鏡像人物能幫助觀(guān)影者完成“理想自我”的建構(gòu)。
此時(shí),觀(guān)影者不是專(zhuān)注于鏡頭、角度、畫(huà)面等,而是用他的主觀(guān)幻覺(jué)填補(bǔ)了這些包含許多空間、敘述和意義的空白,觀(guān)影者不再懷疑他所看到的東西的真實(shí)性,主體之間的“裂縫”得以“縫合”。
2 敘事話(huà)語(yǔ)的情感滲透
2.1 人物塑造:塑造草根形象的身份認(rèn)同
電影憑借其直觀(guān)的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傳播優(yōu)勢(shì),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作為“造夢(mèng)機(jī)制”的藝術(shù),電影對(duì)觀(guān)影者欣賞藝術(shù)與敏感度要求較低,更容易與觀(guān)影者的思想感情產(chǎn)生共鳴。
相較于其他影視題材,草根人物在逆境中掙扎的故事在市場(chǎng)上更受歡迎,因?yàn)榇蠖鄶?shù)觀(guān)影者可以將自己的情感經(jīng)歷和體驗(yàn)代入電影,并在銀幕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盡管景浩這一角色不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某個(gè)具體的人,但他卻是現(xiàn)實(shí)中每一個(gè)普通勞動(dòng)者的化身。導(dǎo)演的意圖就是以鮮明的情感表達(dá)方式調(diào)動(dòng)觀(guān)影者的代入感,電影與觀(guān)影者的精神世界就變成了雙向的情感交流。
法國(guó)心理學(xué)家拉康在1936 年首次提出“鏡像”理論。他認(rèn)為,人類(lèi)心理學(xué)有三個(gè)領(lǐng)域,即“現(xiàn)實(shí)”“想象”和“象征”,與其相應(yīng)的是“理念我”“鏡像我”和“社會(huì)我”,從而置換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層理論。他劃分了人們逐漸能夠與鏡子中的形象合一的階段,即人們逐漸形成“自我”[3],逐漸從“理念我”走向“鏡像我”。
“鏡像”理論后來(lái)在電影領(lǐng)域得到廣泛應(yīng)用。孩子對(duì)鏡子中自己的感知,與坐在黑暗的電影院里,面對(duì)明亮的銀幕并最終離開(kāi)電影院的觀(guān)影者的情感體驗(yàn)和心理認(rèn)知非常相似。“理念我”在觀(guān)影時(shí),會(huì)從電影中尋找“鏡像我”,從電影所描繪的社會(huì)語(yǔ)境中理解“鏡像我”和“理念我”的契合,進(jìn)而變?yōu)椤吧鐣?huì)我”。
導(dǎo)演在人物塑造中并沒(méi)有刻意渲染普通民眾的辛酸苦楚。導(dǎo)演塑造的草根群體人物畫(huà)像及其經(jīng)歷都具有典型性,如:景浩即便拿到質(zhì)檢合格的報(bào)告,也依舊無(wú)法與李平經(jīng)理平等交談;汪春梅勇敢地維護(hù)自身合法權(quán)益卻遭到資本的反抗;梁叔夫婦熱心善良,但還是需要看人眼色行事,只敢在深夜放居無(wú)定所的景浩兄妹進(jìn)療養(yǎng)院。他們的每一絲情感流露都被擁有類(lèi)似經(jīng)歷的觀(guān)影者準(zhǔn)確捕捉,促使其形成強(qiáng)烈的情感共鳴。
幾經(jīng)坎坷,景浩終于獲得成功。此時(shí),典型的草根人物就不再是一群導(dǎo)演虛構(gòu)的與觀(guān)影者無(wú)關(guān)的人物,而是成為觀(guān)影者的“鏡像”。作為“理念我”的觀(guān)影者和作為“鏡像我”的角色在銀幕上得到了統(tǒng)一,實(shí)現(xiàn)了情感交流。
2.2 主題強(qiáng)調(diào):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認(rèn)同
一部作品的靈魂是主題,它是作品內(nèi)容的核心。《奇跡·笨小孩》的主要矛盾就是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景彤必須在8 歲之前做手術(shù)才有治愈的可能,而此時(shí)母親因病去世,父親跑路,只剩下還在讀大學(xué)的哥哥景浩照顧她,并且景浩要在最后一年內(nèi)獨(dú)自籌集到30 萬(wàn)元手術(shù)費(fèi)。從那以后,景浩的一切行動(dòng)以及與其并肩作戰(zhàn)的人物的矛盾沖突,都是為了化解這個(gè)核心矛盾而展開(kāi)的,雖說(shuō)影片呈現(xiàn)的情節(jié)突出了金錢(qián)的重要性,但導(dǎo)演將景浩守護(hù)家人并找到一群異姓家人組成“奇跡小隊(duì)”作為落腳點(diǎn),將對(duì)金錢(qián)的追求替換成了“對(duì)美好生活的追求”這一主題。導(dǎo)演旨在用景浩的奮斗歷程來(lái)闡釋每個(gè)人都平等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quán)利。
《奇跡·笨小孩》番外篇中提到,妹妹在1 歲多就查出得了家族性心臟病,父親于是拋妻棄子,懂事的景浩和重病的母親支撐著家庭的重?fù)?dān)。景浩上大學(xué)后得知深圳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發(fā)達(dá),有掙錢(qián)的機(jī)會(huì),于是他才選擇輟學(xué)到深圳打工。機(jī)緣巧合下景浩發(fā)現(xiàn)舊零件重新組裝成新手機(jī)可以賺到錢(qián),可沒(méi)過(guò)多久,“打擊翻新機(jī)”的政策相繼出臺(tái),景浩事業(yè)遭遇重創(chuàng)。此時(shí),距離妹妹的手術(shù)僅剩最后1 年,于是景浩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重新振作起來(lái),通過(guò)努力爭(zhēng)取到了大公司回收手機(jī)零件的機(jī)會(huì),但卻苦于沒(méi)有定金。最終,景浩在梁叔的幫助下建立起電子元件廠(chǎng),招收了形色各異的草根人物。雖然經(jīng)歷了一系列挫折磨難、天災(zāi)人禍,但都被逐一化解,景浩展現(xiàn)出了卓越的能力和超凡的品格。
“奇跡小隊(duì)”中的每個(gè)人都在追求美好生活,最終電影展現(xiàn)出了一道群像弧光。身患?xì)埣驳溺妭?chuàng)辦了老年公寓,包括其本人在內(nèi)的200 余位老人在此安居;“追風(fēng)少年”張超和劉恒志聯(lián)合創(chuàng)辦了網(wǎng)咖,擁有7 家連鎖店并承辦多場(chǎng)電競(jìng)賽事;張龍豪與汪春梅結(jié)婚并創(chuàng)辦了搏擊俱樂(lè)部,建立流浪動(dòng)物救助站;汪春梅還建立了“打工人幫扶中心”,服務(wù)了千名打工者。影片中每名成員都憑借自己的奮斗收獲了成功與幸福,這無(wú)疑給在場(chǎng)的觀(guān)影者打了一劑強(qiáng)心針,觀(guān)影者為其感到高興的同時(shí)也對(duì)追求美好生活產(chǎn)生情感認(rèn)同。
2.3 情境建構(gòu):呈現(xiàn)深圳景象的地域認(rèn)同
“城市意象”亦可稱(chēng)為“城市印象”,即一座城市在公眾眼中的形態(tài)特征。影片中的城市不僅僅是一個(gè)故事背景,其還具備敘述者的功能,可以直接為電影的敘事作出貢獻(xiàn),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推動(dòng)故事的走向,這就是城市作為一個(gè)場(chǎng)景的參與功能[4]。一部電影一旦在開(kāi)頭交代了地點(diǎn)信息,那么該地點(diǎn)就不再是“低介入”,而是“高介入”,因?yàn)槌鞘幸蛩貢?huì)直接影響、改變甚至決定電影的線(xiàn)索或方向[5]。
2013 年的深圳被選為該劇的空間原型。彼時(shí)深圳是一個(gè)全國(guó)著名的“先進(jìn)示范區(qū)”,是走在改革開(kāi)放前沿的經(jīng)濟(jì)特區(qū)。導(dǎo)演構(gòu)建了2013 年觀(guān)影者熟悉的深圳,觀(guān)影者在看電影的過(guò)程中也會(huì)調(diào)動(dòng)近10 年的記憶,通過(guò)導(dǎo)演塑造的深圳的氣候、深圳的高樓林立、深圳的擁擠破敗等進(jìn)行想象,進(jìn)而達(dá)到鏡像理論的一次同化,觀(guān)影者仿佛置身其中,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地域認(rèn)同。
深圳承載著太多年輕人的希望。景浩來(lái)深圳拼搏,就是因?yàn)樯钲诒揪褪莻€(gè)奇跡之城,景浩希望妹妹的病也能像深圳一樣通過(guò)他的努力賺錢(qián)可以奇跡般好轉(zhuǎn)。景浩在高空擦玻璃時(shí)用水管澆自己,觀(guān)影者隔著熒幕都能感受到深圳天氣的炎熱,餓了就吃饅頭,處處體現(xiàn)出打工人生活不易,這與玻璃窗里的人喝著紅酒、吃著西餐談生意形成鮮明對(duì)比。這樣的對(duì)比還有深圳現(xiàn)代化的高樓大廈與混亂的城中村。歌手陳楚生回憶自己在深圳打拼的那些日子,并創(chuàng)作了首歌,“那是高速生活中為數(shù)不多的喘息角落,也是美妙夢(mèng)想與殘酷現(xiàn)實(shí)雜糅并存的駐足之地……”在這個(gè)高速發(fā)展的城市,各種新興產(chǎn)業(yè)不斷涌現(xiàn),有理想、有闖勁的青年都來(lái)到這個(gè)匯聚夢(mèng)想的城市拼搏,個(gè)體命運(yùn)與時(shí)代大趨勢(shì)具有的天然聯(lián)系,建構(gòu)起觀(guān)影者對(duì)于深圳這座奇跡之城的地域認(rèn)同。
2.4 意象表達(dá):詮釋影像創(chuàng)新的文化認(rèn)同
真實(shí)且生動(dòng)的細(xì)節(jié)是豐富故事情節(jié)、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增強(qiáng)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創(chuàng)作者用來(lái)表情達(dá)意的有利方式。影片中景浩的背一直都是駝的,說(shuō)明景浩每天都背負(fù)著很大的壓力。例如,影片中有關(guān)于房東催房租的情節(jié),第一次房東禮貌地在催租紙上用了個(gè)“請(qǐng)”字,第二次便直接寫(xiě)了“交租”,第三次房東更是用紅筆寫(xiě)下“交租開(kāi)門(mén)”四字,態(tài)度一次比一次強(qiáng)硬,可見(jiàn)景浩背負(fù)著極大的壓力。
片頭中妹妹的分隔裝藥盒表明妹妹需要不斷服藥,但畫(huà)面里卻呈現(xiàn)出鮮艷的色調(diào),如黃色的沙發(fā)、妹妹的黃色杯套、景浩的黃色T 恤衫。諸多意象的對(duì)比更加突出景浩兄妹面對(duì)不幸遭遇依舊不卑不亢、堅(jiān)強(qiáng)樂(lè)觀(guān)的態(tài)度:景浩帶妹妹住進(jìn)工廠(chǎng)里,早上吃稀飯的碗是買(mǎi)泡面送的;妹妹的衣服都是小女孩喜愛(ài)的漂亮的衣服,而景浩的基本都是老款Polo 衫(一種休閑服裝);妹妹睡覺(jué)用的是厚厚的床墊,而景浩的就是薄薄的被褥。影片中還反復(fù)出現(xiàn)螞蟻這個(gè)意象,一方面因?yàn)槲浵伿侨壕觿?dòng)物,能夠利用團(tuán)結(jié)的力量挪動(dòng)超越自己身體數(shù)倍的物體,是自然界的奇跡之一,這與“奇跡小隊(duì)”互助互救相呼應(yīng);另一方面螞蟻身處偌大的城市之中,雖然微不足道卻頑強(qiáng)拼搏,這與景浩的性格很像,即勤奮執(zhí)著充滿(mǎn)力量,通過(guò)自己的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闖出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遭到臺(tái)風(fēng)侵襲后,廠(chǎng)房坍塌,景浩低著頭獨(dú)自面對(duì)巨大的危機(jī),此時(shí)鏡頭轉(zhuǎn)向一只螞蟻,它緊緊把住鐵棚邊緣不讓自己掉落,這是來(lái)自生命深處的生存渴望,也是景浩內(nèi)心的真實(shí)寫(xiě)照。之后廠(chǎng)里的員工都來(lái)了,每個(gè)人都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要承擔(dān)接下來(lái)的拆解工作,同甘共苦的情誼在此刻得到凸顯,強(qiáng)大的凝聚力感染著觀(guān)影者,使其與片中人物同呼吸、共命運(yùn)。
山同樣是影片的重要意象,“奇跡小隊(duì)”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可以說(shuō)是“愚公移山”的現(xiàn)代版本。舊手機(jī)第一次出場(chǎng)就堆成了一座山,這象征著當(dāng)時(shí)壓在景浩肩上的山,但在戰(zhàn)友的通力合作下,這座山被“分解”了。其實(shí),勞動(dòng)人民的一大優(yōu)點(diǎn)就是善于“愚公移山”,不畏艱辛,敢于挑戰(zhàn)。無(wú)論是螞蟻還是山,這些意象的恰當(dāng)運(yùn)用都更易使觀(guān)影者產(chǎn)生文化認(rèn)同。
3 結(jié)語(yǔ)
導(dǎo)演在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創(chuàng)作之外加入巧思,使得觀(guān)影者得到了情緒的釋放和內(nèi)心情感的滿(mǎn)足。對(duì)于講述小人物勵(lì)志成長(zhǎng)故事的新主流電影,可以在鏡像理論視域下分析其敘事策略,研究影片是如何通過(guò)人物的塑造、主題的強(qiáng)調(diào)、情境的建構(gòu)、意象的表達(dá)來(lái)給觀(guān)影者呈現(xiàn)一面自我?jiàn)^斗的鏡像,進(jìn)而完成對(duì)自我的建構(gòu)。影片中的景浩作為觀(guān)影者理想自我的投射,其行為及人格特征都對(duì)觀(guān)影者的自我認(rèn)知和建構(gòu)產(chǎn)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