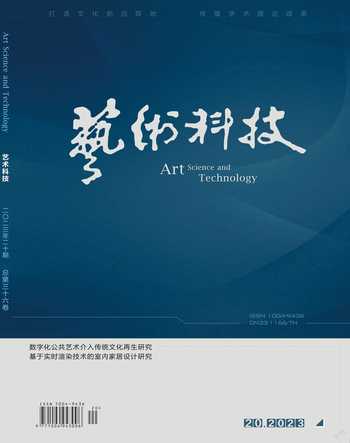《古詩十九首》季節與抒情研究
摘要:《古詩十九首》中涉及季節的詩歌有十五首,詩人們敏銳地捕捉到了四季的變化,展現時序更替的自然景物圖,使得大部分作品中的季節與情感產生了微妙的互動。詩人多用具有物候特征的事物來暗示事件發生的時節,在渲染詩歌感情基調的同時,為后文情感的抒發埋下種子。物象隨季節而變更,詩人的心緒隨四時的變化呈現季節性特征。在不同的季節,詩人抒發不一樣的思想情感,在春夏時節多抒發對時光流逝的感慨,在秋季多表達沉淪失意的痛苦,冬季則多是閨怨相思的詩作。在這些復雜的情感當中,以悲情為詩歌的基調,這也是季節性抒情的另一特點。詩人們對生命的體悟、對人生的追尋,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季節不僅影響著詩人的情感,也成就了《古詩十九首》獨特的抒情特色和藝術魅力。
關鍵詞:《古詩十九首》;季節;抒情;悲情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20-0-03
學界歷來對《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層出不窮,有對內容的獨到闡釋,也有對表現形式的深入分析。近來,《古詩十九首》中的時序觀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即《古詩十九首》的詩人對季節變化的敏銳捕捉,使得大部分作品呈現出季節與情感之間的微妙互動,這也成為《古詩十九首》的魅力所在。
對于季節與抒情之間的關系,古人早深有研究。《文心雕龍·物色》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1]劉勰清晰地闡述了詩歌中季節與抒情之間的密切關系,深入分析了自然現象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情緒受四時景物變化的影響,目之所及,觸之所興,終歸詩人之所感。因此,研究《古詩十九首》中季節與抒情的特征,分析《古詩十九首》季節書寫的獨特效果及《古詩十九首》的抒情特色,有助于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文本,從而達到對文本的深度理解。
1 抒情的季節性
借自然之物象,澆胸中之塊壘。詩人把季節當成抒發情感的媒介,將自己內在情感熔鑄于景物之中,而溝通兩者的橋梁則是詩歌中的季節。《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用具有物候特征的事物來交代時節,在奠定詩歌感情基調的同時,為后文情感的抒發作了鋪墊。詩人將春夏秋冬的自然物候寫進詩歌中,創作出了“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等佳句。自春至冬,生命由旺盛轉向衰敗。《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敏銳地抓住了四季的變化,為人們繪制出了一幅時序更替的物象圖。物象隨季節變更,作者的心緒也呈現出季節性的特征[2]。
從一年的起始到終結,《古詩十九首》描寫了不同季節事物的變化,展現了時間的流逝,以及詩人對生命的感悟。在描繪春天時,詩人們多用花、草、柳等植物意象。如“含英揚光輝”里鮮艷的花朵,“綠葉發華滋”中茂盛的綠葉,“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中蔥郁的春草及垂柳。此外,還有“越鳥朝南枝”中北飛的越鳥,“東風搖百草”里和煦的東風。這些事物無不彰顯出春天的生機與活力。面對這些美好的事物,詩人的心情本應是舒暢歡快的,但實際上,其內心的情感卻是低沉的。仕途上的苦苦追求與現實中時不我待的無奈使得他們對時間的流逝更為敏感,如《回車駕言邁》:
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東風”點明了詩歌創作的背景為春季,詩人在求仕的路上四處奔波,眼前一片萬物復蘇的新氣象,卻從草由榮到枯聯想到人由少而老。春季的到來也暗示著詩人年歲的增長,詩人還未能建功立業就逐漸老去,而人的生命又很短暫,這加深了詩人對時光流逝的憂慮。又如另一首詩《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春日的美景使詩人欣喜,詩人想攀樹折花贈給所思之人,卻因路途遙遠而無法實現。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詩人在折花思念所懷之人的同時,也抒發了傷春的無奈,以及對時光流逝的不可把握之感。《古詩十九首》中關于夏季的詩歌只有《涉江采芙蓉》一首,其保持著與這首詩相同的基調。
春夏屬于思鄉的游子,秋冬則屬于失意的文人。秋季草木凋零,大雁南飛,對于失意的文人來說,秋季已超越了時節概念,成了仕途失意痛苦時真實的情緒寫照。《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多出自寒門,為了求取功名漂泊在外。他們見識過社會的黑暗,如“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青青陵上柏》),以上層統治階層的腐敗荒淫與下層平民的苦難心酸相對比。他們也飽嘗了世間人情的冷漠,《明月皎夜光》就展現了對人情淡薄的憤懣及對自身處境的無奈: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
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馬茂原先生說,“‘東壁促織和‘樹間秋蟬的鳴叫,都是生機沒落的象征,正如何焯所說,是‘自比如蟋蟀的悲吟;至于‘玄鳥的去寒就暖,和‘秋蟬對比,則使詩人進一步聯系到自己和‘同門友的現實處境。這一切重見迭出、縱橫交錯的現象,都統一于詩人情感的滲透而成為有機的整體,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3]123。秋季的凄清冷寂、景致的衰敗在詩句中展現得淋漓盡致,詩人在蕭瑟的秋季里愈發苦悶。前四句先對所處季節的景物進行描繪,以凄清寂靜的氛圍引發出詩人對自身處境的感慨。曾是同道人,如今“我”仍在原地,尋求功名,而朋友卻“高舉振六翮”,身居要職,兩者之間的地位變化自然引起了詩人內心的不平。詩人想策高足,卻得不到同門的幫助,往日的感情隨著世態的變化變得不堪一擊,令詩人深感孤寂與悲涼。深秋時節、落寞的景物、苦悶的詩人三者基調和諧又統一[4]。
此外,還有聽曲而作的詩歌《東城高且長》:“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事件發生在蕭瑟落寞的秋季,詩人寫下聽曲之后的感悟,悲傷的琴音使其產生共鳴,成為失意人的內心寫照。《西北有高樓》也同為秋季聽曲感心之作: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愿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對“清商”進行了注釋:“《清商》大概是漢代民間最流行的樂調。‘商,五聲之一。古代以羽、徵、角、商、宮五聲,配合水、火、木、金、土五行,而五行又分屬四時。商是金行之聲,屬于秋的季節。《呂氏春秋·孟秋紀》、《仲秋紀》和《季秋紀》都說‘其音商。《管子·地員篇》又說:‘凡聽商,如離群羊。足見清商的聲音,清婉悠揚,適宜表現憂愁幽思的哀怨情調。”[3]63由“清商”的曲調推出彈奏的季節,點明本詩寫于凄楚蕭條的秋季。“西北”“高樓”“浮云”,空間上的凄苦意象融匯在秋季的蒼涼之中,深婉且和諧,悲情而濃郁,使詩人所表達的壯志難酬的失意苦悶比以往更為強烈。
在春天遠走他鄉的游子,到冬季仍未歸來,只留下獨守空房的深閨女子日日思念著丈夫。《凜凜歲云暮》和《孟冬寒氣至》是《古詩十九首》中為數不多的以思婦為主人公的作品,《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多不可考,這兩首詩作者或是女性,或為男子作閨音。兩首詩都以寒冬為背景,抒發女子閨怨相思之情[5],以《凜凜歲云暮》為例: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
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
愿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
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詩開頭就展示了嚴冬寒冷的自然環境。凜冽的寒風呼嘯,惡劣的天氣令思婦擔憂他鄉的丈夫是否有保暖的衣物。在寂靜的寒夜中,思婦獨棲獨宿,不由得思念游子,悲傷不能自已,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冬季本就日短夜長,思婦內心波蕩的情絲使其越發覺得夜晚漫長,思念難熬,最后在夢境中與丈夫相守相伴,可謂思之入骨。再如《孟冬寒氣至》: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
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古人對冬季的描寫多由風開頭,本詩也不例外。慘烈的北風呼嘯而來,深冬寒氣刺骨。此外,這首詩還添加了對星宿的描寫,一來點明具體的時節,二來以星宿的歸位與游子的漂泊作比較,以明月的圓滿與思婦與游子的分離相對比。酷寒的冬日,思婦只能閑居在家思念著遠在他鄉的丈夫,讀著丈夫從遠方寄來的家書。這兩首閨怨詩都從寫冬日到寫思夫,以環境的惡劣襯托出思婦的相思之苦,飽含深情。
2 季節中的悲情色彩
整體而言,《古詩十九首》沿襲“傷春悲秋”的傳統。無論是對美好事物的描寫還是對衰敗事物的展現,都帶有濃郁的悲情之美。特別是寫到明媚和煦的春天、萬物生長的夏季時,總帶有明顯的傷感色彩,這與詩人的經歷高度一致,他們對生命的感悟、對世間情感的感受、對人生的追尋,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在勾勒春季美麗的景色時,回歸到情當中,借春景抒發年華易逝、生命短暫的感慨。如“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花朵、綠葉等美好的事物都不能治愈詩人內心的感傷,明媚的春景反而令詩人不由得感嘆年華的流逝,對他鄉之人的思念之情更加濃烈。《回車駕言邁》本描繪了春和景明的畫卷,詩人卻筆鋒一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發出了新草代替“舊物”的感慨,“東風”成了時間的推動者,從客觀景物的更新,想到人生命的短暫。同時,詩人也借春景寄托相思之苦、念鄉之痛。如《青青河畔草》以青草、綠柳來表現春天的季節特征,表達了詩人纏綿悱惻的無盡思念;又如“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中對傷春思歸的嘆息。詩人們繼承了古典詩歌里“傷春”的詩歌傳統,詩歌感傷卻富有春意[6]。
在《古詩十九首》中,秋冬季節出現最多。以秋冬為背景,更契合詩人對故人的追思與懷念,能渲染出落寞之情。如“秋草萋已綠”(《東城高且長》),用枯萎的秋草來比喻年華的流逝、容貌的衰老,實現了詩人主觀感情的物化。在“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明月皎夜光》)中,深秋的寒冷寂靜無疑與詩人內心愁苦和寂寞的心境相適。“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驅車上東門》),“白楊”和“松柏”意象常與死亡和墳墓相伴,大多出現在挽歌、懷古的古詩中,以表達及時行樂、人生無常的感嘆[7]。“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去者日已疏》),以冬季北風的慘烈強調了思婦對游子的思念。“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凜凜歲云暮》),表現出詩人心里的羈旅愁懷之情如冬天刺骨的寒風一般。“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孟冬寒氣至》),慘栗的何止是北風的呼嘯聲,還有女子在寒冬對所思之人的呼號[8]。
3 結語
在《古詩十九首》中,詩人們通過對季節的敏銳捕捉、對時序的精準把握,構建了別 (下轉第頁)(上接第頁)具一格的抒情模式。以心緒牽動對時節的感知,以自然物象的特征觸動情思的泉涌。他們用平易淺白、質而不野的語言風格,表達了最樸實、真摯的情感。
參考文獻:
[1] 丁繼承.《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悲歌與情懷[J].文學教育,2020(8):62-64.
[3] 曹旭.《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
[3] 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123,63.
[4] 陳晶瑩.《古詩十九首》抒情方式探究[D].漳州:閩南師范大學,2019.
[5] 葉嘉瑩.《古詩十九首》的文采與內容[J].人文,2020(1):120-132.
[6] 吳博群.論《古詩十九首》中的時空觀與抒情性[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13-17.
[7] 陳璐瑤.“古詩十九首”中的時序意識[J].文化學刊,2020(12):92-94.
[8]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6:412.
作者簡介:陳文瑤(1997—),女,貴州黎平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