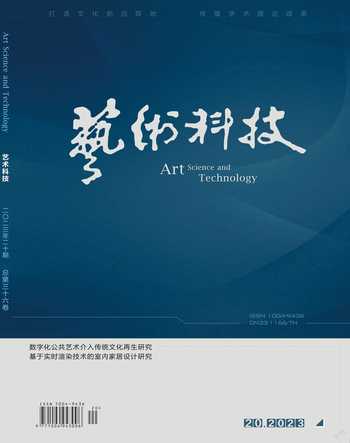程耳電影的“間離效果”研究
摘要:程耳作為當代新銳導演,其作品具有獨特的美學追求和藝術探索精神,展現出獨屬于程耳的作者電影風格。目的:程耳電影在類型創作的基礎上融入了獨特的風格與藝術效果,其藝術風格存在逐漸成熟的過程,但也有一以貫之的風格要素。“陌生化”效果是程耳電影的重要特點,文章力求探究其具體表現方式與技巧。方法:文章以程耳的四部長篇電影與一部畢業短片為文本,從復雜敘事、空間敘事、角色與演員、復雜主題的呈現四個方面對其電影如何營造與增強“間離效果”進行論述。結果:這些電影表現形式的反復出現使程耳的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戲劇理論中的“間離效果”,成為輔助程耳構建自己電影風格的重要環節。在程耳電影中,作品與觀眾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疏離感。當前社會語境下,商業電影的創作以打造沉浸式觀影體驗為重點,程耳電影反而打破傳統觀影過程對視覺的規訓,將觀眾肯定、共鳴的立場轉變為批判的立場,試圖打破“第四面墻”,呼喚電影觀眾的理性在場。結論:程耳電影為中國懸疑類商業化電影打開了新的思路,在影像語言和電影敘事上作出了商業電影的藝術化探索,努力調和商業資本與個體藝術化表達之間的矛盾,對中國商業電影的創新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程耳;電影;“間離效果”;復雜敘事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20-0-03
“間離”(Vertermdung)一詞出自德國戲劇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理論。布萊希特認為,在各種藝術效果里,一種新的戲劇為了完成它的社會批判作用和對社會進行改造的歷史記錄任務,“陌生化”效果是必要的[1]。其中,“間離效果”則是阻止觀眾在觀看演出時完全入戲,從而使觀眾與表演之間產生距離的一種方法,也稱為“陌生化理論”。布萊希特雖然以戲劇作為其理論思考的載體,但在電影的實踐中,“間離效果”也對觀眾接受具有一定的影響。電影中運用各種表現手法創造的“間離效果”能夠呼喚觀眾理性在場,思考影片的內涵,打破傳統觀影過程對視覺的規訓,形構出一種非經典的電影美學觀念,使觀眾脫離深陷虛構情節的幻覺性體驗[2]。
程耳自1999年畢業至今只有一部畢業短片和四部公映的長篇電影作品,但是其獨特的復雜敘事、冷峻疏離的視聽語言與探索人性的嚴肅主題,使其成為21世紀以來獨具特色的中國新銳導演。集導演、編劇、剪輯于一身的“作者型導演”,程耳的作品風格相對統一,以懸疑片、犯罪片為主要創作類型,利用復雜敘事講述人性與時代的故事。在程耳的電影中,觀眾經常會感受到明顯的疏離感,即其與影片人物難以建立完整的聯系。初次觀看時,觀眾便需要在關注劇情的同時對導演所拋出的種種問題進行思考,這種符合布萊希特“間離效果”理論的觀影體驗,是導演通過影片的復雜敘事、空間敘事、對角色的特殊處理與主題深化所刻意創造出來的,它打破了傳統電影對觀眾視覺的規訓,使觀眾在觀影時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參與到影片的情節發展中,是將商業電影藝術化的實驗結果。
1 復雜敘事制造間離效果
大衛·波德維爾在《好萊塢的敘事方法》中首次提出了“puzzle film”的概念,國內電影學界普遍將其翻譯為“謎題電影”,雖然程耳電影并不能算是典型的謎題電影,卻又確實存在謎題電影具有的特殊元素。在敘事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好萊塢興起的謎題電影的敘事方式是類似拼圖游戲那樣碎片化的、非整一的[3]。程耳電影以分段敘事為主,雖然各個段落之間的時空差異不大,但是會由影片人物講述過去的故事,觀眾只要看完整部電影就能將故事的因果邏輯串聯。因此,程耳的復雜敘事與謎題電影相似,但缺乏相應的解謎過程,更像是以“四格拼圖”的形式展現情節(例如《記憶碎片》等謎題電影就是更多格的拼圖)。瑪麗-勞爾·瑞安將沉浸式體驗分為敘事沉浸和游戲沉浸,觀眾在觀看程耳電影的過程中會產生些許困惑,造成敘事沉浸度降低,然而這些困惑會在影片進行中逐漸得到解釋,故而影片的游戲沉浸度不夠。這種對沉浸的特殊處理迫使觀眾始終以旁觀者而非參與者的態度來看待整個電影敘事。
雖然非線性常被視作一個單獨的敘述類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敘事可以利用多種技巧來創造非線性時間模式和體驗。可以發現,識別其中的兩個關鍵類別大有用處,即非線性故事講述和非線性故事世界[4]。然而,程耳電影的敘事邏輯既不完全按照時間的發展進行,也不是單純的多線并行,而是多種結構共同交叉進行,將非線性故事講述和非線性故事世界相結合。觀眾既不是全知的上帝視角,也不是存在盲點的劇中人物視角,而是像快進電影一樣選擇進度條,遇到迷惑的地方則由導演帶領著向前或向后探索,最終在結局時將段落化的故事情節串聯,得到完整的敘事。
《羅曼蒂克消亡史》以小六和陸先生的故事作為主線,同時也有一些沒有結局的人物支線作為閑筆,除了陸先生發現渡部是間諜這件事之外,對于馬仔、王媽、童子雞、趙先生等人的遭遇和結局,主角并不是全知的,但觀眾能相對清楚地了解到在時代大背景下這些人所經歷的事件。可見,在給予觀眾“謎題”,打亂敘事順序的同時,導演給了觀眾“上帝視角”去審視所有人的命運。
《邊境風云》所使用的分段結構與中國的章回體小說有異曲同工之處,在第一章《狗》的結尾處戛然而止。與章回體小說不同的是,程耳依舊使用了非線性敘事,在第二章隨之講述另一個看似沒有關系的故事——《往事》,故事的尾聲才將兩個段落交匯。而《羅曼蒂克消亡史》中雖然沒有使用小標題,但也用字幕將時間地點清晰地展示出來,通過“1937”“三年前”“1945”“1941”等構成了與前述相同的分段效果。這種段落式描述的出現讓觀眾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以碎片化的方式“閱讀”一段歷史,而非親身參與。《無名》則與《羅曼蒂克消亡史》如出一轍,“1938年9月廣州淪陷前夕”“三年后上海”“距離日本戰敗3年零7個月”“1945年5月距離日本戰敗3個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1946年香港”以黃色加粗的標題形式出現在電影中,清晰地提醒觀看者故事的時間進度。
程耳自認為受到博爾赫斯的影響,因此其十分認同伯格森所提出的拒絕將時間空間化的理論起點。由于視角的不斷變換、主要敘事者的缺席和差異,觀眾也可以通過不同角度甚至跳出影片去理解整部電影。
2 空間敘事對“陌生化”的加強
程耳電影中敘事空間的確定、空間造型以及視聽語言的表達對特殊空間的呈現和“陌生化”效果的營造均為導演個人藝術化表達的重要部分,程耳對特殊空間與場景的選取既具備類型片的特點,也有助于電影整體風格的凸顯。
2.1 邊境空間奠定電影基調
程耳電影在空間的定位上偏愛邊境地區,《犯罪分子》《羅曼蒂克消亡史》《無名》的主要情節都發生在上海或香港,都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而《邊境風云》背景則在云南和緬甸,《第三個人》雖然沒有明確說明城市,但在電影中可以發現是個濱海城市,而拍攝地點正是山東青島。對邊境城市的偏愛使程耳電影的鏡頭中內容更加多樣,層次也更加豐富,城市、河湖、海濱、田野等增強了文本的開放性,使觀眾或在熟悉的空間中了解陌生的故事,或在陌生的空間中對敘事進行審視,這種審視的態度也是程耳電影蘊含“陌生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程耳電影中的群眾演員非常少,《第三個人》中何偉開車撞到小女孩時,街上空無一人;《羅曼蒂克消亡史》背景雖然是繁忙的都市上海,但小五和馬仔在車站刺殺二哥時,也只有他們三人與二哥的保鏢在場;《邊境風云》由于毒販的身份特殊,荒涼的云南邊境更是人煙稀少。這種在邊境空間中營造只有角色本身的環境,剝奪了觀眾作為“事件旁觀者”的可能性,這種缺乏“事件旁觀者”的空間對電影“懸疑感”的塑造非常重要,同時角色所處空間真實感的削弱和戲劇性的強化也更強調了“陌生化”效果。
2.2 生活空間敘事
程耳鐘情于在生活場景中表達故事暗含的內容,這種生活空間尤其偏向聚餐時刻。然而,聚餐在程耳的鏡頭中并不是溫馨的,反而是通過刻意的造型表現“最后的晚餐”。從本義來講,場所就是各種事件發生于其中的一種特殊的地方(空間);但從引申義來講,場所則可指代容納某類主題的話語或思想于其中的框架性的“容器”[5]。在敘事的同時,程耳電影中的生活空間有更強的主題性,為揭示影片內涵提供了更豐富的表達效果。如《邊境風云》中毒販、女兒和父親第一次聚餐使用的是長方形餐桌,并且三人的距離非常遠,毒販和女兒分別坐在餐桌的兩邊,一言不發,之后便是毒販出門,去完成最后一次交易,但被父親出賣,最終喪命機場,這次聚餐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最后的晚餐”,具有悲劇色彩。
與此同時,聚餐空間對電影中人物精神狀態的描寫和氣氛營造都有重要作用。《第三個人》中兩次聚餐對肖可的心理變化有一定的暗示作用,第一次聚餐時,肖可得知了姐姐懷孕的事情,從而刺激她找到“林先生”吐露內心的痛苦;第二次聚餐時,何偉拿了藥卻沒有給肖可,更加刺激肖可決定“綁架”何偉問出事實真相。兩次聚餐何偉始終背對鏡頭,與兩姐妹面對面,觀眾并不能像肖可一樣及時察覺到何偉的異樣,只能通過肖可的表情判斷和猜測此次聚餐可能存在的“內涵”與肖可精神的異常。諸如此類,《羅曼蒂克消亡史》與《無名》中主角所作的幾次重大的、影響事件走向的決定都是在飯桌上,生活化場景中的博弈使觀眾將注意力集中于可能的情節發展,而忽略了飲食所帶來的生活氣息,促使電影“陌生化”效果的進一步增強。
3 演員與角色的“陌生化”認知
布萊希特認為,當梅蘭芳示范表演婦女動作時,“他表演的重點不是去表演一個婦女怎樣走路和哭泣,而是表演出一個特定的婦女怎樣走路和哭泣”[6]。布萊希特對中國戲曲中演員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產生的“陌生化”效果和藝術效果十分認同,這種對演員有所要求的表演方法在現在的電影中似乎沒有傳統戲曲中那么明顯,卻可以人為地制造出演員與角色的距離,從而實現“陌生化”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程耳受到較多的評價是“他可以通過好的劇本招來一眾明星出演”,這些明星或許是成熟的優秀演員,如梁朝偉、徐崢、葛優、章子怡等,也有新生代演員甚至歌手,如王一博、高圓圓、楊坤、鐘欣潼等,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國民度很高,觀眾在看電影時可以立即反應過來演員的真實姓名,尤其是當《邊境風云》中所有角色都沒有角色名時,演員的名字就成為觀眾在討論時的符號。當楊坤作為殺手出現在鏡頭中,觀眾會在內心不時地對他跨界出演的效果進行評價;《羅曼蒂克消亡史》中葛優扮演的陸先生也是如此,因為葛優長期的喜劇演員形象深入人心,所以觀眾在未知電影內容的情況下就會不自覺地思考葛優在影片中是否有喜劇戲份。
在電影結束時,觀眾最終會發現這些演員對角色的詮釋十分到位,而不是簡單地以明星為噱頭吸引粉絲觀看的炒作,這種通過現實外力實現的演員與角色的“陌生化”效果,與其他商業電影邀請明星出演,明星始終在“扮演自己”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程耳電影對明星的采用與其角色的選定是導演經過設計和認真思考的結果。
4 “歷史化”條件下的復雜主題呈現
歷史化是布萊希特在實現演員表演“間離效果”中提到的一個重要概念。布萊希特認為,歷史事件是只出現一次的、暫時的、同特定時代相聯系的事件,人物的舉止行為在這里不是單純人性的、一成不變的,它屈服于從下一時代的立場出發所做的批判[7]。這與程耳電影中人物的行為動機有著緊密的關聯。程耳電影中的人物結局通常給人一種不合理但又非此不可的宿命感,如《第三個人》中,肖可最終放棄了報仇,因為她已經命不久矣,她更希望何偉從此活在自責和內疚的困擾之中;《邊境風云》中,毒販雖然竭盡全力希望能夠給妻子一個新生活,但還是因為自己曾經所犯的罪行被擊斃,并且在最后一刻將藏錢地點的鑰匙交給牙醫;《羅曼蒂克消亡史》中,陸先生寧愿殺害自己的外甥也要逼渡部出來,在報仇之后也只能離開上海,給曾經的風云時代畫上句號;《無名》中,葉先生等人在隱蔽戰線與各方勢力較量,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只能虛與委蛇,最終在戰爭勝利后成為“無名的英雄”,繼續隱姓埋名為未竟的事業奮斗。
程耳在體現人性的復雜上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表現方式,在影片中設定的特殊的時間、地點、環境中,主人公對自己和他人的命運選擇是偶然和必然的結合,如當仇恨占據內心的時候,即使什么都失去也要報仇,這種偏激的結局處理雖然符合故事中人物的選擇,卻與現實世界中普通觀眾的認知相去甚遠。因此,其在帶給觀眾對人性和命運的深刻思考的同時,將電影與現實割裂開來,在主題上實現了“間離效果”的強化,觀眾能夠清楚地審視自我,難以與電影中人物的選擇形成共情,更不會代入角色。
在電影中通過角色之口傳達導演對電影的評價也是程耳的一大特色,這一點從他的畢業作品《犯罪分子》中就可窺見端倪。如胡天在影片結尾展現內心獨白:“我知道我做錯了一件事情,以前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我會改。”導演借胡天之口表達了自己對角色所作所為的看法。而《邊境風云》則是直接讓妹妹說出,“這個事情,表面上看是治安問題,實際上是感情問題”,將電影主題和盤托出;《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戲中戲”片段,都在暗示小六的命運,而王媽和吳小姐的對話則點明這部電影是個藝術片,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導演沒打算讓大家看懂等。而《無名》的片頭更是用大紅字體展示“超級商業片”這一導演作出的影片定位。布萊希特 (下轉第頁)(上接第頁)的“間離效果”本身就是一種反思主體自身位置與周圍環境聯系的方式,其重點在于打破戲劇中的沉浸感,在電影中則體現為一種打破流暢敘事的影像語言[7]。這種方式使作者與自己作品的對話很容易被分辨,突然的解釋讓觀眾再一次發現自己是在“看電影”,再一次割裂了觀眾和影片的關系。
5 結語
通過對程耳電影的復雜敘事、空間敘事、演員與角色的“陌生化”認知及其影片復雜性主題的分析,表明導演是有意識地運用相關手段對電影進行“間離化”處理,觀眾也被迫與角色及文本產生距離,以超越傳統的流暢敘事電影的觀影體驗,處于更客觀的理解狀態中,從而對電影進行更理性的思考,解析文本背后更深層次的內涵。這種“陌生化”效果不僅成功輔助程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影像風格,而且更新了觀眾對類型電影的認知,引發了人們對商業與藝術相互融合的深入考量。
作為當前中國的優秀新銳導演,程耳在業內評價始終不錯,但市場評價反而不高,此種現況并不影響程耳的商業價值。或許正是因為其電影打造了不同于其他商業電影的沉浸流暢觀感,才促使商業資本與作品藝術性之間的矛盾得到調和,雖市場回報不如其他商業片,卻始終保持較高的評價。
參考文獻:
[1] 布萊希特.陌生化與中國戲劇[M].張黎,丁揚忠,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21,27.
[2] 黃天樂,王靜.論中國獨立電影中的間離效果[J].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3):121-126.
[3] 張立娜.謎題電影的游戲沉浸體驗與“想象力消費”[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51(2):129-137.
[4] 史蒂文·威廉森,米克洛斯·基什,潘璋敏,等.跟蹤時間:空間和具身認知在理解非線性故事世界中的作用[J].世界電影,2022(3):4-21.
[5] 龍迪勇.歷史敘事的空間基礎[J].思想戰線,2009,35(5):64-73.
[6] 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M].丁揚忠,李健鳴,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213.
[7] 周雪嶠.呂班“喜劇三部曲”的“間離性”研究[J].電影文學,2021(14):95-100.
作者簡介:竇雅倩(1996—),女,河北滄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電影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