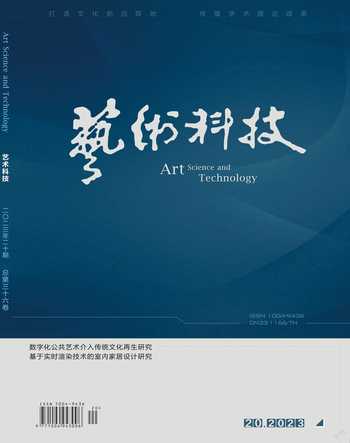地緣文化視域下藏地電影的空間探賾
摘要:在中國電影研究空間轉向的語境下,少數民族影視化作品數量匱乏,繼“西部區域電影”“內蒙古區域電影”研究之后,更多特色區域電影創作研究逐漸興起,藏地電影引起業界和學界的廣泛關注。21世紀以來,導演融合地緣文化和個人經驗,將藏地引人注目的獨特景觀和民族風情呈現給大眾。相繼問世的“藏地三部曲”,還有《氣球》《塔洛》等佳作,打破了固有的影像表意形態,基于地緣文化,對以往藏地電影的城鄉空間、傳統與現實的二元對立展開探討,進一步凸顯了身體與性別、空間與地點等幾重關系。萬瑪才旦電影鏡頭與地緣文化顯現共生的藝術形態,借由地緣空間與日常生活領域,更新了地域文化與藏地電影之間的聯系,塑造了全新的當代藏地電影。文章從空間的視角,探究地緣文化視域下的藏地電影,旨在還原更豐富立體的藏地文化場域,重現更具體的電影史的原貌,甚至促進藏地電影研究和思想史、心靈史、生活史、情感史等相互銜接,從而生發出諸多富有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學術命題。
關鍵詞:地緣文化;萬瑪才旦;藏地電影;戀地情結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20-0-03
“電影作為一種源于真實、反映真實的影像藝術,它的生產發展與地域風貌、地緣文化呈現一種‘共生狀態,同時也深受地緣關系的制約和影響。”社會群體以地方區域為情感紐帶,生活在一定區域內的社會群體,即地緣群體。作為地緣空間中的地緣文化,其與生活在特定區域的人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經過不斷發展逐步形成獨有的文化體系——地緣文化。空間與地緣文化的關系不可分割,探究地緣文化要以空間為基點,空間的生成與發展依附于地緣文化。“藏地電影”更強調在地性,以萬瑪才旦和松太加的影片為代表,不同于漢族導演的審視視角,其執著于探尋戀地情結。
外族視角張楊執導的《岡仁波齊》則是,“純粹地從地域景觀層面表現西藏,從景色至精神勾勒出西藏的壯美,過分強調藏族電影的在地性”。松太加的《阿拉姜色》同樣表現信仰力量,通過極具地域特性的“磕頭”這一標志性宗教行為進行情感輸出,松太加在這部影片中采用了不同于漢族導演張楊的處理手法,比《岡仁波齊》更具探討價值。《岡仁波齊》標志性地緣景觀展示,觀眾對景觀與精神擁有雙重解讀權,但《阿拉姜色》過濾掉壯美景色,觀眾只能捕捉到通過跪拜儀式所展現的特定情境制約并沉浸其中。地理基因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萬瑪才旦電影空間的整體建構,萬瑪才旦始終將藏地作為自己電影的書寫對象,他的電影也在記錄藏地發展和空間演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藏族電影中空間不僅作為敘事背景而展現,還將影像主體整合到人物和故事情節的表征中,由此空間成為藏族電影的特定標簽。
1 歷史:藏地電影的發展脈絡
縱觀藏地電影70多年的發展歷程,受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藏地電影在不同背景下體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同時出現具有差異性的地緣文化。
“十七年時期”,藏地電影與國產電影創作走勢總體一致,具有那個年代獨特的印記。電影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時代感,代表作有李俊的《農奴》(1963)、凌子風的《金銀灘》(1953)、王逸的《暴風雨中的雄鷹》(1957)等。以上藏地影視作品在地緣文化表達方面,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藏民生活、藏區風光,但并未深入藏民的日常生活,依舊呈現出現實政治的表述。
1978—2000年,電影創作市場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誕生了一系列優秀的藏地影視作品,不同影片呈現出不同形態的地緣文化和多元化的趨勢。這一時期的影視代表作品有《冰山雪蓮》(1978)、《盜馬賊》(1986)、《世界屋脊的太陽》(1990)、《益西卓瑪》(2000)等,可以從影片展示的異域奇觀中體會到藏族的地緣文化性格。雖已出現藏族內視角導演的影視作品,但創作主體依舊是漢族導演,影片主要呈現藏族人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未能從根本上擺脫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以漢族導演為創作主體的藏地電影,表達藏族傳統文化與異域風情的視角是內外交織的,自身地緣文化的局限性和民族情感表達的缺失,是外在符號化的呈現,并未深入探究民族文化內涵。
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促使藏地電影發生變化,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當下又出現了一位以原鄉人視野展現藏族、藏人真實生活狀態的作家導演——萬瑪才旦。《靜靜的嘛呢石》(2005)這部由藏族本土導演拍攝的純“母語電影”一上映就獲得了電影界和觀眾的關注。“這部影片是中國百年電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導演獨立編導的藏語對白影片,也是一部以藏族人視角來展示故鄉真實面貌,還原本民族人民當代現實生活圖景的電影。”[1]以藏人非職業演員、“純母語”對白,開啟了藏族導演對藏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新面貌。向觀眾呈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本土內視角為主的藏題材電影,萬瑪才旦拍攝的電影是真正意義上屬于藏族人自己的電影。他摒棄對異域藏地奇觀化的呈現,采用紀實手法并以空間建構電影的敘事,呈現了藏區的地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以超越文化隔膜的視野和格局對當下藏族人在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現代文化多重沖擊下面臨的生存問題、生活困境、傳統文化繼承和身份認同等問題展開思考”[2]。毫無疑問,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藏族作家導演萬瑪才旦便是在藏地這一方沃土上成長起來的。藏地電影不僅從獨特深厚的民族文化中源源不斷地汲取養分,而且與博大精深的雪域文化有一定的關聯。
迄今為止,非本族導演拍攝的“他者化”視野的藏題材電影對藏地空間的投射是驚鴻一瞥。而以萬瑪才旦為代表的藏族本土導演在藏地鏡像描摹中,往往從內視域出發,去景觀符號化,善于挖掘藏人的心理,注重客觀真實地展現處于變遷中的藏地。
2 邊界:藏地電影的空間呈現
電影空間造就了一種特殊的影像空間敘事形式,將文字書寫轉化為視聽語言的傳播,可以保留和再現人類現實生活中原不可重來的構序性場景。電影空間的場域源于非現實的第一空間,它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場地,還蘊含故事人物在場域中的情感寄托。前文提及,具有地緣性的區域產生了相應的文化、宗教、民俗,要想探討地緣文化,就要關注這些區域文化生活的共生體,具有區域邊界性。
要依靠地緣文化真實再現地理空間的獨特魅力,展現差異化的地理風貌、民俗風情及象征意義。在影片中,地理空間起到表意作用,推動情節發展。電影《可可西里》《轉山》《岡仁波齊》《皮繩上的魂》等,以奇觀化的視聽語言向觀眾展示充滿異域色彩的自然奇觀,并反映新的時代語境下藏人真正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惑。藏族導演萬瑪才旦以紀實的拍攝手法凸顯藏地特色,展示藏人真實的生活狀態,以內視角展現藏族民俗等,將邊緣藏地展現在大眾面前。
福柯的異托邦(另類空間)是多個空間的并置,是不同時空的糅合。寺廟看似是一個單一的空間,卻存在其他的空間想象,是承載萬瑪才旦電影里的異托邦的場所。異托邦是一個開放系統,空間關系多變且與其他空間相互滲透。徐曉東說:“嘛呢石堆處在寺廟和村莊之間,是個過渡地,聯結著兩邊,空間意味深長。”[3]影片將電視媒介、嘛呢石堆、家宅等聯系起來。在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中,寺廟是一個聯系多地的場所,既有傳統性又有現代性,與其他空間相互滲透,與媒介、家宅并置。在這里異托邦側重揭示藏區的真實狀態,看上去似乎是一個縹緲的存在。
意象表達作為一種精神象征,具有虛構性,寄托空間人物的信仰,是一種象征的空間。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可以從物質領域、抽象精神領域和社會領域這三個領域去識別,從而將空間的生產、空間的再現、再現的空間等列為重要的議程。“第二空間”的指向是精神空間。精神不是漂浮其中,而是確實與第一物質空間相聯系。索亞認為,空間也具有符號性,充滿真實與想象,有著不同的意象表達。
在萬瑪才旦的電影中,精神空間是依托第一物質空間和地理空間構織的。人在某個地理位置,與事物發生某種聯系,滋生出人物的心理空間,也構建了電影的文本表意空間。在寺廟這一地理場所中,電影《靜靜的嘛呢石》的媒介體電視打破了原有的秩序,與小喇嘛面對現代化媒介產生的心理變化,構成了某種寓意。萬瑪才旦在電影中通過空間中人群的流動、不同人物的空間實踐等成功地構建了藏民的日常生活。電影《尋找智美更登》借用公路片的敘事結構,濃墨重彩地表現電影里人物、公路和汽車的互通關系,將不同空間的“智美更登”這一傳統藏戲結合起來,令其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撞死了一只羊》中,兩個“金巴”分不出彼此,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身份相互映襯。兩者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關系,萬瑪才旦的思考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以看到對于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相互并置的呈現。
總的來說,萬瑪才旦在影片中借人與空間的關聯,展現時代快速發展帶來的諸多困境。創作實踐中形成了特有的視聽技法與影像修辭,是萬瑪才旦對邊緣群體的情感投射。同時,用生活流的方式記錄藏人的生活狀態,用電影鏡頭將時間的流逝和人物狀態推進現實社會。
3 文化:藏地電影的文化表達
文化包羅萬象,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都有所體現。從地緣文化來看,“文化可劃分為技術和價值兩極體系。技術體系是指人類加工制造形成的物質、客觀的東西;價值體系是指人類在加工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意識性的東西,具有主觀能動性”[4]。在藏地電影研究中,民俗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同的地域空間擁有不同的地理環境和人文,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景觀,萬瑪才旦借助藏地的民族特質和獨特的自然風光造就了多元的奇特文化景觀,通過習俗、服飾、建筑等營造相應的文化形態。
家宅是容納親情的容器,在萬瑪才旦的電影中,家宅始終是人物情感的最終歸屬。萬瑪才旦擅長利用家宅空間彰顯傳統文化的地位,在影片中注重呈現傳統親情秩序和節慶儀式。萬瑪才旦的電影《老狗》中的藏獒既是原始牧區生活的象征,又代表了一種精神和文化。作為牧區優秀的家園保衛者和羊群的守衛者的藏獒得到了影片中的父親的認可,他認為藏獒保障了羊群的安全,離開藏獒牧民會陷入生活危機。影片中的兒子卻認為,與其讓藏獒被偷走,倒不如把藏獒賣個好價錢,父子觀念存在沖突。《老狗》展現了人物情感關系由疏離到親密的變化。電影最后一個長鏡頭呈現了父子倆相互依偎的背影,標志著父子觀念最終達成一致,共同完成了對傳統的堅守。《五彩神箭》中扎東家最顯眼的位置懸掛著神箭,一方面象征著尖扎縣藏族人的精魂,標志著射箭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象征著父權。萬瑪才旦在家宅空間的細節中隱喻了藏族人對傳統的堅守。而《靜靜的嘛呢石》通過一家人參加在藏歷新年舉行的節慶儀式,體現出傳統文化的意義。家中成員在藏歷新年來臨之際,遵循長幼有序的原則安排座次,還有布施等細節體現出藏族人對傳統儀式和慣例的遵循。
“生活流”式的視語呈現在萬瑪才旦的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中,通過寺院的日常生活突出藏區僧人對修行的堅持。藏區僧人修行的常態,如師傅與小喇嘛誦經的鏡頭,師傅隨后再現在佛堂凈燈禮佛的過程。在藏歷新年,師傅帶上小喇嘛去給小活佛拜年。年老的師傅請小活佛為他摸頂等細節彰顯了藏族人對小活佛的尊敬。隨后師傅在聊天中表示自己將去拉薩朝圣,就算死在路上他也愿意,突出了藏族人的虔誠。電影《撞死了一只羊》《氣球》,彰顯了信奉藏傳佛教的藏族人對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價值觀的堅守。在人煙稀少的青藏無人區撞死了一只羊的司機金巴覺得內心不安,他將羊扛到寺院,請求僧人為羊超度,讓羊的靈魂早日轉入下一個輪回。金巴說服僧人為羊誦經超度,給予羊高規格的天葬,認為這樣既可以幫助羊的靈魂早日輪回,又可以為自己積累福報。司機金巴竟然寧愿給乞丐錢也不讓乞丐吃羊肉,整個故事看似荒誕,卻體現了藏族人對追求真善美的藏傳佛教的堅守。
4 結語
縱觀藏地電影地緣文化表達,其在類型化創新表達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呈現了新的時代語境下多元的社會情景和藏民的日常生活,拓寬了藏族電影的敘事空間。在“內外視角”的書寫中,藏地電影地緣文化表達呈現出多元化形式,多頻共振的民族精神與地緣文化,不斷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不同的地域空間孕育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藏地空間為地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支撐,體現了藏族獨有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氣質,藏地電影的地緣文化也更加豐富。
參考文獻:
[1] 饒曙光.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概念·策略·戰略[J].當代文壇,2011(2):4-11.
[2] 林青.萬瑪才旦電影空間敘事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9.
[3] 徐曉東.遇到萬瑪才旦[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7.
[4] 霍冉.地域空間與民族想象:蒙古族題材電影地緣文化探賾[J].電影文學,2021(3):28-32.
作者簡介:蔣林燕(1998—),女,甘肅甘南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與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