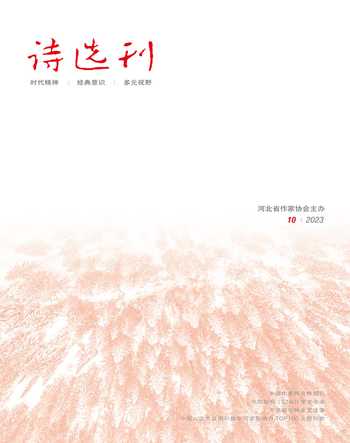創作談:詩以寧靜呈現世界的復雜
孟醒石
我常常凌晨一時許從單位下班,乘坐出租車往西郊去,沿途霓虹燈逐漸減少,夜色越來越深,我卻越來越亢奮。到了小區胡同口,下車后還有很長一段夜路要走,抬頭看到太行山脈如藍鯨浮出水面,噴出滿天星斗。回到家,往往已經凌晨兩點了,萬籟俱寂,非常疲憊,但亢奮的慣性仍在持續,難以入睡。此時,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讀書了。有時讀著讀著就睡著了,有時越讀越清醒,不知東方既白。
我在冀中平原的小縣城讀高中時,流行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和《讀者》
《青年文摘》等期刊。忽然有一天,一位女生捧著一部比漢語詞典還厚的精裝本的外國小說——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在讀。我特別好奇,借來一讀,便被吸引進去,讀了三天三夜,昏天黑地。隨后,我又到新華書店買了幾本簡裝的外國小說,包括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等。這些外國名著有一種獨特的氣息,就是不管故事情節多么波瀾壯闊、曲折離奇,但它們的語言都是寧靜的。閱讀的過程,如同行走在蓊郁蒼翠的山林中。后來,我在許多中國作家的文字中也讀到過這種寧靜。
這種寧靜的語言,是我寫作的源泉,也是我終生探求的境界。我希望自己敲擊鍵盤時,便有一行行簡潔、準確、寧靜的語言流出來。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總是發現自己的語言特別擰巴。寫完放一段時間再讀,依然感覺有一種難以消弭的“火氣”。重新再改,鍛打,淬火,直至在煉鋼廠聞到鳥語花香,在鐵匠鋪聽到自然的和聲。
我認為,每一個詞語都像一條魚,魚兒在深水、淺水中穿梭暢游覓食,是最自然的。當魚兒紛紛躍出水面,或停在水面上大口喘氣時,說明水中缺氧了,或水體己被污染。此時,我們的語言肯定出了問題。
詩歌在人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詩人雪萊說:“自有人類便有詩。”小說家毛姆說:“文學的最高形式是詩歌。詩歌是文學的終極目的。它是人的心靈最崇高的活動。它是美的捷徑。”
我有了靈感,首先想到的也是寫成詩。但必須承認,閱讀各種非詩的文本,尤其是小說,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寫作者就像登山運動員,在攀登詩歌的珠穆朗瑪峰之前,可以先通過閱讀攀登小說的乞力馬扎羅山、紀實文學的麥金利峰,感受一下不同體裁的景觀與氣候……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并不是簡單的詩歌美學論文,而是討論悲劇和史詩的起源、情節與結構、寫作風格、評價方法等,內容包羅萬象,極其寬泛,為后來者解析各種文學體裁開掘出源泉。
現代詩是抽象的藝術,即便是容納了許多日常生活細節,雞毛蒜皮、曉風殘月、落日炊煙,最終落實在紙上,仍然具有純粹的抽象感。而近現代小說是具象的藝術,它同樣具有一定的抽象形式,時代命運、蜃景人間、海納百川,但落在紙上,必須觸手可及可感。當現代詩與小說,這兩座高峰的文體標識越來越鮮明,二者相距越來越遠時,說明二者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融合,越來越成為一種必要。
前兩年,我在編自己的詩集和幫某位詩人編他的詩集的時候,都感受到題材、視角、語言、意象、手法等方面大面積的雷同。我發現我們都困在故鄉的枯井中,坐井觀天,不停地重復自己。此時,閱讀,尤其是閱讀小說等非詩文本,就成為我每天的必修課。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故鄉的版圖在慢慢擴大,超出了冀中平原,跨越了太行山脈,曼延到了新疆、云南……凡是我走過的地方,都是靈魂的故鄉。
一日睡前讀《-瓢詩話》,我看到作者評論杜甫:“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想到杜甫一生,把中國人的千百種情感都寫遍了,尤其是《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己卒”。正如繆塞所說:“最美麗的詩歌,是最絕望的詩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純粹的眼淚。”杜甫的詩,同時呈現了世界的復雜性,可以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來解析它。
古今中外,時光百轉干回,世界依舊復雜如初。我們寫作,就是以寧靜呈現世界的復雜性,在“悲欣交集”中,懷揣那份對人世的沉重悲情,對乾坤的無止境探問,“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