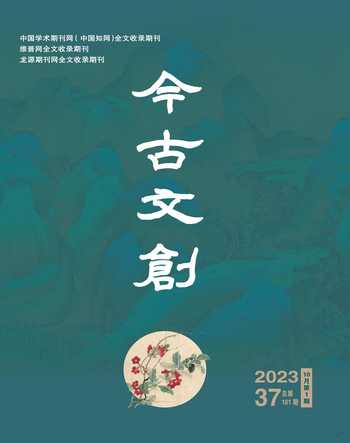自我的破碎與修復
【摘要】當代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在大量的自畫像創作中以破碎的自我形象表達了病殘所帶來的傷痛體驗,同時,又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實現了自我療愈和自我修復,最終錨定了其藝術家的自我身份意識。
【關鍵詞】弗里達·卡洛;病殘意象;自我療愈;自畫像
【中圖分類號】J23?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7-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27
毋庸置疑,弗里達·卡洛具有一種堅毅而獨特的個人風格,赫雷拉將其形容為“面對肉體痛苦的灑脫和勇敢、對驚奇和怪異的特殊偏愛、將隱私和尊嚴隱藏于表象之下的嗜好” ①,這種風格在體現在其藝術創作之中,或者可以說,她的作品既表達了自我,也強化甚至塑造了自我,藝術與自我融為一體,正如勒克萊齊奧所說,“藝術是她的全部一切,所以對于任何限制她自由,扭曲她本意的事情,她拒不接受,絕不妥協” ②。弗里達在生命的各個階段經歷命運重錘所帶來的徹骨傷痛,她的自我意識強大敏銳,但自我意象卻支離破碎,為了與這種破碎感相抗衡,她不斷地在畫布上描繪自己的形象,以藝術的方式完成自我重構。她筆下的病殘意象,既是經驗再現和情感宣泄,同時也是在凝視和復制傷口的過程中重新確定自我存在,在病殘的軀體上主動烙下印記,從而修復、整合、錨定出一個重生的藝術家自我。自始至終的人畫合一,對于弗里達而言,毋寧說是出于一種對破碎的自我意象的修復與超越的必然追求——“我畫我自己的現實,我只知道繪畫是我的一種需要”。③
一、身體意象的破碎與重組
弗利達6歲時感染病毒,脊髓灰質炎使她的右腿和右腳萎縮變形,這種身體畸變打破了童年時期完美的自我意象,在1938年的一幅作品中,弗里達畫了一個穿著粉色及地長裙的女孩,裙身被一段絲帶環繞,兩端分別系在兩根楔入地面的黑色鐵釘上,畫面前方正中有一架玩具飛機,女孩一只手輕從底部輕輕撫著它,身后是一對麥稈翅膀,被兩根繩子吊在空中,女孩冷淡的眼神穿透畫面,畫面下方寫著“他們想要飛機,卻得到了麥稈翅膀”,這是弗里達在回憶起幼年在節日扮演天使的情形時所作。回顧童年趣事的作品卻沉重壓抑,因為它正是關于疾病和痛苦的最初記憶,長裙掩住的是患病腿腳的丑陋與羞恥,絲帶縛住的是歡跳和逃脫的渴望,對這個畫中這個孩子而言,不管是得到的稻草翅膀,還是心心念念的玩具飛機,都是虛有其表的自由幻象。
到了18歲,在弗里達的努力下,這種被拴住的桎梏感幾乎被拋諸身后,她運動、讀書、戀愛,直到被1925年的一場公交車事故徹底重創——脊椎斷裂,鎖骨斷裂,肋骨斷裂,骨盆破碎,右腿碎裂,右腳壓壞,左肩脫位,一根鐵條穿過腹部……在治療和恢復過程中,她幽默和快樂的天性逐漸被染上憂郁和無助的色調:“這是一次奇怪的車禍,它并不極度兇猛,但卻默默地、慢慢地折磨每一個人,我是最慘的一個……人必須得忍受這些,我開始對苦難感到習以為常了。” ④弗里達從此必須要經常性地用靜止的姿態等待破裂的骨骼長好,那根象征束縛的紅色絲帶越纏越緊,她開始畫自己受傷的身體,軀體的殘破不斷出現在她各個時期的自畫像中。在1938年的《水之賜予》中,破損的腳趾、流血的傷口與夢魘的碎片被同時放置于狹小的浴缸之中,充分體現了病殘經驗對于身體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影響,同時,“弗里達正是通過直面淋漓地闡發這種隔絕感,來揭示這種暴力,引發對正常性的反思” ⑤。
1944年,在一次失敗的脊柱手術后,弗里達畫下代表作《破裂的柱》,畫中的身體意象呈現出令人震驚的矛盾性,在碩大駭人的傷口中,脊柱被斷裂的羅馬式鐵柱取代,鋼制矯形胸衣綁住裂成幾乎兩半的軀體,鐵釘遍布全身,白布裹住的下半身隱隱露出更巨大的傷口,殘酷、傷痛、意外、侵入的象征比比皆是,但最重要的是一種強烈對比,在展示破裂的同時,軀體保持著線條柔美、膚色暖黃、頭發烏順,乳房完美的整體形態,那張有著鮮明特征的臉上,眼神執著,嘴唇堅毅,雙眼和面頰下的淚珠明確地表達著痛苦,但是假若遮住淚珠,表情似乎又是超然甚至冷漠的。鐵柱、胸衣、鐵釘一方面具象化了身心痛苦,另一方面,它們似乎也是弗里達內在自我的某種外顯,即一種堅定的整合和表達的意識——身體既是被外物侵入和傷害的,也是被自我意志支撐和環繞的。這幅自畫像充分展現了弗里達身上并存的兩面性——破碎與完整、脆弱與堅毅、痛苦與超然,而這正是弗里達在車禍之后逐漸展現的自我形象——真實與假面的共舞。假面并非偽飾,而是某些性格——堅強、樂觀、活潑、豪爽、機智的強化,“她創造了一個足夠堅強的自我,一個能夠直面生活的重擊的自我, 可以生存下來。” ⑥
二、情感創傷的釋放與超越
弗里達和丈夫迭戈·里維拉之間建立了一種復雜而深刻的情感關系。勒克萊齊奧曾說:“這對畫家夫妻的故事具有典范性。生活中的不測風云、鉤心斗角、幻滅失望都無法打破他們之間的關系,這不是一種依賴,而是一種永久的交流溝通,就像流動的血液,呼吸的空氣一般。” ⑦他們相愛、爭吵、離婚又復婚,數十年相互糾纏,藝術風格上又彼此獨立,二人不僅僅是愛人,相識之初,成名已久的里維拉就發現了弗里達的天賦,他鼓勵她成為獨立畫家,為她開辟進入藝術圈的道路,是弗里達一生的導師、偶像和摯愛,但他也給弗里達帶來巨大的情感創傷,她曾經說自己一生當中遭受了兩大變故的折磨:其一是那場車禍,其二就是迭戈。如果說車禍使弗里達的身體支離破碎,與丈夫的相處則迫使她不得不重構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里維拉有一種情緒不穩、風流難抑的天性,他甚至與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保持著長期曖昧關系,1935年的作品《稍稍掐了幾下》具象化了這種傷害——裸體女人躺在床上,雙目緊閉,渾身傷口,一個醉酒男子持刀站在床邊,整個畫面甚至畫框都布滿鮮血——她以社會新聞為原型畫了一個具有黑色幽默風味的謀殺現場,卻表達出自己“被生活謀殺了”的真實感受。
此后,在《回憶》(1937)和《一道開裂的傷口的記憶》(1938)中,破裂的身體依然是痛苦的隱喻,但姿態發生了變化,弗里達開始用玩味和犀利的眼神(這也是她的標志)直視觀眾。赫雷拉認為,情感的折磨使她成長為一個更獨立和堅強的女性,通過訴說其脆弱而獲得力量,并且獲得了某種對于性的體驗的開放性,一個更加復雜獨特、更具魅力的弗里達獲得新生。
多次流產也同樣令弗里達深受情感打擊,1944年日記中一段不連貫的文字揭示了她對不育的悲哀,即使她找到了其他的事來填充生活也無濟于事:“我毫無所獲……我不相信幻覺……真是無所適從……被淹死的蜘蛛,生活于酒精之中。孩子是明天而我卻終于此。” ⑧1932年,弗里達陪伴里維拉在美國底特律工作期間,她意外懷孕,根據其身體狀態,醫生建議人工流產,但弗里達決定冒險留下“小迭戈”,胎兒在三個大月時突然流產,弗里達在亨利·福特醫院住了半個月,期間開始畫自己和胎兒的素描,最終,一副名為《亨利·福特醫院》的作品在痛苦中問世,畫中,弗里達赤裸著躺在病床上,鮮紅的血在往床單上流淌。一大顆淚珠淌過她的面頰,她的肚子因懷孕而腫脹著。她的手放在鼓起的肚皮上,拿著六根血管一樣的紅色帶子,每根帶子的末端都飄浮著象征流產后情感的事物。半身模型象征女性身體的內部空間;胎兒是失去的“小迭戈”;蝸牛象征流產過程柔軟、隱蔽又公開的特征;機器象征整樁事情中的機械性的部分;紫羅蘭象征著性愛和子宮;破裂的骨盆是流產的禍根。病床突兀地放置于室外光禿禿的褐色土地上,遠處是工廠、煙囪和機器。畫面空間被作者刻意扭曲成一種超現實的比例,病床很大,城市背景很小,六個象征物,尤其是漂浮在畫面正上方的死去的胎兒都很大,相比之下,病床上的女性身體顯得非常弱小、孤單、敞開、無助,“亨利·福特醫院”的字跡被寫在床板邊緣,高聳的床頭和床尾看起來像是冰冷的監獄鐵柵,凸顯了醫院生活的孤立、異常與隔離屬性。里維拉對這幅畫作的藝術價值非常肯定,“這是此前的藝術史上所沒有的——贊揚女性對現實、殘忍和磨難的承受力。此前絕沒有人如弗里達此時在底特律所做的那樣將如此極度痛苦的詩意表達到畫板上”。⑨繪畫對弗里達來說是治療傷痛的解藥:正如她在晚年對朋友的坦言:“我的繪畫承載著那種痛苦的信息……繪畫由生命來完成。我失去了三個孩子……繪畫是一種替代品,我相信工作是最好的事。” ⑩
三、自我身份的游移與確立
正如Gallant和Howie所說,弗里達的身體創傷“超越了個人特定的精神、性和肉體的層面”,她樂于在創作中發掘自我生命的緣起和聯結 ?。她的畫作一方面展現了一種深厚寬廣的歷史意識和宇宙景觀,另一方面卻又始終與自我的形象和感受為中心,弗里達正是在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過程中,逐漸描畫和錨定了自我身份。
弗里達在創作最初就有著深厚的民族與文化身份意識。1936年,處于藝術生涯早期的她畫了《祖先、父母和我》,講述其家族譜系和出生環境。她把自己畫成一個兩歲女孩,站在家中院落里,一棵無花果樹遮住似乎更細弱一些的右腿,手中拿著象征著血脈連接的深紅絲帶。巨大的父母形象占據畫面正中,穿著結婚禮服,母親的白裙上有一個受孕的胎兒。母親上方的云朵中漂浮著印第安血統的外祖父和西班牙血統的外祖母,其下是連綿的山脈,父親上方則是德國風范的祖父母,其下則是一片海洋。弗里達將自己家的房子放置于荒野,猶如世界的中心和庇護,映襯著不遠處的印第安土屋。
1937年所作的《奶媽與我》中,深色皮膚的印第安奶媽正抱著嬰兒般的弗里達喂奶,臉上帶著屬于南美大陸古文明的石質面具,看不到任何表情。
《墨西哥的四個居民》創作于1938年,畫中幼小的弗里達正凝視著四個代表墨西哥命運的人物(神像、猶大、骷髏、麥稈人)中那個前哥倫布時期的黏土女神雕像,她被塑造成裸體孕婦的形象,既象征著古墨西哥印第安文明, 也暗示著女孩的未來——這個神像是破碎的,手腳缺損,頭部破碎不堪,同時孕育著死去的生命。
這些早期畫作即充滿歷史和現實中的墨西哥文化元素,也展示了作為個人和整體的墨西哥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血脈和文化淵源。1932年所作的《墨西哥與美國交界的自畫像》明確表達了弗里達對美墨文化的思考,畫中的她站在兩國邊境線上,兩側風景迥異。代表美國的右側畫面中是大樓、機器、油罐、工廠和濃煙,更加明亮、喧囂、緊湊;代表墨西哥的左側畫面中是月亮、太陽、金字塔、植物、滿地的石塊和破裂的神像,更多的陰影,更柔軟和遼闊。在弗里達腳下,左右兩側在土地深層的截面連成一塊。畫中的美墨對比正如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所表達的:“墨西哥仍然和往常一樣,散亂不堪,情況很糟,唯一讓人熱愛的是這塊土地的壯美和印第安人的純粹。但美國的丑陋每天都蠶食它一點,這是可悲的。但人民總得吃飯,大魚吃小魚是沒有辦法的事。” ?
與如此清晰的文化立場不同的是,弗里達的職業和性別意識卻生長得較為緩慢,雖然有著極其獨特的天賦和藝術表達方式,但她仍甘愿將自己隱藏在里維拉的光芒之下,熱愛和信仰他的一切,正如赫雷拉所說:“毫無疑問,即使弗里達恨迭戈的時候,她也是崇拜他的,她生存的支點即是那種成為他的賢妻的動機。”對于早期的弗里達來說,“成為藝術家”便是滿足里維拉期望這一動機的副產品,然而一旦這種成長開始起步,在生活和繪畫的雙重促發下,弗里達最終將生成作為藝術家的自我身份意識,這一過程清晰地體現在她的作品中。
在1931年的《弗里達和里維拉》中,弗里達畫下新婚的二人,畫中的里維拉手持畫筆,如同巨人一般筆直站立,目光如炬,弗里達則柔軟溫順,身體和頭部都側向丈夫,幾乎像是里維拉的一個漂亮輕巧的裝飾品,此時弗里達對自己的畫家身份并不確定,雖然她已經開始惹人關注,但她總是強調自己的“業余愛好者”的身份。在畫下《兩個弗里達》的1939年,在與里維拉分居和離婚的痛苦中,弗里達用這幅畫展現了一種令人震驚的深度自我剖析,心臟和血管被置于身體之外,自我分裂為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連接的弗里達形象——歐洲的和墨西哥的弗里達、里維拉熱愛和厭惡的弗里達、現在和過去的弗里達,依戀和決絕的弗里達……《兩個弗里達》已經充分表達了一種對自我存在之復雜性的深刻洞見。
至創作晚期,在1951年的《在法里爾醫生肖像前的自畫像》中,弗里達成功地將這種復雜性挖掘到更深的維度,更為重要的是,她在畫中明確將自己表現為一個創作者——她像自己曾經畫的里維拉一樣手持畫筆和調色板,端坐在自己的作品《法里爾醫生的肖像》旁,肖像畫中的法里爾醫生雙眉之間陰影重重,似乎又映射著弗里達的自我形象,至此,弗里達的內心世界和藝術創作中均已完整含蘊了身為一位藝術家的自我。
四、結語
在弗里達短暫的一生中,病殘經歷占據了大半時間,是她體認自我和世界的重要基礎,也是她藝術創作的主要內容,病殘并沒有削弱其生命力量,反而激發起她對生命的激情和熱愛,促使她堅定地拿起畫筆進行表達,最終完成了破碎身體的重組、個體傷痛的超越和自我身份的重構。
注釋:
①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②勒克萊齊奧著,談佳譯:《迭戈和弗里達》,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頁。
③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④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頁。
⑤林婧、胡可:《從弗里達看殘障藝術的歷史性出場》,《美術觀察》2020年第10期。
⑥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頁。
⑦勒克萊齊奧著,談佳譯:《迭戈和弗里達》,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頁。
⑧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頁。
⑨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頁。
⑩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頁。
?Ann Millett-Gallant, Elizabeth Howie, Disability and Art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7.
?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譯:《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頁。
參考文獻:
[1]海登·赫雷拉.弗里達:傳奇女畫家的一生[M].夏雨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2]林婧,胡可.從弗里達看殘障藝術的歷史性出場[J].美術觀察,2020,(10).
[3]Ann Millett-Gallant, Elizabeth Howie, Disability and Art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7.
[4]勒克萊齊奧.迭戈和弗里達[M].談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黃莉莉,女,漢族,安徽淮北人,南京大學博士,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殘障文學與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