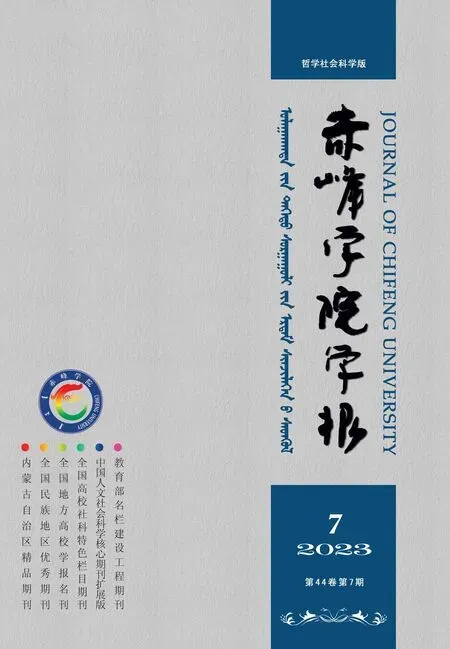“苦”字緣起及其文化意蘊蠡測
武國強,賀 穎,余 陽
(麗江文化旅游學院,云南 麗江 674199)
“苦”意蘊深厚,涉及頗廣,味覺方面有“酸甜苦辣辛”;生活體驗方面,常言“辛苦”“凄苦”“悲苦”;心理狀態方面,常道“苦悶”“苦惱”“痛苦”;磨礪人生方面,有“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文論學說方面,有“詩窮而后工”“國家不幸詩家幸”“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等;生命智慧方面,“苦”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均有體現,是一種思維模式、行為準則、生活方式,其有共性亦有異處,尤其是在佛教文化中,“苦集滅道”四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苦”字的緣起及其發展走向,不僅可以深入理解其內涵,還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到儒釋道三者之間相互交融之處。
一、“苦”之涵義
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說:“苦,大苦苓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苦,大苦苓也。見《邶風》《唐風》毛傳注云:‘今甘草也。’按《說文》‘苷’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名‘苓’,則何以不類列,而割分異處乎?”《說文解字》:“苷,甘草也。”此處段玉裁對“苦”與“苷”提出疑問,實是慧眼識珠、思考至深。如果“苦”就是指“大苦苓”“大苦苓”就是甘草,那么如何引申出“味苦”之意,這就令人頗為費解。
“苦”“苷”二者是否一義? 是否同源? 需要進一步考證。《古代漢語詞典》中對“苦”進行了解釋,言其本義是“苦菜”,如《詩經·唐風·采苓》:“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孔穎達疏《詩經·唐風·采苓》引陸璣疏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爾雅·釋草》中說:“荼,苦菜。”晉人郭璞注曰:“可食”,近人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解釋說:“苦菜,該是菊科苦苣菜屬和萵苣屬的植物。”“苦菜” 是否是一種植物的專有名稱,當下不得而知,后引申出“味道苦”,與“甜”相對,《詩經·邶風·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后又引申出勞苦、辛苦、刻苦、痛苦,苦于、為……所苦,困辱、折磨,悲憫、憐憫,竭力、極,過分、多,急,甚、很之意[1]。當下最流行的王力先生的 《古代漢語》 中則沒有收錄“苦”字,不免遺憾。
語言文字在不同的時代,內涵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有些詞義擴大或減少,有些詞義感情加重或減輕,有些涵義已消失、生出新意,有些涵義直接發展走向了反義,如“臭”開始指一切氣味,含香味和臭味,后專指不好的氣味。“受”有“接受”和“授予”相反義。“亂”有“治理”和“紊亂”相反義。“苦”“苷”有可能在早期涵義相同,在后面的發展過程中,“苦”字涵義發生變化。
二、“苦”之探源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字都最先起步于象形文字,只不過在后期的發展過程中,其發展緩慢不同、方向異路,才產生了后面人類不同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字。綜觀納西族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篆文,我們會發現它們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如納西文中的人、山、水等都與納西象形文字大同小異,這就說明如果有些文字在甲骨文、金文、篆文中等缺失或無法考其古義時,我們可以借鑒相近文字進行類推考證;另外一方面,在納西族的構成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就是源自遠古時期我國西北河湟地區的“古羌”人,后面歷盡艱辛才遷居到西南一帶,這說明在文字起源上,納西族可能就與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篆文有密切的關系,后面在發展過程中,其他文字演變進化比較快,而納西族文字相對變化少,基本停留在原始階段,因此,借助納西象形文字推測某些古文字的含義,是具有一定實踐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有關“苦”字目前可查找釋義的工具書并不多,《釋名》《釋言》中說:“苦即大咸”,“咸”即“鹹”,二者有相同之處亦有區別,相同之處是二字同義時釋為“鹽的味道”,這里的“苦即大咸”就是指“鹽的味道”,口語中,在燒飯做菜時,常言及“甜還是咸”,其實就是指菜的味道濃淡。平日所言“五味”,即酸、甘、苦、辛、咸五種味道,“苦”與“咸”又分別發展成程度不同的味道,“苦即大咸”亦可解為味道太咸者謂之“苦”。郝懿行《爾雅義疏》中記載:“苦者對甘而言”,更能清楚說明“苦”與“甘”相對。以上解釋,恰好就是今本《古代漢語詞典》中對“苦”的引申義之一“‘味道苦’與‘甜’相對”的解釋,如此看來,我們就可以從“甘”字入手追尋“苦”義。《說文解字》中說:“甘,美也、從口含一。”《說文解字注》:“美也。羊部曰:美,甘也。甘為五味之一。而五味之可口皆曰甘。從口含一,道也,食物不一,而道則一。所謂味道之腴也。”[2]《釋名》亦說:“甘,含也,人所含也。”由《說文解字注》可知,人口中所含之物,皆是味甘甜可口之物,否則不可能含。學者俞越在《兒苫錄》就有此看法,他說:“甘字象形,而非會意,于口之中作一,其本義當為含一,即所含之物至甘。古字當做苷,猶‘苦’亦從艸。”《說文解字》解釋:“苷,甘草也。從艸,從甘,會意。甘亦聲。”《淮南子·覽冥》載:“甘草主生肉之藥。”前面古漢詞典所記“苦”就是“苦菜”,這里“甘”與“苷”同,是指甘草。象形字不用解釋,山川日月一眼看出,會意字則是要在象形基礎上稍加引申而成,然其亦不會脫離實際生活,如“東”字,古字有寫作“”,《說文解字》:“從日在木中”,意謂太陽在樹后上升,方向即是東;又如“祭”字,古字有寫為“”,《說文解字》:“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意謂雙手執肉放在樽俎之內,是為祭祀。正如黃仁宇所說:“中文的前置辭和聯系辭少,抽象的意義只能重樓疊架構成。也要將可以眼見耳聞的事物極度的延伸,才能成為可以理解的觀念(有如‘抽象’即抽出其相,與‘具體’之具有其體相對)。”[3]由此可知,人們在造字表達自己的認知情感時,往往與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甘”與“苦”最早的本義可能就是源于植物,這與古人最早的認知也是相契的。
通過研究發現,由“苦”引申出來的含義,多數都是消極的,同樣由“古”字衍生出來的字,往往也都是消極含義,這再次證明,“苦”與“古”在古代含義是一樣的,且二字古音亦同。方國瑜從訓詁方面對二字進行了說明:“《說文》從古得聲的字,多有消極含義。清人陳立著《說文諧聲孳生述》所列從古得聲字近三十個,其意多貶。譚嗣同《仁學篇》說:‘于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網則罟,從辛則辜,從文則故,從口則固,從疒口則痼,從水口則涸,叢人為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為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為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5]
三、“苦”之文化意蘊
理清“苦”字的緣起之后,即可進一步探究“苦”的文化意蘊。從語言學、人類學角度看,文化類似語言的結構,可以分為技術的、意識之中的、意識之外的三個層次。技術的和意識之中的文化現象,群體社會成員都能感受到;意識之外的文化,則潛移默化的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左右著人們的日常行為、價值觀念與宗教信仰,但人們卻習焉不察。通過分析這“無聲的語言”,諸如“苦”字在《老子》《論語》中均未出現,但在《莊子》《孟子》等書中確實有出現的現象,就可以挖掘出不同時代不同學派所深藏的隱性的文化因子,了解不同時代的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精神面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說“苦中作樂”“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苦”由其最初的本義引申至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和思維模式時,就成了一個民族約定俗成日而行之的實踐規范。從味覺層面看,與“苦”相對的是“甘”是“甜”;從為人處世、人生境遇層面來看,與“苦”相對的便是“樂”是“悅”。“苦”“樂”與人生哲學和倫理學密切相關,但在中文語境中還不是純粹的哲學概念。學術界專門研究“苦樂觀”的著作也沒有出現。本文為更加清晰地理解有關“苦”的文化意蘊,常從其對立面“樂”的角度進行闡釋。
翻檢古代經典作品會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道家代表作典籍《老子》沒有一個“苦”字,也很少談“樂”;儒家經典《論語》中也無“苦”字,但出現“樂”“悅”字較多;而佛家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則多“苦”字,而無一“樂”字。梁漱溟先生曾就儒佛兩家的差異做過論述,他認為這個差異既非無關緊要的文字差異,亦非事出偶然,而是因為兩家共同的研究對象或者說兩極之分,儒家比較關注人類接近動物的一面,佛家比較在意人高于動物的一面。儒釋道三種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儒家注重人與社會的關系,道家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佛家注重人與自我的關系。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人類自古以來,就有三個敵人:自然、他人與自我,人類的文化系統基本上也是在應對這“三個敵人”。因此,有學者將人類文化系統概括為三個層面:一是物質文化或技術文化,因克服自然并借以獲得生存所需而產生,包括衣食住行所需之工具以至于現代科技。二是社群文化或倫理文化,因社會生活而產生,包括道德倫理、社會規范、典章制度、律法等。三是精神文化或表達文化,因克服自我心中之“鬼”而產生,包括藝術、音樂、文學、戲劇以及宗教信仰等[6]。由上述人類學對文化系統的分類,儒釋道三種文化似乎不能完全與之相應,在很多方面存在交叉和相異之處,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民族,人們關注的焦點就是自然、社會與自我。
儒道兩家都非常重視人生意義問題,但二者存在很大差異,如孔子和莊子雖都注重個人的身心感受、生活體驗,然觀察事物的角度及得出的結論均存在較大差異。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當時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政道廢馳仁義不施,他從社會道德危機層面出發,生出極重的憂患意識,產生了整飭社會環境的強烈使命感。莊子則不然,他所處的時代是更進一步的社會大動蕩時代,作為時代的一分子,他對當時人的痛苦境遇具有深切地體驗,他在不斷思索著人生的意義和人生的歸宿。孔子是以天下為己任,懷著“任重而道遠”的強烈使命,將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莊子則始終以哲人智者的冷峻眼光關懷著個體的解脫。《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上有關“樂”之篇章,可以看出孔子對莊重崇高的道德追求和萬世之名的社會價值追求。《莊子·秋水》篇記載其與惠施在濠梁之上觀魚,莊子觀魚思人、觸類旁通,說:“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在莊子眼中,“魚”兒無貪欲、無私心、無紛爭、無爾虞我詐,出游從容順其自然,正是他自然人生觀的體現。莊子所追求的“樂”與感受的“苦”都在于精神層面,他認為現實之苦在于世俗生活的拘束與奴役,在于人們無法擺脫的現實處境,在于人類有限的認知視野[7]。莊子及其道家后學所探究的“苦”,更多指的是心靈受到限制和束縛,是一種精神上的不自由。
儒家文化倡導積極入世,聚焦于人與社會的關系,認為人生要有意義,就要弘道、踐道、改造社會。一個人想在社會上卓有建樹,必須要經歷一番磨煉,經歷一番痛苦的心路歷程。孟子言:“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北宋大儒張載所著《西銘》中說道:“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意為生活中貧窮低賤、憂愁煩惱往往可以磨礪人的意志,助人取得成功。)蘇軾在《晁錯論》中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亦言:“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從儒家文化角度闡釋,“苦”字之義多與“甘”“甜”“樂”“悅”等相對,一個人只有不懈努力奮斗才能“苦盡甘來”; 一個人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為“人上人”。儒家講究一個人在逆境中得到成長,在逆境中得到淬煉;道家則更加注重“化苦為樂”,道家認為一個人雖然不能改變個體肉身的不幸、社會的困境,但他可以通過轉化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從現實之苦中解脫出來,得到精神上的喜悅,達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8]的境界。
本文結合儒釋道文化,探究了有關“苦”的文化內蘊,可看出“苦”是儒釋道文化相互交織融合的最佳契合點之一[9]。“苦”之意蘊,難以盡言;“苦”之文化,博大精深;“苦”之真諦,奧妙無窮。星云大師說:“一件事總是有好有壞,有苦有樂,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間,一念善,就是天堂,一念惡,就是地獄,全看我們怎么去體會。只要看破放下,也就隨喜自在了。”[10]道家講“福禍相依”,儒家講“陰陽變化”,都是在說矛盾既對立又統一,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只有勘破障礙,正確看待世間人事、物我關系,才能心生歡喜、得大自在。儒者顏元說:“人世苦處都樂,如為父養子而苦,父之樂也;為子事父而苦,子之樂也;茍無所苦,便無所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