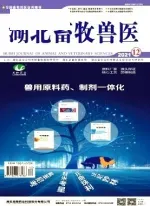廣東省稻田福壽螺的發生與防治情況
——基于全省597 份問卷的調查分析
郭 靖,李 娟,張少斌,彭紅元,賀愛蘭
(韶關學院生物與農業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際貿易、國際旅游等不斷發展,外來物種入侵日益加劇,對中國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農林業生產和人類健康等造成極大威脅[1,2]。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強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來物種侵害”,外來入侵物種是影響中國生物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國先后通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外來入侵物種管理辦法》等,以應對外來入侵物種造成的侵害。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調查統計,外來入侵物種數已近800 種,對農林生態系統造成危害的物種數達669種[3]。自2003 年起,中國相關部門先后發布了多批外來入侵物種管理名單,以加強對大面積發生和危害嚴重的重大入侵生物的管控。原環境保護部與中國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第1 至第4 批,原農業部制定的《國家重點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名錄》,農業農村部牽頭制定并于2023 年1 月1 日實施的《重點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名錄》,小管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均位列其中。
福壽螺又名大瓶螺、蘋果螺,原產于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世界范圍內100 種危害最為嚴重的入侵物種[4]。1980 年,福壽螺作為水生經濟動物從阿根廷引入中國臺灣省,次年引入廣東省中山市養殖,隨后在20 世紀80 年代興起的養殖狂潮中迅速擴散到全國15 個省(區、市),20 世紀90 年代因福壽螺市場化失敗和危害水稻等農作物生長狀況頻發致使養殖熱度降低,但此時福壽螺已在中國建立了野外自然種群,隨著無意的人為擴散和水系的自然傳播,福壽螺入侵不斷加劇[5,6]。引入中國40 余年,福壽螺入侵情況呈現如下特點:一是品種混雜,小管福壽螺、斑點福壽螺(P.maculata)和隱秘福壽螺(P.occulta)三者混雜,且出現雜交漸滲,遺傳多樣性的提升為適應多變環境創造了條件[7,8];二是范圍北擴,受冬季低溫限制,福壽螺基本分布于中國30°N 以南[6],但后來在山東省濟寧市發現了福壽螺野外自然種群[9];三是貽害無窮,福壽螺嚴重危害水生作物生長和水生生態系統,中國農田發生面積已增至170 萬hm2以上[10],福壽螺體內可寄生引起人體嗜酸性腦膜炎的廣州管圓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截至2022 年,仍不斷出現因取食福壽螺而導致感染的病例發生[11]。
廣東省作為中國大陸福壽螺入侵的初始地,氣候常年溫暖濕潤,水網眾多,一直以來都是福壽螺危害的重災區。1988 年,福壽螺擴散至全省37 個縣(區),為害作物面積達2.5 萬hm2,1991 年發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區,1994 年擴散至全省[12,13]。由于螺害日益嚴重,《廣東農村統計年鑒》于1997 年開始將螺害列為農作物主要危害,每年全面進行統計匯報。1997—2006 年福壽螺發生面積在20 萬hm2左右,之后大幅增加[14],2021 年農田螺害發生面積高達54.8 萬hm2。作為全國福壽螺危害嚴重的省份,廣東省對螺害的防控力度一直較高,2009—2022年,全省農田每年福壽螺防治面積均高于發生面積,挽回損失遠高于實際損失。但長期以來防控手段單一、區域防控不協同、農戶各自為戰等問題導致福壽螺危害面積居高不下,加強公眾對福壽螺防治的重視及促進相應技術的推廣應用是福壽螺防治的必由之路[15,16]。本研究基于問卷調查獲取的有效樣本,分析了廣東省稻田福壽螺的發生及防治情況,厘清存在的問題,旨在為福壽螺綜合防控技術體系的開發與應用提供參考。
1 調查方法
1.1 問卷設計
利用問卷星發放問卷,調查廣東省稻田福壽螺的發生和防治情況。調查問卷共設16 題,其中前4題包含受訪者的基本信息(職業、年齡、所在位置)及其了解的稻田所在地,另外12 題從稻田基本情況、福壽螺的發生、福壽螺的防治等3 個方面進行調查。這12 道題包括9 道單選題、2 道不定項選擇題和1 道主觀題。
1.2 樣本情況
調查于2022 年1 月開展,正值學生寒假期間,組織了數十名大學生通過觀察、訪談、問卷等方式對廣東省稻田福壽螺的發生和防治情況進行調查,共回收問卷618 份,去除稻田所處地非廣東省的問卷21 份,得到有效問卷597 份。被調查者職業和年齡情況見表1,被調查者職業所占比重從高到低依次是學生、農業勞動者、農業科技工作者、農業管理工作者,共占全部樣本的87.5%。受訪者覆蓋各個年齡段,主要集中在20~60 歲,占比達81.8%。問卷調查稻田涉及廣東省所有地級市的85 個縣(市、區),其中珠三角、粵東、粵西、粵北的樣本數分別占20.8%、3.9%、16.8%、58.5%。受訪者調查時所處位置與其了解的稻田所在地為同一縣(市、區)的樣本數達514 份,占總樣本數的86.1%,因此調查數據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表1 被調查者基本特征
1.3 數據分析
試驗數據采用Excel 2007、SPSS 20.0 軟件進行整理與統計分析,用Origin 8.0 軟件繪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稻田基本情況
調查中了解到近70%稻田采取雙季稻種植模式,一季中稻和一季晚稻分別占全部樣本的11.1 %和13.1%(圖1a)。一季稻休耕期間,稻田主要種植花生和蔬菜,占比均超過55%,余下依次為玉米、大豆、煙草,分別占38.9%、23.6%、19.4%,另有8.3%的稻田會種植油菜、西瓜、綠肥等植物(以上比例含套種模式)。此外,有12.5%的稻田休耕期處于丟荒狀態(圖1b)。

圖1 廣東省稻田種植模式(a)和一季稻休耕期種植情況(b)
2.2 福壽螺的發生
根據受訪者反饋的稻田福壽螺的種群密度來看(圖2),雙季稻福壽螺的危害較為嚴重,每平方米10.0 只以上的比例最高,達11.7%,而沒有福壽螺的比例最低;一季中稻福壽螺的種群平均密度略低于雙季稻,其每平方米5.0~10.0 只的比例達26.0%;接近50%的一季晚稻田的福壽螺密度為每平方米2.0~5.0 只,超過每平方米5.0 只密度的比例遠低于前兩者,總體平均密度為3.4 只/m2;相對于雙季稻和單季稻,不種水稻的情況下福壽螺種群平均密度最低(2.3 只/m2),不及雙季稻的60%,每平方米5.0 只以上密度的占比僅7.7%,而有將近25%的稻田沒有福壽螺。調查發現,未種水稻的稻田多數種植蔬菜、花生、玉米,甚至種植了果樹。

圖2 廣東省稻田福壽螺的種群密度分布
對于不采取任何控制福壽螺的措施,水稻減產多少的問題,超過70%的受訪者表示減產在50%以內,近35%的人表示減產11%~30%;另有20.1%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減產情況,余下近10%的受訪者認為水稻減產將超過50%(圖3a)。在問及當地稻田福壽螺危害情況時,同樣約有20%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有33.7%的受訪者表示當地不足20%的稻田受害,認為稻田受害比重在21%~50%、51%~80%的分別為26.1%和10.1%(圖3b)。當問到螺害在水稻遭受的所有病蟲害當中排位時,42.8%的受訪者表示螺害在第2 至第3 位,有18.1%的受訪者認為福壽螺是影響水稻生產最大的病蟲害,而認為螺害不在前三位的受訪者占比為22.5%,余下16.6%的受訪者則表示不清楚。

圖3 水稻遭受福壽螺危害的減產情況(a)和發生面積(b)
2.3 福壽螺的防治
基于福壽螺對水稻生產造成的嚴重危害,農戶采取多種方式防控福壽螺(非單項選擇)。高達71.9%的受訪者表示通過殺螺劑滅殺福壽螺,接著是人工撿拾和稻田養鴨,分別占總樣本的41.9%和29.3%,而采取水旱輪作、入水口攔截、茶麩等手段防控福壽螺的農戶均占總樣本的20%左右,另有不到5%的受訪者表示對螺害放任不管,或采取曬田、烹飪的方式防控福壽螺(圖4a)。而針對螺卵,68.0%的受訪者選擇就地粉碎,有13.1%的受訪者通過將螺卵潑入水中進行防控,而有14.2%的受訪者表示對螺卵放任不管,余下4.7%的受訪者則表示不清楚,或通過施藥、拋至路邊、喂鴨等方式防控螺卵(圖4b)。當問及福壽螺的數量相比以前時,32.9%受訪者表示變少了,29.1%的受訪者表示差不多,17.9%的表示更多了,余下20.1%的受訪者則表示不清楚。

圖4 稻田福壽螺(a)和卵塊(b)防控策略
關于防控福壽螺需要的資金投入(圖5),30.2%的受訪者表示每公頃稻田(單季)控制福壽螺需要151~300 元,相比而言,認為花銷超過300 元及不足150 元的受訪者分別占全部受訪者的23.8% 和16.8%,另有23.5%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余下5.7%的受訪者則完全不花錢用于防控福壽螺;總體而言,每公頃水稻種植季花費288 元(圖5a)。而對于福壽螺的利用,超過60%的受訪者選擇丟棄福壽螺,近33%的受訪者將福壽螺用作動物的飼料,另有3.5%的受訪者表示當地人取食福壽螺(圖5b)。

圖5 稻田福壽螺防治投入(a)和利用(b)情況
3 對策與建議
3.1 實施水旱輪作,破壞福壽螺的適生環境與休眠場所
根據調查,廣東省稻田以雙季稻為主,豐富的水熱資源和長時間的有水環境為福壽螺種群的繁殖暴發創造了有利條件。郭靖等[17]發現螺害較嚴重的水稻田改種旱地作物,能有效減少福壽螺擴散繁殖和為害作物的機會。本研究亦發現不種水稻的稻田福壽螺密度較低,其可能主要集中在稻田溝渠中。國內外均有研究證實稻田實施水旱輪作能夠有效遏制福壽螺的暴發[17,18],此次調查中亦有20%的受訪者采用水旱輪作模式控螺。何銘謙等[19]調查發現惠州市惠東縣福壽螺數量明顯較少,這得益于當地習慣雙季稻田冬種馬鈴薯等旱地作物,該模式有效控螺可能是通過干擾休眠環境、休眠行為及機械損傷來實現的[17]。相較于雙季稻冬季旱作,一季稻水旱輪作模式延長了稻田的干旱時長,強化了對福壽螺的干旱脅迫,也延緩了福壽螺種群生長繁殖時間,勢必會導致福壽螺種群發展更為緩慢。根據調查,一季稻休耕期種植花生、蔬菜、玉米、大豆等旱地作物是廣東省水稻種植戶的首選,這是一種有效抑制福壽螺種群的模式,但需注意對稻田溝渠福壽螺的防控。走訪調查發現,不少稻田菜地會挖溝蓄水,因此時水溝中福壽螺難以對作物造成威脅,致使大量螺聚集于溝中,這可能會影響后續的水稻種植。本研究發現一季中稻田福壽螺密度高于一季晚稻,可能是廣東省中稻種植通常在5—10 月,這與華南地區福壽螺繁殖盛期(5—8月)高度重合[20]。
值得一提的是,煙草也是廣東省一季稻田中的重要作物,與粵北地區樣本量高有較大關系。據《廣東農村統計年鑒》記載,韶關、梅州、清遠3 市的煙草種植面積占全省的85.8%,由于煙草不耐連作,易出現土傳病害,煙稻輪作是解決這兩大問題的關鍵舉措,已經成為粵北地區煙草種植的主要模式[21]。煙草中生物堿有40 多種,其中煙堿含量約在95%以上,煙堿有很強的內吸活性、胃毒性和觸殺毒性,是傳統的植物源殺蟲劑[22,23]。已有研究證實煙草對福壽螺有較強的控制效果[24],煙稻輪作有望通過“旱作”和“煙堿”雙重作用對稻田福壽螺進行控制。除了煙草,姬靜華等[25]的研究表明華南地區晚稻收割后可種植青蒜,青蒜根系分泌物可以對后茬早稻田中的福壽螺產生驅離甚至毒殺作用,從而實現“旱作”之余的附加控螺效應。
3.2 減少殺螺劑使用,構建生態防控技術體系
調查發現殺螺劑仍是大多數農民的首選,如45% 三苯基乙酸錫、殺螺胺、殺螺胺乙醇胺鹽等[26,27],控螺效果明顯,但對稻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且藥劑殘留可能引發食品安全問題,殺螺劑的持續使用還會導致福壽螺產生耐藥性,致使進一步增加投入成本[28]。通過分析僅使用殺螺劑防控福壽螺的受訪者,發現水稻種植季每季投入殺螺劑的經濟成本平均達288 元/hm2。單一手段防控福壽螺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可以通過構建生態防控技術體系來實現。章家恩等[15]圍繞水稻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構建了水稻生產周年全程防控體系,涵蓋農業防治、物理防治、化學防治、生物防治等技術手段,認為只有全方位“多管齊下”,才能取得好的控制效果。從受訪者反饋來看,茶麩、稻田養鴨、入水口攔截結合人工撿螺摘卵取得了理想控效,相關技術亦在以往研究中得到證實[29,30]。走訪調查發現,韶關市部分地區已普遍使用茶麩代替殺螺劑,大田使用量約為150 kg/hm2。茶皂素是茶麩殺螺的有效成分,稻田使用量達2.03 kg/hm2時,可致90%以上的福壽螺在2 d 內死亡,與常用殺螺劑四聚乙醛和殺螺胺乙醇胺鹽的控效無明顯差異,且對非靶標生物相對安全,具有較好的應用前景[27]。
3.3 加強宣傳普及,構筑全民參與、統防統治防線
針對農民的農業技術培訓多以作物的種植、病蟲害的防治為主,較少福壽螺防控相關的培訓。農民掌握的控螺技術多來自農資店及相互之間的口頭轉述[19],控螺手段較為單一。加上南方水網密布、水生生境類型多樣,極易發生福壽螺的擴散、蔓延和交叉傳播,需進行區域性協同防控甚至構建跨區域的福壽螺聯防聯控體系[15]。從調查反饋來看,受訪者對統防統治及專業部門的科學防控指導呼聲很高,同時發現,仍存在少部分人主動食用福壽螺的現象,從而增加感染廣州管圓線蟲的風險。福壽螺作為中國重點管理的外來入侵有害生物,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一方面需要提升公眾對福壽螺的識別能力和防范意識,仍有不少民眾對福壽螺的危害認識不足,難以區分福壽螺和田螺,存在福壽螺隨意丟棄、釋放、誤食的現象;另一方面需加強福壽螺生態防控技術體系的推廣示范,加大防控典型案例的宣傳力度,組織引導區域性科學防控,推動構筑起全民參與、統防統治的防線。
3.4 加強農業廢棄物控螺和福壽螺資源化利用,發展循環農業
農民多是通過購買殺螺劑、茶麩等控制福壽螺,成本較高,可將一些農業廢棄物用于控螺,從而實現“變廢為寶”和“強本節用”的雙重效果。具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①可向稻田投放不宜食用的菜葉、水果誘捕福壽螺,或插入竹竿誘導其產卵,集中消滅[31];②可在插秧時放養浮萍等適口性較好的植物誘集福壽螺取食,減少螺對水稻的危害[32];③可采集煙草腳葉、下腳料等還田,毒殺絕大部分福壽螺[33];④可將廢棄秧盤折疊成稻田入水口攔截網。除了加強農業廢棄物控螺,將福壽螺進行資源化利用也不失為一種理想的防控方式。本研究發現將福壽螺當做飼料是利用的主流方式,其蛋白質含量豐富,已被開發為鴨、中華鱉、草魚、青魚、寬體金線蛭等動物的飼料[34]。一些探索性研究揭示了福壽螺資源化利用的可能性,包括①螺肉可提取出多種卵磷脂和生物酶[15,35];②螺殼可吸附重金屬,或加工為納米碳酸鈣、生物柴油催化劑、土壤改良劑等[15,36];③螺卵可提取類胡蘿卜素,或開發為觀賞魚的著色劑并提高其抗氧化酶活性[37,38]。
致謝:韶關學院生物與農業學院數十位大學生協助開展走訪調查,謹致謝忱!